- +1
应奇:我与钱永祥先生的交往
记忆中第一次得见钱永祥先生夫子真身,当是十余年前在丽娃河畔的那次“公共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既然是这样主题的会议,作为彼岸“旧时代”之“见证者”、“新时代”之“催生者”之一的永祥先生自然是少不了要到场压阵的。那时候大陆的“钱粉”可能还远没有后来和现在那么多,不过随着《纵欲与虚无之上》简体字版在三联的推出,他“老”也一定已是名满此岸之士林学界了。这不,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在会议间歇“见缝插针”地逮到机会向他请教,所谈的也无非是我读《之上》一书的感受,特别是其中关于罗尔斯、社群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政治观和平等观的篇章。只记得永祥先生静静地听我讲,最后的“反馈”很“简约”:“你把握得很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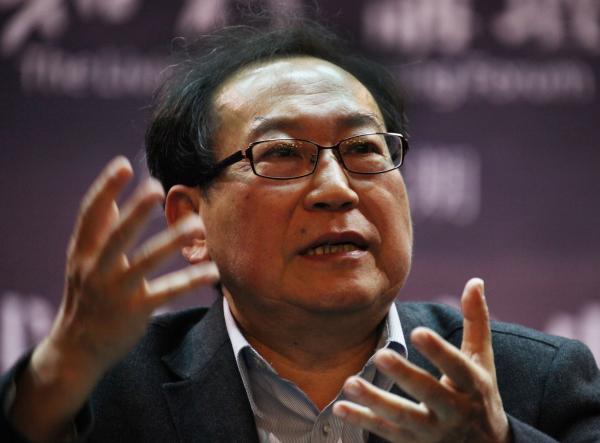
除了从同样与会的陈来教授处得知余英时先生“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之“消息”,那次会议也还有两个情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其间的某个晚上,一众人到其时刚落成不久的新天地“泡吧”,初次谋面的冯克利先生见我“侃侃而谈”,忽然很“质朴”地发出一句:“你(小子)读书不少啊!”不意我不假思索就回了句:“要不然我成天在家里空呆着干啥啊?”闻听我言,也是初次见面的、可是见过八十年代的“大世面”的王焱老哥发出了不知是“齿冷”别人还是让别人“齿冷”的“狡黠”浅笑,虽然他后来明确否认那笑里有什么“微言大义”。二是会议闭幕的大会上,在自由发言和辩论的阶段,永祥先生批评了“中研院”前院长在“前总统”选举上的表现,谓智识人应当慎用自己的“权威”,避免在其自身知识范围外的议题上“误导”大众。永祥先生话音刚落,闭幕式主持人就立即站起来“商榷”了,其意谓身在那种“位阶”的智识人似也有其“不得已”处——这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话题,颇可以引出很多复杂精深的辨析,遗憾的是大概因为那个场合的关系,并没有能够深入地讨论下去。
固然和那次会议没有什么“内在”联系,但确是从那次会议之后,我就踏上了编书的“不归路”:从“编年史”的意义上,我最早开始张罗的丛书是在人民出版社的刘丽华女士支持下在东方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实践哲学译丛”,那也许可以反映些我在“学问”上的“旨趣”;但是比较“狭义”而“专业”地聚焦在政治哲学上,则仍然要算在时任副总编辑的佘江涛先生支持下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创设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系列”,也是通过那套丛书,我和永祥先生建立了电邮联系——主要是为了给丛书壮声威,我请永祥先生、石元康先生还有佩蒂特和金里卡中外一共四位“大咖”担任丛书的学术顾问。洋人当然是来免费“站台”的,但我记得石先生在看到他那时在中正文学院的秘书为他打印出来的我为丛书撰写的序言后,还来信表示“赞赏”,而永祥先生更是没有闲着,我记不得他有没有为读本中的某册做推荐了,不过我记得他很欣赏我在为拙编《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撰写的作者“小传”中把Seyla Benhabib的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这个书名中的Reluctant一词译为“欲迎还拒”,以为颇有“风姿”;他也很赞赏我把吕增奎小友编的那册柯亨文集命名为《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据增奎告诉我,柯亨教授本人也对此书名极为称赏——得知这个消息,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其实并没有对柯亨下过任何功夫,我只记得曾在心里默默地把他的一篇文章标题中译为《何以马克思主义者会对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批评无动于衷?》。
2007年3月至5月间,我在宜兰佛光大学客座。我的台湾朋友本就很少的,于是自然早早地行前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永祥先生,记得他回信告诉我:四五月份正是南台湾最美的时节。其意似乎在为我能够在那时到访台湾而高兴抑或替我“庆幸”——他说得并没有错,当我五月初参加完中正的德沃金研讨会并造访印顺法师在那里“安住”的妙云兰若之后独自一人上到阿里山,虽然那里的樱花几乎已经凋落殆尽,但我仍然必须说,在其山巅可以远眺台湾最高峰玉山的阿里山所看到的日出,确实是我平生看过的日出中最为甜蜜也最为忧伤的。
有些出乎我以及邀我访台的张培伦兄意外的是,在我到佛光后的某天,永祥先生忽然来信,说是要请我在台大附近的金华路(街?)上共餐——于是培伦兄二话没说就慷慨地载我一起到台北“赴宴”。就正如陈来先生某次“称道”在下乃是“笔胜舌”。我确是记不得那次我们都聊了些啥了,只记得我把自己编译的几本书面呈给他,永祥先生则为我们点了一瓶金门高粱,而我本就是“好酒无量”的,再说——不好意思啊,永祥先生——餐桌上也没有什么可下酒的菜,于是我们三人都没有喝完那瓶酒。永祥先生很客气,说是让我们把那小半瓶酒带走,大概我们走得匆忙,终究还是把那个酒瓶忘记在那家小餐馆了。
过了十天半个月,在得知我将到他供职的“人社中心”演讲后,永祥先生特意写信来,告诉我他将参加我的演讲会,但因为当晚另有安排,他向我抱歉不能参加招待我的晚宴了。不过当我后来到“人社中心”查找资料时,永祥先生还是在他的研究室里接待了我,记得他坐在一张书桌前的转椅上,似乎又是面带歉意地告诉我他没有什么书可以送给我,于是指着一本关于动物伦理的书,问我有没有兴趣。当得知我似乎对新儒家更有“兴趣”后,他表示对后者的“情怀”颇有同情,但始终不太清楚他们在哲学上可以说得清楚的“贡献”到底在哪里。我也是“事后”才想起,他那时大概已经在酝酿甚或已经写完那篇《如何理解儒家的“道德内在说”》。
在“人社中心”找资料还有个意外的收获,我竟然发现了永祥先生早年(大概是在英国期间)所撰一篇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论文,于是回到宜兰的某晚,我就把那种有点儿兴奋的心情写信告诉给他,因为那天在资料室刚巧“偶遇”萧高彦教授,我于是把那封信也抄送给了萧教授。永祥先生的回信照例很客气,大意是虽然并不悔少作,但仍然自叹在哲学上才具不够,所以后来就只能做点儿形而下的社会政治哲学。不想高彦教授回说:“可是永祥您已经是一位很好的哲学家了啊!”呵呵,其“惺惺相惜”一至于此,让我想起在赴台前夕,永祥先生还曾告诉我:“本组萧高彦先生于共和主义研究精深,兄来台后不妨与之好好切磋!”
同年6月间,我趁“人社中心”政治思想史组诸同仁到上海华东师大开会之际,顺邀他们来杭州参加一个我“炮制”的主题为“中文语境下如何做政治哲学”的座谈会。在会后征集书面发言稿时,永祥先生虑及在下毕竟曾为“地主”,就要求我也提供一篇稿子“充数”。于是我就果真本着“滥竽”其间的精神,把刚杀青的《中立性》“编序”做了一番增写发给了他。我心想他大概会是不甚满意于我的文稿“质量”的,但估摸同样是念在“地主”分上,我的稿子竟也在《思想》上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那年秋天到转年初夏,我在普林斯顿访问,异乡客居未免寂寞,于是每每在“工余”制作些闲散文字前去叨扰包括永祥先生在内的诸位高僧大德。他对我还是很客气,说是很喜欢我的访书记,我当然只是把这话作为一种鼓励的了,竟至于后来真还“系统地”把我的访书经历给写出来了。虽然我一直并没有机缘把那册小册子呈送给他,其实那种“写作”在我也只不过是代表一种怀旧的心情罢了。
这些年我也还是有机会在自己参加不多的几次会议上见到永祥先生。记得那年沙田中文大学保松君筹办的会议他是从纽约飞过来参加的,我很奇怪那样的长途旅行,他还带着好多期他所主编的《思想》,记得他一边疲倦地坐在酒店外面的长椅上“倒时差”,一边要把其中几期《思想》送给我。那时候我的精神状态也很差,竟是淡漠地从他手里接过了在我眼中“花花绿绿”的那几期《思想》,至今想来都还有些惭愧;三年前在清华的伯林会上,在自由发言阶段,我记得他结合费希特的自由理论谈到伯林之区分自由与成就的重要意义,我在感叹他对于伯林之精熟有得的同时,再次非常具象地感受到自由派的理论原也是可以很渊深的,自由派的理论家原也是可以很博学的!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三年多前在人民大学周濂君的那次会议上,我追着他讨论在中文世界由他首先引入探讨的自由的价值问题,看着我喋喋不休绕弯子嘀嘀咕咕不罢休的样子,他突然来了句:“你老兄为什么非得要证明自由是有价值的呢?!”
近三年我彻底地“淡出江湖”,几乎没有出去开过会了,而自从得到永祥先生那次“棒喝”后,我也似乎觉得再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疑难问题要向他请教了。除了今年春夏时节某天在光影变幻的玉泉老和山上从随身携带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上看到永祥先生当年在建国中学和台大初期那帅呆了的青春“魅影”,我只是偶然在这样那样的邮件组中“见到”他那“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的“身影”,抑或“听闻”他那“顾盼自雄婉约多姿”的“话音”。记得一次我们谈到了黑格尔最重要的中文译者贺麟先生“天翻地覆慨而慷”前后思想的变化以及怎样评价这种变化,似乎我们对相关人士及人事的观感和意见并不是很一致。在这种闲谈中大家似乎都没有较真地想要说服对方,但我一直还是对那一段的议论留有很深的印象。不久前,我“心血来潮”写下了关于贺麟先生的得意弟子、目前国内最重要的黑格尔译者薛华先生的一则“段子”,因为与曾经的“议题”有些“关联”,永祥先生收到了这个“段子”。他没有什么评论,只是回复说:“我今年春天出了本书,请告知你的地址,我可以寄给你。”因为我的那则段子题为《“等待”之“等待”》,我于是玩笑回说:“原来‘等待’也还是有效果的啊!”
昨天是每周一次的撒米娜时间,这学期我在和自己的学生一起阅读John McDowell的Mind and World,用的是北大韩林合教授刚出的重译本。在课程的间歇,我打开自己的信箱,见永祥先生新著已到——联经学习牛津剑桥的做派,初版书还是精装的!翻看目录,大部分篇什我其实都是比较熟悉的,当初在各式场合见到时也曾大致学习过,但是“熟知并非真知”,而且我确实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好好读读永祥先生了,虽然正如我许多年前在枫林晚和丁丁“同台”时说过的,我再读汪丁丁也不会变成汪丁丁,“所以”我再读永祥先生也不会变成永祥先生。但是人生不易,读到耐读的书更是不易,所以就正如叶秀山先生多年前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总还是得“读那总是有读头的书”!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