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赵现海:明末大瘟疫的元凶
人类历史的自然性
人类历史一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是自然变化的一部分,“自然性”是人类历史的特征之一。这是无须论证的事实。但由于科技的发展,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主动性越来越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们的日常意识中,逐渐被淡化,以致影响了我们审视历史的角度。每当我们忽略自然的时候,它便会以自己的方式,提醒我们它的强大存在和巨大影响。事实上,气候暖寒、水旱灾害、地震发生、瘟疫流行,一直都是影响人类历史的重要因素,甚至有时会直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相应地,中国古代的正史编纂也一直将天文、五行、地理,作为志书必不可少的章节。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著史的理想追求。可见,在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中,一直有将自然环境作为历史写作大背景的定位和诉求。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历史学和研究自然环境的学科,基本分属文、理两个不同的大类,尤其是在国内现行学科培养模式下,不同学科之间画地为牢、藩篱重重,导致历史学研究与自然环境研究之间有十分严重的隔膜。即使以研究自然灾害为主题的灾荒史,也长期倾向于关注政治举措,对于自然灾害本身的专业分析相对较少。当下生态史虽逐渐成为国际史学界的前沿方向,但由于历史学者本身在自然环境专业知识的储备方面先天不足,生态史的未来发展,无疑需要长期的艰苦跋涉,才能真正揭示自然与历史之间全面而深刻的内在联系。
作为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历史的表现之一,瘟疫长期而巨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与灾荒相比,瘟疫不仅同样对于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在古代,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医疗救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于瘟疫的救治远逊于对于灾荒的救助,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只能仓皇无助地面对瘟疫,从而对瘟疫这个看似无形却十分恐怖的威胁,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中国古代由此形成了瘟神信仰与驱赶瘟神的各种仪式。在《封神演义》中,不仅有瘟癀昊天大帝吕岳,而且他麾下还有六位正神,分别是东方行瘟使者周信、南方行瘟使者李奇、西方行瘟使者朱天麟、北方行瘟使者杨文辉、劝善大师陈庚、和瘟道士李平。
中国古人很早便对瘟疫形成了深刻印象。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疫,民皆疾也”,强调瘟疫的流行性和传染性。在中国古代,瘟疫的名称很多,如疫、疠、瘟、瘟疫、温病、伤寒、时气等。对于瘟疫的产生原因,古人认为是塑造并维系世界的“气”未按正常顺序流转,从而导致自然环境和人体都发生紊乱,使人们普遍生病。《礼记·月令》便说:“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相应地,古人也从“气”的角度,推衍出认知、诊治各种瘟疫的医疗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医的重要内涵。

影视作品中展现明朝瘟疫状况
小冰河期气候的影响
从万历初年到明朝灭亡这段时间,大江南北暴发了规模巨大的瘟疫,北方地区尤甚。瘟疫种类多样,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造成了上千万人的死亡,严重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根基,是明朝瓦解、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与这一时期在欧洲蔓延的黑死病形成东西呼应之势,是“十七世纪危机”的重要特征之一。
所谓“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晚明瘟疫暴发的直接原因是旱灾的频发。如万历十五年(1587)五月,“京师亢旸,疫气盛行”。万历四十五年(1617)六月,阁臣方从哲言:“日者天时亢旱,雨泽稀微,赤日流金,土焦泉涸,都城内外,疠疫盛行。”
明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旱灾呈现密集性暴发的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属于小冰河时期。太阳光照使地球保持了温暖,但太阳本身也在不断产生物理变化,对于人类而言,最能直接观察到的太阳变化,便是太阳黑子活动。所谓太阳黑子,是指太阳表面一种炽热气体的巨大旋涡,由于这一旋涡温度相比太阳表面温度较低,因此远看上去,好像太阳呈现出一些黑暗斑点。太阳活动比较强的时候,太阳黑子就比较明显;反之,太阳活动比较弱的时候,太阳黑子就不明显。太阳活动的强弱,直接影响地球的气温升降,因此太阳黑子活动的情况,便可以作为全球气候寒暖的直接表征。
元明时期,太阳黑子并不明显,全球气候变冷,处于气候学的小冰河期。气候变冷的直接后果,便是降雨量减少。降雨量减少对于湿润的中国南方地区而言,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于降雨本就较少的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附近敏感的地区而言,会形成直接冲击,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甚至直接促成旱灾的发生。
明中后期北方旱灾的发生,还与北方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随着人口的增长,大量民众为生存开始开垦草地、砍伐森林,开辟出更多可进行农业种植的土地,农垦规模的扩大加剧了地表水的蒸发。不仅如此,明后期皇家和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大兴土木,开展工程建设,对木材产生了巨大需求,这同样严重加剧了对森林的破坏。这些活动无疑都恶化了生态环境,减少了地表水的储存,诱发了旱灾的发生。明代山西有“十年九旱”之说,成化时期便出现由于发生旱灾而导致瘟疫流行的现象。万历时期,瘟疫大多是在旱灾发生之后开始大规模暴发的。
天灾已至
明末的瘟疫致命性高、暴发地点广、种类繁多复杂,因而对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对时人的心态、国家的政局也都造成深刻影响。
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北京一带盛行“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崇祯十七年(1644)秋,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市)大疫,病者“多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而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吊”。
史籍中所记载的瘟疫远不只于此。明末诸多种类的瘟疫,多是当时人们根据患病者症状所命名的:
上文所述之“疙瘩瘟”,出现于北京等地,患者身上全身红肿,长满“血块”,严重者“发块如瘤,遍身流走”,“数刻立死”,因此而得名。
“西瓜瘟”,出现于江苏地区,又名“瓜瓤瘟”,患病者胸口肿胀,“目赤肿痛”“呕血暴下”,“吐血一口,如西瓜状,立刻死”。
“羊毛瘟”,出现于崇祯年间的北京等地,患者胸口后背长出黑点,“如疙蚤斑”,黑点内有白丝,状似羊毛,“用小针于黑处一挖,即出羊毛一茎”,故名。有的患者身上的黑点甚至多达上百,能用针“取数百茎”的“羊毛”。
明末瘟疫之所以对时人造成难以磨灭的印象,不只是因为各种瘟疫的致死性强,有的地区“瘟蝗沴厉,尸山血海,万死一生”,“绝户”“灭门”之语数见于史籍;还有更令人们感到恐怖的,就是患病者的病状。患病者的身体几乎都产生了可怕的变形,患病后或是口吐如西瓜瓤的血块,或是背上长出“羊毛”。这些可怕的症状,带给人们的恐惧比战争、灾荒更甚,给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心态都造成重大影响。
瘟疫造成的恐惧,使百姓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在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百姓自然将这些病状可怖的恶性传染病归为超自然力量,从而诉诸鬼神。在“西瓜瘟”盛行的江苏,“巫风遍郡,日夜歌舞祀神,优人做台,戏一本费钱四十千,两年钱贱亦抵中金十四金矣”;人们为乞平安,祭拜瘟神,希望能逃出其魔爪,祭拜者人数众多,“日行街市,导从之盛,过于督抚”;吴江地区“一神甚灵”,甚至连当地县令都“行香跪拜”。
巴蜀地区瘟疫盛行之下,民间开始出现传说:“时鬼魅昼见,与人争道;夜聚室中,噪聒不休。有梦魂魔者,人就枕,隐隐摄魂去,觉者疾呼,可活,少顷不救。抹脸魔者,黄昏时寒噤如冰,面皮自脱。二物来时,影形模糊,梦魂魔犹可赶逐,抹脸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这或许是由于患病者、病死者的状况而引发的传说。
崇祯十六年(1643),“河北传一小儿,见人白而毛,逐之入废棺中,发则白毛飞空几满”,不久后“羊毛瘟”开始迅速蔓延开来,传播至江南地区。当时民间认为,“羊毛瘟”来源于茄类植物,故有“无食茄食,食者必病”的传说,有人“以手折茄中分之”,发现茄中有“羊毛”,认为这就是导致瘟疫的“白眚”(不祥之兆、妖魔),并“断之以刀”。又有谣传,认为“羊,金也。金气伤,故羊祸转”,相传一种“釜底朱书”的道符,这种道符可“解疫生民短折,人主不能救,而天救之”,一时间“民争效之”。但显然,这些做法不可能制止瘟疫。
总之,求神和谣言,都可见社会上下在面对瘟疫时的绝望心态。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信奉“天人感应”,认为各种灾害的发生都是上天的惩罚或预警,预示社会将要出现更大的动荡和灾难。瘟疫也是如此,历代的史书和地方志,均将瘟疫大规模暴发和流行的事件记入“灾异”“灾祥”“五行”等目录下,这同样反映出“天人感应”的思想。明末瘟疫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甚大,又恰逢明清易代的历史节点,更是使当时文人士大夫将其视为上天的警示。在明末清初的文人徐树丕的记述中,仅在崇祯甲申年(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年,北京暴发了“疙瘩瘟”、江苏暴发了“西瓜瘟”,各地百姓祭祀鬼神祈求保佑,徐树丕将这一年南北的大疫称作“甲申奇疫”,并叹道:“国将亡,听命于神,哀哉!”很明显,徐树丕将明末的瘟疫与明朝的灭亡联系在一起。
而同时代的刘景伯在叙述巴蜀地区瘟疫时,更是认为:
终春秋二百四十年无疫瘟魔者,以予观遗书叙略,皆谓灾害为人事所致,信矣。孟子曰,人性皆善,其不善者习为之。今不责贪官污吏之横于上,而概谓顽梗难驯,是诬民也。
刘景伯直接把“疫瘟魔者”定性为“人事所致”,并指明“贪官污吏之横于上”,同样也是将恶疫与明末政治的腐败联系起来。

影视作品中展现明朝瘟疫状况
“瘟神”的真面目
对明末流行的种种瘟疫,传统中医积极地寻求医治方法,他们多基于“气”的理论,对瘟疫进行分析。比如中医认为“羊毛瘟”的病因是“凉气”。清代咸丰年间,昆明地区出现“羊毛瘟”疫情,清人许起观察病情后,查阅医书典籍,认为病因是“天气郁勃,潮湿酷热,夜不能睡,将曙,露体承凉风中,有丝乘虚而入者也”。
中医根据“气”的理论对明末流行的瘟疫进行病理分析,与现代病理学分析相差甚远,使今人无法准确判定这些瘟疫属于哪些疾病。而且瘟疫病情的严重,“惟疙瘩瘟之阖门暴发、暴死”,也令当时的中医无法对其进行分析解释,“不敢妄加名目也”,“瓜瓤瘟、疙瘩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证,不可以常疫并论也”。史料中对于病死率的记载多是“十室九空”“死者枕藉”“阖门俱灭”“十无一二”等词语,这些形容表述模糊,不乏夸大之嫌;考虑到明末瘟疫正值明清易代,战乱频发,兵燹遍布,诸多的人口死亡可能并非由于瘟疫,但也包含在疫情肆虐下的“十室九空”中。记载明末瘟疫的方志、笔记等史料,大都是入清以后,甚至是在康熙、乾隆年间完成,距离瘟疫发生的时代,已经过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对明末疫情的叙述,难免发生偏差;而时人对瘟疫的恐惧心态,也加重了文献史籍中对瘟疫影响的描述。
这些因素都无法让人们探究出明末瘟疫的真面目,也无从得知病源是什么。不过,文献中对于瘟疫的病症、暴发和流行时间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给了现代医学家、疾病史专家提供了重要线索。
吴有性在《瘟疫论》中记载了“疙瘩瘟”的症状之一,就是“瘿痎”;而暴发于潞安的瘟疫也出现了患者腋下、股间有“核”的症状。近代医学家根据这一病情,对此类疾病进行了定性。清末民初的医学家余伯陶总结认为,“盖疫毒恶血,凝结成核,核痛甚剧。审是,则鼠疫之必夹核,核瘟之必夹瘀,益明矣”,“有核”和疫区有无死鼠,这二者是诊断瘟疫是否是鼠疫的关键情况,所谓“有鼠无鼠,有核无核,界限分明”。而以现代医学标准来看,腺鼠疫会导致患者淋巴结肿痛而结核,这与文献记载的“生核”症状极为相似。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的创始人伍连德博士认为,潞安瘟疫的“患者项部和腋下长有硬血块,而且还记载患者会突然吐血死亡。就我所知,这是目前有关中国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记载”。
“西瓜瘟”除吐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症状。在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的“西瓜瘟”疫情中,判断患者病情严重与否的方法是“看膝弯后有筋肿起”,“紫色无救”,而“红色速刺,出血可无患,以此救活多人,病亦渐息”,当时的中医将此解释为“血出则疫毒外泄,故得生也”。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膝弯后有筋肿起”且呈红色或紫色,明显是股间结核的症状,属于典型的黑死病症状。
而在某些记载中,“羊毛瘟”也有股间结核的病状。虽然在明末的记载中,有助于判断“羊毛瘟”的史料较少,但是清代的记述给出了明确的内容。嘉庆九年(1804)秋冬之际,昆明暴发“羊毛瘟”,疫情严重。时有传闻,点天灯可以祈禳去疫,一时间昆明城上下“树竿悬灯,火光烛天,限满一百八日始罢,计清油之费,万金不敷”。而在这场瘟疫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被记载下来:“鼠先人死,病人皮肤中生羊毛,蔬果亦生之,俗名羊子,即吴梅村《绥寇纪略》所谓‘羊毛瘟’也。”当时也有诗云:“羊毛着物能生死,鼠鬼随人有后先。”出现大量死鼠的现象,让许多现代学者认为“羊毛瘟”也是某种鼠疫。
至此,明末瘟疫的真面目终于揭晓——对社会造成巨大动荡和严重破坏的元凶,正是鼠疫。
来自长城外的“敌人”
鼠疫是世界历史上,传播最烈、致死率最高、影响最大的瘟疫。英文中用“鼠疫”(plague)代指瘟疫。鼠疫曾经长期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传播,其中有三次大流行。第一次是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导致东罗马帝国失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断送了帝国最后的复兴希望。第二次是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导致欧洲三千万以上人口的死亡,世界范围内约一亿人口的死亡。第三次是19世纪后期发源于云南的鼠疫,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导致一千多万人死亡。随着生活条件、医疗技术的提升,尤其是疫苗的研制,当前鼠疫不再流行,但仍不断有零散病例出现。
鼠疫易发于热带、温带的半干旱荒漠草原、半湿润草原(包括高寒草甸和草原)和湿热的沿海森林。广袤的内蒙古草原,是啮食草根及其他植物的野栖性鼠类即野鼠的生活天堂。鼠疫病菌寄生在野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身上,通过鼠蚤传播。但在气候干旱、变冷的环境下,草原上的草类及其他植物,无法满足野鼠的食物需求,于是野鼠开始离开自然疫源地,进入到南边气候温暖、人类集中的地区寻找食物,进而将鼠疫菌传播到没有抗体的家鼠、家禽甚至人类身上。人类之间通过呼吸、接触,从而造成鼠疫的暴发和传播。曹树基、李玉尚便指出:“历史时期北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即当时的农牧分界线”。
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大体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这一条线大致经过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中国半湿润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在北方边疆地带,农牧分界线最明显的标志便是长城。北方边疆在历史上,是瘟疫尤其是鼠疫的高发地带。首先,由于处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位置,北方边疆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降水量的微小变化,都会导致旱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发生,最终影响社会体系乃至政权统治的稳定;同时也会导致生物界产生连锁反应,缺少食物的啮齿类动物,尤其是野鼠进入到人类社会,从而引发鼠疫的暴发和流行。其次,北方边疆长期的拉锯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促使民众流离失所,容易遭受饥饿、寒冷的侵袭,给瘟疫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最后,在各种自然灾害、战争和国家赋役压力之下,北方边疆容易爆发大规模农民战争,从根本上摧毁地方秩序,进而引发大规模的人类灾难和瘟疫流行。
明代在气候上处于小冰河期,干旱少雨的气候,促使北方边疆长期处于生态恶化的临界状态;明朝、蒙古之间的长期战争,不仅促使北方边疆动荡不安,而且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极为繁重的赋役压力。最终,在大规模旱灾和国家赋役的压力下,农民战争在陕北率先爆发,最终席卷了北方边疆,不仅成为明朝政权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造成北方地区大量人口死亡,引发了瘟疫的大规模流行。
明朝人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长城外的敌人不只有蒙古部落,还有携带病菌的野鼠;恰恰是后者的“入侵”,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不是前者。长城可以阻挡游牧民族的南下,但无法阻挡自然环境的影响。
可见,在历史研究中,应从自然环境的视角,审视由其塑造的不同区域社会,在地理空间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揭示其对于整体中国和历史进程的区域影响。长城边疆便是中国历史上鼠疫的重要疫源地和历史的“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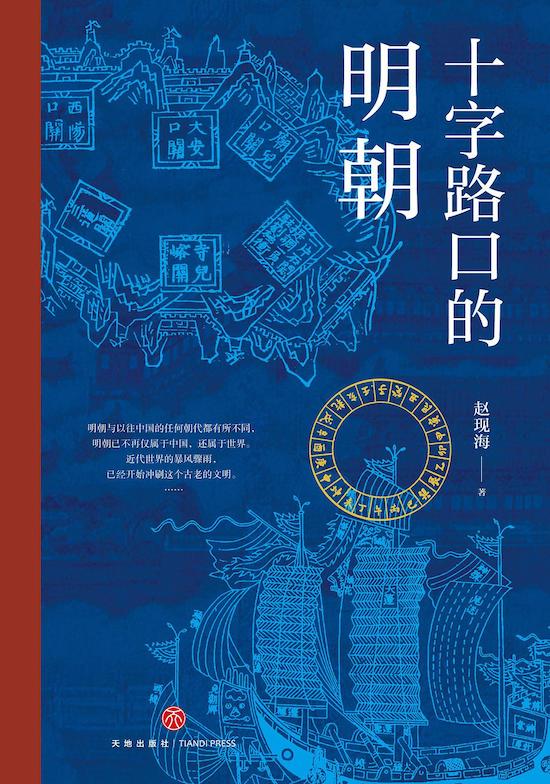
(本文摘自赵现海著《十字路口的明朝》,天地出版社,2021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