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手语者
舞动的双手创造语词,
使你本身成为那语言的一部分。
你必须聋了才能明白。
——美国聋人的诗作《你必须聋了才明白》
从杭州下沙街道的东方路由南向北行驶,那些刚刚从绕城高速或快速路出来的车子像是经历了一场高压阀排气,可以体会到瞬间解放的自由。这个地方地处偏僻,路广、车少,司机几乎不用怎么考虑减速。但在东方路距离元北路不到一百米的地方,马路的东侧有一块交通警示牌提醒前面的车辆:“杭州聋人学校,减速慢行”。
杭州聋人学校创建于1931年,最早叫“吴山聋哑学校”,校名来自杭州的名山吴山。后来几经更名,1941年改称“杭州聋哑学校”,2007年又更名为现在的“杭州聋人学校”。“聋哑学校”同“聋人学校”只一字之差,人们说起来更习惯旧称。“聋哑学校”这个使用时间更长的名称,反映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观念:一个人若是听不见,就等于他不会讲话。
语言学家经常这样描述语言习得的方式:听力是输入系统,口语则扮演着输出的角色。我们第一次听到“大象”这个词,不但捕获了这个词的发音,还获得了“大象”这个概念,下次当我们要表达大象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会发出相应的声音。而聋人因为听不到声音,失去了输入的来源,输出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很长时间里,聋人总是“哑巴”。科学研究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过时和不正确的。聋人虽然听不到,但是发声器官并没有受到损害,也就是说,聋哑人并不哑。换句话说,聋人也可以说话:如果他受到恰当的教育的话。
而且,真正全部丧失了听力的聋人其实并不多。听力的丧失是一个连续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1997)听力障碍分级标准,听力损失程度可以将其分为四级:轻度在26~40dB;中度41~60dB;重度61~80dB;极重度在81分贝以上。但是普通人的说话声音在40~60dB之间,因此中度级别的听力损伤,足以使人不知道旁边人对他讲什么,只能看到对方的嘴唇在微微翕动,尽管他们靠得很近,可是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盲是人跟物的相隔,聋是人跟人的相隔。”三月的一个下午,在杭州聋人学校的一堂专为本校老师培训手语的讲座上,董慧芳引述了美国盲聋人作家海伦·凯勒的这句名言。董慧芳是来自浙江省残联的一位资深手语翻译,许多年她来习惯了在两种语言间来回切换、穿梭,她的口语好听得像播音员,讲话时就像一连串音符在流动,而她的手语则在视觉上呈现这样的效果。
描述聋人生活时,海伦凯勒的这句话常常被拿出来引用,但这句话的确切来源已经无从考证。在海伦凯勒写给友人Dr. Kerr Love的信中,出现过这样一段描述,或许可以看作这句话的佐证:“与盲相比,聋的问题即使不是更重要,也比盲的问题更加深刻、复杂。聋要不幸得多,因为它意味着失去了最有活力的刺激来源——一种带来语言、激活思想、能使我们与人智性相伴的声音。”
在多年的手语翻译职业生涯中,这份工作和其他工作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女性和母亲的本能却将一种难以察觉的恐惧投射在董慧芳的梦境里。有时候她梦见自己的孩子也听不见声音。梦醒了,心里的恐惧却没有散去。
“你们做过这样的梦吗?”她问台下的聋校老师。
现场躁动起来。很多人喊道,“有”。
梦见自己的孩子是聋儿似乎成了聋校老师共有的经验。假如梦变成现实,董慧芳设想过,她说她一定要学习手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孩子交流,参与他的成长。
父母确认孩子部分或完全丧失听力的那一刻是残酷的。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艰难的抉择将伴随父母和孩子的一生。语言是他们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选择:学习手语,还是学习口语。

2016年3月15日的上午,在杭州聋人学校的语言训练教室里,低年级的孩子在这儿接受语言康复训练。教室很小,它用于一对一或一对几的小班化教学。墙面刷成让人感觉到平静的蓝色,卡通图案的点缀又把孩子们引入活泼、明亮的童话世界。年轻的女老师用教学棒指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话,让孩子们逐字清晰地念出来。所有孩子的耳朵上都戴着弯弯的夹子状的助听器。
“打瞌睡”是一个有难度的词组,有学生试了好几次仍然发成“da he shui”,“ke”和“he”是两个需要仔细辨别才能听出区别来的发音。老师张大了嘴巴一个字一个字重复,让孩子们盯着自己的口型看。然而单从口型上来看,它们几乎相差无异。听不清声音的孩子们单靠模仿老师的口型,始终无法将它准确地还原出来。
最终,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打破了这个魔咒,她清晰地发出了“ke”这个音。老师后来提醒我说,小女孩出生不久后成功地动了一次人工耳蜗手术,相当于进行了一次听力再造。
除了助听器配戴、语言康复训练、人工耳蜗手术,听力筛查也是人们对听力损失进行早期干预的一种方式。出生3天后的新生儿就可以进行听力的检测和诊断,在42天内没有通过听力初筛,或者初筛存在隐患的婴幼儿,可以再进行复筛。
“学校的招生数量总的来讲是在减少的。”杭州聋人学校的黄晓琴老师说道。随着医疗知识的普及、科技的进步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聋人的出生率下降,因此聋生数量也呈逐步下降的趋势。
即便如此,存在听力障碍的总人数仍然令人震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的聋人数量大概在2054万。浙江省的聋人数量大约为106万。
他们中只有很少人能够接受普通高中甚至更高层次的教育。根据《2015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截至2015年,在普通高中里设置的特殊教育班(部)仅有109个,聋人在校生为6191人。公报中有关聋人受教育情况的数据非常有限,我们无从得知当年参加高考的聋生人数,也无法获知中国大学中有多少聋人学生。
但公报详尽罗列了接受听力康复训练、接受政府资助植入人工耳蜗和配戴助听器的人数,以及各级听力康复机构的数字。公报还显示,在政府资助下,2015年中国对4.2万名听障孩子的家长进行了培训。
数字详尽程度的差别显示了政策和政府资源投入的重心所在。中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施三项残疾人康复国家计划:白内障手术复明、儿麻后遗症矫正术和聋儿听力语言训练。抢救聋儿的生育听力一直是一项国家工程。
顾定倩是这项国家工程的见证者。顾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殊教育系教授,1982年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他就进入听觉障碍教育领域从事研究。对当年的他而言,这是一个包分配工作的起点,但也许他细致、温和的性格正好契合这项工作的要领,从那以后的近四十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
“大部分聋人的家长不是聋人,是听人。从家长的角度来说,首要考虑是通过治疗和训练,看孩子能不能回到听人的社会。”
家长希望孩子能恢复听力,从那“聋人”里脱离出来,免去日后被社会边缘化的痛苦,相信这对孩子以后走上社会有所帮助。在经济条件发达的地方,父母的这种愿望更加强烈,也更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家长的心理需求与国家政策有一种互相强化的趋势。政策资源的投放重心,首先是听力康复,其次是口语训练,手语教育则基本被排除在外。在《2015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手语”一词出现仅三次,一次是提到一份标题中含有“手语”二字的文件,另外两次是统计“电视手语栏目”数量时出现的。
语言的性质不同于我写这篇文章时使用的笔记本电脑。语言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它的反馈机制要比计算机复杂得多。语言反映了一个人和其他人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是在多变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换句话说,我们看待和使用语言的方式,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对那些熟知聋人处境,并且目睹许多听障孩子长大成人的聋校教师而言,听障孩子学习口语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学习和使用本身的困难,而是他们无法从听人的环境中获得预期的反应。
我在杭州聋人学校参加了一堂摄影课。上课的是聋人老师杜铁军。上课地点安排在室外,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合在一起上课。杜老师计划教他们抓拍跳跃的动作:整个人要在地上伏下来,镜头对准前面正在跳起来的这个人,捕捉双脚离开地面的瞬间。学生们充满了好奇和实验精神,拍完一张后就忍不住拿去给杜老师看,要求点评。
这本来是一堂无声的课,学生和老师之间只通过手语专注地交流,但是陈振茹和她的朋友爱讲话,她们之间常常爆发出亲密的大笑。笑声在空旷的操场上掀起一阵阵涟漪。这个穿着黑色卫衣、扎着马尾的小姑娘弯着一双细细的眼睛,两颊的酒窝因为爱笑凹得更加明显了。
她是这个班上的新生,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从江苏转学到了浙江。尽管她的发音听上去很生涩,但她很爱“讲话”,比起手语她更喜欢用口语上课,在家里父母也会和她通过口语进行沟通。“也可能跟手语的地域差异有关。”学校的童老师提醒了另一个可能会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江苏手语与浙江手语之间存在差异。手语也有“方言”,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手语表达方式不尽相同,异地的聋人会有一个沟通的磨合期,也许陈振茹还不习惯于用她的“母语手语”与同学们交谈。
高年级学生中,一个整堂课几乎都没怎么讲话的女生表示,更愿意选择用手语上课,她用手指指自己的嘴巴,然后摇摇头,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表示自己不太会口语。其他大多数的学生对于“喜欢用手语还是口语授课这个问题”,则给出了“口语、手语都用”的答案。又或者犹豫了一下,不置可否。
杭州聋人学校的校长严丽萍说,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对于低年段的孩子尽可能地开发残余听力,课堂教育以口语为主,手语为辅。学校希望听障孩子尽可能恢复语言能力,融入普通孩子的生活圈子。如果他们的交往被限定在聋人朋友的圈子,在信息获得、情感交流、个人发展等方面容易变得相对闭塞。
在聋校,低年级孩子的行为模式和普通学校的孩子没有什么分别。他们在上课时好动、不安分,在别的同学被点名批评的时候哄堂大笑,在教学楼走廊上见到老师时大声地打招呼,体育课上踩着滑板帅气地辗转腾挪。但随着年龄增长,总有一天,他们将发现听力缺损的事实,进而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
“越小的孩子越阳光。”杭州聋人学校学生处的张燕琴老师说道,她兼任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
那些令他们确认差异,并带来一个聋人的自我意识的诱因,有时候是异常细微的,通常是来自拥有正常听觉的人们不经意的反应。
“比如学校里有一个来访活动,聋生被要求读一段文字。当这个孩子开口后,听的人发现这个声音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怪,忍不住眉头一皱。读的孩子留意到了这个细微的变化,他就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张燕琴老师举例,再加上学生此时处于变声的青春期,更能意识到自己声音的“难听”。
他不再愿意当众朗读。他开始退回到自己的世界。
口语的世界从此慢慢萎缩相比。与此同时,手语的世界开始生长起来——尽管父母、老师和社会都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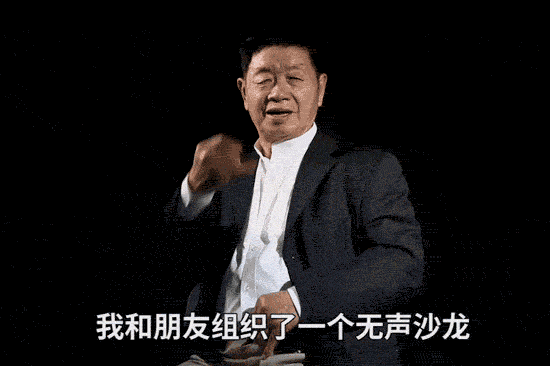
但不是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手语翻译那样,聋人之间交谈的手语,恐怕一点都称不上优雅。每周三的下午,上海市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宝华里居委会的活动室里,徐剑平和他的聋人朋友们会聚在一起聊天。曾祥开是这一天的主讲,他正在跟朋友们讲述最近的台湾公投、九二共识的重要性,还有香港经济的走势。他的眼睑有些下垂,嘴角微微耷拉,每一个手势都很有力,有时候甚至会拍到面颊,这让他看起来好像正在生气。但是当下一个人开始发言后,你就会发现差不多每个人都是这样。真实的手语就是这样,手势的力度、夸张的面部表情都是语言表达的一部分。

曾祥开和刘家春是这个“书香无声读书会”的组织者。八十二岁的曾祥开年轻时是京剧业余演员,退休后除了在家做木工,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组织这个沙龙上。在口语环境的包围下,相比普通人,聋人获得信息的渠道要狭窄得多。刘家春是闸北区的聋协干事,他为沙龙拟定的目标是“增加知识,了解祖国各地特点,讲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世界观”。参加者以中老年聋人为主,他们年轻时读书不多,这样的定期聚会讨论可以让他们保持着与社会的同步。
“但也有很多人不来,他们可能去搓麻将了。”刘家春做了一个抹开来的动作。
徐剑平很少缺席沙龙。他住得不远,骑车单程只要10分钟时间。他和母亲住在一起,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干花、盆栽、小玩偶随处可见,阳台外还关着一只比熊犬。看见有人进来,小狗常常兴奋地跳到玻璃移门上,眼睛巴巴地望着屋内,一旦移门打开,就满屋子颤颠颠地跑,谁也阻止不了它——除了奶奶,它最怕她。
奶奶就是徐剑平的母亲程莺英。程莺英出生在印尼,后来回国读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车间太忙,她没空带孩子,也没有发现孩子有什么异常。直到有一天托儿所的老师告诉他,孩子听不见别人说话。她赶回家,叫了一声在眼前的儿子,徐剑平没有回转过来应答。
医生无法给出徐剑平失聪的准确原因,只能猜测是肺炎时注射庆大霉素产生了副作用。从此,程莺英开始了和命运之间的马拉松式抗争。她从成都寻找中药配方,带着徐剑平四处针灸,尝试一切办法去唤醒那根被医生判定为无效的听力神经。孩子入学年龄到了,她坚持把徐剑平送到普通学校上学。这是个糟糕的决定。上到三年级,始终跟不上的徐剑平只能退学了,他上课时根本听不到老师在讲什么。大部分同学对他不错,但也有少数会叫他“哑巴”。
程莺英说起当初错误的坚持很激动,白发会跟着她瘦小的身躯一起颤动。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她是倔强的,也是诚实的。最终程莺英只能说服自己另觅聋校。把儿子送到聋校的第一天,她哭得比任何时候都伤心。那意味着她做了妥协,放弃了让孩子重新回到普通人的可能性。
徐剑平第一天上学的经历不太愉快。他很害怕,因为之前他没有接触过其他聋人,结果他吓得从学校逃了回来。
让程莺英安慰的是,不适应是暂时的,徐剑平慢慢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上课时老师从拼音开始重新指导他,在打好基础后,他获得了独立读书的能力。他很快体验到原来在普通学校没有体会过的自信。
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程莺英让儿子躲去福州老家探亲,顺便学艺。儿子回来之前,丈夫在加班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程莺英来不及过多悲伤,因为在上海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就读的儿子面临着升学或就业的问题。聋人就业分配是个难题,丈夫生前所在的工厂照顾程莺英家庭的情况,提出让徐剑平去工厂顶替他父亲的工作。
这也许是丈夫过世后最大的安慰了。但是徐剑平不愿意。他爱画画,想继续读大学。最后工厂给徐剑平每周三天时间在外面念书。边工边读,徐剑平考上了上海市徐汇区业余大学的实用美术专业。2004年,工矿企业不景气,徐剑平做的精雕工作每天刻钢印的时间从一整天缩短到了半天,还有半天时间被分配到其他工作流水线。徐剑平索性辞职了。程莺英为此很是生气,尽管儿子已经三十七岁了,可是她没有办法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2007年徐剑平开始在自己生活的花园城社区居委会里担任残联工作助理员,为社区出黑板报、拍活动照。2010年,他又努力争取做了世博会志愿者。
徐剑平把志愿者的工作看得很重。上岗前他揣着地图挨个到各场馆考察,以保证能有效提供服务。上岗后,一有空闲时间,他就教其他志愿者手语。
不管在哪个意义上,徐剑平已经接受了他的聋人身份。可是程莺英不,“我现在看到聋人做手势,看到还是会反感,心里非常难受,所以我不去做也不去学手语。”程莺英用手指指自己的胸前,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内心似乎努力对抗着某种无法排遣的折磨。走在路上,如果儿子打着手语引来旁边人的侧目,那些眼神总是像针一样刺进程莺英的心里。

所以程莺英对手语的看法不是没有原因的。语言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但语言也会造成人和人之间的隔绝状态。在一个社会中,使用人数较少、使用范围较小的语言总是处于相对劣势,而使用手语的人就像一个个孤岛,被使用口语的人群像海水一样包围着。
沈炳峰刚刚从人力资源市场回来。那里传达室的保安甚至连门都不愿意开,他从窗口探出头来,粗声粗气地说:“喂,干什么,不能进去!”但是炳峰远远地看到,里面这栋大楼的电子屏上,滚动的红色字幕显示:第二天将有一场大型的人才招聘活动在这里举行。保安没好气地对他说:“你明天再来过吧。”
明天会怎么样呢?回去的路上,炳峰从一辆公交车上下来,去换乘另一辆公交车,他的心里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一辆送外卖的电瓶车从他身边飞快掠过,很快消失在前方的路口,电瓶车自如地穿梭,仿佛经过的人都是不会动的柱子。炳峰正朝着旁边的店铺张看,什么都没发现,依然毫无知觉地往前走——电瓶车发出的声音很小,只有在它驶近时才能听到轻微的响声,而炳峰的耳朵辨别不出这样的声音。
炳峰说他想找的下一份工作希望能包吃包住,工资和正常人一样。他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我离家的话能留下了,包住很安全,每晚回家骑车不安全。去年我同学走(去)世了。”去年他有位朋友在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被转弯的汽车撞倒了。
2008年从中专毕业后,沈炳峰在服装厂、肯德基、麦当劳、纺织厂工作过,两个月前他刚刚从一家纺织厂离职。离开的原因是不喜欢那里的环境,天热的时候室内高达40多摄氏度,而且多灰尘。炳峰的父母很少在第一时间知道儿子换工作的消息,直到他们看到儿子好几天不去上班之后,才猜测儿子是不是前一份工作不干了。
炳峰的父母以制作蜡箔为生。父母和炳峰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在吃饭、睡觉等生活上一些简单的沟通可以借助手势。炳峰父母所认字不多,难以通过写字沟通。
和听人交谈时,炳峰会用到纸和笔,但是他有着比写字更强烈的自我表达的愿望。看着纸上的问题,他的嘴巴轻轻嚅动,不时发出一些声响——通过唇读能够帮助他理解语句。当他思考下一个问题该怎么回答时,他会不由自主地比划手语,帮助自己组织语言。

手语语法和汉语语法不同。受手语这种母语的影响,聋人的书面表达有时会出现让听人难以理解的语序和用词。这种现象的原因众说纷纭,但这种现象的结果是使得人群隔离变得更为可见。
炳峰带我去看他的一位同学。这个年轻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像大多数人赌气时的做法一样。更糟糕的是,他听不到外面母亲的敲门声。炳峰动员他下楼来。
这个男孩裹在一件黑色的短棉袄里,眉目清秀。距离他的上一份工作已经有一年多了,毕业后他最早在一家印刷厂工作,是一家福利厂。低头、弯腰……他所在的生产线要求他不断地重复这个动作,后来他觉得太累,干了几天腰板直不起来了,于是就离开了印刷厂。在上一家工厂,引发他离开的是工作岗位的变动,他被安排到了从未做过的最后一道工序,他感到完全来不及做。母亲劝他坚持一段时间,等熟悉了以后就能上手了,可是他再不想去了,他内心隐隐地把工作不顺心和自己的身份联系起来。
“他觉得不公平。”他的母亲说道。
母亲已经很难改变他。男孩对自己的身份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在饭桌上,家人们会避免高声谈话说笑,“他向我们看来看去,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那种感觉就像他被囚禁在了一个口语的牢笼中。
如果不是父母或子女存在听力障碍,听力健全的人们几乎觉察不到这种牢笼的存在。尽管对聋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生存的基本社会环境。

聋人的就业范围通常局限在一些“安静”的工作领域,比如手工、摄影、动漫、广告、淘宝页面设计——互联网的兴起对聋人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有许多操作可以在后台完成。但由于沟通上存在障碍,没有多少企业愿意招收聋人,除了福利厂或者愿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帮助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即使税收上对企业招聘残疾人有一系列优惠政策,仍不足以吸引企业主动招聘聋人,有些企业的员工名录里有残疾人,但只是挂名,并不让他们真正参与工作。
公共服务同样如此。政府机构极少配置手语翻译,因此聋人办许多事都需要额外请手语翻译。“平时我们这里的老师常常被叫去派出所、医院做翻译。”杭州聋人学校的童老师说。
从2007年起,手语翻译已经是一项有标准化等级考试的职业。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是中国最早设立手语翻译专业的高校之一。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982年教育部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是我国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单位。在这个以特殊教育为特色的学校里,几乎每个人都多少会点手语。“手(语)翻(译)班的学生会学三年的手语课程,听(力)障(碍)班会学习一年,其他的班级也会学一个学期。”教授手语课的史玉凤老师说道。
该校手语翻译专业的招生人数从最早28人,最多的时候发展到80人,近年来稳定在三十人左右。每一年都能招满,就业也还可以,大部分学生去了公安、残联、康复机构和聋校。这个专业正处在一边研究一边教学的摸索阶段,一个显著的问题是以手语为母语的教师特别少。高校对教师有学历要求,而中国以手语为母语的聋人中,有研究生学历的极少。

因为语速比较慢而且带点口音,她常常被误认为是外国人。
“这样也好。”她偷笑道,可是过了一会儿她收拢了笑脸,转了一副困惑的表情:“但是时间长了会觉得自己的身份有点怪。”
在读高中之前,陈玲琳没有接触过手语。这听上去颇为奇怪,但在一些致力于语言康复的聋人学校,手语的地位极为边缘。比如陈玲琳就读的上海市闵行区启音学校,顾名思义,这是一所强调口语教学的学校。到了高中阶段,她来到了上海唯一的一所聋人高中——上海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忽然她发现身边的同学用的是另外一种语言,而老师在上课时除了用口语,同时也会用到一些她看不懂的手势。为了和班上的同学沟通,融入他们的圈子,陈玲琳开始了和手语的接触。
大学从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的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她希望读研。“当时许多学校没有招收聋人学生的经验,不敢收。”在和父亲商量之后,陈玲琳决定出国念书。
她想选择一个跟聋人事业有关的专业。正好她在网上看到了有个聋人学生在韩国读国际手语翻译专业。除了可以学习手语语言学、手语翻译理论知识,这个专业还包括三门“外语”:韩国手语、美国手语和国际手语。
学习手语颠覆了她的身份认同。从口语教学为主的聋校,到手语教学为主的聋校,再到看不懂手语的韩国学校,陈玲琳一次又一次地置身陌生的环境。

高中以前,她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听人。到了高中,接触到手语之后,她开始有点困惑自己到底算是聋人还是听人,游走在边缘型的身份认知中。初到韩国的那段时间,她开始前所未有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聋人”,因为她既无法和韩国听人交流,也无法和韩国聋人交流。而现在,她既可以接受自己是一个聋人,也可以接受自己是一个听人,也就是所谓的双身份主义。
而出国念国际手语翻译专业,颠覆了陈玲琳有关手语教学的看法。在韩国的学习经时她曾去美国交流研修两周,在访问一所聋人中学的过程中,发现该校教学上注重培养聋学生流利使用美国手语和英文写作双语能力。
和中国推行的标准手语不一样,美国手语并不模仿书面语的语法,因此不是书面语的手势版。美国手语和英语一样,是一门独立而完整的语言——也即中国所说的自然手语。这和陈玲琳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完全不同。出国之前,和许多中国语言学家和特殊教育专家一样,陈玲琳认为,自然手语会影响聋人学习书面写作。自然手语是按照聋人自己的语言习惯、自身的生理特点形成的语言。学习标准手语,又叫做手势汉语,才可以改善他们的写作能力。而在美国,陈玲琳看到,学习自然手语并不妨碍聋人掌握阅读和写作能力。
陈玲琳的同事盛焕幼年时寄放在外公家。在她十四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发现她听不见声音,医生诊断她接近全聋。和许多家长不一样,母亲放弃了给她配戴助听器的尝试。这源自医生的一句忠告:接近全聋,意味着孩子之前的世界是静默的,当忽然闯进了声音之后,难以想象她的内心将迎来多大的冲击。
母亲将她接回身边后,完全无法交流。盛焕不能讲话,不识字,而母亲不会手语。母亲还记得送盛焕进幼儿园的第一天那次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分别。她不能像其他父母一样告诉孩子:“乖,妈妈会来接你。”只能看着女儿睁着惊慌的眼睛离开。她去观摩过几次幼儿园教学,渐渐确定了对女儿的教学方法:一个概念分别用拼音、汉字和手语讲授一次。她自己简单地学习了一些手语。她用手语教女儿学习拼音、查字典。
盛焕上小学后,班级教室的墙上贴着孩子们的作业,盛焕母亲从这些作业里读到一个奇怪的句子:我们要做学校规范。她反应过来,这是因为“做”和“执行”用的是同一个手势语。母亲敏锐地意识到,学校的语文教育自有其局限。于是买来许多连环画,陪盛焕逐字逐行阅读,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就帮助她查字典,并用手语加以解释。每天晚上,盛焕家里总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读报时间。一家四口聚在灯下,房间里充满了琅琅的读书声。
父母相信盛焕可以通过加强阅读来提高写作和逻辑思辨能力。小学一二年级,盛焕已经可以阅读文学作品,初中父亲工作调动至新加坡,盛焕进入当地学校念书,母亲陪她学习了一个月的美国手语,盛焕又用半年的时间掌握了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大学毕业后,她进入新加坡科思达教育集团工作,除了设计师的本职工作之外,还客串做了大量的中英翻译工作。而这一切都始于她的母亲跟她学习手语,陪她查字典。
和盛焕的母亲不同,多数听觉健全的人对聋人世界的看法单调刻板,缺乏反省和挑战。即使是深爱孩子的父母,也会不由自主地将听力健全和听力缺损转换成两个分离的世界:听人的世界是正常的,而聋人的世界是不健康、不正常甚至是不自然的。
在被分离出去的世界中,聋人的命运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自己的生理特征,学会和听力健全的人一样使用同一种语言和表达方式。这不但决定了分配给聋人的社会资源的投放方向,也决定了聋人的自我认知:他们的命运就是不断模仿、接近听人世界,期待有一天被后者接受。
第一个站出来审视这两个世界的关系的,是一个长头发、戴着垂式耳环、留一小撮灰色胡子、常常穿着拖鞋的男人。
Paddy Ladd的长相和装扮,一眼就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他是英国BBC手语节目See Hear最早期的主持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Paddy 出生在一个听人的家庭,母亲在他8岁的时候过世,他进入主流口语学校就读。直到22岁,他才见到了第一个聋人,并开始学习手语。
在很长时间里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听人还是聋人。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们告诉他:你不是聋人,只是恰好听不太见罢了。而当他离开学校开始寻找工作,去应聘聋人老师时,同样的人却对他讲:你不能教聋孩子,因为你是聋的。他有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直到在聋人社群内部做了社工之后,Paddy才觉得自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长时间地迎合听人社会让Paddy感到压抑,当意识到有这个问题的不止他一个之后,他决定要做点什么去改变。Paddy不喜欢“聋”(deafness)这个词,因为它把重点放在现代医疗对听力缺陷的改造上面,他想要创造一个新的词去挑战这个观点。
“如果一个人为自己的聋人身份感到害羞,那么他的内核是很小的,如果一个人为他的聋人身份感到自豪,那么这个内核就会大一些。”
Paddy Ladd创造了一个新词Deafhood。英文中,“hood”可以作为词缀放在单名词的后面,表示身份、资格、时期,而“Deaf”源于James Woodward提出的对聋人文化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和小写的“deaf”区别开来,后者指代生理学上听力有缺损的聋人,而前者指代享有同一种语言(手语)、同一套文化认同的聋人。
Paddy Ladd想用这个词表达自己的看法:聋人是完整的;手语和口语一样完整而丰富,而不是一种次一等语言。他努力将手语推上了电视,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支手语流行音乐录影带,建立了与聋文化有关的硕士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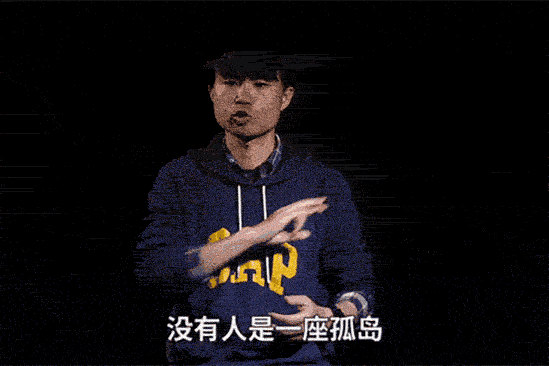
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2.9%的聋人学生、63.2%的成年聋人“希望我国聋人有都能看懂的通用手语”。但推行通用手语的过程常被听人的看法所主导。自1950年代起,中国政府就试图像推进普通话一样,推进统一手语。官方希望通过推广统一手语,促进全国各地聋人交流。1990年,中国聋人协会编辑出版了《中国手语》。2003年,该书经修订后出版了第二版,正是这个修订版本,引起了极大争议。
手语和汉语的语法差异很大。比如,汉语“你吃饭了吗”,用手语表达是“你”+“吃”+“饭”,或者“你”+“饭”+“吃”,再配上疑惑的表情——没有副词,没有语气词,语序存在多种可能性。聋人学习书面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母语——手语的影响。《中国手语》第二版的出现试图改变这一现象,将手语和汉语合并成一种语言,迫使手语改变原有语法形态,而跟从书面汉语的表达习惯。这种跟随汉语书面语法的新手语被称作手势汉语,而原有手语被命名为自然手语。
要求手语向汉语语法和拼音靠拢,争议很大。指拼法也是手语向汉语靠拢的尝试一直。在上海闵行区启音学校,孩子们在说到“爸爸”、“妈妈”的时候,用自然手语表达是不被接受的,尽管它很形象直接:把你的大拇指放在嘴唇前,轻轻点两次,表示“爸爸”,大拇指表示最大的意思,食指次之,同样的点两下表示“妈妈”。他们要用手指的指式打出字母“ba ba”、“ma ma”,这麻烦多了。而这样的教学方式是为了让孩子们更多地接触拼音,确切地说,是接触汉语。
2010年,上海有一家手语培训学校关闭,从里面出来的几位学员取得了中级手语证书,但仍然不能和聋人交流——他们学习的是新版的中国手语,而上海聋人用的是本地的自然手语。就在这一年年初,苏少波在公交车上偶然看到有人拿着手语课本在自学手语,就给他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这次邂逅导致了苏少波后来发起了豆瓣小组“跟我一起学上海手语”,每周末在静安公园授课。这个小组乍看是要保护本地的手语文化,但无疑与推行统一手语的失败尝试有关,苏少波的初衷是为了改善极其低效的手语学习。
2011年苏少波创办的手语小组正式更名为“随手执梦手语文化中心”。“教手语一开始是我们的起点。”通过豆瓣发布、公益活动等途径,五六年下来随手执梦大概接触了5000多位学生,但效果同样不佳。

“我们毕竟不是很专业,也没有经验,五六年来真正能够毕业的没几个。”苏少波和他的合作伙伴都是艺术设计专业出身,共同打理一家创意公司。这份稳定的工作能够帮助他们维持随手执梦的运转。
随手执梦的工作室在上海市中心的一间民居里,绕进小巷,走上几步木台阶,就可以看到边上的门铃——尽管它有时候并不那么可靠。工作室房间的门是由里向外推的,进门的柜子里放着各色茶具、杯子,除了办公用品,这个不到三十平米的房间里还恰到好处地摆放着微波炉、冰箱、咖啡机、烧水壶、衣架。对面的墙壁上贴着这个月的工作计划,从二月份起,他们就暂停了手语学生的招收。
但停课整顿是暂时的,重新开始的时间要看陈玲琳从韩国回来后的准备情况。陈玲琳大学期间担任学生会里“一帮一”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在校内外开展手语课,教听人手语。苏少波邀请她加入“随手执梦”时,她曾质疑说:“我们这群人力量太渺小,很难改变社会的,选择这条路很辛苦。”但去韩国读书之前,她已经每天为项目策划熬夜,因为忙着和企业机构负责人洽谈项目,几乎找不到喘息的时间。
2015年,这家机构已经从民间组织变身为企业。盛焕辞去了原公司的工作,全职在此工作,机构发展重心也转移到了CODA(child of deaf adults,聋人父母的健听子女简称)上。
“建立专业的手语翻译队伍的时机也许不太成熟,商业效益也不大。CODA群体是唯一可以帮助聋人最亲的,进可以无障碍沟通,退可以当翻译力量的储备。”苏少波说。
随手执梦的聋人子女手语助学项目,目标是帮助低收入、无业的聋人子女学习手语,改善与聋人父母的沟通问题,并为当上手语翻译铺下一条路。
公益组织很难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他们希望转型为商业机构能引入更多资金,以商业方式解决问题。苏少波的设想是未来做与聋人文化相关的移动社区,不光是聋人、聋人家庭成员、服务者(比如手语组织、相关手语企业),普通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进一步推动手语或聋人相关行业和工作机会。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