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美墨战争︱自由与扩张悖论:选择理想,还是选择利益
“天赋使命”让美国不断扩张
从美国革命开始,美国具有了自己的外部利益,扩张便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美利坚民族是一个扩张的民族,其扩张意识主要起源于“天赋使命观”或者清教徒的“宿命论”,即美利坚的扩张是为了实现上帝赋予的传播基督教文明、征服野蛮民族和落后文明这一神圣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从杰斐逊执政开始,自由的观念就开始与扩张性的外交政策相结合。杰斐逊将美国看作是世界民主的发祥地和世界自由的避难所,他从农业共和的理想出发,认为美国的共和制度建立在自由土地充裕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之上,如果不扩大领土,一个领土有限、人口日繁的共和国注定要衰落,因此他主张不断地向西部扩张空间,从而保证共和制度的经久不衰。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后,美国领土扩大了一倍,之后历届总统都选择用领土扩张的形式来诠释美国的自由观念,在维护自由的名义下,将美国的领土不断向西推进。

伴随着领土的急剧扩张,各种扩张理论迅速兴盛,其中最流行的便是“流动共和国”(Dynamic Republic )理论。这一理论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流动着的共和国,她的人民是自由的特殊持有者,并且一直处于流动状态。这一理论得到了众多观点的支撑,例如“文明中心西移论”和“熟果理论”。“文明中心西移论”认为文明的中心是朝西转移的,美国穿越大陆向西进军的过程是为了将文明延伸到亚洲这一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熟果理论”则是根据物理学的引力定律,建立在美国对邻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一基础之上,将邻近的别国领土比作熟透的果子,在政治引力的作用下必将落入美国的手中。
与“流动共和国”理论相呼应,1840年代出现的“天定命运论”使得美墨战争期间美国领土的扩张进一步合理化。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天定命运”的正式提出者是《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The 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 )的创立者约翰•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
1845年七八月份,奥沙利文在《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兼并》的社论,谴责欧洲国家干预德克萨斯兼并的目的在于阻止美国实现美国的“天定命运”。所谓“天定命运”,即拓展到上帝为美国每年倍增的几百万人口的自由发展而指定的整个大陆,这是奥沙利文第一次使用 “天定命运”。12月27日,他在《纽约早间新闻》(New York Morning News)上发表了一篇针对俄勒冈问题的社论,第二次运用“天定命运”这一概念。他提出不管怎样,美国对俄勒冈领土的所有权将是最强有力的,这一所有权凭借的是美国的“天定命运”。“天定命运论”融合了以往美国国内流行的各种扩张主义思潮,是这些思潮的抽象和浓缩。其中,美国人口的急速增长、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上帝的赐福或者上帝的眷顾是奥沙利文定义“天定命运”的基础,而这些基础早就扎根于美国早期历史当中了。
大辩论:崇尚自由的美国该不该扩张
然而,美墨战争毕竟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次以战争的方式从弱小邻国获取领土,战争带来的诸多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扩张的再思考。美国向来以自身的“纯洁性”(innocence)自居,但这种赤裸裸的武力掠夺无异于将自己等同于欧洲强权。因此,波尔克政府的扩张政策必然激起众多批评,其中最广泛、最尖锐的批评是:扩张政策有害于美国的自由事业,侵略战争违反了“美国的信念”,违反了美国的自由原则和共和制度。但是波尔克政府及其扩张政策的拥护者们则从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出发,认为扩张可以增强美国的国家实力或权力(power),这是国内自由的保证,也有利于自由在国外土地上传播。

针对扩张与自由的关系,美墨战争期间战争异议者与扩张主义者之间围绕以下三方面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美国是否会重蹈古罗马的覆辙?
辩论再次引起人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重蹈古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覆辙的关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美国的存在是一次伟大的“实验”(experiment),还是一种预定的“天命”(destiny)。
“实验思想”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普遍怀有的一种思想。在共和国的早期,人们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出发,结合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命运,认为所有世俗政权都是有限的,有繁荣就有衰败,有开始就有结束,任何共和国都摆脱不了最终走向腐败、堕落的命运。从这样一种历史假设出发,建国之父们将美国的诞生和存在看作是一次伟大的“实验”,一次摆脱古典共和厄运(classical republican doom)的“实验”。随着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共和国在新大陆上扎根并得以茁壮成长,美国人的自信心也在迅速增长,“天命”的思想开始逐步取代“实验”的思想。
这一思想同样来自于基督教,不同的是它从基督教的“上帝选民说”出发,将历史看成是“救赎的历史”(redemptive history),美国是上帝选定的国家(the elect nation),美国人是上帝选定的民族(the chosen race),担负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救赎的重任,因此可以超越历史。“实验”思想暗含着美国未来发展的某种不确定性,体现着建国之父们对美国未来的谨慎乐观,而“天命”思想则折射出美国人对美国特殊性的绝对信任,这两种心态都是美国独特的历史经历的产物,两者的对立与冲突也就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美墨战争期间,人们就波尔克政府的武力扩张政策所展开的辩论充分体现了这一内容。“实验”思想的信奉者从美国的武力扩张中看到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辉格党的一位社论撰稿人贺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就援引“希腊、罗马用剑去扩张帝国版图以至自由被毁灭的历史”,认为只有“白痴与恶魔”才会去寻求对国家如此有害的征服的荣耀。但是“天命”思想的信奉者则认为希腊、罗马灭亡的历史规律不适用于美国。美国是用与众不同的材料打造的,她有“一种扩张的特殊能力,一种其他政府从未有过的天赋才能”,她的命运得天独厚,那里没有出现暴君、卖国贼的危险,也不会有其他时代有过的使自由人民受害的无意义的战争。因此,美国的武力扩张不会导致与古罗马帝国相同的命运,美国“注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
扩张是国内自由的保证还是威胁?
在“流动共和国理论”的支持下,扩张主义者将扩张看作是自由的保证,正如一位支持战争的参议员在辩论中说:自由需要国家不断地发展与“几乎无限地扩张势力”。另一位参议员紧接着说:“必须依靠无休止的不断行动”,美国才能维护自由。“让我们伸展到准确的、适当的范围,我们的自由才能永存;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力量将得到加强,火焰将更加明艳,它将照亮一个更加广阔的田野。”如果不这样,一个被动的美国将停滞不前,最终沦为欧洲的盘中餐、砧上肉,而欧洲早已是人口密集、社会弊病丛生、不堪重负了。
针对扩张主义者为自由寻求发展空间的理论,反对派议员托马斯•科尔温(Thomas Corwin)发表演说,讽刺这种毫无意义的寻求。他说如果他是墨西哥人,他将用这样的话来回应:“难道你们国家没有地方埋葬死人了吗?如果你们胆敢进入我的国家,我们将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住进我们好客的坟墓。”他很早就预见到扩张主义的战争将产生地方冲突,致使联邦内的姊妹州陷入内战的深渊。就扩张可能给国内自由带来损害和威胁这一问题,卡尔霍恩也发表演讲说“历史上没有例子说明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试图占领像墨西哥这么大的一片领土而不出现灾难性后果的”。他将墨西哥比作一颗“禁果”,吞下这颗禁果,将给美国政治体系带来致命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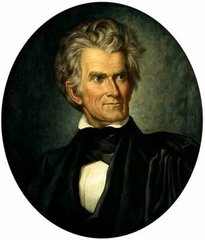
扩张能否促进自由的传播?
早在美墨战争初期,作为反对派的辉格党议员就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并对此加以强烈谴责。国会在讨论波尔克总统的宣战请求时,约翰•克里滕登(John J. Crittenden)参议员发表演讲,指出:“南美和墨西哥独立国家一度被看作是与旧世界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的伟大的共和体系的一部分,作为共和体系的领袖,我们的政策是珍视这些国家,领导她们以我们为榜样走向自由。但我们现在却发现自己是第一个与这些共和国中最大的,也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处于一种战争状态。这一事件将成为一个坏典范,给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和共和主义造成不良后果。”一位年轻的辉格党议员也发表演讲说,尽管他欢迎“我们的制度在整个大陆上扩展,共和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但他认为这样一种“使命”的完成绝对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靠自愿,“战场上的流血和屠杀也许会使人变得英勇,但很少使国家变得富强、伟大、有道德”。侵略性的扩张主义只会破坏共和美德,因为它能摧毁所有的法律、秩序和宪法本身。
面对辉格党议员的诸多指责,扩张主义者将“天定命运”作为他们的理论武器,从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出发,强调让大陆上的落后民族获得新生是美国的责任和义务。“再生”(regeneration)一说将美国的扩张主义与旧世界的扩张主义区别开来,前者是为了拯救落后民族,后者则是为了统治其他民族。随着墨西哥战争的逐步深入,到“全墨西哥运动”时期,“再生”理论被扩张主义者发挥到极致。他们一方面宣扬墨西哥人民渴望加入联邦,另一方面将美国在墨西哥的侵略战争和美国对墨西哥的兼并解释成,这是为了将墨西哥民族从残忍、自私的统治者手中解救出来,并使其得以分享美国秩序、和平与自由的恩惠。

尽管扩张主义者坚持认为兼并有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美国共和使命的完成,以及“落后的”墨西哥民族的再生,但这些观点却招致辉格党人的嘲讽。
针对扩张主义者的“再生”理论,反对派辉格党议员提出异议:首先,他们认为美国兼并墨西哥违反了统治者须经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其次,他们对于伴随领土兼并而来的大量异族、混血人口能否得到新生表示怀疑,对于拯救“落后的”墨西哥民族普遍持怀疑态度。弗吉尼亚州前辉格党参议员威廉•卡贝尔•里夫斯(William Cabell Rives)在弗吉尼亚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说,美国“没有干涉其他国家制度的使命”。其他民族也应该像“我们以最适合我们的方式追寻我们的幸福一样”自由地追寻他们自己的命运。“通过武力和侵略”扩展国家的边界是“一个卑贱的、不荣誉的企图”,不值得美国去追求,“扩展法律、和平、自由和宗教的道德帝国才是值得美国不懈追求的一个梦想”。
扩张与自由:美国外交政策中无法回避的矛盾
美墨战争期间美国国内就扩张与自由的关系所展开的大辩论并没有削弱“流动共和国”理论的传播和“天定命运”学说的盛行,更不可能改变美国的扩张进程。原因在于:
其一,对自由的捍卫并不能否定领土扩张对于美国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大陆扩张是美国发展的必经阶段。1840年代的大陆扩张既是早期领土扩张的延续,又是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北部工业革命的发展急需扩大国内市场;西部农业的商品化迫切要求向西部纵深地区拓殖;南部种植园经济的衰落促使奴隶主求助于周期性的土地扩张,所有这些都促使这一时期的领土扩张表现为更加急进的形式。
其二,与大陆扩张的迅猛发展相同步,美国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也在逐步发展、完善。成熟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将扩张性的对外政策与美国的自由事业相结合,从而清除了美国扩张道路上的“路障”。
自由派未能阻止美国兼并墨西哥领土并不表明将自由作为美国国家目标的自由派已经完全失败,对自由的珍视始终是制约美国武力扩张的重要力量,这在后来美西战争前后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有充分表现。美西战争是美国从大陆扩张走向海外扩张的开始,美国国会和各地就美国是否应该进行海外扩张、吞并海外领土展开辩论,从而形成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外交大辩论,扩张与自由的关系再次成为辩论的焦点。美国的扩张到底是有利于自由的事业,还是会损害自由的事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与矛盾。在现实利益与自由理想之间,美国外交始终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