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莱布雷希特专栏:歌剧创作让女人走开?
当大都会歌剧院宣布下一季要上演凯雅·萨里亚霍(Kaija Saariaho)的《爱在远方》(L'amour de loin),媒体立刻大肆渲染这是一百多年来大都会歌剧院首度上演女性作曲家的作品。上一次还是1903年演埃塞尔·史密斯的《森林》(Der Wald),不过很容易被遗忘。

我不确定哪个细节更叫人遗憾:是那不可原谅的间断还是媒体只知道围着作曲家的性别打转。在2016年,女性主管强子对撞机或是当脸书的首席运营官不会引起什么议论,但她要是写了一出歌剧,就能上《纽约时报》的首页。也许更深层的信号是,歌剧已经脱离了我们的时代。
女性是如何被排除在歌剧大门外的?牛津史家安娜·比尔(Anna Beer)在《声音和甜蜜之歌》中通过八位作曲家(三位十七世纪人,一位十八世纪人,两位十九世纪人,两位二十世纪人)的生平追溯了此种逐渐排斥女性的模式。虽然其中没有一位享誉全球,但我们依然惊讶于得知古典时代的女性要比现代女性更容易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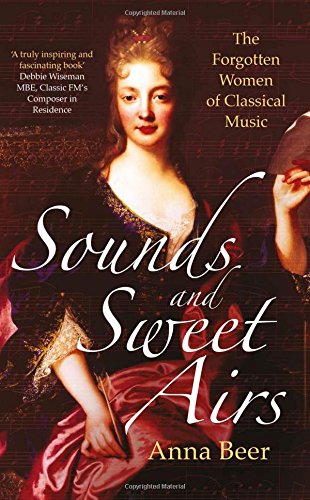
安娜·比尔在今年出版的《声音和甜蜜之歌》(Sounds and Sweet Airs:The Forgotten Women of Classical Music)一书。
比如,弗朗切斯卡·卡契尼1587年出生于弗洛伦萨的音乐之家,十三岁时在父亲写的歌剧中献唱,二十岁时应米开朗基罗的诗人侄孙之邀写了一首嘉年华音乐,小米开朗基罗为之作词并编舞。他认为她的乐曲“非常优美”,还将她写进了诗里。美第奇家族封她为“乐师”,定期委约她作曲。
在王妃的宫廷里,卡契尼如鱼得水。她结了两次婚,两次都继承了丈夫的家产,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曲。她唯一不喜的是宫廷里常见的奴颜婢膝。1641年她离开美第奇家族,他们抹掉了关于她的一切行踪。她后来去了哪里,何时离世都无从知晓。只有一册薄薄的歌曲集留了下来。若这是个才情相当的男人,会消失得如此彻底吗?
比卡契尼小一辈的芭芭拉·斯特罗奇生于1619年,在威尼斯长大,当地的性产业和歌剧一样发达。芭芭拉是个交际花,老爸是皮条客。在作曲时,她常常挑选淫词配乐。安娜·比尔评价她为女高音写的歌曲“自信而精雅”。据说男人根本无法“越过她的丰胸”去欣赏她的音乐,不过生活在印刷业兴隆的时代,她于1651-1664年间出版了七卷作品集,比当地任何一位同时代人都要多。因为不太光彩的出身,她未能在宫廷里谋得一席之地,但她的音乐流传至今(YouTube上能听到),人声部分性感、强烈而坚定。
伊丽莎白·雅凯·德·拉·盖尔(1665-1729)是位多产的巴黎作曲家,专攻大键琴。维也纳神童玛丽亚娜·马丁内斯(1744-1812)是莫扎特的同时代人,当然天才无法与之匹敌。克拉拉·舒曼早年的创作火花被丈夫不羁的天才给熄灭了,何况还有八次怀孕之苦,以及身为钢琴家的演出事业。1856年舒曼去世后,克拉拉再没写过一个音符。舒曼著名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手稿上几处关键主题是克拉拉的笔迹。
在这连篇累牍的失落天才故事里,范妮·门德尔松最令人扼腕。她的才华被父母压制,因为他们更看好小儿子的天才。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被誉为“莫扎特再世”,但范妮并没有放弃。她继续作曲,并经历了成家、流产和忧郁症。弟弟也不帮忙,“我没法鼓励她出版作品,因为这与我的观念和信念背道而驰。她是个妇人,守本分就好”。当范妮发表了第一套艺术歌曲,费利克斯整个儿唱了一遍,据他的妻子说:“每唱完一首就发誓他要扳回来。”他知道自己的对手多厉害。
1845年,费利克斯写了一首钢琴三重奏,范妮次年也写了一首。他们一起演出,争先恐后。1847年4月范妮抱怨遇上了作曲瓶颈:“一点儿音乐灵感都没有。”5月,年仅四十一岁的她在排练时倒地,死于中风。费利克斯听到这悲惨的消息,摔倒在地,导致脑溢血。很快他也撒手人寰,死前悔恨交加。直到今日,范妮的音乐仍不为人知。
比尔女士笔下的现代作曲家典型是可敬的伊丽莎白·麦康基,她在1930年代的伦敦面对男性抵制,与伊莫金·霍尔斯特、格蕾丝·威廉斯和伊丽莎白·勒琴斯一同创建了半女性主义的音乐会协会。本杰明·布里顿帮她抄过乐谱。在得了肺结核后,麦康基与丈夫去乡间休养,写了十三首极为个性化的弦乐四重奏,比她的世纪中任何一位不列颠作曲家写出的室内乐作品都要连贯。她的女儿妮寇拉·莱法钮是“曲二代”。
勒琴斯是第一位用勋伯格的序列主义作曲的英国女性,她曾用过目难忘的比较高度概括了女作曲家的挣扎。“如果布里顿写了部糟糕的作品,”她说,“他们会说,‘他大概那天心情不好。’如果我写了部差作品,他们会说因为我是女人。”性别不平等今日依然存在。
2012年科芬园上演了朱迪斯·韦尔(Judith Weir)的差劲歌剧《好运姐》(Miss Fortune),评论界立刻转向性别贬低。一个右翼评论人写道:“我们陷入了一种困境,女人成为作曲家的障碍已经被移除,但她们依然享受着当女人的好处。”

歌剧《好运姐》(Miss Fortune)。
比尔笔下的女作曲家生平剪影生动机智,但有时不免小心翼翼。作为一位文化通史家,她不愿提供太多批判分析,遵从学院派音乐学者的正统观点以弱化自己的激情所在。她本可以拓宽视野,收入奥古斯塔·奥尔梅斯(被迫用男性假名出版作品)、战前捷克作曲家维洁斯拉娃·卡普拉洛娃,还有崛起的美国女性安娜·克莱因、珍妮弗·希格登、米西·玛佐丽等等,她们都还没有被大都会歌剧院相中过。不过这遗漏只会凸显比尔女士研究的及时性——古典音乐这个封闭世界中亟需女性的声音。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