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元节做离魂梦:上辈子的妻子这辈子的妈

台湾作家王溢嘉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魂魄》(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1月版。后有修订本更名为《中国文化中的魂魄密码》,新星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一书中,再命名、重述并分析了明清笔记中的八十八个鬼故事。其中第五个故事“梦魂受享”(广西师大版第8-9页,新星版10页)颇值得更作深究,其开头称:“江西布政使黄岩林,在某年中元节的午后,因疲倦而入睡,梦见一位老妇人摆着香案酒食,正对着他祭拜……”并记出处为“明·王琦《寓圃杂记》”。
查《寓圃杂记》并非稀见书,节本有《丛书集成初编》影《纪录汇编》二卷等,全本有《玄览堂丛书》影明钞本十卷,中华书局点校本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皆以此为底本。作者当作王锜(1433-1499),江苏吴县人,不曾仕宦,未见他处有写作“王琦”者。核对原文,发现在不同版本中,这个故事的文句与情节都有所出入。《纪录汇编》本收在卷上,无题名:
黄岩林公一鹗为江西布政时,尝中元日昼寝,梦一妇人祭之,觉而所享之物若在齿颊,家坊户舍宛然不忘。
公怪之,命一健卒,指其所向,物色之。果于其坊见一老妇,年七十余,祭其故夫,所焚纸灰尚未寒。问其祭物与夫死之年、月、日、时,以复于公。其物乃公梦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日、月、时与公之生无不同者。
亦甚异也。
这是王溢嘉译述之母本无疑,尤其是他将开头籍贯与姓氏连称的三个字当作了主角的姓名,可以为证。而《玄览堂丛书》十卷本卷七中那个名为“林鹗昼梦”的故事,开头的文字与结尾的情节都有所不同:
林一鹗为江西方伯,尝中元日昼寝,梦享一妇人之祭,既醒,所享之物若在齿颊,屋宇街坊宛然在目。
因命一健卒,指其所向,往物色之。果于坊中得一老妇,年七十余,祭其故夫,所焚纸钱灰尚未冷。问其祭物与其夫死之年、月、日、时。复于林,与梦合,而其死乃林之生日也。
林大惊异,知为此妇之夫后身也。亦稍以物给养之焉。
林一鹗的故事在清代不止一次被重述与征引过。浙人查继佐《明书》之“外志·梦兆”中字句有差异,开头称“黄岩林一鹗以进士藩江西,中元日午,梦身至某坊,一老妇祭之”,结尾谓“林怆然悟前身为老妇之夫,厚廪妇,终其年”(齐鲁书社2000年5月排印本,1204页)。又,张尚瑗《石里杂识》在“前生”一篇后半部分称名征引王锜《寓圃杂记》。张尚瑗,江苏吴江人,1688年进士,1701年左右在世,官至江西兴国县令,主纂有康熙《赣州府志》和《潋水志林》。吴江与吴县相毗邻,今皆属苏州。该书所引文字与《纪录汇编》本几无差别,唯文前称是景泰中事(1450-1457)。
江西布政史林一鹗实有其人,《明史》卷一五七有传。一鹗乃他的字,名鹗(?-1476),景泰二年(1451)进士,天顺(1457-1464)初年为镇江知府,居五年,调苏州。成化(1464-1487)初年迁江西按察使。据《明代职官年表》(张德信著,黄山书社2009年12月版,3273-3276页),成化三年十二月,自江西按察使迁布政右使,五年迁布政左使。六年三月迁南京刑部右侍郎,十二年卒于任。林的任职经历,作为苏州人的王锜、张尚瑗可能会有所听闻,尤其张尚瑗的人生轨迹与林还有江西的重合点,又熟知赣省史地。但是,张让林比史实提早十年去了江西。
以上提到林一鹗故事的五个版本,就结尾可略分出两个系统:十卷本《寓圃杂记》和《明书》两种,在文末多出一段,录有林一鹗何以面对与处置前世的妻子即如今的老妪。十卷本《寓圃杂记》谓“林大惊异”,《明书》重述时作“怆然悟”。“惊异”乃第一反应,“怆然”式的感伤,或许是林一鹗后续的心绪写照;可能也有重述者在了然情节始末,感怀轮回贵贱种种世界规则时的心绪,存有不觉以身代入的意味。相认前生亲属的各种叙事,大都会提及“恤其妻、子”,譬如《聊斋志异》卷八“邵士梅”一篇。十卷本《寓圃杂记》和《明书·外志》多出的结尾,也是林资助了很可能已成孤老的老妪。不过,各个故事力度不一,十卷本《寓圃杂记》“亦稍以物给养之”,“亦”且“稍”,稍稍见出林在情感上不能接受,而道义上又无法逃逋的矛盾,以及由是产生的躲闪。但到了清人所撰史书的重述中,责任感被夸大,人物形象变高大,赡养终生。养老送终,这举动是不是更像对待一位母亲而不是妻子,年纪上的差异也正相吻合——上辈子的妻子这辈子的妈,正可以与疑似台湾一位励志作家首倡的流行语“这辈子的女儿上辈子的情人”相映成趣。
清代还有一个记认前(生之)妻的故事,其中人物更高大,即资助力度更大,见袁枚《子不语》卷十三“曹能始记前生”。王溢嘉也重述了这个故事,略谓:明代末年,曹能始(即曹学佺,福建侯官人,1574-1646)在游玩仙霞岭过程中觉得景物熟悉,晚上闻旅馆隔壁妇人夜哭,去打听,发觉自己是其三十年前故去的亡夫。仙霞岭在闽、浙、赣的交界处。与林一鹗的故事相比,没有午睡,不在宦途。“曹以家财分半与之,俾终余年”,把家财对半平分给前(生之)妻,这让人想起如今男女平等观念下的离婚原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平权是现代意识,并且平分的是婚后共同财产;在曹的故事中,家财是今世的,妻子是前生的。除了特别充沛的慈悲心或者前生特浓的感情记忆之外,这更像是在震惊之下的非理性冲动。还有一种可能,不同寻常的巨额赠金或赡养,乃是以经济方式了结前世情缘的象征行为,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前世今生不全然只是生命或灵魂的继承关系,还伴随着一种本体或喻体意义上不曾了账的债务纠葛。
袁枚在曹的故事结尾处引述《文苑英华》录唐代白敏中所记滑州太守崔彦武的事迹,称其相似:崔突然记得自己前世是一个叫杜明福的人之妻,遂骑马直抵杜家,诉说前事。杜已老,而崔是男身,不排除有隐秘的同性情谊,但未曾声张;崔只是将前生私自藏在墙里的金钗找出来,并把屋子施舍为佛庙,起名叫“明福寺”云云——就算不提性别问题,崔并非从梦中得到前生的线索和奇怪的味觉;他找金钗、捐庙没有动用今生的财产;因此,跟曹能始,包括跟《明书》所记林一鹗所为,并不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捐庙也有了却尘缘——积满岁月尘埃的前世姻缘——之意。
王溢嘉在书中提到,梦魂受享故事单在明代笔记小说中,至少《涉异志》、陆粲所撰《庚己编》两种有大同小异者。近年颇值得关注的另一部谈鬼的著作,栾保群著《扪虱谈鬼录》一书也谈及这个故事类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80页),同样提到了这三种文献。我们先来看《涉异志》:
天台卢希哲浚举进士,弘治间知黄州府。一日,坐堂上隐几假寐,梦老妪延至市中桥旁民家,饷以馄饨,餍饱而归。及觉,口犹脂腻。
亟遣左右,告以其所,走访之。其家八十老妪方设祭将彻,问之,答曰:“吾夫死三十余年,平生嗜馄饨。今乃忌日,设馄饨祭之耳。”左右还报。
希哲惊讶,时年三十余,意其为后身也?召老妪入,婉然梦中所见者,给以白金一斤。自为文白其事。([明]闵文振《涉异志》“卢太守”篇,《丛书集成初编》影《纪录汇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27页)
卢自己明确成了奇遇的首次叙述者,这“自传”惜乎不传。与林一鹗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也发生在宦所。可明确说有馄饨的滋味,并前生嗜馄饨,是林所不备的细节。另一个区别是:故事中林的年龄俟考,前(生之)妻看上去七十多岁;卢在故事中三十多岁,前(生之)妻却已经八十多岁。前(生之)妻与卢之间更像是祖孙辈差两代人,而不是母子。
卢希哲也实有其人。名浚(1464-1509),据《天台文史资料》第五辑“天台历史名人专辑”(许尚枢《卢浚》,1989年1月版,115-116页),二十二岁中进士。素有清官之誉。历知湖广黄州、江西南安、福建邵武。
林和卢这两个故事的时空坐标也是相重的,前者是十五世纪时候江南苏州一带所述一个转到江西去做官的浙江人的奇遇记。卢希哲大致也是十五世纪一个到江西做官的浙江人,而稍复杂的是:《涉异志》的作者闵文振是明嘉靖间(1522-1566)江西浮梁人;卢的故事发生在黄州即调任江西之前。但黄州东南与九江隔江相望,明初迁入黄州府的江西移民氏族约占当时当地氏族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大事年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348页)。可以判定,其后一两个世纪中,黄州与江西的文化关系必然还十分密切。
不过,梦魂受享故事并不只是流传于江南、江西局部。前述曹能始故事犹有福建籍的背景,写自传的卢最终也在福建做官。《扪虱谈鬼录》还征引了一则宋代笔记,认为这是该类型最原始的一个记录,讲的就是一个福建人的故事:
殿中丞丘舜元,闽人也。舟溯汴,遇生日,舣津亭。家人酌酒为寿,忽昏睡,梦登岸,过林薄至一村舍,主人具食。
既觉,行岸上,皆如梦中所见。至村舍,有老翁方撤席,如宾退者。问之,曰:“吾先以是日亡一子,祭之耳。”
舜元默然,知前身为老翁子也,厚遗之以去。([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无题,中华书局1983年8月点校本,235页)
栾保群的注引颇有数句遗漏,“闽人也”、“舣津亭”、“如宾退者”、“厚遗之以去”等皆无,不知所据何版。如前所谓,这些信息不可谓不重要。以上是时间维度的传播痕迹早于明代十五世纪的例证。而在空间维度上,之前我在点校越南和韩国汉文小说时亦有所发现:
有一宰,自儿时每年常梦到一村家受祭,有妇人设馔哀痛。及少年登第,官至宰列,其妇人随岁渐衰,已成老婆。心常疑怪。年至三十,为平安监司,到营后,又当受祭之夜,出营后门,行不百步,到其家受祭。惊觉,听之,其妇人哭声尚不止,急问在傍贡生曰:“此何哭声?”对曰:“此是老妓祭其幼子哭声也。”
宰与贡生寻到其家,茅屋精洒,花木分列,历历皆梦中所见。而陈设祭物,妓方哀痛,其衰颜白发,宛然梦中所见之婆也。宰问曰:“汝之所祭者谁也?”妓知其为监司,慌忙收泪而对曰:“是亡儿之祭也。”宰曰:“汝子几岁而亡?”妓对曰:“渠本生而颖敏,年才十五,备巡营通引,见巡使道到任威仪,归语妾曰:‘儿亦长成,亦可为平安监司乎?’妾曰:‘儿妄矣!汝本贱生,功名极不过吏户旁营吏,安敢望监司乎?’儿闻此言,奋然曰:‘男儿生世间,不作平安监司,生亦何为?’因厌厌沉病,虽开谕万端,终不改,竟至数月而亡。自此,妾至痛在心,每值亡日,辄哀痛矣。”宰问曰:“儿之亡,今几岁?”妓曰:“三十年矣。”
宰默计儿亡之岁,即己生之年也。自知为妓之亡儿后身,潸然出涕,谓妓曰:“尔今衰老无依,若随我同处一室,则凡衣食送终之节,吾当尽诚奉之矣。”妓大喜愿从,宰遂与同还。虽以此事不泄于人,世多有知之者。宰事妓如亲母,效诚不替云。由此论之,佛家所谓轮回与还生之说,信不诬矣。([韩]徐有英[1801-1873]《锦溪笔谈》,卷上末则,无题,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
与朝鲜一样,越南同受汉文化影响极深,亦曾见有转世相认故事,情节又有所不同,表述为名臣轶闻,见诸《大南奇传》《本国异闻录》《喝东书异》等越南笔记(参见《越南汉文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月版),略谓:状元冯克宽(1528-1613)每次从家出发上京城的时候,在云耕桥小憩,总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对着他哭。有一天冯终于按捺不住,上前询问,老人说哭儿子,四十年前,他十三岁(有版本作三十)的亡儿没来得及参加科举考试即夭折了,冯与其形貌手足,乃至面庞的瘢痕都一模一样。冯看其所存留下来的笔墨遗书,惊奇地发现与自己的手迹一模一样,语气习惯也一致,于是奉老人为义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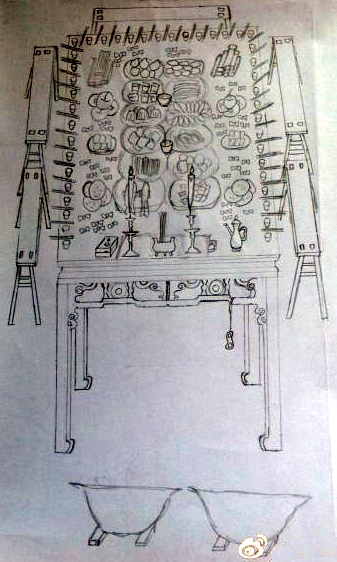
家祭
越南家谱及家族传说中,多有声称祖上来自闽越者,连其近一千年自立以来几个王朝的统治者犹如是说。这两个域外文本因此可能是东南沿海直接传播过去的,其中记录前世今生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夫妻,而是亲子关系,联系丘舜元故事,或许这正是故事的原始形态。
越南故事出现了认父情节,可视为一种推进,在夫妻亚型中的赡养终老,因此可判定是认亲的转化。与朝鲜版本一样,越南版本同以后世成功赓续了前生未竟之仕途梦想,得到验证的是生命意志跨越死亡之顽强。照理说,认母也一样,但对比冯克宽、丘舜元故事,朝鲜某宰的版本从表述到情节设定上,约略有三处优胜的特色。首先,梦魂受享的情节以死生时间上的严丝合缝来确认两世关系,乃冯克宽版所不备。
其次,某宰所遇是前生老母而不是丘、冯所遇老父。比起父子,母亲对亡子的哀伤,及对祭礼的讲究,又及她自身的寿命,都会更加长久一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锦溪笔谈》使用了“老婆”一辞来指称老母。老父、老母皆有两层含义,一层专指与人有亲子血缘关系的老人,一层泛指无血缘关系的老年男女。而在中古以来的白话中,老婆也有两个义项,除了妻子的通称,还有一种语义“老太婆”,即老年妇女,包括朝鲜与越南在内的近古汉文叙事文献中也常这么用。《锦溪笔谈》里,“老婆”在两种词义的背景关照中,特有意外之妙,使其有了宝贵的复杂性,或者说暧昧。本来,功名执念、贱民痛苦、中年丧子的认前世情节,与夙世姻缘所感相比,看似经验丰富,实则结构拖沓。夫妇间因祭祀而隔世相会,比之父子版本,后出转精,更有冲击力。与前(生之)妻——即可简称前妻、老婆矣——相会的那个版本系统中,确认的不止是前世身份,而且还唤醒了已经被生死隔绝的记忆以及记忆中的深情;此中更有力推动的,可能是情欲而不是孺慕,即:被记忆、身份、轮回奥妙带来的震惊等等所伪装与包裹起来的,乃是一种中青年男子深藏着的对年长妇女的奇特爱慕。意大利著名学者兼小说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曾用戏仿的方式对应纳博科夫的名作《洛丽塔》所述中年男性对少女的欲望,命名了更夸张的这一种中青年对老年妇女之爱,为“奶莉她”(Nonita,出其《小纪事》一书)情结。朝鲜版本疑似有他,所以不曾动用人脸识别和笔迹鉴定这两种越南故事所见的刑侦式手段,某宰仅凭梦兆就把一位老妓奉为母亲,若不以小说家荒忽轻率论之,其中包括妓的身份,包括“同处一室”的承诺、“不泄于人”的做派,皆可以包含有性伴侣的暗示。因此,“老婆”一辞在这一隐藏的语义层面上,算是导夫先路的铺垫了。这个故事也可以看作是梦魂受享故事从殇子亚型向夫妻亚型过渡的痕迹。
还有一点,朝鲜版本意味深长的是,比起四十岁的越南冯克宽,这个朝鲜某宰与卢希哲、曹能始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是三十岁。三十年,在古代被称为一世,《论语·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安国的批注也提及:“三十年曰世。”我们不妨大胆假想:林一鹗也应该是在三十岁的时候认出了前妻,只是不曾被故事明确记录——那他约生于1434年或稍早几年,弱冠前后即中了进士。甚至越南冯克宽也如此,只是叙述者往往不详知,转将三十岁安在前生的享年上了,后又虑及其父因此过于老迈——前生三十岁时死,前父当时应该近五十;而转生后冯克宽又已届不惑的话,这意味着老翁有九十来岁——所以改成了十三。
三十岁时恍若隔世般,领会转世奥妙,这也没有出现在苏州人陆粲的《庚己编》版本中:
嘉定僧如公者,尝昼假寐,梦至苏城枫桥北里许,度板桥,入一家,瓦屋三间,饮馔满案。己据中坐,有妇人前立,年可四十许,展拜垂泣,少者数人,侍立于后。有顷进馄饨,妇人取案上纸钱焚之地。及醒,乃觉饱,且喉中有馄饨气,怪之。
后以事至枫桥,顺途访之,到一处宛如梦中所见,入门,几案陈设皆梦中物也。有少年出迎之,扣其家事,云父死矣。其死忌之日,正僧得梦日也。乃知是时,其家设祭耳。([明]陆粲《庚己编》,卷二“如公”,“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六编,台湾新兴书局1977年3月影印本,2584页)
《庚己编》共四卷,《扪虱谈鬼录》称是文在卷四,不知何据,或是总卷数的倒错。其书卷二之后有“怪石”一篇,知作者陆粲在枫桥有别业,所以此一则算是乡里杂谈。与先前林一鹗、卢希哲的故事参合起来看,可以支持一个推论:这个梦魂受享的故事,乃是到十五世纪在浙、苏、赣几地成型,被反复申说的。但如公故事实有一大半偏出了林、卢的典型版本:不止有三十岁的问题;如公和尚已经不再是转世而来,而只是偶尔梦游而已;所逢是丧葬所祀,而不是忌日例祭;对妇人而言,如公的意义有若“尸”的指代,而不是作为“屍”的亡夫;而那位四十来岁的设祭妇人,对如公而言,也只是红尘中一位无名过客,一个可以验证神道设祭之不诬也的符号罢了。
偶尔感梦,遗失了梦魂受享故事在前生后世的背面隐藏着的必然或宿命:只要林一鹗抵达江西、卢希哲莅临黄州、某宰官任平安,甚而冯克宽路过云耕、曹能始游至仙霞;梦游与恍惚、依稀,以及相认种种,皆注定了要接踵而至。前妻(母、父)在那里一年年地,用祭奠的方式等着他、催着他呢。但如公与枫桥却与这一家毫无关系,信息不足,纯属乱入。而在此需要补充说明,朝鲜版并越南版有一处与明代几个版本不同,但毫不逊色:明代各故事中受享之梦都是一次性的,到了前生原籍,才会被某种引力所左右,而做一次这样的梦,继而利用权力去调查验证。但某宰和冯克宽都是一再进入引发指认前生的情境或梦境,把一年一年过成一节一节的,像诗歌中的韵脚,反复敲打着主人公,也提醒着读者,步步相逼着接近前世的死亡及祭奠现场。在此基础上,差贡生陪访,欲迎还拒,乃解惑或证否;稍给以物给养之,以进为退,相认或了账;皆自有其平衡的美感。

元代盂兰盆道场
一个令人惊艳的故事,可能会因为一批讲述者不曾抓住奥义而黯然无光;但也可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改动中暴露出更多信息。为什么陆粲所闻说的版本中出现了和尚?前文提到白敏中所记的崔彦武故事中,也舍家为寺,将很可能已成孤老的前世“老公”的名字冠诸僧庙。和尚意味着持戒出家,因此,与性欲相隔绝的本义,或者直接说是性的无能,正是故事要影射的:鸳盟不可再续,性关系不可恢复。真实原因或是女方年纪太大,或因性别改换。隔世再作夫妻的叙事,所以见有在性别关系上倒过来的,譬如《池北偶谈》卷二四“邵进士三世姻”,老夫始终犹在,老妻再三转世成少妻,实是喜新厌旧的隐喻,另当别论。因此,当男性了然夙世姻缘,而前世的妻子已然年高,性方面的退避与决绝才是常态;朝鲜版本定位为母子是一条原始而有效的出路,遁入空门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不管是唐代那个男主人公把前夫杜明福送进明福寺的,还是这位“如公”和尚在一个短梦中将自己临时变得像个有食色性也之欲望的凡俗男子,都规避了进一步相认之后相处过程中的奇特尴尬。
还有一个梦魂受享故事明确与佛教有关:《子不语》卷二二首篇“王昊庐宗伯是莲花长老”,略谓,王昊庐自黄州黄冈途经庐山去京师赶考,宿莲花宫,梦见自己坐大殿上受和尚环拜,随手取供品枣子吃了几枚。醒来得知,这一日是寺中长老净月上人的忌辰,仪式现场的一盏斋果正好像缺了顶上两三枚的样子;故事最后提到,王昊庐的名字是纪念他父亲明末殉节庐山之故。王昊庐故事将黄州与江西勾连起来,而不待宦游经历、移民文化与地理毗邻的证据,像是为卢希哲故事补充了注解似的。这也是一个是父子亚型的故事。父子关系乃是故事中反复强调的因素,是以最后的闲笔写到此生的父亲与儿子、庐山之关联。但佛教背景,把父子关系转化成了同构的师徒,把如公和尚梦见享用俗家祭品,倒转为举子王昊庐梦见享用了斋供。
王昊庐故事中以枣子取代馄饨,可以避免如公和尚当时喉中的馄饨气到底是菜馄饨、甜馄饨、空心馄饨还是肉馄饨的戒律困境。但这可能还不是重点,馄饨亦是卢希哲故事中的重要道具。江西浮梁人闵文振记录下黄州地方的老妪,以亡夫“平生嗜馄饨。今乃忌日,设馄饨祭之耳”,回复官府来人的盘问。但考察馄饨在历史上其实与枣子同类:南宋时,馄饨即已经成为杭州一带冬至享先时的主要祭品,见周密《武林旧事》卷三。明代万历年间编修的浙地方志如《绍兴府志》《会稽县志》并有相似记载。这一习俗晚至明代,已随中元节风俗并有设祭一项而转移到夏季,谢肇淛《五杂组》卷二记福建有中元夜以馄饨施食的风俗;而苏州、嘉兴、松江等江南诸府,至今如常熟、张家港河阳地区以及上海七宝等地犹有用馄饨设供斋田的习惯。因此馄饨的性质是一种泛用的祭品,不惟亡者生前特别的嗜好。
卢希哲故事中以嗜好来解释,因馄饨的习俗背景而显得像个主位的托辞。或许因为馄饨设祭的传统并未播及赣地,或许只是个人食癖与广泛食俗之间的巧合。巧合固然是该类型故事最大的逻辑,前生死于中元节,任官恰到上辈子所在,微小概率成为故事的最大动力。但不如进一步理解:梦魂受享故事在情节设计上深藏了一与多、个体独有与社会共约之间的意义对立关系,癖好与习俗间被遮蔽的矛盾只是其中之一。故事的发生时间往往设在中元日,习俗上有家家户户祭祖先并祭无祀者的活动,这是一个作为节日而通用有序、不具个性的时间点;但对前妻老妪来说,中元节又有一层特殊意味,由于丈夫即主人公的前世在鬼节登鬼籍,节日逢忌日即纪念日,双关意义使她不在正常的节日秩序中。而在某种程度上,来做官的异乡人可能也会被排除在这一礼俗之外,他此生的血脉祖先不在这里,远在浙江或是福建,梦的强大力量,引导他,使之在千家万户中,认出了另一个不在秩序中的孤独个体。
事实上,这种对立可能是江浙闽一带中元节习俗里潜在固有的:家祭与野祭,可谓有各自专祀与无特定指涉的通祭之间的差异。后者受佛教盂兰盆会文化影响而成为风尚,固在解释性传说中也起自目犍连祭母救母的个体事件;但如论者所言,那可以看作是佛教伦理与中国固有本土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孝道之间矛盾的调和。而梦魂受享故事成立的核心理念,恰恰就是:佛教与本土传统之间,就生死问题的另一个深刻矛盾,它们在民间也一直并不完全能自圆其说,却长期同存并轨。即:中国固有文化观念里,死者长已已,长眠九泉之下,故有定时设祭;而佛教带来印度的转世理论,亡魂会投胎。栾保群在《扪虱谈鬼录》中,以这个故事作为祭祀、轮回不可通约关系的例外,并认为乃是叙事者企图“以家祭证明轮回的确凿”,同时也意外地“用轮回来证明了家祭的无益”。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两种生死观之间的相互拆台,不若讲:两种矛盾的灵魂理念,在这个故事中,藉由重重对立关系的掩护,而奇异地依存在一起了,相互配合,演绎传奇。
(本文载2016年8月1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标题为《中元节午睡做离魂梦?——“梦魂受享”类型故事札记》。)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