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陈丹燕谈塞尔维亚:面对动荡与未知,他们的态度是坚强和享乐
2016年11月15日,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宣布任命作家陈丹燕为塞尔维亚旅游形象大使,陈丹燕在今年出版的新作《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也将被翻译成塞尔维亚文在塞尔维亚出版。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陈丹燕曾与来自塞尔维亚的诗人德拉根·德拉格耶洛维奇、小说家邱华栋就她笔下的“捕梦之乡”塞尔维亚展开了一段对话,他们谈论了这块土地上错综复杂的历史,和它所孕育的文学。塞尔维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陈丹燕曾4次前往塞尔维亚,她说,那里的咖啡20年一个价,人们唱着披头士开反战音乐会,跳着舞喝着酒来应对未知的明天——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坚强的,也是享乐的。
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这段关于塞尔维亚的对话。

陈丹燕:我从小是一个很喜欢看欧洲小说的人,我相信很多上海长大的小孩都是这样子的。小时候小孩子看欧洲小说都觉得这是神话一样,不晓得这个地方。到后来真的长大成为作家,我的书开始在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这些地方出版,就有了版税,我开始用这些版税去玩儿。对我来讲这其实是一个梦想的实现,我看小说的时候,不知道我会去小说故事发生的地方。这对我来讲,好像是重新回到少年时代,去到看的那些欧洲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次我对欧洲大陆上的某一个地方有非常深的感受的时候,就是普希金的《皇村回忆》。去了皇村那天正好在下雪,就能够突然想起来少年时代看的普希金的诗歌,他好多诗歌都写在皇村中学,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让我非常身心愉快的体验。也不一定是纯阅读的,也不一定是纯旅行的,它是混合在一起的。

20世纪过去以后,欧洲的小说有一个共识,就是20世纪的欧洲小说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尤利西斯》,爱尔兰的作家写的。一个是《哈扎尔辞典》,塞尔维亚的作家写的。这两个高峰,一个所谓的小说创作的高峰就是,《尤利西斯》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思维,对思维的描写变成了艺术方式来描写塑造人物,来管理时间。另外一个是《哈扎尔辞典》,打破了欧洲小说线性结构,是迷宫结构。不同的故事都可以进入到小说的主结构里面去。在上海,我觉得这两个小说我看得不是很懂,看完了也看不懂。看一些文学教授的分析,觉得不一定他们是看懂了才分析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有机会,我要到那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去看小说。这其实就是小说爱好者的一个爱好,并不是说我一定知道我要写一本书,然后我去。所以《捕梦之乡》是《哈扎尔辞典》的地理笔记,《驰想日》是《尤利西斯》的地理笔记。
很多人有很多种旅行方式,我自己的旅行更多的是跟阅读放在一起的,因为读书可以让我对一个陌生的地方有亲近感,让我可以比较多一点去了解不了解的地方,包括食物,这些在小说里面都会有详尽的描写,我觉得我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德拉根·德拉格耶洛维奇,他的姓太长所以我叫他德拉根·D,他的故乡发生了这些故事。我请德拉根·德拉格耶洛维奇来,他不光是一个小说家,他也是安德里奇基金会的主席,安德里奇是塞尔维亚第一个获得文学奖的作家。他写的三部曲帮助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不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觉得他很好。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安德里奇在上中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文学社,这个文学社的另一个成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枪打死储君的少年,他打死储君的时候才17岁。安德里奇和这个少年是在同一个文学社,他们当时在储君遇刺之后被抓了,但是安德里奇被放出来了。我要讲这两个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建立了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感情基础和文化基础。他们曾经被整个世界认同,但是也曾经被整个世界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神奇。接下来,安德里奇之后,就是帕维奇和他的《哈扎尔辞典》。我认为帕维奇是个非常神奇的人,为什么这本书要叫《捕梦之乡》,因为在《哈扎尔辞典》里面,帕维奇制造的一个梦境的世界,人可以进出,一个古老的宗教是抓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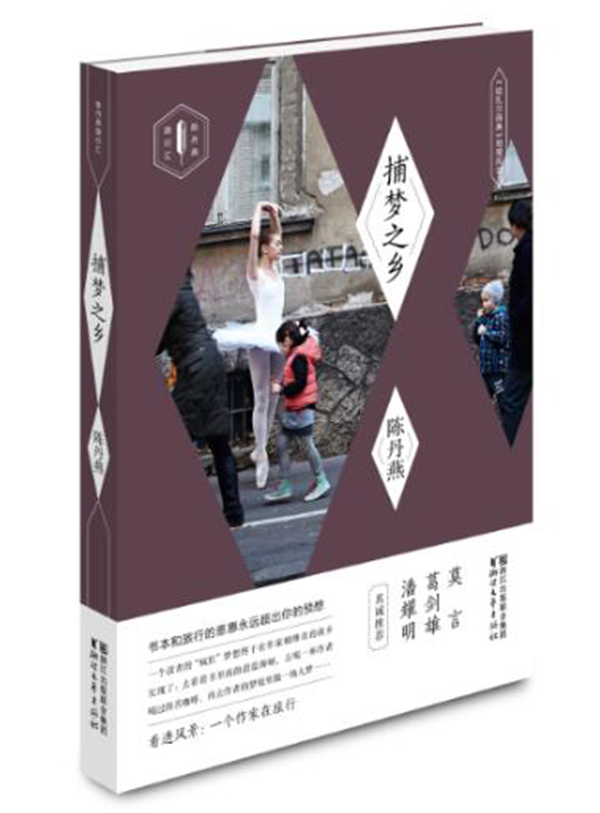
等我去到南斯拉夫的时候,南斯拉夫已经不存在,变成塞尔维亚。帕维奇已经过世了,我去他的家。他的夫人告诉我帕维奇的24小时是两天,中午12点他要睡一觉,中午睡的时候他的梦特别多。在《哈扎尔辞典》里面所有梦的描写,大多数是来自于帕维奇中午睡觉时候做的梦。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说,亲爱的帕夫人,我非常喜欢《哈扎尔辞典》,我能不能在帕维奇先生中午睡觉的床上睡一觉。我想她肯定会扇过来,后来等到她的邮件,她说“you are welcome”,我真的很高兴,我说你应该告诉我你们是一张双人床,帕先生是睡哪一边,她说我会告诉你。我问帕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睡觉,她说中午12点到1点左右开始睡觉,睡一个小时到2点。她说我们的卧室现在是你的,你去好了。
去到她家以后我觉得,如果她这么好说话我应该再要多一点,因为我是一万公里飞去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听到塞尔维亚语,但是我不会说塞尔维亚语。所以我每次在塞尔维亚,我都是跟他们说的英文。但是我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有人用母语来朗读帕维奇写的小说。我说能不能麻烦你在我睡觉的时候帮我读一章。我知道这是非分之想,但是她看看我然后说OK,你要我读哪一章。我说我要你读捕梦的那一章,因为那一章其实讲他梦的世界的规则。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个摄影师的团队一起去工作了,但是我们没有钱带那么多仪器去。所以我们没有带轨道去。帕夫人在那边读书,我在这边的床上睡觉。我们还请了一个年轻的芭蕾舞演员,我说这是一个幻想的故事,所以我希望有一个芭蕾舞演员在我快睡着的时候,让我看见她在窗前跳舞。我们就真的找到了芭蕾舞演员,芭蕾舞演员就站在窗旁边。我就开始睡觉,帕夫人就开始读书了。我们的想法是整个镜头是通过帕夫人,然后进到我睡觉的床上,看我睡着了没有,最后去到窗前拍芭蕾舞演员。我们因为没有轨道,但三个摄影师非常好,就三个摄影师站在三个不同的位置,摄像机是开着的,通过人工的轨道转过来,拍了一条。后来我看我自己的影像,我的手是耷拉下来,我相信我是睡着了。结果等到我起来,所有的人都在问我你梦见什么了没有。我就说什么都没梦到,因为还有时差,到下午一点多快两点的时候,是真睡着了。
这就是这个书的故事。不是那么好玩儿,我现在讲得比较好玩儿。但是如果你跟当地人接触,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心里面天长地久沉重的阴影。这个阴影是我们在中国看《哈扎尔辞典》的时候认为是他写作的手段、是写作技巧的那个迷宫。但是在外国人来看,就知道他是对整个巴尔干历史的回顾。他没有说清楚,他也不敢说清楚,所以他要用这个方法。我在那里其实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知道了所有的技巧和运用都是内容的一部分。现在只能讲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是通过了很多写作得来的。
邱华栋:陈丹燕老师的写作让我想起英国作家奈保尔,他的内容也是全球游动走来走去,把游记变成了一种非常具有深度的文学,你看我们读他的《印度三部曲》还有在非洲的游记,他哪儿都去。他的游记都很长,每一个国家都写一本书,他把国家背后的内容,历史风云的变幻都写出来了。陈丹燕老师左手写小说,右手写非常生动的游记,可以说在非虚构文体上她是有贡献的。这是我们搞文学的专业人士特别高兴和重视的,另外我觉得作为读者也能够开阔视野。
所以等于说,跟着一个国家的心灵,进入到另外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心灵隐蔽的地带,甚至上了“床”,这个就特别精彩,而且的确是有意思,真是很兴奋。同时我们还请了德拉根·德拉格耶洛维奇,他是南斯拉夫以及塞尔维亚安德里奇基金会的主席。安德里奇是在196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三部很有名的,关于一个桥的小说叫《德里纳河上的桥》,还有《特拉夫尼克纪事》、《萨拉热窝的女士》,都是长篇小说,而且都有中文译本,可见在文学上我们汉语中文和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他们之间的文学交流早就开始了。另外据我所知,出版陈丹燕老师作品系列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也将继续在德拉根·德拉格耶洛维奇先生的支持下推出安德里奇的短篇小说系列丛书。
德拉根·德拉格耶洛维奇: 首先非常感谢陈丹燕老师,感谢她的努力,为了找出这本书以及它的作者的故事,她不仅去拜访了帕维奇的家,而且去了帕维奇去过的地方,不仅去了塞尔维亚,甚至去到了塞尔维亚周边的地方。这是一种热情,如果你不喜欢做的话是不能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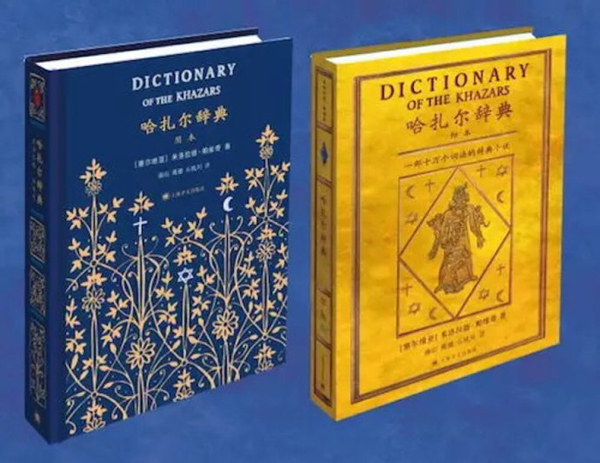
在我的感觉当中,《哈扎尔辞典》不仅仅是塞尔维亚的一本文学作品,在世界上也是一本数一数二的文学作品。我和帕维奇先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帕维奇是1921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生的,他的出生地就靠着多瑙河,土耳其人已经把贝尔格莱德叫做大门,基督徒把贝尔格莱德称为是尘埃,基督徒还把贝尔格莱德称为基督教不能踏进去的城墙。他们12岁的时候,贝尔格莱德遭到了爆炸,是二战期间希特勒的军队干的。十五年后,在他70岁的时候,贝尔格莱德又遭受了一次爆炸。他一生见证了贝尔格莱德的三次轰炸,整个城市全部被炸毁。 帕维奇是一个学识非常广泛的人,在我感觉中,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在经受了这样一个经历之后,都能写出像《哈扎尔辞典》这样的一本书。
陈丹燕:其实,我要看《哈扎尔辞典》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中,塞族人常常充当着先头军跟阿族打,在这次争执的过程中,社会的主流是帮助阿族人来反对塞族人的,所以帕维奇一直说他是这个世界上被所有的民族诅咒的民族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家,所以他认为,因为大家都觉得塞族人制造了很多现代的屠杀,所以他们就会说塞族人现在仍是一个血腥的种族。但是帕维奇要说,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我必须还是要证明,我们是没有罪的。这种情绪就很深地贯穿在《哈扎尔辞典》里。但是《哈扎尔辞典》给了你一个梦境的世界来表达这种感情,所以他就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写作技巧,他有能力在小说里面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就是那个梦境世界为什么要被创造出来。讲的是这个历史的原因。
德拉根·德拉格耶洛维奇: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帕维奇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教授。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诗歌的书。第二本书还是关于诗歌的,然后有很多很多关于短篇小说的书。他还写了有关塞尔维亚在巴尔干的历史书,是中世纪到17、18世纪。还有对塞尔维亚的经典文学作品有研究,也有本书。所以为了写诗歌,为了写历史,为了写文学这些书,他必定是要做很多功课,查很多资料。要了解这块地区,你会发现我们是一个多宗教多种族的地区,三种宗教可以共存,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天主教。几百年来这三种宗教在这个土地上永远是有冲突的,对于我们那边的人来说,如果改变了自己的宗教,就很自然地必须改变自己的国籍。那时候土耳其打过来的时候,把塞尔维亚整个都侵占了,大家都知道土耳其是伊斯兰教,而我们这边是天主教。许多塞族人就必须改变他们的宗教,变成他们的一部分。我觉得有可能在这种不断的身份转化当中产生的思想,让他写了这样的一本书。在《哈扎尔辞典》当中其实不是说塞族人是这本书,而是哈扎尔人在这本书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中世纪的时候,哈扎尔是作为一个民族逐渐逐渐消失的,是借助了这样一个故事来引入我们塞尔维亚人。基本上所有的历史学家,或者对这个历史感兴趣的都会寻找哈扎尔人去了哪里,当你去做研究搜寻资料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少有资料被保存下来。你怎么做研究呢?曾经在历史上就是记录过有这么强大的哈扎尔国家,但是现在他们去哪里了呢?发生了什么?帕维奇不想把这个历史再重述一遍,他还是想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这段历史。因为他学识渊博,所以他就会把各个方面的资料黏合在一起——宗教、神话各个方面,再用上自己梦境当中的想象。他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作家。当你第一次读这辞典的时候,你想这怎么是一本小说,读上去有点像科幻故事,甚至是关于写了什么都说不上。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个辞典,或者不如当作一个百科全书来看。但是当你真正看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像百科全书一样枯燥的书,它是有情节的,并且可以牢牢抓住你的记忆。而且他写得非常具有诗意,你一页页翻过去,就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变成了什么。而且他用了想象,用了虚构的想法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历史当中有很多断裂的事情,他只能找到线索,并且用自己的想象把这些线索一个个串起来。但是当时这本辞典出版以后,被多次翻译、广泛传播。所以这本书写于20世纪,所有的评论家就说这本书是21世纪写的,他们觉得他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在这本辞典之后,世界上很多作家都试图模仿这种形式,也写一个辞典式的小说,结果他们都失败了,没能做成,因为这个书真的是有独特的背景在。这本书读了之后,会让读者留下很多的想象,让你知道很多的事情、很多东西都是由读者后续去做的。不仅仅是陈丹燕老师一个人,很多读了这本辞典的读者,也都想要像他一样在书里面做这些事情,比如去把这些神话故事重新找回来看看。或者去找寻哈扎尔人到底到哪里去了,他们也想验证他们到底还在不在。去年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是讲阿富汗的战争,我在那个文章里面竟然也读到了哈扎尔的事。也有说哈扎尔人去了西班牙,也有说去了土耳其,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样。但是大家都希望去考证证据。
陈丹燕:我跟他讲过,我去塞尔维亚以前,我想要看懂塞尔维亚,所以我先去了土耳其。因为奥斯曼帝国曾经有600年历史,我去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因为奥地利和匈牙利帝国从背面过来也占领他们很多年。之后去塞尔维亚,但是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我在伊斯坦国找到哈扎尔人的一个墓地,通过这个墓地找到一个活着的哈扎尔人。这个人在我的书里边有写到,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找,结果最后找到这个人,这个人说他的奶奶是哈扎尔人,在现在的克里米亚。这个人的奶奶是哈扎尔人,就是从克里米亚来的,这个传说中的哈扎尔人是一个女士内衣店的店主,他曾经在帕维奇到伊斯坦国去查哈扎尔人资料的时候,提供资料给帕维奇,他说你们作家又来了。在这个书里,他站在一个女士老式的胸罩下面拍了一个照片。
德拉根·德拉格耶洛维奇:最后有的记载就是,俄罗斯的军队完全占领了哈扎尔的领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哈扎尔辞典》里面读到,当时哈扎尔的国王非常想跟三个宗教的宗教领袖都来对抗一次,来决定我们这个民族到底信哪个宗教,信哪个国家。他的一个游戏就是,有人能够破解这个梦境,他就会满意这个宗教。在《哈扎尔辞典》里面,也是没有人知道在这之前,哈扎尔到底是信的哪一个宗教。现在也有作家对新的哈扎尔人的生活开始感兴趣,为他们写书。我相信陈老师作了一个很好的功课,并写了这样一本书。
邱华栋:就我个人来讲,还有一些疑问。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很多年,我现在调到新闻文学院负责作家的培训。我们这两年注重非虚构文学的作家,我们发现有两大问题,一种有行动能力的人没有写作能力,有些记者是这样,我是记者出身的,一写东西就浮在一些事件的表面。再有一类小说家,蹲在屋子里有写作能力,但没有行动能力。真正把这两种能力集于一身的是陈丹燕,既有行动能力又有写作能力。但我内心非常担心您的安全,您去的地方都是战火纷飞的地方,您说些安全不安全的事好不好?
陈丹燕:我没有觉得不安全,大家对塞尔维亚一点都不了解。但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去的时候,也觉得塞尔维亚远得好像南美国家一样。其实飞机只要飞10个小时,跟上海是一个纬度,天气都差不多。我一开始说我去塞尔维亚,然后我妈说是不是那个地上有很多地雷的地方,其实不是的。我去塞尔维亚是因为那里有很多修道院,去修道院其实唯一的目的是因为《哈扎尔辞典》里面有一个描写,有一个魔鬼转世成为一个东正教的一个修士,他可以画非常漂亮的湿壁画,塞尔维亚的修道院墙上湿壁画是整个东正教最好的,我很想去看从塞尔维亚故事里面出来的湿壁画。东正教跟天主教唯一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是,他们教堂上面,东正教人的脸很瘦,巨大的黑眼睛。他用的画法是,你一进来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你,这个眼睛是精神世界的眼睛,所以当他一直看着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心是在被他问很多严肃的问题。天主教会画很多漂亮的小天使,非常胖,血色很好,有现实感。东正教是精神世界,而且我喜欢那个黑眼睛的耶稣,所以我很想看他。很重要的是,东正教的修道院是在科索沃,这是我想要去科索沃的重要原因,但是我每次去大家都跟我讲不可以去,找了很多办法就是不能去。所有的亚洲脸理论上是不能进科索沃的,我们一堆亚洲脸进去,在马路上一站,警察就会问你签证哪里来的。我们聪明的一个姑娘陈老师说,这个超出了我的理智控制范围,所以我不跟你去。另外一个小孩开无人飞机的,他说我去科索沃。他说我得去飞飞机,我说你可能真的不能在那里飞飞机。就算我们进去了,连一个旅游者的签证都没有,他说不要紧的,我拿锡纸把飞机包起来飞,我说这个跟锡纸没关系,是身份的关系。结果他打电话咨询他的朋友,他朋友说那个地方就是有地雷的,而且阿族人一高兴是往天上开枪的,很危险。然后他说我也不去了,我不想枪打在我脑袋上。然后有一个是做记者的,资深记者,说陈丹燕我跟你去。你去写书我去写报道,我很快就出名了。
贝尔格莱德的人们常说: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所以今天有太阳我马上就要晒太阳,然后我喝一个咖啡,这个咖啡0.8欧元,20年没变过价格。我觉得他们这个生活态度,他们是坚强,也是享乐主义,就是我明天会死,但是我今天会好好玩儿,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态度。还有1999年,他们天天晚上被炸,而且炸的时候他们先得到通知的,今天6点半要炸你们家电视台,这时候轰炸其实是侮辱你,他们知道你没有能力反抗。市民们就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广场上面开反战音乐会,天天唱歌跳舞喝酒,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就炸了。我问你们是不是唱歌唱祖国的歌曲,他说我们唱披头士,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就是坚强,同时是享乐的,这才是真正的对待生活的态度。我觉得我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玩儿,半夜听听他们唱歌都很好。半夜里面在街上走,很多人就说,嗨,要来跟我们喝酒吗。我们说,不认识你,不来喝酒。他说没关系,过来坐坐不是就认识了吗?他们不会让你觉得紧张,觉得有人要抢你,没有人要抢你,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喜欢这个。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