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麦克尼尔:全球史视野下四大宗教的传播
各种普世性宗教,在公元200年以后不久获得了各种各样新的形式,并且具有了对欧亚大陆网络体系更大的支配能力。当对来世幸福的渴求开始充满每个人内心之时,日常经验便具有了一种新的特征;而且这些新的信仰非常迅速地创造出新的仪式、新的艺术类型和新的知识群体,并将来自印度、伊朗、犹太和希腊化的各种传统都融为一体,转化成独特而持久的形式。当受苦受难者能够对未来美好生活有所预期之时,人们对各种灾难与不公正便具有了更大的承受能力。这些新宗教还将对穷人、病人、孤寡老人、孤儿以及其他受难者施以救助作为宗教职责之一。此外,加入一个不断成功发达的宗教之中,还往往会带来各种经济益处,正如商人们皈依伊斯兰教之后所立刻感受到的那样。
世俗统治者与宗教之间所建立起来的那种暧昧联盟,是这一新时代的一个具有首要意义的特征。各种宗教机构团体——如修道院、寺庙、教堂、清真寺和马德拉斯(madrassas,伊斯兰教宗教学校)等机构所享受的官方庇护,既令它们通过接受捐献等途径大大受益,同时,又以迫使统治者如同普通信众那样遵守同样的道德和宗教规定,从而对王国或帝国的专制权力加以一定限制。这种王冠与祭坛之间的联盟最早起源于伊朗,当时正值萨珊王朝的第一代君王在琐罗亚斯德教一个复兴和修正派别的支持下,于226年获得了王位。然而,当651年伊朗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琐罗亚斯德教便衰退消亡了,萨珊王朝的宗教政策对后世历史的影响远远没有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在312年皈依基督教信仰那般重要。君士坦丁大帝虽然内心偏爱基督教信仰,但是他并没有对传统异教信仰和其他宗教予以取缔和禁止。他的后继者于395年将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境内唯一的合法宗教。沿着商路,基督教一直向东传播到中国,并通过水路,传播到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但除了埃塞俄比亚以外,基督教在这些地区仍是一种影响微弱的外来宗教。

就在佛教在东亚各地赢得数以百万计信徒的时候,一种新近合并而成的宗教——印度教(Hinduism)却在印度本土取代了佛教的地位。笈多王朝(其统治时期大约为320—535年)不再像自己的前辈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其统治时期大约为公元前321—184年)那样宠信佛教,而是更加偏爱印度教。尽管在笈多王朝时期,富有的佛教寺庙仍在印度继续存在,但佛教的地位已经丧失。在中亚入侵者于490—549年间对佛教圣地和寺庙大肆劫掠之后,佛教出家修道团体就再也没有重组复兴过,这大概是因为这一时期,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印度教所主张的通过个体与湿婆(Siva)或毗湿奴(Vishnu)直接的交往便可获得拯救的道路,要比以往需通过富有的拥有特权的佛教僧侣团体的中介才能达到涅槃境界的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的缘故。

在中国,佛教也同样遭遇到严重挫折,当时极为憎恨佛教的儒家知识分子劝说唐朝皇帝,于845年关闭了上千所佛教寺庙,没收了佛教僧侣拥有的广大地产。此后,中国佛教只能以民间教派形式秘密地存在,偶尔通过公开反叛的方式爆发一下。而在印度,佛教以一种人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渐渐地消失了,在印度人看来,佛教只不过是试图摆脱现实生活的幻觉和苦难的种种途径中的一种而已,并且是以一种人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的束身自修的苦行方式。
但是印度教却不是一种传播性的信仰。各种印度教仪式中爽朗活泼的情感和那种认为处于歇斯底里狂欢状态中的崇拜者就是同某位神灵,或者是湿婆或者是毗湿奴达到浑然一体的观念,从未传播到印度次大陆和位于各地海岸印度人集中居住的飞地以外的地区。另一方面,印度教圣人所详加传授的那些神秘技巧也从一开始就渗透到基督教修道运动之中,并在1000年之后,对伊斯兰教产生了一定的改变作用;与此同时,佛教还把众多更为明显的印度影响因素带给了东亚地区的各种不同宗教。但印度教对无数地方教派合法性和各种各样地方崇拜形式所给予的认可,比如将各种地方性神祇均视为最高精神实在的不同化身的观念,则没有向外输出。印度教对千奇百怪的各种习俗和缺乏核心教义的宗教的容忍与宽容,主要并非基于它的神圣经典和教法。简而言之,印度教对极端多样性的认同和其拯救理论在逻辑上的不完备特征,是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非常适应的,而在其他地方社会则根本无法通行。

在罗马帝国边境以外的欧洲北部地区,基督教也有过类似的成功经历,当时的僧侣和其他教士们(但不是商人)把基督教的拯救福音传播给了凯尔特、日耳曼和斯拉夫等各个民族。这些宗教改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观念对统治权的肯定以及对地方统治者权力的扩展。通过引入文化,一位基督教教士可以使国家政权管理得以强化,并使这个国家更为统一。结果,到1000年时,传教士们把整个欧洲都带入基督教世界之中,只有波罗的海南岸地区的一小部分异教徒是例外。最后一个皈依的民族是立陶宛人,直到1387年,他们才皈依基督教。
传播如此广泛的各种救赎性宗教在众多方面都存在差异,但是也有某些共同之处。首先,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对以往人类古老的期望进行了根本性修定。过去的宗教一直允诺的神对尘世财富的保佑全都被取替,这些新的宗教将人类期待引向永恒的、先验的世界——如天堂、涅槃、与湿婆和黑天(Krishna)合为一体,以及伊甸园等方向上来。有关日常生活行为的各种道德规范要求并没有降低,反而因对末日审判或印度教、佛教那种痛苦难当、无尽无休的转世轮回所产生的恐惧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这类宗教转变使文明城市生活中的各种现实苦难较之以往更易被人们所承受。首先,那些专门化职业之间的相互依赖虽给城市带来了财富和权势,但它们也并非总是处于稳定状态,而常常在关键时刻出现缺失,并且还极易在厄运到来时出现令人痛苦的破裂。在未来生活中能够获得补偿的希望会令现实中的不公正和灾难易于被人们承受,因为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无论现实生活多么艰难,终究可以在死后持有一份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允诺。对这种现实中承受的苦难可以在未来生活中获得补偿的希望,乡村农民们也是持欢迎态度的。这类希望大概也使农民反叛暴动的频率得以降低。总而言之,在苦难之际所获得的希望是这些新的宗教信仰馈赠给每一个人类个体最丰厚的礼物。所以,这些新的宗教的传播扩展使文明开化社会中的分化状况更加易于维持、恢复和向新的程度扩展。这种相适性可使我们对某种拯救性宗教的皈依同200—1000年间文明国家、社会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地区的迅速繁殖传播,这一世界历史的突出特征之间的密切关系做出解释。
我们考察的所有宗教共有的第二个特点是,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可以单独被拯救或被惩罚。在与人为善的被拯救者和心怀愧疚的作恶者之间的精确计算决定着最后结局。然而,妇女同男人一样具有灵魂,并且还发挥了某些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她们将自己的信仰传播给孩子们,从而使对宗教的虔信得以传承下去,并且还将新的宗教信仰牢牢地植根于家庭日常生活习惯之中。妇女还可以从事慈善事业,有时还获得一些新的权利,诸如继承权等等。至少,各个新宗教的教规、教义较之以往更为明确清晰地改善了男女性别之间的关系,对寡妇和孤儿予以抚慰,有时还以施舍方式来对她们施行救助。

这些信仰所造成的政治赞助常常也潜伏着深刻的歧义。某位统治者是否是一名公正的君主、虔诚的信徒,是否奉行正确的教义教规?倘若他不是,公开反抗是否就成为一种宗教的责任?许多严格奉行教义的宗派常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而以神圣的名义对各种反叛给予支持的说法也四处传播,通常这种宣传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但在个别情况下也径直诉诸武力。因此,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中就曾大量爆发过这类对现存统治体制的宗派挑战,并且,虽然不是经常的,那些宗教异端派别往往要同统治阶层或其他竞争者就社会集团的划分展开长期论争。在中国也是如此,845年以后,佛教各个宗派同大多数反叛行为都有着一定关联。然而,印度的两大宗教信仰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比,好战性通常要弱一些,它们认为获得拯救是一个过程,承认不同的途径同样有效,并且它们也并不是真正地对统治者本身表示尊崇,因为在它们的幻想世界中,只把这些统治者视为某位圣人甚或就是正义的化身而已。
最后,各种新的宗教信仰对以往艺术和思想的传统进行了重新加工改造,并且无论在哪儿扎根,就把文化带到哪里,同时还使数百万民众一齐分享一个共同的意义世界。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最初主要是通过他们对于各种基于神圣经典的规则和仪式的熟悉和尊崇程度来加以界定的。确定无疑的是,由基督教权威神学家和主教会议所发布的理论,对《圣经》所记载的话语做了进一步补充,而由穆斯林的律法专家所做出的决定也对《古兰经》做了进一步详细阐述,与此同时,印度两大宗教的神圣经典则过于充分,种类极为繁杂。印度教将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与某些灵修、祈祷和赞美诗一道奉为神圣学说的宝藏,而佛教各个宗派则把数量浩瀚的宗教经典都汇集为一体,有时则选择特定的经典作为它们独特修行方式的指导理论。但是无论在何地,文献、获得拯救的希望、归属于某种特定文明之中的身份感,这些因素十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而创造出各种由宗教加以界定的文化屏障,正是这些屏障使整个世界仍旧被划分为不同的几个部分。
200—1000年间的宗教再造重建,形成了四大主要信仰体系。这四种宗教皆具有各自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它们适应了文明的扩散及其令人不满之处。面对各种不可避免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愈来愈严重的局面,有些宗教对忠实信徒的安抚是不成功的。在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向欧亚大陆和非洲落后地区渗透的过程中,许多这类宗教被吞并或被消除,处于偏远森林和山区的各个民族纷纷皈依了四大宗教。四大宗教还传入东南亚、非洲和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朝鲜的各个新的地区。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四大宗教对欧亚大陆交往体系的扩展极有助益,从而使这一体系转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旧大陆交往体系,其幅员由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森林一直延展到印度洋。
(本文摘自《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约翰•R. 麦克尼尔、威廉•H. 麦克尼尔合著,王晋新、宋保军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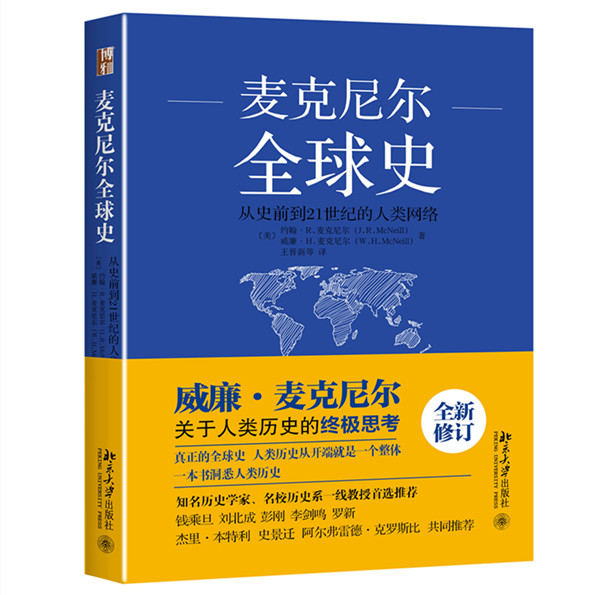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