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董牧杭︱日本知名学者为何到中国亚马逊来谩骂同行?
哈罗德·布鲁姆不容置喙地称莎士比亚“设立了文学的标准和限度”,他就是“一切经典的中心”。然而与中国颇多由话本发展而来的小说相仿,莎翁生前实际上只是创作颇受掣肘的剧团专属写手,恰恰是在十九世纪后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下文简称《故事集》)编著者查尔斯·兰姆姐弟的鼓吹下,莎剧才被人们认为价值主要在于其文学性上,而根本不适宜演出。二十世纪以降,大部分搞明白了莎著剧本性质的学者们可与布鲁姆不同,都回过了神来。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中,相关戏剧演出的重要性也可谓完全不逊色于各式各样的翻译出版物。此前汉语学界不但相关著述寥寥,而且成果也有陈旧老套之嫌。去年正值莎翁去世四百周年,陈凌虹老师翻译、中国近代戏剧史专家濑户宏教授《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下文简称《在中国》)一书的出版本是填补空白、可喜可贺之事,然而另一日本学界巨擘一桩耍活宝般的举动却为之平添了些许喜剧色彩。
如果我们打开《在中国》的中国亚马逊销售页面,就会赫然发现仅有一条用户评分,并且是个一星差评。一个ID为“樽本照雄”的账号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濑户宏的愤怒与不屑,从其中稍嫌怪异的汉语表达来看,或许他真的是个日本人:

濑户博士要说的是他被林纾欺骗了,所以他误会了。他就变成受害者了。批评林纾的研究者都冒充受害者。受害者可以随便谩骂林纾。这真是濑户博士所提出的个奇怪论点。濑户博士没有任何证据却鉴定林纾是诈骗者,而诽谤林纾。
作为研究员采用评测的双重标准是个致命的缺陷。濑户博士敢于莫名地自我毁灭。他的研究员生命已经没有了。在我阅读汉译莎士比亚研究文献直到现在为止,濑户博士的论文内容又最低又最差。
如此一针见血的批评恐怕不像是随便一个缺乏教养的吃瓜群众可以写得出来的,恐怕真有大行家在处心积虑的“抹黑”。巧合的是,樽本照雄恰恰是一位传奇式日本学者的名字,可谓卓然大家,陈平原先生甚至说过,“(近年关于林纾的翻译)实证研究中,最值得推荐的是樽本照雄”。(陈平原,《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
由此看来这八九不离十就是樽本本人跑到了中国亚马逊上来骂人。然而在旁人看来无辜地就“敢于莫名地自我毁灭,研究生命已经没有了,论文质量最低又最差”的濑户宏先生恐怕对这来者不善的“称许”不会缺少心理准备,因为早在1992年2月,日本《东方》杂志第136号就已经刊登过濑户宏的《清末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樽本照雄〈清末小说论集〉书评》一文,樽本先生早已领受过来自濑户氏犀利程度不遑多让的“礼赞”:

本书不论是在纵向(文学史),还是在横向(与其他领域进行比较)上都很难说充分说明了“清末小说”的意义。丸山升先生曾在几年前评价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现状时说:“……看待问题过于狭窄,有不良的学术主义……论说虽然属实,然而通过这种论说能够证明什么却不清楚”(《野草》39号)……丸山先生的批评是否适用于整个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尚存疑问,不过倒是很适用于樽本先生的研究……再次重申,在清末小说这样一个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研究领域,樽本先生的努力恰如洒下第一把桑叶种子一般重要,他的研究应该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樽本先生也承认清末小说的研究刚刚起步。最后,希望樽本先生的研究取得进一步进展,从而消除笔者的不满。
有着这等新仇旧怨,两位日本学界大佬在有生之年恐怕都很难会停止他们的耍活宝行为了。不过要想搞清楚这桩恩怨的来龙去脉,就非得从樽本照雄以为的一起由《新青年》制造、林纾主演的莎士比亚翻译冤案说起了。
不懂外语的翻译者,分不清小说和戏剧?
称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位译者可谓毫不为过。林琴南觉着自己的古文是“六百年来,震川外无一敢当我者”,对翻译却极为蔑视。钱锺书的老师、士林耆宿陈衍得知钱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是因林译而产生后,竟感叹道:“这事做颠倒了。琴南如果知道,未必高兴。你读了他的翻译,应该进而学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国了?”而那“不为文雅雄”的译事在林心目中只怕比自比为“狗吠驴鸣”的诗艺还要不如,石遗老人说在“康长素捧他的翻译”时,竟“惹得他发脾气”。
他早年的翻译甚至饱含着“西人为有父矣,西人不尽不孝矣,西学可以学矣”的启蒙情怀,但事情的结果往往与人的初衷不同。“断尽支那荡子肠”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本是林纾连自己的译名都不愿意去题署的作品,不料却风靡全国。自此以后,这位完全不懂任何外语、被新文化青年们视为“桐城谬种”的古文家竟仅仅借由他人口述的帮助,翻译了多达一百九十种左右外国文学作品, “自19世纪末至1920年代可说是形成了一个林译小说的时代”。(张治,《中西因缘》)在林译作品中,莎剧自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莎士比亚的译名首次出现在林则徐等人《四洲志》(《海国图志》的蓝本)中对英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的片段翻译里,被译为“沙士比阿”。然而《海国图志》长期遭到禁毁,自梁启超于《饮冰室诗话》中鼓吹“近代诗家,如莎士比亚……其诗动亦数万言”后,“莎士比亚”才得以成为通行的译名并真正产生影响。

最早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是1903年出版的《澥外奇谭》,译者已无据可考,此书译出了《故事集》二十篇故事中的十篇,凡例有“是书原系诗体,经英儒兰卜行以散文,定名曰Tales From Shakespeare”的说法,濑户宏着重强调道这“明确表示翻译的底本是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
林纾与魏易合译、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吟边燕语》出版于次年,全部翻译了《故事集》的所有篇章,序中林纾有“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已;则付之梨园,用为院本”的说法。
《吟边燕语》影响巨大,上世纪二十年代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莎剧文明戏(即中国早期话剧)大多以林译为蓝本进行演出。然而自商人们发现文明戏是个生财之道,纷纷涌入投机后,演出登时变味,业余的演员们莫说剧本,甚至连幕表都一并省去了。
但与《澥外奇谭》相反,这回濑户宏根据林纾序中的上述文字,对他进行了严厉指控:“可见在林纾的理解里,莎士比亚首先把作品以诗的形式写下,后来被改写为戏剧剧本。而实际上众所周知莎士比亚作品的发表过程和林纾的理解恰恰相反。林纾没有充分理解小说和戏剧的不同之处,更没有认识到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与翻译经兰姆故事化、小说化的《故事集》的不同。”
1916年,林纾在十余年后突然集中翻译了一批莎翁的历史剧。 “樽本照雄先生2007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底本是奎勒·库奇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濑户宏在提及“中国亚马逊评论者”的研究后,依然做出了“历史剧译文皆为小说形式,且仅记为英国莎士比亚原著”的批判。

濑户宏的说法其来有自。1924年林纾去世后,新文化运动中贡献最著的社团之一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上随即刊布了郑振铎的《林琴南先生》一文。西谛先生彼时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小说月报》更可谓具有 “官媒”性质,此文公认定下了后世评价林琴南的基调。以林纾在新青年们心目中的地位,郑当然没有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尽说好话。除了指责林“(翻译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和“任意删节原文”外,郑做出了与濑户宏相同的严厉指控:
“小说与戏剧,性质本不大相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了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失不见,这简直是步却尔斯·兰(即兰姆)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即故事集),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呢?林先生大约是不大明白小说与戏曲的分别的——中国的旧文人本都不会分别小说与戏曲,如小说考证一书,名为小说,却包罗了无数传奇在内——但口译者何以不告诉他呢?”
除了钱锺书近乎以一种赞扬的口吻“指责”林纾会时不时做出“碰见心目中原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去代他写”的增补原作式翻译之外,时下学界也往往不以删减原著作为林氏的罪状,这些富有“了解之同情”的看法显然更为明智,“如果没有那几年‘译述’的风行,翻译小说的发展能直接进入常态吗”?(陈大康,《当年“译述”正风行》)
于是分不清小说与戏剧一时间竟成了林纾翻译上最大的罪名,樽本的亚马逊留言中所谓“中国学术界上罕见的大冤枉”正是指此林纾冤案而言。他在自己一篇具有学术史意义的重要论文中申说得更详细,“这种说法与胡适所说‘这真是Shakespeare的大罪人’如出一辙。从此这样的批评成为一种定论,没有一个专家反对这个看法,定论益坚,批评者益多,规模极大。”自刘半农、郑振铎、寒光、马泰来至现代学者林薇、郑振环、郭延礼、濑户宏等尽皆认同这种看法。(郑文惠译,《林琴南冤狱》)
林纾的腐朽形象,是新青年们塑造出来的?
然而林纾的罪名可不仅仅只有弄不清小说与戏曲这一条。众所周知,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提出了“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校训原型,林琴南万分不幸地成为蔡元培平生影响最大的“五四精神”纲领性文件中“答”的对象,真是倒霉透顶。
其实这晦气也纯属他自找,谁叫这位被解聘的前北大“教授”非得去信蔡元培,尽说些“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之类不合时宜的昏话,终于导致公愤,陈平原先生形象地称他为“新文化运动自己找上门来的靶子”。
遭遇连番羞辱的林纾终于大失风度,写出了“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的影射小说《荆生》《妖梦》。《荆生》中,林纾以“伟丈夫”荆生自喻,痛骂田其美(陈独秀)、金心异(钱玄同)、狄莫(胡适)是“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并把他们痛打了一顿,《妖梦》连带着把蔡元培也骂了,甚至说他们“化之为粪,宜矣”,影射得如此明目张胆,有人想看不出来恐怕都很难。这两文一出,他自己“头号靶子”的位置可算是怎么都推脱不掉了。
林纾甫一去世,就已经“众望所归”地被郑振铎定性为“反革命”:“在康有为未上书以前,可算是当时的一个先进的维新党。但后来,他的思想却停滞了——也许还有些向旧的方向倒流回去的倾势。到了最近四五年,他更成了一个守旧党的领袖了。”
自此以后,莫说舆论,就是在学界中,林纾也几乎同样一直都是这样的形象,林纾冤案就此定型。中国清末小说研究在上个世纪可称显学,鲁迅导其先路,阿英定其筋骨,魏绍昌富其血肉,尽管已经硕果累累,却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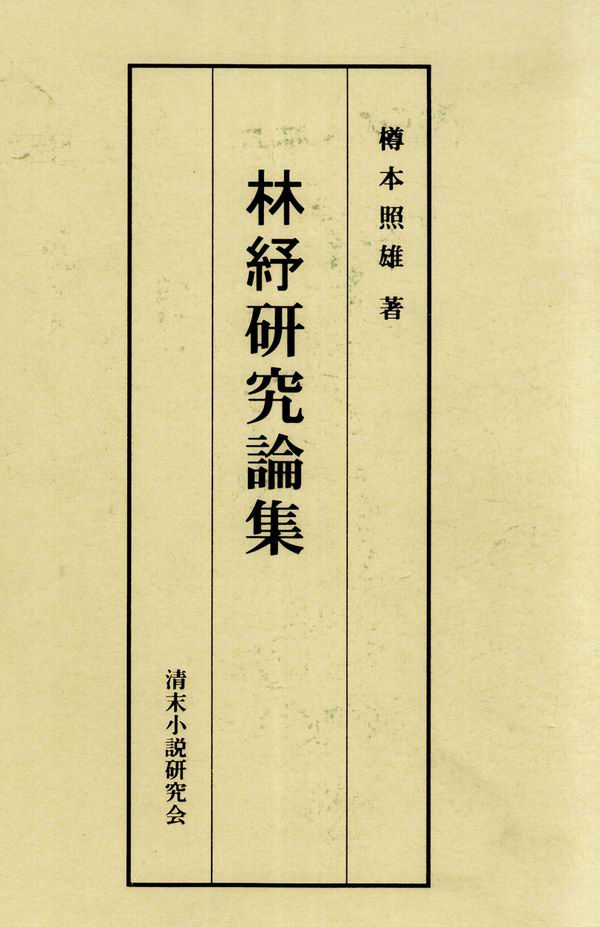
然而樽本却力图以一己之力为林纾“平冤”。樽本的学术著作几乎都由清末小说研究会刊行。成立于1977年的清末小说研究会是一个相当神秘的机构,它没有组织、会员与宗旨。研究会期刊虽然汇集了世界各国相关学者的论文,但竟是以刊发樽本一人的文章为主,每期花销几乎等同于一辆小轿车的价钱。令人震惊的是,这价值数十辆小轿车的费用竟几乎都由这位传奇学者独自承担。
樽本考订出林译莎翁历史剧所用底本为奎勒·库奇的故事集、《梅孽》(即林译易卜生《群鬼》)底本也并非易卜生原著,亚马逊评论中所说“林纾翻译时使用的蓝本都不是剧本而是小说”的新发现正是就此而言。这些考证如今已成定谳,可谓樽本最大的学术贡献之一,只是他谦虚地没有提及自己的名字。
如果以往的学者直接把林纾翻译的底本都搞错了,那么对其翻译准确程度的预估自然会得出完全错误的判断。樽本在一一比对林氏所有底本与译文后,竟得出惊人结论:“林琴南虽然不是逐字翻译,但译文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没有注明原奎勒·库奇改写莎士比亚作品,因此不该责备其将莎士比亚剧本译为小说,而该责备郑振铎等评者未探索林琴南翻译所采用的版本。”
濑户宏当然知晓樽本的考证,并在《在中国》第二章前言中明确写到“本章是与樽本先生争论后的产物,所以保留对樽本先生的尊称”。他不得不承认“林纾将莎士比亚剧作改译成小说形式这种定论并不正确”,却赌气般地坚称林纾与中国的旧文人不明白小说与戏曲的分别,而他之所以坚信这点,除了林译莎剧不署改编者之名外,也与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就把两者混为一谈有关。
然而樽本为证明自己“北大处于文学改革的重要领导中心,需要树立一位文学、思想上的敌人加以抨击来巩固自身的改革理论……批评林译莎士比亚及易卜生只是一小部分,而他们立林琴南为敌人,把他与军人列为压迫新思想的人物,才是全体新青年们所要的,而这其实与林琴南本身无关”的颠覆与创造性大胆推论,为影射小说《荆生》《妖梦》等进行了看起来相当绵软无力的辩护,“小说是虚构的,脱离任何束缚、有着高度的自由,所以怎么写都没问题”的理由可谓糟糕透顶,显然难以服人,自然要被濑户宏揪住把柄,在《在中国》一书中大加批判。

不管如何,濑户宏著述的价值不会因为樽本照雄偏激的攻讦而有所减损,樽本照雄洞见的睿智更是令后学敬服。但遗憾的是,樽本先生实在不太了解现在中国的读书人——如果他有意把这项事业进行到底,或许最明智的做法是在一个叫做豆瓣的网站再注册一个ID“樽本照雄”,并且把自己的这条耍宝评论在豆瓣的《莎士比亚在中国》图书页面上复制粘贴,还可以顺带再出口恶气,多刷一个有价值得多的一星差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