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英国现代化并非来自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而是“陌生人社会”
现代世界一向以快捷、便利、自由著称,而就在19世纪之前,人们却处处受制于时空的阻隔和传统的规训。短短的200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无“关系”就寸步难行的熟人社会逆转为陌生人的天堂? 《远方的陌生人》以英国的现代化转型为例,对19世纪前后的大量社会细节进行对比和分析,从选举制度、金融体系、人口普查、社交传媒等多个方面,描绘了英国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图景。
作者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他一反主流史学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并非促成现代社会诞生的主要因素,“陌生人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管理与经济交易模式才是背后动因。《远方的陌生人》7月由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文《陌生人社会》摘自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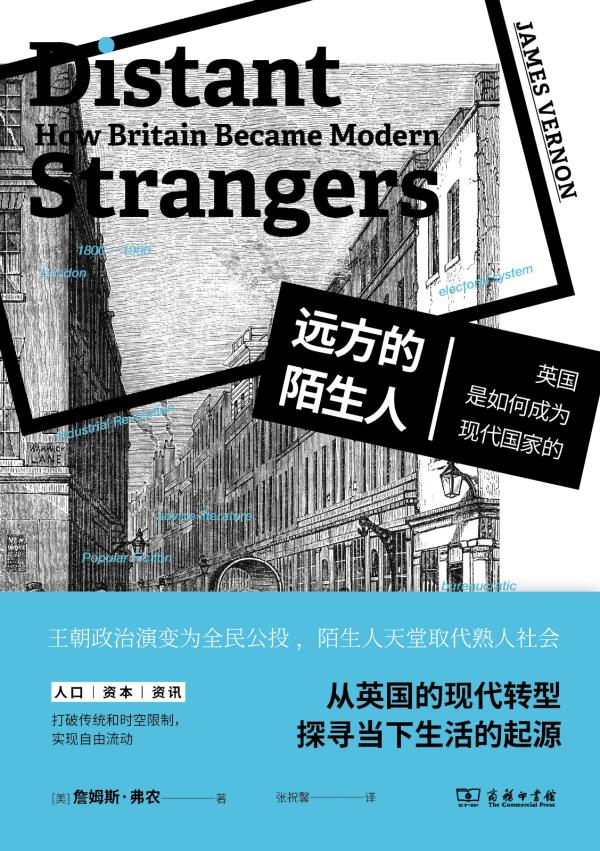
英国人在本土、帝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移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交通运输的革命,这场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瓦解了距离(以及跨越距离所需的时间)。18世纪起开始建造的运河和公路,以及19世纪里出现的铁路和汽船使英国人在更广范围内的流动性逐渐提高,因而也使他们更有可能邂逅陌生人并与之生活在一起。
道路状况最初得到改善是出于军事任务的需要。在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签订《合并法案》、1715年和1745年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之后,军事勘察员、工程师和士兵共同协作,铺路900英里,将苏格兰高地与低地上的防御要塞连接起来。随着18世纪50年代兴起的修建收费公路的热潮,勘察、切割筑堤以及铺路的技术在筑路过程中不断发展,这些公路向南延伸,最终与地方行政区维护的道路相通。1750—1772年间,英国设立的国家信托机构超过500个,修筑道路1.5万英里。即便如此,在政府于1785年投资设立了自己的长途邮政车队之后,英国邮政总局(General PostOffice,GPO)仍然设置了一组调查员专门测量这个不断扩张的交通网络的距离范围,勘察糟糕的路面状况。在1801年英国与爱尔兰签订《合并法案》后,这个国家又一次迎来了军事任务,它促使两条由国家资助的卡车公路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延长了1700英里。这两条公路分别连接了英格兰与威尔士、威尔士与爱尔兰(途经霍利黑德)。而连接了伦敦和爱丁堡的大北路(the Great North Road)也因此得到了完善。1835年《公路法》(Highways Act)颁布后,总长12万英里的公路网络的其余部分——其中98%的道路由超过1.7万个行政区和公路信托机构维护——都必须根据中央标准采用碎石铺路法(“碎石铺路”[macadamize]这个词源于发明这种铺路方法的工程师的名字“麦克亚当”[McAdam]),使用此法铺成的道路中间拱起,以助于排水,同时还打下了10英尺深的石子地基。
随着道路的完善,英国迅速“缩水”,过去分散、分离的人口聚集进了一个日趋紧凑的国家空间。1715年,每周离开伦敦的马车(stagecoach)已有800辆,但不论到目的地的距离有多短,乘坐这些马车的旅行者所面对的,仍然是折磨人的漫长旅程。即便到了18世纪60年代,从伦敦出发驶向爱丁堡的马车每月仍然只有一班,且整个行程需要两周时间。一个世纪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公路网络覆盖的广阔范围、改善了的路面状况、改良后的马车设计以及邮政总局对更快速的送信马车的采用,这些因素都大大缩短了旅行的时间。及至19世纪20年代,每周离开伦敦的马车数量已达到1500辆,另有700辆邮政马车和3300辆私人马车,它们构成了公路旅行的全国性网络,马车的旅行速度较18世纪50年代快了近3倍。
伴随着1830年“曼彻斯特—利物浦”铁路线的盛大启动,铁路的时代到来了,但它的出现并未终结公路上的马车旅行。首先,铁路延伸得很慢。1838年,英国仅有500英里的铁道,但19世纪40年代的投机热潮使得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所描绘的“横贯我们国家框架的全新钢铁脉络”在1850年以前已然就位,600英里的铁道贯穿了英国的主要城镇。一些地区——尤其是康沃尔、威尔士和苏格兰高地——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进入迅速成熟的铁路网络。及至1914年,这个网络已经覆盖了2万英里的范围。然而,仍有1/6的地区未设立火车站点,其中许多地方仍然依靠马车进行旅行——的确,在1901年从事商业载客的马匹相较于1851年多出了3倍。即使单个的公路—马车旅程数量在1835年达到了1000万的峰值,但铁路仍然迎来了一个快速大众运输的全新时代。早在1845年,就有3000万趟旅程在铁轨上完成,而铁路网络的发展和票价的降低更是使得这个数字在1870年前就上升到了3.3365亿。是年,持有三等票的乘客占总乘客数的1/3,而到了1890年,他们已经占到火车乘客总数的2/3。这不仅仅是因为更多人开始将火车作为长途旅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更是因为火车的行进速度是前所未有的。1845年,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的一趟旅程要花费6小时,而到了1910年,乘火车从伦敦到爱丁堡仅需10小时,同样的旅程,一个半世纪前最快也要花上10天。距离被抹除了,但旅行的愈加高速也使其在想象上缩水了。尽管很明显,英国人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性更强了,但对于该现象对移民模式的影响,我们所知甚少。最显而易见的后果是人口开始定居在轨道沿线,而像米德尔斯布勒(Middlesbrough)这样的城市,则完全是因铁路而生的。在斯托克顿(Stockton)和达灵顿(Darlington)铁路延伸至米德尔斯布勒之后,这个城市的人口数从1821年的40人飙升至1851年的7631人。这些移民大多来自约克郡的周边郡县,但及至1871年,米德尔斯布勒已拥有99 705的人口数,其中来自约克郡的人数不足一半。
……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做长距离旅行的经验意味着,不论是否为移民,英国人邂逅陌生人的概率都愈加增长了。尤其是公路和铁路,此二者成了打乱社会空间的新型交通形式。而社会空间则不得不受到全新的社交传统的引导。自18世纪中叶起,英国不断扩张的公路网络开始充斥着士兵、工匠、临时工、牧师以及锅匠、仆人、国家职员(收税人员、邮政人员)和激进的政治领袖。这些人却很少通过公路从甲地抵达乙地,他们是属于某个区域线路,比如卫理公会的牧师每个月都会在同一个线路中行走150—250英里,而收税人员的任务则是每天在乡村骑行38英里。此时的步行还未具有日后浪漫主义诗人,在《流浪法》(vagrancy laws)的严格控制以及19世纪40年代铁路旅行的到来之时,赋予步行的“理想型漫游”(peripatetic ideal)意义。和优美的田园经验完全不同,步行对体力要求极高,且通常很危险。在公路大盗迪克·特平(Dick Turpin)于1739年被送上绞刑架之后一个世纪里,他的形象已经从一个残暴的罪犯转变为一个潇洒又浪漫的人物,对这种现象,没有比“虚构性转型”更好的阐释了。这种对公路抢劫案的虚构性再刻画夸张了一直以来人们在面对公路上的危险及途中邂逅的陌生人时所产生的焦虑,类似的案例还有同一时期人们对杀人无数的印度图基教(Thuggees)的描述。于是,最重要的问题成了如何得知谁是可以信赖的。18世纪下半叶,一些交易协会和友好的社团是首先开始发展区域性步行网络,欢迎并支持这些被称为“兄弟”和“朋友”之人的组织。
从这些在公路上步行的混乱人群中抽身之后,正直的中层阶级需要面对属于他们的难题,即在高大体面的新车站必然会遇见大批陌生人,而在马车或火车车厢内又会与陌生人发生新的近距离接触。马车旅行非常艰巨:行程漫长,往往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停靠休息、伸展腿脚或解手的机会都很少。人们也很难与同行的乘客保持礼貌的距离,因为他们都被“打包”、闭锁在车厢内,行驶于颠簸的路上,彼此紧紧挨着,甚至相互交叠。很快,英国出现了一种“建议型文学”,它帮助、指导旅行者改进自己开展合宜对话的技能和自身的行为举止,比如寒暄的恰当尺度,以及避免不必要的眼神交流的重要性。一种典型的观点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旅行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有我们国家这么大,因此我们尤其需要理解旅行的品行。”
火车的情况略有不同。尽管1844年以前,三等座的乘客都像货物一样在敞开式的车厢中旅行,但一等座和二等座乘客的车厢都是以马车的U形座位为模型设计的。由于铁路行进的速度令许多想要看看窗外风景的乘客作呕,阅读这个在颠簸的马车车厢中不可能完成的活动成了避免与陌生人眼神交流,以及合理规避其他同行乘客的办法。图书和报纸摊位很快遍布了英国的火车站。19世纪60年代期间,两起臭名昭著的火车谋杀案为老式车厢拉响了死亡的警钟——与凶残的陌生人共用一个独立的隔间开始被视为危险之事。在尝试于内厢隔间之间安装“猫眼”、于火车外部安装踏足板之后,火车车厢被重新设计,使各个隔间有边廊相连,每个隔间由滑门进入。这也使得乘客能够到处走动和使用洗手间。自19世纪60年代起,新一代的城市旅行为体面的通勤城市阶级而发展起来,其中的交通工具包括伦敦的马拉迷你巴士、电车和地铁。伴随着更短的行程以及更随意的乘客“混搭”,它们的车厢设计遵循了低等火车车厢更开放、流动的原则,这使旅行者常常不得不与陌生人紧挨着站。这些旅行的形式造成了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比如如何应对横行扒手,如何避免不必要的交谈并维护私人空间,如何规避与陌生人及其携带细菌的肢体接触。
理解陌生人社会
与陌生人日益频繁的邂逅都主要是发生在城市里以及城市的街道上。伦敦是典型的例子,也是最早的例子。从17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开始有这座城市的导览类书籍出版,如内德·沃德(Ned Ward)的《伦敦密探》(The London Spy,1698—1700)或约翰·盖伊(John Gay)的诗集《琐事,或行走于伦敦街道的艺术》(Trivia; or, The Art of Walking the Streets of London,1716)。不过,这类书的数量在一个世纪后才开始激增,那时城市黄页也开始多了起来。《伦敦密探》成为经典作品,它开创了一种文类,其特点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娱乐、财富、秘密和危险的地方知识都是为了一样东西所准备的——沃德诗意地称之为“流动”。在街道上移动,会听见嘈杂的声音,闻到多种多样的气味,遇见无止境的人流,这就需要人们知道如何安全、体面地处事的方法。城市指南和礼仪手册提醒那些好奇的人,不要直勾勾地盯着陌生人或是在私家住宅外探头探脑,走路要靠左行,不要在人群中推搡。你必须学会如何成为陌生人人群的一部分。个体的肢体行为,如推搡、小便、吐痰,都会引来他人的不快。18世纪伦敦的咖啡厅和娱乐花园都是确定礼数规则和商业交际的臭名昭著的试验之地。1773年在沃克尔豪斯娱乐花园发生的著名的“通心粉斗殴事件”(Macaroni Array)就证明了这些礼节都是靠琐事和过失而慢慢建立起来的——该事件中的两位绅士就男女之间恰当的交往形式这一议题产生矛盾,最后以决斗告终。
尽管如此,在19世纪早期,文人墨客还是有规律地对伦敦惊人的规模及其匿名性做出评论。他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在庞杂人群中茫然若失的感受,因此他们使用“流质”的意向,如水流、激浪和河川来捕捉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容量以及持续不断的流动的感受。华兹华斯在《序章》(“Prelude”,1804—1805)一诗中对自己在伦敦“流动的盛会”的描写常常被认为是文学史上对现代城市生活之脱序状态的第一个——也是典范式的——陈述。二十年后,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也像华兹华斯一样,发现了居住在一个不知邻居姓甚名谁的城市的古怪之处,但他对此却没那么强烈的疏离感。对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而言,世上最孤独之事莫过于第一次与伦敦街道的邂逅。“他站在往来人流的中心,这些面孔穿梭不停,不与他交谈一词一句;无数双眼睛,瞳眸间却没有他能读懂的东西;男男女女匆忙的身影交织在一起,于陌生人而言却是谜一般的存在……”由于在19世纪以前,街道上很少有指示牌或路名,房子也大多没有门牌号码,因此要穿行于伦敦意味着为了获得本地信息,你必须信任陌生人。渐渐地,指南——如W. G. 佩里(W. G. Perry)那本《伦敦指南和对抗诈骗、骗子和扒手的措施》(London Guide and Strangers’ Safeguard against the Cheats, Swindlers, and Pickpockets that Abound ...,1818),标题已说明一切。这些指南读物提醒诸位读者对他们问路的对象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被无赖、骗子和伪装者盯上。相信陌生人是件危险之事。正如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所发现的,扒手和妓女有时会扮成着装入时的淑女。G. W. 雷诺兹(G. W. M. Reynolds)《伦敦悲剧》(Mysteries of London)中的一位警察也嘲讽地说过:“如果把我们知道的所有伪装者抓起来,大概半个伦敦的人都要被收监。”及至19世纪晚期,甚至连城市督察员和警察都开始以“便衣”展开调查,更不必说那些为了亲历贫穷生活而伪装自己、驻扎进城市贫民窟的记者和慈善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永远也无法确认一个陌生人的身份,遑论对其抱有信任,因而对欺诈、犯罪和性侵害的恐惧迅速蔓延开来。结伴寻欢的男人们是敲诈骗局的受害者,名誉扫地、身陷丑闻是对他们最好的威胁。在伦敦西区这个看似体面的、安全的地区购物的女人们,则吸引了一些男人不怀好意的目光——他们将她们误认为是妓女。城市期刊和建议性文学给出的忠告是,无伴的妇女如果要在白天出行,不要在商店橱窗或公交车站徘徊,也不要回应任何一个陌生男人的凝视或招呼,“目标坚定”的行走能避免遭到骚扰。
由于伪装者无所不在,且无法准确地通过他们所在的位置或着装打扮辨认出,围绕城市人类型的分类及刻画的新式专业知识产生了。自19世纪40年代起,对在这个黑暗又危险的城市迷宫里的城市人种类和人格的表述充斥着不同档次的文学流派,甚至还有初期的社会科学。G. W. 雷诺兹作为“英格兰最受欢迎作家”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他的《伦敦悲剧》所获得的巨大成功,1844年,此书销量为4万本一周,令人瞠目结舌。在一系列影响力惊人的小品文中,雷诺兹将穷人与富人生活及陋习并置描写,如狄更斯的小说或之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雷诺兹通过对人格细致入微的观察,对城市地域和人的社会类型进行了一次“考古工作”。当然,其中一些对于在纸上应付和探究陌生人社会的尝试——如礼仪书籍或城市指南——早在欧亚的近代印刷文化中就已见雏形,但仅仅是少量地、零散地出现。以上就是18世纪伦敦的例子。然而,印刷文化的盛行以及伦敦在19世纪前所未有的规模确保了,人们对将陌生人阅读和描绘为可知类型的努力会以可观的势头进行下去。这在视觉文化中尤为明显。世纪中期的同一时段,一些艺术家,如威廉·鲍威尔·费斯(William Powell Firth),威廉·莫·埃格莱(William Maw Egley)和乔治·埃尔加·希克斯(George Elgar Hicks),都非常重视城市生活的“匿名”本质,尤其注意那些繁忙的社交场合,如邮政总局和帕丁顿火车站。埃格莱的画作《伦敦的巴士生活》(Omnibus Life in London,1859)很好地代表了这个流派。这幅画生动地描绘了一辆巴士,尽管已经拥挤不堪,但仍有更多的乘客想要上车。画面展示了各种不同类别的社会人,体现了现代生活不可避免的尴尬。观画者,和巴士的乘客一样,不仅会发现在陌生人面前交谈、注视他们是不礼貌的,而且还被鼓励去猜测这些聚集在如此窘迫、拥挤空间中的陌生人的人品性格。
我们可以将19世纪后半叶逐渐出现的社会科学作品理解为一个人们试图通过识别不同种族和阶级、性格和地区的人群来解读陌生人社会的高潮。“游荡群伙”(wandering tribe)这个定义最早出现在1849年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在《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上连载的文章中。这个群体构成了伦敦街道生活,梅休详细刻画了该“犯罪阶级”的着装、语言和面相,方便他人能够避开他们。他写道:“他们都或多或少有着高颧骨和突出的下巴——这是由于他们使用的黑话、他们对财产的非分之想、他们普遍目光短浅的特质、他们对稳定工作的厌恶、他们对女性的不尊重、他们对残酷手段的热爱、他们好斗的品性以及他们对宗教的狂热。”从梅休的写作到19世纪70年代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对不同罪犯类型进行照片合成的实验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在欧陆社会理论家尝试去想象将陌生人凝聚为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时,英国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则将研究重点置于对差异的调查和描绘。
在17—18世纪,不同类型的社会描写和差异在阶层和次序、站位和级别、类型和阶级交织的网中不断繁衍。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的“1688年后人口研究”影响力巨大,它包含了一份详细的清单,罗列出超过20种群体,分别具有不同的“阶层、级别、头衔和素质”。金的分类——政治官职和素质,社会阶层和头衔,经济活动的混成——不算是精准的定义,但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秩序,在其中,每个人各处其位、各司其职,组成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等级制度。到了19世纪初期,这种分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不仅仅因为维持和描述这样一个差异微小的精密等级制度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很难做到,更是由于社会描述这项高强度的工作创造了对社会的一种新理解:它是个自成一体的疆域,拥有其独有的分类形式。
18世纪晚期以前,动物学家首先使用“社会”一词来解释动物中的一种独特的交际组织系统,此后这个术语就被用于指代一系列特殊的联系和从属关系。直到19世纪初期,“社会”的概念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区分于政治和经济——才被应用于人类的情况中。随着19世纪30年代起社会的迅速发展,记者、统计学家、医生、慈善家、雇主和政客所做的大量工作帮助我们厘清了“英格兰的境况”,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劳工穷人的危害。尽管他们的方法、途径、流派、政治理念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工作都从整个社会独有的(与经济和政治不同的)节奏、疑问和问题切入,逐渐将其构建成一个独特的场域。社会的节奏和法律可以通过对某些疑问和问题的研究来理解识别,但其作为一个“自治系统”的观点却形成得十分缓慢。相较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ion)在1857年和1886年的作品,这一点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1873)和亨利·梅因(Henry Maine)的《东西方的乡村社区》(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1876)体现得更为明显。前者通过进化生物学将社会概念化为一个有机的、不断复杂化的系统;后者解释了维系“传统”社会的地方和父权纽带。即便是在1903年,当社会学的学术学科在英国正式以社会学社团(Sociological Society)的形式姗姗来迟地现身,相较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和描述、分类社会差异,它分析社会发展之铁律这一功能始终不太受到重视。相反,欧陆社会学家致力于观察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城市中最新出现的高密度和匿名化现象,试图去理解未分化的城市“人群”的集体特征和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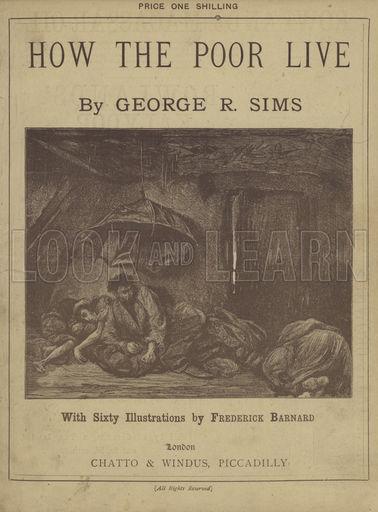
在英国兴起的社会科学的文化作品力图使陌生人社会变得可理解,它们首先描绘了构成陌生人社会复杂性的差异的种类,接着想象出将这个离散系统维系起来的纽带。毫无意外,在英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社会研究者和调查者更依赖于种族分类,而非阶级,来理解在世界最大、最富裕的这座城市里所产生的贫困问题。他们不必远行千里即可探究《穷人是如何生活的》(How the Poor Live),因为正如乔治·西姆(George Sim)在1883年所说,“这是一块黑暗的大陆,其跨度不过是步行到邮政总局的距离”。人们愈加相信“穷人”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人种,并将其等同于帝国疆域上那些“原始的”“野蛮的”民族,将伦敦的东区比作东方或非洲的黑暗大陆。这种对国内穷人的种族化与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和1866年牙买加莫兰特湾叛乱(Morant Bay Rebellion)之后,英国人对于帝国范围内种族差异的固化观念密切相关。伦敦穷人的原始特质和英国人的帝国主义主体是深深根植于他们人口的种族差异的——人们逐渐倾向于通过决定性的生物学,而非文化或历史来做出解释。在高尔顿做不同犯罪类型的合成照片实验时,他也在研究优生学。查尔斯·布斯对于伦敦贫困现象做出了更有统计学逻辑的解释,也难以避免种族化的影响。他将每条街道按照其居民的富裕程度划分,用黄色代表最富裕的“中上阶级”,用黑色标记“底层阶级”,然而这部分被进一步归纳为“恶毒、半犯罪”区域。尽管布斯已经尽力了,但他的分类仍旧无法跳脱将穷人视作一个种族的观点。当“阶级”真正以构成社会秩序的分类标准出现时,它也不是社会学想象的结果,而是语言政治的产物。甚至即便马克思在英国长期流亡,阶级作为分类始终是边缘的,它首先是作为政治——而非社会——术语,被理解为与国家和公民身份的关系。直到社会科学家记录了中产阶级的扩张(伴随着工作的新型技术模式、新的住宅类型、新的休闲活动的出现)以及20世纪30—60年代间美国式大众文化、城市规划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对传统工人阶级社区和文化的侵蚀,阶级分类才逐渐被接受。在这种意义上,阶级最为明显之时,正是在其消解和重构的时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