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画很美但自闭症一点也不美好,浪漫化宣传也许会起反作用
腾讯公益一元买画的行为,昨日刷爆朋友圈。
热度持续一天后,争议、质疑又冒出头角。网络爱心发酵之后,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如何才能真正帮助自闭症患者?澎湃新闻采访了几位从事特殊儿童治疗、自闭症患者行为干涉研究的工作人员和教师。
某些宣传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希望大家在奉献爱心之后,能够真正去了解这个群体,而不是浪漫化自闭症,推动社会福利(残疾人保障)的健全化,才是对这些苦难家庭有效的帮助,”严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严星(当事人要求匿名)是一名从事特殊儿童音乐治疗的教师,从国外取得音乐、特殊儿童治疗相关学历后回到上海。“我工作在一线,每周会接待五、六位孩子的一对一治疗。如果你要问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我是不赞成的。尤其是当我看到那些美丽得令人炫目的画作时,我的第一感受是愕然,怎么别人家孩子的自闭症那么‘美好’?”
“精神病人可以被叫做外星人的使者,他们其实是真正通晓宇宙真理的小部分人,用特殊的行为和思维启发我们这些庸人。”
面对澎湃新闻记者的询问,严星反问:“你觉得上面这句话有问题吗?很荒谬吧,颠倒黑白,并且会妨碍对疾病的正确诊断和干预治疗。那么你把主语换成‘自闭症儿童’看看,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描述:他们是来自星星的孩子。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世界中。但他们有我们无法企及的某种特殊能力的。他们在某个方面超乎常人。他们是特殊的,珍贵的。”
严星强调:“我当然希望社会能够给予更多的重视和爱心,但是这样的宣传是起反作用的。似乎他们只是话不多,会有点奇特举动的人。很抱歉,自闭症一点也不美好。我接触到的孩子,大部分完全无法沟通,不要说拿画笔,就是叫他/她名字都没有反应。有的孩子会反复开水龙头,必须要一直听到流水声,不然就会做出极端行为,一些父母每天要保持警醒,这是很大的痛苦和无法言说的折磨。我还接触到一个孩子,已经成年了,但依然处于有需求只会喊妈妈的阶段,有一次在我这里当场解决大小便,这样你还觉得浪漫吗?”
“确实有孩子对画笔感兴趣,但也仅限于拿一支笔在纸上机械地划一些简单的线条,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换笔、换色彩、设计构图,”考虑到有小概率人群,严星补充,“也许有那种画得特别好的,但我在临床上没有遇到,概率也许是千万分之一吧?”
“父母把孩子送到我这里呆一小时,有的甚至不是为了孩子,而是父母们得以有一个小时喘息的时间。这其中的生活艰辛很难为外人道。你能理解吗?”未等澎湃新闻记者回答,严星紧接了一句,“你很难理解的。”
严星的“工具”是音乐,然而面对自闭症患者,她觉得自己百般武器无处使用。“自闭症没有明确的病因,所以也没有所谓的治愈性,就是很绝望的,只能生活下去,所有认真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人员都是在黑夜里摸索。有的孩子仅仅是听到某种乐器声,容易安静下来一会会儿,这就非常好了。自闭症的状况千差万别,虽然统称‘自闭症’,但每个孩子是完全不同的,随着年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多,会有一定的好转,但如果碰到创伤也会恶化,所以我们呼吁有健全的体制去保障这些孩子有可以活动的场所、这些家庭有经济保障。”
“在一些宣传中,会说有自闭症孩子通过画画,协调性变好了,生活能自我打理了。这没有必然关系,只是说孩子们在一个组织内有事情做好过无事可做,出来多活动多接触人对社会行为发展有一定帮助。”在严星看来:“金钱支持、对自闭症儿童父母的心理疏导和关怀、社会的陪护体系,能做到这三点就比较完备了。”
自闭症真正的痛苦是什么
曲解自闭症患者会有哪些影响?梅兰妮博士常年参与自闭症患者的培训、研究工作,也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
梅兰妮博士表示:“曲解自闭症的表现很多,每一种表现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公众平时不大有机会接触到自闭症儿童,大多是从电影或者通过其他媒介获知自闭症的表现,认为自闭症儿童都是具有非凡的数学、长跑、绘画、音乐和记忆等天赋的超能儿童。当真正见到自闭症儿童的时候,才发现不是这样的,颠覆了他们从文学作品和媒介报道中的认知,开始重新认识自闭症,认识这一个群体及其背后家庭、社会的生态环境,开始同情、理解、包容并开始帮助。
第一层面的痛苦,是对自己的谴责,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报应会降到我的孩子身上。作为不是很自信的女人,她们更加对丈夫和整个家族有愧疚感。
第二层面的痛苦,与社会断裂的痛苦。家庭的一个成员会辞去工作,专心一辈子带孩子,基本上与社会断层,而人是一个社会动物,缺乏社会关系的生活是单调、孤独和痛苦的。
第三层面的痛苦,感情付出无回报的痛苦。他们无数次反反复复地教孩子怎么吃饭、怎么上厕所、怎么洗澡、怎么叫妈妈,可是都不会;甚至有严重行为的自闭症孩子会伤害亲人,永远不懂得感情和回报,我们很难体会这些母亲和父亲的那种悲凉和孤独。
第四个层面的痛苦,不被社会认知的痛苦。是社会的不理解带来的痛苦,不能够被社会认知和认同,永远处于一种解释、求得原谅和理解的卑微心理中。
第五个层面的痛苦,对现状和未来的绝望感。这是切切实实的痛苦,父母没有一刻得到喘息,那种身心俱疲的感觉,绝望的感觉,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到。 担心孩子长大了,父母老去了,孩子怎么办?
2015年,梅兰妮博士与心理学家莱贝克博士前往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马奎斯自闭症中心(Marcus Autism Center),马奎斯自闭症中心是亚特兰大最大的自闭症研究和诊疗中心。该中心有六个不同的治疗内容,包括语言和学习诊所;严重行为治疗部门;喂食部门;自闭症研究所;精神病或者远程指导部门;儿童活动部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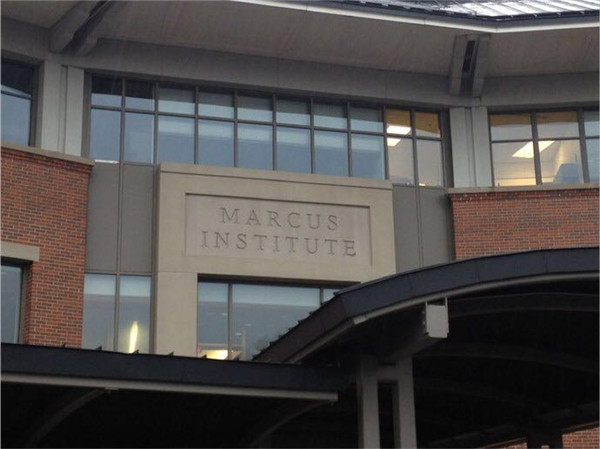
“到中心来治疗的家庭,基本上是通过他们的家庭医生推荐到这里的,以诊断为目的,并通过诊断进一步确定治疗方案。去年一年,约有6000个孩子来中心,其中60%是来接受诊断和评估的,25%来接受治疗,15%诊断并治疗。有亚洲人在这里治疗,其中以韩国人居多,因为在佐治亚州,亚洲移民中以韩国移民最多,其次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当然也有其他各个国家的人。”
考尔博士(Dr.Call)是严重行为的治疗部门专门负责和治疗自闭症儿童的严重行为(severe behavior)的专家,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
梅兰妮博士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当时恰逢考尔博士团队正在收集一个约十岁左右黑人男孩的数据,并且同时给予治疗。
“我们站在分析室里,透过窗户能够看到治疗室的一切,但是治疗室的孩子及旁边的工作人员看不到分析室。治疗室墙壁是绿色的,没有任何装饰。这个黑人男孩大约十岁左右,他头戴特制的头盔,只露出眼睛,两只手戴着特制的手套,不断轮换击打自己的面部,耳部和头部。考尔说,平时这个孩子总是不停地击打自己,甚至用双手抠自己的眼睛。如果他停下来,旁边的黑人女工作人员立即用语言赞扬,这样的击打持续了十分钟,电脑数据很快就分析出来了,接着会为他制定为期11周的治疗计划。对于这个自闭症群体,他们不会把语言作为首要的问题去治疗。”


梅兰妮博士说,这几分钟对她来说都是煎熬,不能获取分析数据,也不能拍照,即便被允许,也很难记录这个男孩不断击打自己而停不下手的过程。旁边的护士没有笑容,使用简单的语言,程式化地完成工作。有些自闭症的孩子不懂得笑容,不懂得超过三个字的长句。
夏普博士(Dr.Sharp)负责自闭症儿童的吃饭问题诊疗。这些孩子只吃一种他熟悉的东西,其他一概拒绝。如果在一个派对上,桌子上摆着很多种饭菜,他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如果没有他需要的那种食物,他是不会去吃其他食物的,也拒绝去吃,极度的饥饿也不能促使他们去吃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食物,有些孩子压根儿就没有吃东西的意识,没有吃的欲望。
在一间分析室,透过玻璃望向诊疗室,一个约三岁的黑人小男孩坐在一个特制的儿童就餐椅上,一位男医生正在和他玩汽车玩具,旁边医生操作台上有四种木质小木勺,没有食物,医生时不时找机会给孩子喂一口空勺。当医生取走小玩具,换上了米老鼠布玩具,小男孩抗议,蹬腿,哭叫,医生又成功地喂了一口空勺,孩子深情地亲吻米老鼠,夏普博士通过麦克风对医生的工作表示赞扬。
治疗费用主要通过保险支付,每天500美金,这只是一个白天,夜晚不治疗,家长把孩子接回家。双休日诊疗中心休息。考尔博士说他一直对这个病症的治疗有信心,尽管常常受到困扰。这是一个令父母们心焦的病,但是医生们不会无休无止地全天候呆在诊疗中心。在中国也是这个问题,父母必须有一方放弃工作,全天陪护孩子。
梅兰妮博士介绍:“美国有37个州对自闭症儿童保险,但是情况不一。关于美国政府在财政支持方面,政府只负责穷人和基本的医疗,所以很多美国人因为家庭有自闭症儿童而陷入灾难性境遇。不过,佐治亚政府正在商议对3到10岁的自闭症儿童每人每年给予35,000美金的财政支持。”
但10岁以上、马上接近成人的自闭症孩子怎么办?在这里也没有答案。
马奎斯中心每年能收到几百万美金的捐助,大多来自基金,也有很多来自个人。但是中心没有志愿者,所有的人都是工作人员,中心不依靠志愿者的力量,不需要志愿者。主要因美国儿童保护法,以及美国人高度保护隐私使然。
“我在2014年接受上海爱好康复培训中心的培训时,培训中心的刘乐老师讲到上海目前统计出来的自闭症儿童患者数量是八千多人,那么多的其他孩子在哪里?不知道。”
“美国的自闭症儿童没有专门的学校,无论自闭行为轻微或者严重的孩子,都可以正常地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但是分班级学习,和正常孩子不在同一个班级,所谓同校不同班。自闭症患者的父母非常期待通过干预治疗后,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和正常孩子有基本的交流,或者奢望通过与正常孩子的交流,能够被影响,更好地让自己的孩子被改变,能够被社会接纳。”

梅兰妮博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每一个自闭症孩子的表现都是不同的,今年4月我参加滴水湖蓝丝带公益骑行活动,大约有不到二十个自闭症孩子骑行,他们最后上台领奖的时候,我观察着,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他们至少还是幸运的。还有多少各种程度的孩子以及家庭在挣扎?因此,能够对这个家庭有帮助的才是最好的,花拳绣腿的事情不要去做,帮助这些父母,能够让他们稍事休息都是伟大的。”
关于自闭症儿童的话题还在发酵,在献出爱心的同时,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你愿意与一个可能大吵大闹的孩子同处一家餐厅、一个活动空间吗?如果自闭症孩子与自己的孩子同在一个学校学习,你愿意吗?我们可以直面那些毫无美感的残酷吗?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