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自由的自我艺术家:白羊座文学大咖TOP10
在季节的轮换中象征着春季生命开始的白羊座,因为生命从无到有的存在意志,表现出来的是意志力的张扬、生命力的燃烧。他们一旦面对世界,永远是以一个人的姿态投入战斗,所以往往导致自身的陷困和毁灭,但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因为把自己陷入极端境遇中,往往能激发自身的潜力,让生命力完全张扬,而他们在生命力的完全张扬中会产生挥发生命的快感,白羊座的文学家就是在写作中时时展现自我,追求自由,从而获得生命快感的人。
这必然导致他们永远耻居人后,成为新事物的开创者。如果文学的原创性和疏异性是文学家们永恒的追求,那么白羊座文学家的魅力,就在于无论面对多强大的“敌人”和“影响的焦虑”,一旦选择了自己的疆场,他们就会正面撞击过去,要么撞出一条新路,要么就脑袋开花什么都不存在。他们是文学世界的“野蛮人”,手拿战斧,傻傻地冲在战场的最前面。
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4月7日)
《华兹华斯诗选》
华兹华斯在中国读者眼中的印象,主要来自那首被无数选本收录的《孤独的割麦女》,实在很难过分欣赏这首诗的所谓优美之处,除非审美停留在小学时每次春游回来语文老师必定布置的作文题。再加上我们心中的英雄拜伦——他和雪莱、济慈一起成为了我们浪漫派英诗启蒙的“三件套”——对他极力嘲讽,称他为诗坛的江湖骗子和政界的寄生虫,“这个变节的雅各宾派早已变成了一个小丑般的阿谀者,不惜把贵族的最恶劣的偏见加以颂扬”。于是华兹华斯就被一棍子打死,他的湖畔隐居就成了伪装陶渊明的“终南捷径”。其实华兹华斯之于现代诗的地位是开创性的,几乎影响了他之后所有的英语诗人。仅仅是因为他早期的成就太卓绝,以至于连他本人的后半生也只好望尘莫及。要么走向必然性的“平庸”,要么死,这是每一个天才最为恐惧的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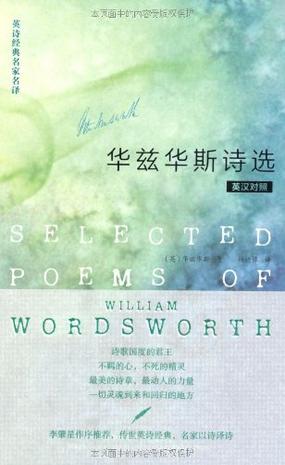
波德莱尔(1821年4月9日)
《恶之花》
波德莱尔比华兹华斯幸运得多,因为华兹华斯生活在英国的乡下,而波德莱尔生活在世界的巴黎。十九世纪的巴黎,简直比二十一世纪的许多地方都显得更为现代。例如那个比波德莱尔多活了近二十年的雨果,大概因为长年不在巴黎的缘故,他的诗和他笔下的中世纪圣母院一样古老,引不起我们的兴致。但波德莱尔神奇地活到了今天,他和我们时代的关系,就像荷马之于古希腊,维吉尔之于古罗马,只要这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没有死去,只要巴黎还是城市生活的永恒坐标,他的作品就会一直鲜活。游走于巴黎大街小巷的波德莱尔像先知一样,把眼前万象都捕捉到敏感的语词之中,把人类一切正常或不正常的情感、思想,都升华为诗,正如他的诗句所宣示的:“我爱你,臭名昭著的城市!卖笑的、逃缉的,自有他们的赏心乐事,芸芸众生却永远无法理解。”

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年3月26日)
《弗罗斯特诗选》
活跃于二十世纪的美国诗人,想不受惠特曼的影响是极其困难的。惠特曼在美国占据了华兹华斯在英国的地位,而且比华兹华斯更完整而难以超越。如果有,那就是罗伯特·弗罗斯特。这位在高等学府林立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做过鞋匠、教师和农场主的“乡下人”,诗歌多从农村生活中汲取题材,但不是华兹华斯式的下乡采风“体验生活”,那是弗罗斯特真实的生活。对比同时代的华莱士·史蒂文斯、T.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哈特·克莱恩碾压读者智商的现代派诗风,弗罗斯特实在是太“亲民”了,他选择了一条同代大诗人中“少有人走的路”,却最终走到了读者的心里,因为他看上去略显传统的诗歌形式,却蕴含着极具当下实感经验的新颖、深邃的思考。

安徒生(1805年4月2日)
《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
安徒生把自传命名为《我的童话人生》,然而这份自传对比虚拟而让儿童能够承受苦难的童话实在是太沉重了。这里面是他如何经历各种痛苦,从工人群体中脱颖而出的“光荣的荆棘路”。他走遍欧洲拜访各式各样的文学大咖如海涅、雨果、狄更斯、罗伯特·勃朗宁等,像个出席各种活动逮到名人就在朋友圈晒签名、合影的名人搜寻者。他渴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文学名家,所以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各种体裁都疯狂生产了大量让出版社亏不起的作品,最终,他通过看上去不登文学大雅之堂的童话创作,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你可能没看过莎士比亚的任何一部剧,但丁的任何一篇诗,但你一定读过安徒生童话。

果戈理(1809年4月1日)
《彼得堡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走出来的”。这句形象的评价奠定了果戈理在俄国小说史上的地位。然而就是这个被我们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大作家,生活得几乎毫无现实感,从没见他有过深入群众的实际行动,他的小说素材,也基本上是从朋友们——例如永远不缺乏素材的普希金——那里“偷”来的,然后依靠“剪刀加浆糊”的方式,把费尽心机搜罗的诸如风俗、传说、新词、段子、穿着、食谱等各个方面的材料加工打磨,成为小说,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拿人家第一手材料“洗稿”的方式,实在是洗出了新境界。果戈理的真实人生,只能用“乏味而沉闷”来形容,甚至自私、“龌龊”(他本人的自我评价)。但他打磨作品的专注与虔诚,却绝对是艺术大师的级别,那些材料落到他手上,才是一点也不会浪费的。

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年3月25日)
《好人难寻》
在常人眼里,果戈理已经是够古怪的,但来自美国南部的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古怪这一点上,绝对不遑多让,甚至还被冠以邪恶、怪诞、暴力的头衔。然而,同果戈理一样,奥康纳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几乎每部作品都有着宗教的诉求。她说:“我是站在基督教正统教派的立场上看世界的。这意味着,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集中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世间万物在我的眼里无不与此有关。”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我们这个堕落的尘世,正如哈姆雷特所说,“要是照每一个人应得的名分对待他,那么谁逃得了一顿鞭子呢”?所以哈罗德·布鲁姆精辟地指出,拥挤在奥康纳那些令人惊叹的故事中的人物,都是被罚入地狱的人。这位自海明威以来美国作家中最富原创性的讲故事者,把她那些(在我们这些准下地狱者看来)怪异的“宗教判词”谱写成了芸芸众生的诗歌。

左拉(1840年4月12日)
《娜娜》
自然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也曾显赫一时,诞生了左拉和莫泊桑这一对“难兄难弟”。对比后来居上的契诃夫,莫泊桑永远停留在了大众小说家的位置上,他的可读性仿佛成了过于简单的客套褒奖。当左拉“拉大旗作虎皮”地称福楼拜为自然主义的典范,把《包法利夫人》作为了“文学的不可动摇的楷模”,他所挖的这个坑,就是他用二十年写出二十部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也填不平的了。福楼拜的写作是注重文学技艺的严谨,而左拉的写作是注重直面社会的勇气,所以他的小说充斥实录性的详尽细节,随处都有“盯着女性裸体的窥视者的目光”,到处是“坦率得近乎放肆、甚至是粗俗不堪的语言”,“对性生活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描写”。读者因此获得了放荡生活的感性直观,至于是否会像正义的左拉一样义愤填膺,天知道。

亨利·詹姆斯(1843年4月15日)
《一位女士的画像》
亨利·詹姆斯在西方的地位,远远比中国读者想象的高得多。在一些文学界的后来者看来,他是英语小说艺术的大师,“善于创造模棱两可的情节,使读者费脑筋,但因此也可被永无休止地读下去”(博尔赫斯语)。他的作品,写出来就是为了要让人慢慢回味、细细分析的。但对于通过译文阅读外国文学的人口来说,詹姆斯那所谓“晦涩的词句,堆砌的比喻,雕琢的对话,含混的意义”,就成了我们拒绝受译者虐待的理由。再加上我们拥有了菲茨杰拉德、乔伊斯之后,亨利·詹姆斯就成了老派绅士读者的品牌了。

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说到米兰·昆德拉,就无法不想起那个笑话:有个捷克人,申请移民签证,官员问:“你打算到哪里去?”“哪儿都行。”官员给了他一个地球仪:“自己挑吧!”他看了看,慢慢转了转,对官员道:“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这位东欧的流浪“思想者”,和拉美“讲故事的人”马尔克斯一起,成为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两个作家代表。无论如何,马尔克斯是会讲故事的,所以《百年孤独》即便谁是谁爸爸傻傻分不清,但叙述的故事细节极见精彩,没头没脑的,反而耐读得很。昆德拉写小说显然只想到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不太考虑大众的口味,因为大众不喜欢思考,大众喜欢故事。写小说太用头脑不是件讨巧的事,尤其是思考,过多的思考,使小说变得越来越不好玩。

萨缪尔·贝克特(1906年4月13日)
《等待戈多》
贝克特年轻时曾给詹姆斯·乔伊斯做过助手,还专门研究过普鲁斯特的小说。两位英法文学的旷世天才,哺育出了荒诞派戏剧首屈一指的巨匠。贝克特既有乔伊斯冷峻背后的洞若观火,又蕴含着普鲁斯特的似水诗情。《等待戈多》就像一部禅宗公案,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的对话,如同参禅一样。贝克特让这两个流浪汉以重复说空话的方式,把人生的空话(Words, words, words!)统统浓缩到里头。读过这部剧的人,也许会因此沉下心想一想,在自己说过的那么多“喧哗与骚动”的空话里,到底有几句是有意思的。但贝克特是善良的,他深厚的同情心和无尽的慈爱,使得他把我们的空话写成了“翅膀的声音”,“羽毛一样的声音”,在《等待戈多》里写成了诗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