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许宏评《第五次开始》︱想象考古学家发现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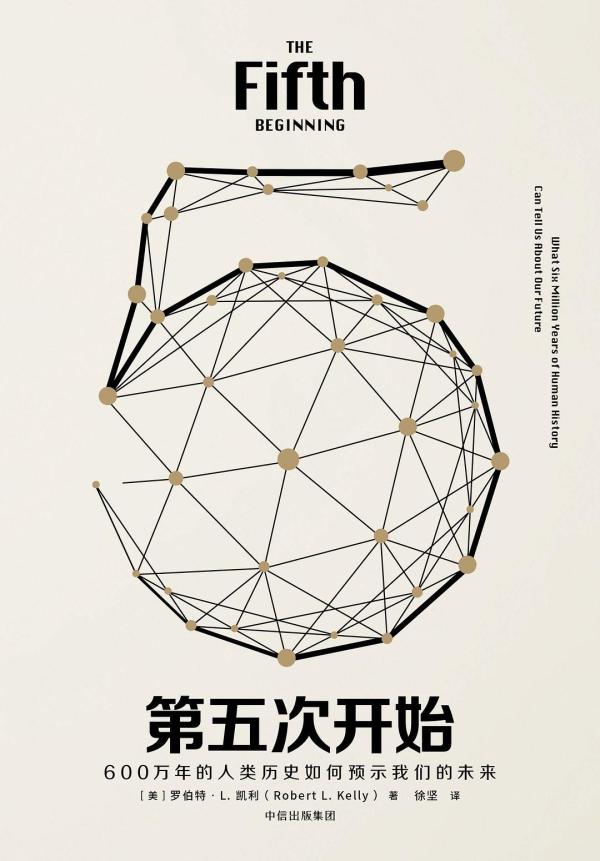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时代,把学者都变成了高速旋转的陀螺,让他们在庸忙中沉静不下来。本人也未能免俗,近年来很少能把一本书一气呵成地读下来。但罗伯特•L•凯利教授的这本《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是个例外。
作为凯利教授的同行,我也常常苦恼于回答诸如为什么要考古这类问题。尽管我和我的同行内心里常常会想这实在是个傻问题,但你总得有个人家能接受的说法。“没有历史,就没有根,而没有根,就没有未来”之类的说教,如何落地,的确是个问题。
在女儿面前,我就很受挫。她知道她有个考古人爸爸,也引以为豪,但就是对考古无感,她应该没有读过我面向大众、还有一定市场的考古小书。这也许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想法:考古学家一般只勾勒过去尤其是远古的图景,讲过去的事儿,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在本书中,凯利教授却没有止步于过往,他从考古人独特的超宏观视角引你继续看当下、看未来,试图回答“史前史如何指示未来方向”的问题,回答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他告诉你世间万物,从无永恒,我们正置身于人类发展的第五次开始,而一切都源自第一次开始——我们的祖先打出第一块石器那一刻。在这部极简人类史中,作者举重若轻地道出了六百万年以来人类行为的关联性,最终提出人类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他的文笔轻松诙谐,但立意高远,思考令人荡气回肠。
是的,考古学本来不该是枯燥的。凯利教授自视为“泥土考古学家”,四十多年来奔波于田野考古第一线,他有太多赋予“临场感”的细节故事可以呈现给读者。他指出,恰恰是这种“临场感”将我们和过去在个人层面上联系在一起,“当事物以对作为个人的我们而言有意义的方式呈现时,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它们。没人有兴趣阅读关于婚姻不忠的统计研究的社会学期刊论文,但是政客绯闻总能登上头条”(29页)。显然,凯利教授熟谙读者心理,希望写一本短小、愉悦、轻松的,“大家真的会阅读的书”。他做到了。
一口气读完后,我决定向正读大学、据说对社会学有感的女儿隆重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把远古和当下乃至未来串联起来了,而凯利教授的确是个讲故事的高手。
与作者优美的文笔和译者信达雅的译文相比,转述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笔者还是尽可能地引用本书中文版的原文,剧透其中的精妙表述,引导读者诸君走进这本书展示的多彩的世界。
在大的史观上,凯利教授同意著名经济学家的论断:世界万物皆不可能永恒,而是变动不居。“对古代世界的惊鸿一瞥也能告诉我们,古今大不一样。一万五千年前,全世界无人不是狩猎—采集者;今天,狩猎—采集者几乎荡然无存。甚至连农民也所剩不多,事实上,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才直接投身于食物生产……对人类过去变化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未来和现在将大不一样”(5页)。
他指出,“进化并无更远大的目标”,“今天人人——从荷兰奶农到硅谷计算机科学家——都是竭力成为最佳狩猎—采集者的祖先的后代。为了成为一物,细胞组织触及临界点,结果变成完全不同的物种”(5-6页)。道理浅显明白,人类在异化于自然界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一认知框架下,作者指出在过去的六百万年中,人类经历了四个这样的临界点,他称之为“开始(beginning)”。按照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技术、文化、农业和被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的开始。最终,他按照考古学家确认这些开始的方法——对物质遗存的观察,得出了我们正面临另一个临界点——第五次开始的重要结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基于合作的竞争的时代、一个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的开始。
他在书中勾画出了一幅宏阔的适者生存、竞争有力的图景。“人口增殖带来的竞争加剧是最主要的驱动力”,结果是,“使用石器的更新世祖先战胜了不用者;拥有文化能力的战胜了缺失者;农夫最终超过了狩猎—采集者;酋邦和部落臣服于国家社会,后者迄今仍然主导社会”。作者指出,在适者生存、竞争有力之外,“利他主义和合作也是进化过程的基本因素”(6-7页)。他乐观地总结道:“史前史告诉我们,人类擅长解决问题,进化常常重塑我们。”(20页)
对这一过程,作者娓娓道来。
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技术的开始。“从历史长河的鸟瞰位置上,我们看到,1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栖居树上、以果叶为食、不知制作工具的灵长类摇身一变:直立行走、居于地面、使用工具、极有可能狩猎、可能烹食、可能形成对偶制度。在努力成为最好的树居灵长动物的道路上,进化把我们变成完全不同的种属。”(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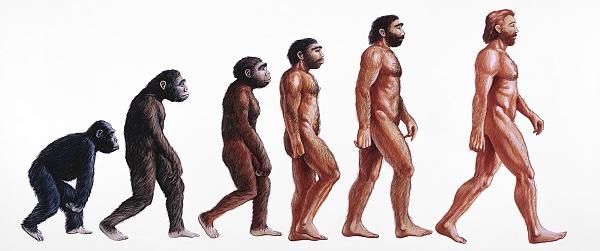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作者指出,人类可能更早就已经具备了栽培作物的能力,但只有到更新世末期,地球在气候和环境上“才调整到位:狩猎—采集者充斥世界,再也无法通过迁徙解决食物问题了”(135页)。“在某些地区,气候变迁和偶然的植物基因变异导致农业成为可能的选项,而狩猎—采集者把握了时代契机。在地质时间上不过是短短一瞬,狩猎—采集者就成为农民,创建出定居村落。人口继续增长,生存空间的竞争加剧”(152页)。而“所有一切——定居社会、农业和竞争性盛宴——基本上都是人口和食物之间失衡关系的产物”(146页)。
接下来,“从你在历史长河中的鸟瞰位置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万至五千年前撒播在世界各地,众多渺小、沉闷的农业社会,被拥有庞大公共建筑的大都会所替代”(158-159页)。与农业时代的早期宗教建筑包容和志在联合的特征相比,“国家的宗教和政治建筑则显得更加排外、志在控制,以及沟通信众和非信众”(163页)。这类建筑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法老时代的埃及金字塔。“宏大的公共项目出现在增产努力奏效、农业蓬勃发展之地”。而“产量增加不仅支持人口不断增长,也将部分人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继以世界上第一座城市——乌鲁克著称的乌鲁克国家诞生于公元前4000年的两河流域之后,早期国家风起云涌。“最终,城市成为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功能的枢纽”(164页)。而“所有这些物质文化——计数系统、书写、科学和艺术——就是很多人所称的‘文明’。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这并不是始终都令人愉悦的”(174页)。
他一语道破了国家的本质:“对于国家而言,超越以亲属关系为治国之本的转变至关重要。这个转变推动了两项重要的变化: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和有组织的战争”,而这两项重要的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是没有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180页)。“从考古学家的角度看,故事主线并没有变化:这是一场长达5000年的权力与控制的竞争。”(182页)而作者关于战争“是精心计算的冒险”、“肮脏的交易”(184页)的论断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他是冷峻而富有情感的:“国家的起源启动了邪恶的文化周期……结果导致大地上一轮又一轮的破坏浪潮。坐在历史长河的鸟瞰位置上的你,都忍不住闭上双眼。”(191页)
好啦,如果你说上面这些是考古学家不足为奇的看家本领,那么大家最感兴趣的,应该是看一位考古学家如何看现在、谈未来,这也是凯利教授这本书最令我着迷的部分。
他总结到,“过去的开始都伴随着我们对地球的显著改造,比如,石器、洞穴艺术、栽培作物和庙宇群。因此,让我们设想,一万年以后的考古学家如何看待今天;让我们以对待史前史的方式对待今天”。他提示我们用考古学家“寻找物质记录上的变迁”的方式,就会注意到人类物质记录的几处新迹象:
数以万计的沉船都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飞行器的年代不早于二十世纪晚期;可以在太空发现绕地飞行器残骸,在月球、火星甚至在彗星上发现人类遗物。此外,考古学家还会发现全球战争的证据;公元1500年之后的证据还指向跨大陆的商品流动。检查公元1500年后的墓葬遗存时,一度整齐的人类基因的地理分布(譬如肤色的分布)已经瓦解,这是人类迁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证据。人类骨骼中的同位素成分告诉我们,公元1500年之后同样存在着人类分布上地理分区的崩塌。此前,人人都吃本地食物,但自从有了进口食物,很多人日常摄入来自全球各地的产品。
未来的考古学家可以看到人类足迹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显著增加。他们可能断言,2007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而非农村。当今最为显著的物质特征之一是地球上的二十八个超级城市,每个都容纳了超过一千万的人口。世界最高建筑在这些城市里不断被拔高。十九世纪之前,世界人口每一千七百年翻一番;1850年之后,不到五十年就翻了一番。
水电站、太阳能电池阵、风力涡轮和发电厂遗迹,巨型露天矿坑、被削平的山峰;垃圾山、垃圾岛、巨型垃圾填埋场;海洋中的高密度塑料微粒;树木年轮等记录的大气中二氧化碳达到八十万年以来的峰值,珊瑚记录的海洋酸度的提升……在此前人类长达六百万年的历史中,还从未有人类活动引起环境变迁的证据。这一切都告诉未来的考古学家,被学者们称为“人类世”甚至“大灾难世”的时代显然已来临了。还有就是物质文化加速度变化的事实:狩猎-采集时代五百年间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公元1500年和今天的差异呢,甚至,二十世纪初期和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差异,请想一下。
考古学家从独特的视角观察到的地球上人类遗存的这些变化,不是足以振聋发聩吗?这才有了作者关于第五次开始的推论: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是继技术、文化、农业和国家开始之后的另一个伟大转型的时代,一个全新的开始”(222页)。
第五次开始将带来什么?凯利教授也有自己的思考:“毫无疑问,技术将融入我们未来的生活,但是,作为考古学家,我更关心人类组织,关心人们如何相处上的变迁。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新技术,而是组织我们自己的新方式”(225页)。他指出,在过去四次开始中,人类都创造了合作新阶段:对偶制、分享、联盟和贸易。而这次开始也没有区别。“资本主义、战争和文化全球化呼吁全新阶段的合作”(241页)。作者对新的合作抱持乐观态度:全球化虽然带来文化冲突,但是二十世纪也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合作,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和无国界组织层出不穷。文化上超越本土、跨国的新一代正在崛起。“这是走向世界公民的文化变迁的证据”(248页)。
凯利教授认为,两项要义使第五次开始不同于此前各次:第一是人类现在已经拥有了改造世界的能力;第二是我们有自我教育的历史。而唯一开放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利用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干预进化进程,掌控自己的未来,以简易模式还是困难模式开启第五次开始。最后的结论是,人类进化一直是,而且应该是,甚至必须是由我们自己掌控的。
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这才应该是对人类史做过全景扫描的考古学家说的话,但坦率地讲,还真就罕见考古学家有如此的人文关怀、如此宽阔的胸襟,能站到如此高度来鸟瞰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当读到作者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局势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作为凯利教授的同行,我是自惭形秽的。我的一位哲学家朋友说,考古学是一门本原性的学科,它能给其他众多的学科提供灵感和给养。在凯利教授身上,优秀考古学家的这种潜质和学养彰显无遗。
与此同时,凯利教授有着学者特有的理性和审慎。他坦承考古学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时光机,考古学家无法判断自己是否正确。我们不断完善方法,但是必须承认,任何时候,我们说,‘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实际意味着,‘这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确信发生的事情。’”(26页)同时又乐观地预见考古学满足好奇心的能力只会越来越好。在这一点上,我与凯利教授颇有同感,很大程度是因为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然后,作者又冷静地提示到,考古学家永远没法如我们所愿,复原出过去的详尽场景。而与此同时,“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想象他者的世界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214页)。显然,这种想象并非无据的幻想。
他深谙考古学的特点:“我们的故事依赖于物质,更精确地说,我们依赖跨越时空的物质的模式”(36页),“令物质遗存复活就是考古学的意义所在——从过去的静态遗存走向制造它们的动态行为”(37页)。尽管书中不乏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如关于5100年前奥茨冰人的栩栩如生的描述,但作者坦言他更“关注宏观格局,因为我认为这才是考古学的最大的贡献”(《前言》),“没有其他学科能以考古学的尺度观察人类。在纵横数万里,上下百万年的范围,我们‘看到’人类行为”。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是,“考古学家不一定始终能看见树木,但可以极其清晰地捕捉到森林”(36页)。“我们通过整理细节,尝试发现浩瀚森林的模式”(38页)。人类的五次开始,正是凯利教授敏锐地捕捉到的人类史“浩瀚森林的模式”。
回想起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庸忙,是否也是凯利教授所说的“第五次开始”的一个标志?我们何尝不是都被这个大的潮流向前拥着走,甚至在其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读读这本小书,多一点自觉、多一点自省,不亦清醒乎,不亦有益乎?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