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最好的歌手都巡演,所以这个北京最酷的理发师去巡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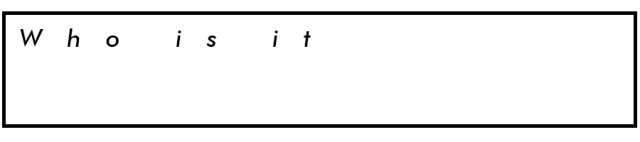

大聪,40岁,发型师,蕪衎发型设计所创办人,国内最早期的嘻哈、电音爱好者。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聪。他头上带着彩色的发带,正在客厅角落的碟机上搓碟。进门的第一时间,我就被碟机旁的一个木架震惊了,上面杂乱地摞着大概有上千张黑胶。大聪对房间的杂乱向我们表示抱歉,招呼我们随便找地方坐。
比起正常的理发店,这里更像个人工作室,唱片、书籍、老式录音机、球鞋、干花、挂旗,各种私人物件散落摆放,墙被漆成暗绿色,只有窗边摆着的转椅、立镜,角落的工具架,才能看出这里有个剪头发的样子。

原来理发师还能有这样的,见到大聪的这一面,彻底地颠覆了我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
从第一次接触大聪到Figure成片上线,总共经过了四个月的时间。这四个月里的许多次的拍摄,让我们逐渐变得熟络。大聪耿直、较真儿、说话着急的时候有点语无伦次,喝醉的时候像个孩子。大聪说自己不是个浪漫的人,但是开蕪衎是他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了。
他认为的浪漫跟别人都不一样,背着抵押房子的贷款,却依旧不遵循商业规则,大聪想的是,把蕪衎做成一个乌托邦,赚钱不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儿。
拍片的几个月里,我经常和周围的朋友谈起大聪的片子,结果发现不少人都记得当年北新桥地铁口,曾经有一家很酷的理发店,剪出的发型特别时髦,经常开一些有趣的小派对,「往来无白丁」。这家店就是大聪的蕪衎。
从蕪衎开业那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年的时间。曾经那个理发店已经变成了一家日本餐厅店,大聪也已进入不惑之年,那个地址和他唯一的关系也只是他还在还蕪衎没还清的贷款。

「先做事,再挣钱」,做一个 「影响社会」的人,这是大聪的坚持。
老蕪衎的关张、近些年来的潦倒,丝毫没有动摇过他的坚持,他说自己只能在这儿做这个事,只能这么去做这个事。
我不知道眼前这个人会走到哪一步,能不能像他说的那样一直坚持下去,只是觉得,每次看到还有这样的人,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总想为他鼓掌,衷心地祝他好运。
自述 | 大聪
小学五六年级,开始给同学剪头发
我叫大聪,英文名是Daczong,这个英文名是在美国的表弟给我起的,我是剪头发的。
大概2000年左右国内剪头发的环境里,好像每个发型师都得起个英文名,我不想叫Tony或者Jack,我大名叫周思聪,就用英文拼了个Daczong,老外也能叫出来。
我们家最早是清华的,后来小学三年级左右搬去了东四,在那边长大。有一句话说,北京人都逛隆福寺,外地来旅游的人都逛王府井。八九十年代东四、隆福寺是个挺潮的地儿,一帮人就拉着三轮车卖王朔写的那些东西,南方来的蛤蟆镜、牛仔裤、电子表、磁带什么的。

九零年左右五道口那边儿开始有卖打口磁带、打口CD、没打过口的原盘,再往后就有唱片了。那时候在中国朋克特时髦,比摇滚乐更新一点,hip-hop其实在美国也挺火的,打口带里也进来了一些,我就淘这些,觉得黑人音乐特有意思。
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接触到了美国的hip-hop录像带,里边的那些人他们头发两边都搓特高、倍儿秃,然后上面长,我就特想剪一个这个头发,结果外面发廊剪不出来,然后没辙了,我回来自己拿推子给自己推了。学校班里有一些同学说这有意思,你给我剪吧,我就给他们剪。然后初中没毕业我琢磨着自己喜欢这个,就去学了剪头发。
毕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有热爱的,但干起来就觉得不是原来喜欢那样。这行业其实在九十年代左右已经变成商业了,比如说你来了剪一头发,我不能让你剪一个就走,因为才五块钱、十块钱,我得让你烫一个、染一个、焗一个。就变成这个行业里更重要是要劝别人花更多的钱,但是我更想先把头发剪好了,需要烫再烫,需要染再染。

然后有一个事特别重要,我有一天遇到了一个以前的同学,他说他特别喜欢剪头,他看一帮人剪头发剪得特好,他在学,我说那你带我进去看看,我也想学学,他说我就站门口看。那帮人当时挺有名的,在一个橱窗里剪,你在外头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其实可以站在外面看。当时大雪天,他看人剪头发,给我特别大一个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干,实在挣不着钱我可以长本事啊。
然后就开始学了。学校是教给你一个技能,说难听点你出去像一个剪头发的了,但真正的东西我是从社会上学来的。
我出去打工从来没能超过三个月
等于我从17岁毕业实习,一直到26、27岁,我都没正经在发廊干过,都是在认识这些行业里的牛人,跟他们一块玩,然后看他们剪头发。偶尔实在吃不上饭了,就去外面打一段工,但从来没有能够超过三个月。
当时美发行业是早十点到晚十点,一个礼拜休息一天,而且当时都是拿提成,如果你这么干的话提成特多,整个行业就都这样。但是我实在受不了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年轻,我有喜欢玩的东西,所以最终就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觉得这种「不务正业」可能导致了我后来还算对这行业保持了一种热情。不是睁眼就是剪头发,闭眼就是睡觉早上起来继续剪,然后休息一天就是洗衣服、收拾,完了就赶紧继续干。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应该有生活。

有一次我忘了是哪一年了,我突然被身边的朋友叫走,在东单地下的一个停车场,一群人在那儿放那种不是夜店的电子音乐,在那儿跳舞。当时我以为电子音乐就是迪厅那种音乐,特别烦,全是流行歌,但是后来我发现怎么都是特别机械那种声儿。应该是九几年,比长城派对(2005年北京著名的一场锐舞派对)早几年,我觉得那是前身的YEN(焱,派对品牌),反正挺有意思的。2000年左右北京有一系列好玩的派对,YEN那时候特火。
近多少年我好像没那么大兴趣了,以前好玩主要是因为人好玩,现在人人都去派对,但真正有意思的人不多,可能大家都是为了从派对找点意思去的。
我就想开一个不放凤凰传奇也不鞠躬的店
开蕪衎那一年是2012年,我34岁。在那之前,或者说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赚到过钱。剪头发在九十年代就能挣一万多,后来就好几万,有的干几年就能买房买车。开店前几年我也去过几家挺高档的理发店,有法国人开的,有日本人开的,干了一段时间发现其实大家都是按一个套路在运营。我也去过东田,我觉得东田挺适合我的,结果人家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圈里的各种长辈老师们也都说大聪剪头可以,我也觉得自己技能、审美方面比很多人都强,我觉得我有一身本领,但是没地儿用。后来我就去胡同里、小区里的理发店,全是给大爷剪头的那种地儿,结果我去那儿干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也干不了,因为那儿全是劝老年人办卡。
我觉得我挺较真的,我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是哪有问题,我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到哪都干不下去。所以我想开个店证明一下,我豁出去了。当时父母给我太大的支持了,我把房子贷了三十万,后面又往里填了好多钱,就开了蕪衎。

蕪衎不办卡,也没有装修,就是一些最基本的水泥地啊什么的。我这是剪头发,没有必要把它弄成一个宫殿,一进来好多人给你鞠躬那种。我把我的兴趣爱好放在这个发廊里,我收集的唱片、我的打碟机,还有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的派对文化。我没有按照这个行业里商业的路子去走,音乐和剪头发都被我放在了这里面。我希望它是一个能让我踏踏实实开开心心剪头发的地方,然后一个礼拜你能让我休息一两天,剪头的时候别天天被凤凰传奇、小苹果一遍遍地轰炸。那些东西真的让我觉得特别痛苦。
曾经有一些有意思的人,后来都没了
其实2012年那年开蕪衎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头充满了好多幻想,我觉得当时社会在变,中国好像终于开始要所谓全民追求文艺复兴了,我们要追求文化艺术这些东西了,我们不是表面上吃得好穿得暖、有房有车有媳妇就好了。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好的事情,所以我抱着那个理想干了个事,而且我觉得确实当时来了一些有意思的人,有一些真诚的人,但是后来都没了,真不知道跑哪去了。
开店的时候我没有宣传,但是来了好多各界有意思的人,一开始老外特多,后来中国人也越来越多,有做建筑设计的、有玩音乐的、有留学回来的,嬉皮的人占了大多数,也有一些稍微知名一点的,比如何勇、罗琦、Nova Heart的主唱冯海伦什么的。还有好几家杂志都给我做过采访。

当时我那的派对也办得挺热闹的,隔三差五就有一些活动,变装派对、复古舞会什么的。我那地儿也没多大,最多的时候能来百十来号人。玩得最疯的时候比如噪音派对,就是现在还挺有名的一帮玩噪音的老外。我那地儿是两边门都开着,对着地铁口,那噪音,大音响都给放纰了,全纰了。那哥们自己在那玩得特开心,放着放着自己在那跑圈,从屋里跑到外头,转到地铁口,然后再回来接着弄,真的是撒欢了。
蕪衎开了三年,我当时的初衷是证明自己,也能给这个社会一些影响,最终我觉得我做到了。有些该被影响的人是被影响了,他们可能去干他们觉得认为对的事了,我觉得这就对了,这已经够了。
我现在四十岁,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就想有什么事能让我活得开心,或者说高于生死
老蕪衎关门之后,我自己撤回到了一个居民楼里,不要那个特酷的形式了,一个人在居民楼里给别人剪头发。还有一部分老客人持续地在来,但是也在慢慢减少。好像追求生活品质的人越来越少在北京呆着了,这个地方假的东西看起来比真的还真。
我当然是想把蕪衎一直做下去,做得越长久越好,能真正地影响一下。后来关门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能跟我一起做事的人。可能我这事儿让人觉得不是长久之计,觉得我干这事没用,你为什么想影响环境,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影响环境。但是我想只要你这个人在做着一件跟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事,你自然就在影响环境。
他们想的可能还是赶紧赚钱,赶紧走人。其实我也想挣钱,但是能不能边挣钱边有点社会责任感,能不能先把事情做好了,然后自然而然挣到钱。而不是说咣叽一下这个事火了,暴发户了,那样其实是在毁,毁各种行业,最后导致这种土壤长不出花来,只能长出那种吞噬花草的东西。

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能一边流浪一边剪头发活着,我原来去澳洲旅行什么的也在国外给人剪过头发。所以我现在下一步想去看看别的城市,个把月就回来。中国也在变,可能别的城市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人。反正老天爷饿不死巧家雀,反正人人都得剪头。
我也想过,如果有一天我真有钱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做一个工作室,让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让真正有追求的人呆在北京,形成一个影响力让这个市场变得更专业更纯粹一点。剩下的东西对我没有意义,我父母对我也没有太大要求。
我现在四十岁,我十六七岁那个时候,就觉得人肯定有怕死的阶段,有什么事能让我活得开心、不怕死,或者说高于生死。可能就是我为了某些事真正去付出了,然后不管有没有回报。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