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战震慑了这名20岁男孩的心灵,他日后写出了纳尼亚传奇
编者按:C.S.路易斯(1898-1963),20世纪英国重要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基督教护教家。路易斯被誉为“最伟大的牛津人”。代表作有《纳尼亚传奇》《返璞归真》《四种爱》《痛苦的奥秘》《牛津英国文学史•16世纪卷》等。《纳尼亚传奇》在20世纪儿童文学中稳居经典地位。这本关于C.S.路易斯的传记以时间为主线,以生动的笔触记叙了路易斯的生平,并以广泛的研究为基础,对路易斯本人的成长道路与思想发展给予了特别关注。
一战夺去了人们的生命,摧毁了人们的梦想,迫使许多人为祖国舍弃了自己的未来。路易斯就是个典型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士兵——一个年轻人心系文学,充满学术理想,却发现自己的人生被外力扭转了方向,最终自己却无力抵抗。
——麦格拉思《C.S.路易斯》

C.S.路易斯(1898-1963)
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说得妙,了解一个人的最佳方法是找出此人二十岁时世界发生了什么。1918年11月29日——路易斯二十岁生日——几周之前,一战终于结束。许多人幸存了下来,却深感愧疚,因为他们的同伴在战争中倒下了。参加过堑壕战的士兵亲历暴力、毁灭和恐怖,永远背负上了这些印记。路易斯在生命里的第二十个年头,亲身经历了武装冲突,深受影响。他在十九岁生日的时候来到位于法国西北部靠近阿拉斯的战壕,到了二十岁时仍未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如果拿破仑的话是对的,那么路易斯的思想和经验世界都会深受战争、创伤及损失的影响,一切无可挽回也不可逆转。我们也许有理由认定,路易斯在战场上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的精神世界必然深受这段经历的掌控。 路易斯却矢口否认。他告诉我们,他的战时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关紧要的”。比起在法国战壕里的岁月,他似乎认为在英国寄宿学校的经历才更让人不愉快。
路易斯在1917~1918年间参加了法国的战事,亲历了现代战争的惨状,但是《惊悦》对此却着墨甚少。路易斯显然认为,他在莫尔文中学的经历远比整个战时遭遇重要得多。而且,即使谈及战争,他似乎也更乐意把叙事聚焦在他当时读过的书、遇到的人。周遭世界充斥着不可言说的痛苦和惨状,但都被滤掉了。按路易斯的说法,其他人已经描述得足够多,他没什么可再添补的了。他后来虽然著述颇丰,却很少提及这场战争。
有些读者会感觉到失衡。为什么路易斯在《惊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详述他在莫尔文中学时那相对轻微的痛苦,却不大关注一战中更为深重的暴力、创伤和惨状?通读路易斯的作品之后,这种不均衡感更加明显,因为一战几乎被忽略不计——即使被提及,也仿佛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路易斯似乎在试着与他的战时记忆保持距离,或是抽身而出。这是为什么?
最简单的解释也是最可靠的: 路易斯无法承受战时记忆的创伤,因为这些经历缺乏理性,引发了他对宇宙整体意义以及自身个体存在意义的怀疑。关于一战及其后果的文学作品都强调,这场战争给当时士兵的身心都带来了伤害,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士兵们返乡之后。许多学生从战场返回牛津大学之后难以适应正常的生活,时常出现精神崩溃。路易斯为了保持心智健全,似乎把生活“分割”或“隔间”了。他的那些创伤性回忆本来都极具摧毁力,但因他谨慎控制,对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便也降到了最低。文学——尤其是诗歌——是路易斯的防火墙,把混乱、无意义的外在世界拦截在安全的距离之外。因此,其他人遭受毁灭性打击之时,他却能幸免。
《惊悦》中刻画了上述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路易斯尽力在让自己远离战争的景象。他对未来可能发生残酷战争的看法,似乎也映射出他日后对待历史的态度。
我把战争放在一旁。有些人会觉得这很可耻,有些人会觉得这令人生疑,还有一些人会称之为逃离现实。我坚持认为这是与现实立约定界。
路易斯做好了心理准备,要将自己的身躯奉献给祖国——但并不献出自己的灵魂。他的内心已划定疆界,布置了巡逻哨岗,严禁某些扰人的思想越界。路易斯不会逃离现实。相反,他与现实签订了“条约”,去驯服、改写、限定现实。“边界”之内,有些思想是不允许渗入的。
这种“与现实立约”的方式在路易斯的成长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往后的章节中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路易斯脑中勾勒出的现实,与一战的创伤实难相容。爱德华时代的许多人都遵循一套既定的方式看待世界。和这些人一样,路易斯发现这种方式已经被至今最为残酷的毁灭性战争给摧毁了。路易斯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总是在寻觅某种意义——不仅是寻求自我实现和稳定感,也在试图理解内在和外在世界,好让自己焦躁不安、寻根究底的头脑得到满足。
若要了解路易斯对一战的态度,首先要看看他是怎样被卷进战争的。1917年初,路易斯在大布克汉姆努力学习数学(结果不是很理想)。路易斯4月29日进入牛津的大学学院学习。历史上,查理一世曾于1643年在牛津城内设立军事总部。自英国内战之后,牛津再度成为军营。牛津的大学公园变成了新兵训练地和阅兵场。许多年轻的教师和校工都上了战场。即便开课,听讲者也寥寥无几。以前,《牛津大学公报》是用来发布讲座和大学任命通知的,现在上面却是长串的阵亡名单,让人沮丧万分。黑框名单不祥地诉说着战争大屠杀的场面。
到了1917年,牛津实际上已经没有学生了,各学院必须寻找对策,应对收入剧减。大学学院通常是熙熙攘攘的,如今住宿生也所剩不多。41914年,学院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有一百四十八名住宿生,而到1917年则人数剧减,只剩下七名。在一张摄于1917年三一学期的罕见合影上,整个学院只有十人。根据1915年5月施行的紧急法令,大学学院的九名指导教师中有七名被解除了职务,因为他们实在无事可做。
大学学院面临学生数量骤减的问题,急需资助。它的内部收入从1913年的八千七百五十五英镑降至1918年的九百二十五英镑。和许多学院一样,大学学院转而依赖战时机关获取资金来源,出租学院的房间及设备,作为军队营房和军事医院之用。其他的学院则收容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难民,尤其是来自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难民。
这一时期,大学学院的许多地方都腾出来做军事医院。路易斯被安排在拉德克利夫方庭12号楼5号房间。他虽然住进了牛津的学院,却不能算是真正开始接受牛津的教育。这时的牛津几乎没有导师,大学里的讲座也极少。路易斯对学院的早年印象是“广袤的孤独”。1917年7月的某个晚上,他独自徘徊于静寂的楼梯,漫步在空荡的楼道里,惊讶于那“奇异的诗意”。
路易斯在1917年夏季住进了牛津,主要目的是加入牛津大学军官训练团。他在抵达牛津之前,已于4月25日递交了申请。五天之后,他的申请顺利通过,且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可能是因为他在莫尔文中学时即已在为高年级学生所设的军官联合部队里受训过。学院主任拒绝为路易斯安排任何学业指导,理由是军官训练团的训练会占用他全部的时间。不过,路易斯并不气馁。他私下已有了安排,即跟随赫特福德学院的约翰·爱德华·坎贝尔学习算数,对方拒绝收取任何指导费用。
通常来说,数学与研究古典世界的生活、思想并不相关,为什么路易斯突然希望掌握数学?一部分原因是路易斯想通过“初试”,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阿尔伯特认定儿子若能成为炮兵军官,他在战争中活下来的几率会更大。阿尔伯特的想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的堑壕战已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杀伤力极强,相比之下,在后方轰炸德军显然安全许多。但是,皇家炮兵队要求下级军官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尤其是三角学,而路易斯在这方面是一片空白。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永远也无法掌握这个领域的知识。他为此感到难过,沮丧地告诉父亲自己“成为炮兵的机会”很低,因为他们只招募那些“掌握了某些特定数学知识”的军人。
路易斯在大学学院时日不长,那段日子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跟格雷夫斯分享过自己的一些情感和经历,但跟父亲和兄长的交流却少之又少。他在信中跟格雷夫斯讲述游泳的快乐,“但又无需遵守游泳那些令人厌烦的规矩”,他又谈到牛津联合协会那气氛十足的图书馆。“我的生活从未这么快乐过”。他编造了另一些事情哄父亲,急切想要掩饰自己越发坚定的无神论信仰。他在给父亲的信中提到自己经常去做礼拜,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去。
路易斯自知,此时受训的目标就是参加堑壕战。他在军官训练团的日子将近尾声时,常写信给父亲,提到参加法国战事的预备训练,描述了战壕的模型,还提到了“防空洞、弹痕以及——坟墓”。时任牛津大学军官训练团副官的G.H.克莱珀尔中尉在评定路易斯的表现时写道,路易斯“有潜力成为一名能干的军官,但因训练不足,在6月底之前尚不能进入军官训练组。他被安排在步兵队。路易斯的命运已定。他会被派往步兵队——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去法国参加堑壕战了。
一战夺去了人们的生命,摧毁了人们的梦想,迫使许多人为祖国舍弃了自己的未来。路易斯就是个典型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士兵——一个年轻人心系文学,充满学术理想,却发现自己的人生被外力扭转了方向,最终自己却无力抵抗。大学学院共有七百七十名学生参加一战,阵亡人员达一百七十五名。1917年夏,虽然路易斯在大学学院度过的时间不长,他也能感觉到有多少大学生前往战场,一去不返。维尼弗雷德·玛丽·雷茨16于1916年创作了《牛津的塔尖》(The Spires of Oxford)一诗,忧郁的诗行捕捉到了许多人的命运:
我望见牛津的塔尖
当我正要经过的时候,
牛津的灰色塔尖
顶着珍珠灰的天穹;
我的心跟牛津人在一起
一道离开祖国,去了死亡之地。
……
路易斯很少提及堑壕战的恐怖,反倒证实了它的客观存在(“几乎被炸了个粉碎的士兵还像没了半条命的甲壳虫那样爬着,到处是尸体,坐着的、站着的,这片土地上连一片草叶的影子都没有”),也表明他主观上有意识地跟这段经历保持距离(它“极少出现在记忆里,模模糊糊地”,“跟我的其他经历断联了”)。这大概是路易斯“与现实立约”最为显著的特征了。他筑起一道防线,划出一条边界,保护自己不受那些骇人意象的困扰,不去想起那些“几乎被炸了个粉碎的士兵”,如此方得以继续生活,好像这些不过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可怕遭遇。路易斯织茧裹住自己,让思想远离那些正在腐烂的尸体和带来毁灭的技术。他不让这个世界逼近自己,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阅读,用他人的言语和思想来保护自己,远离周遭正在发生的事件。
路易斯亲历了这场技术最高端又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现场,但是这种体验被文学的棱镜过滤和弱化了。对路易斯而言,书籍既留存——感伤、夸张地说——已逝往昔的快乐,又好似膏油,能治愈当下的创伤与绝望。书籍连接了往昔与当下。几个月后,他在给亚瑟·格雷夫斯的信中写道,他渴望回到过去快乐的日子,那时他可以拥抱那“小小的书房,翻阅一本一本的书”。他不无忧伤地怀念那一切。但是,那些日子已逝去。
克莱蒙特·艾德礼是大学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后来荣任英国首相。他置身一战的炮弹硝烟中,却想象自己是在牛津穿行,好让自己的神经镇定下来。路易斯更喜欢的方式则是读书。不过,路易斯在法参战期间所做的不只是读书——虽然他如饥似渴地啃读。他还写诗。他的《被缚的精灵》是组诗,明显是在对亲历的战争做出回应,比如《法国夜曲(蒙希-勒-普勒)》。路易斯发现,除了读书,把情感汇聚成自己的语言也能应对周围的环境,让自己平静下来。最初因情感而生发思绪,但在遣词造句的过程中,头脑逐渐控制、驯服了情感。他也曾跟格雷夫斯如此建议,“无论你何时厌倦了生活,开始写作吧: 墨水是治愈人类所有恶疾的良药,这是我许久以前就发现了的。”
1918年2月,路易斯在英国红十字会第十医院度过了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医院地处勒特雷波尔,离法国海岸的迪耶普不远。同许多人一样,路易斯染上了“战壕热”。此病俗称P.O.U.(“发热病因不明”),通常认为是虱子传播病菌所致。路易斯写信回家,回忆起和母亲、兄长在迪耶普附近的贝尔讷瓦勒勒格朗度过的美好时光。那是1907年,度假的地点距离医院仅十八英里。那时,他在给格雷夫斯的信中常提到他正在阅读或是打算阅读的书——例如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的自传。他写道,如果众神对他是仁慈的,他的病也许会复发,可以在医院再住上一阵子。但是,他不无挖苦地说道,众神是恨他的。不过,他既然对他们心怀怨恨,又怎能怪他们恨他呢?一周过后,路易斯出院了。他所在的连队被调离战区,前往旺凯丹接受强化训练。他们在那里要练习“分区突袭”,备战正在酝酿的大突袭,然后在3月19日返回阿拉斯附近的方普前线。
……
4月14日傍晚六点半,萨默塞特轻装步兵队发动了对德军占领的小村庄里耶杜维纳日的突袭。英国的重型大炮在后方布下火力网,步兵队向前挺进。不过,火力网不敌德军的反击,前进中的步兵队难挡机关枪的猛烈扫射。劳伦斯·约翰逊少尉也在突袭战中受伤,第二天早晨身亡。约翰逊是牛津大学女王学院的一名学者,于1917年4月17日入伍。路易斯在军中的朋友寥寥无几,约翰逊是其中一位。
不过,路易斯随所在的连队安全抵达了里耶杜维纳日。“我‘拿下了’约六十名囚犯——这群身着野战服的家伙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但都举着手,让我松了一口气。”到了晚上七点十五分,战役结束。萨默塞特轻装步兵队攻下了里耶杜维纳日。
德军立刻发动了反攻,先是炮轰村庄,后是步兵队突袭,均遭到英军回击。德军发射的一枚炮弹在路易斯旁边爆炸。路易斯仅是受伤而已,但当时站在他身边的哈里·艾尔斯中士却不幸身亡。路易斯被送往埃塔普勒附近的英国红十字会第六医院。阿尔伯特很快收到一封信,得知儿子“受了轻伤”。这封信据说是某位护士写的。英国战时机关也随即发出了类似电报:“萨默塞特轻装步兵队的C.S.路易斯少尉在4月15日受伤。”
……
事实上,路易斯当时被弹片击中,伤势也算严重,也够条件被送回英国。但这伤毕竟不危及生命——当时军队里的人称此为“需遣送回国治疗的伤”(Blighty wound)。跟别人相比,路易斯受的算是轻伤。
本文节选自《C.S.路易斯》,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5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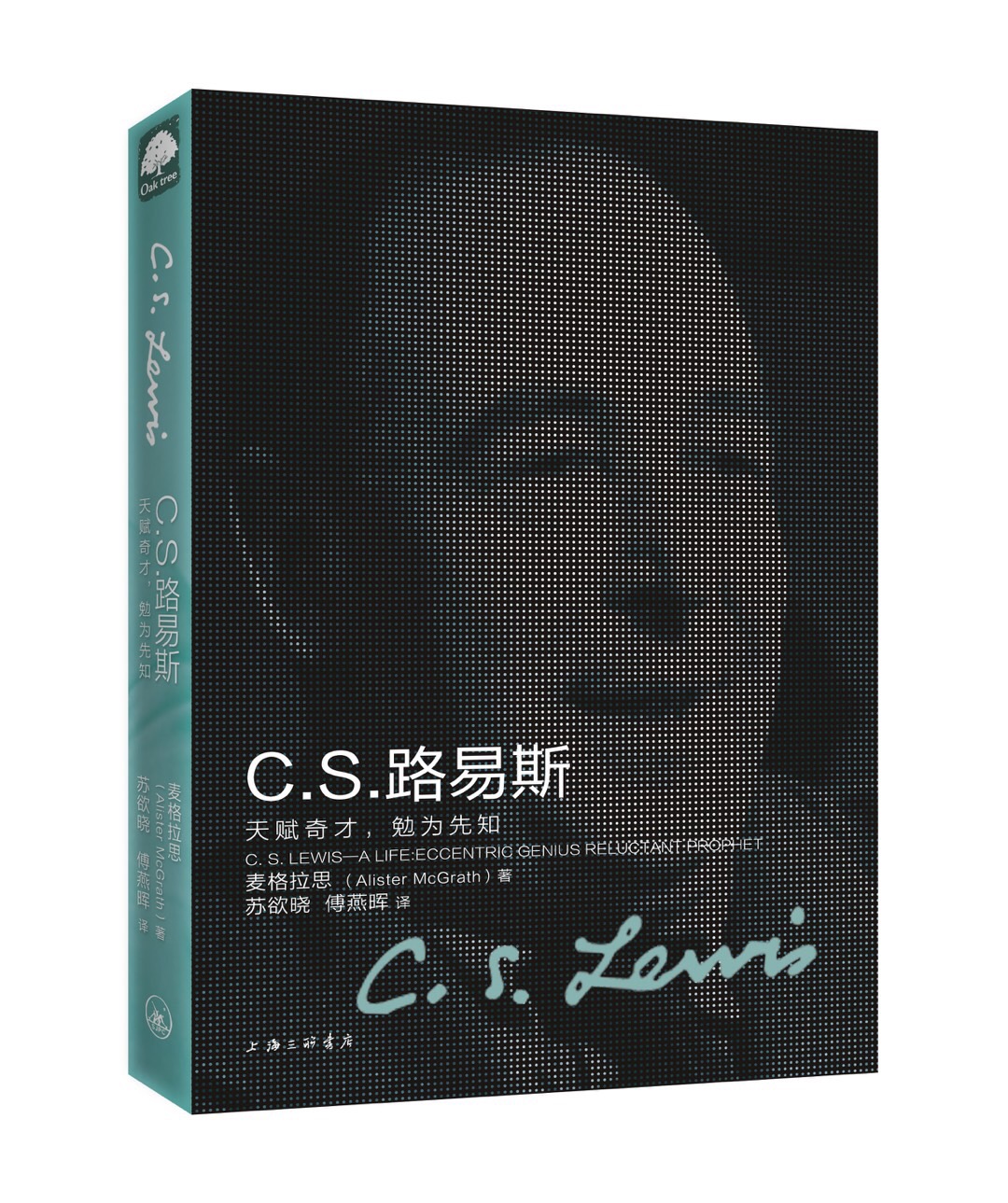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