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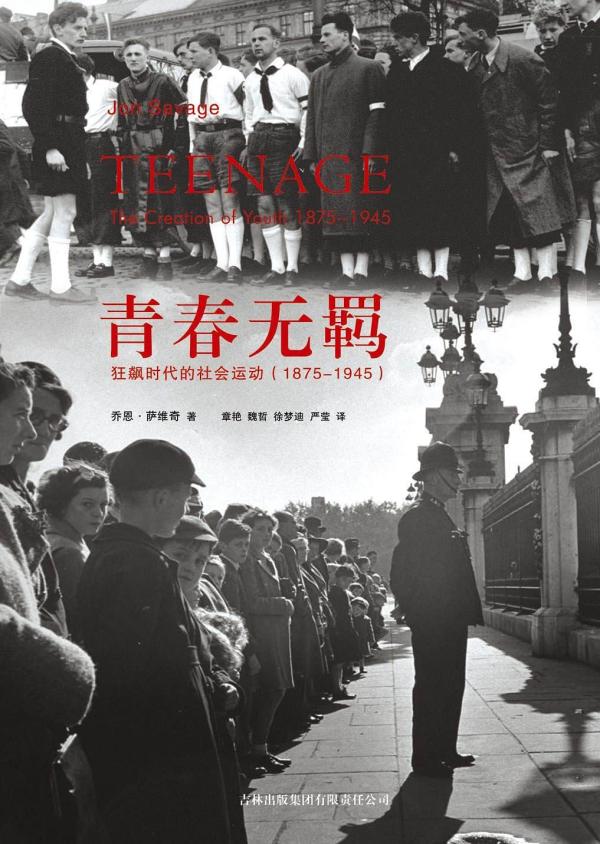
诗歌与图像、音乐的关系相当复杂,是文艺研究中的重大议题。在最好的意义上,它们总是能够相互激发,就像一排巨浪撞击着另一排巨浪、一颗子弹催迫着另一颗子弹,有时甚至又以沉默互致最高的敬意。一个诗人看到一幅图像,本想写一首诗,终于还是放下笔,说“我的诗配不上这样的青春”。诗人的读图极为精准,读出了很多人眼中永远读不出来的青春主题;而且他的心灵显然被刺痛了,他知道什么是语言无法表达的那种青春。一群青年歌者在唱:“当我们听到了恳切的呼唤……有些地方的人们正逐渐死亡……我们不能日复一日地伪装下去了,在某些地方总有人要改变自己,我们正在做的选择,是在拯救我们的生命”(We are the World)。还有20世纪英国作曲家迈克尔·肯普·蒂皮特 (Michael Kemp Tippett)创作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A Child of Our Time),在社会强权的轰鸣、压迫中,那些孩子的命运使人心悸不已。作者说“我要让悲剧唱出声来!”据说当这部清唱剧在欧洲各地上演的时候,曾令无数人泪流满面……
这些图像、诗歌和音乐所围绕的青春主题,使我在近日重读一部关于青年研究的文化史著作,英国作家乔恩·萨维奇的《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章艳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这是一部独特的青年文化史,也是一部透过青年运动的视角来观看世界的独特的西方亚文化史。作者在“序言”中说,“这本书讲述了欧美两个大洲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试图定义、说明和控制青春期的历史。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之间的对话外,这本书中还包含了其他一些内容,如青春期阶段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剑拔弩张,以及为提升或捕捉这些转瞬即逝的状态所做的种种尝试。个人证词——在青春期以日记的形式试图寻找自己和世界的意义,同媒体报道和政府政策一起出现在书中。……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和心理学家为了使青少年正常化做出了各种努力,他们认为青春期是一个人人都要经历的阶段,并不只属于特殊的群体。这些青少年代表了一个时代,并正走向即将到来的未来。”(4页)这也是通常关于青春期文化的研究框架,历史学、社会学和青春心理学是基本论域,犯罪学则使人联想到与年龄段相关的特殊性。从作者对“个人证词”的定义中可以发现,作为英国朋克时代一位著名的播音员、音乐评论家和作家,他显然对青春期文化有更深刻的感性体验和情感倾向。在时代浪潮中,青年总是敏感和激进的,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总是历史发展中最鲜活的部分和最尖锐的前沿。萨维奇在书中通过对时代变化、意识形态的发展以及权力管制的考察,描述和分析了欧美各国不同时期的青少年运动的整个历程,描绘出一部青少年如何努力发出真实声音、追寻理想并摆脱成年人控制的反抗史。
萨维奇在“序言”中简要回顾了青年研究的发展谱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次从跨学科角度提出“亚文化”这一课题,迪克·何柏第(Dick Hebdige)1979 年出版的《亚文化:时尚的含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将社会学、文艺阐释和法国理论融为一体,对英国战后的许多青年风尚进行了历史回顾,同时也关注诸如阶级、种族等其他因素。(1页)这几乎也可以用来表述萨维奇的这部《青春无羁》。再前的一个重要学术界碑是1904年出版的G.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的《青春期》(Adolescence),他预言性地指出青少年阶段将要独立面临着巨大压力和负担,因此应予以特别的照顾和关注。接下来萨维奇提到了L.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 的《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和J.M.巴里(J. M. Barrie)的《彼得·潘》(Peter Pan),认为这是可以与《青春期》互相印证的重要文献,这让我有点出乎意料。他解释说“这些虚构的作品探索了各种感情的诸多可能,即使不能代表整个社会,他们也预示了青春——或稍纵即逝,或万古长青。”(3页)这提醒我们关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青春期中的虚构作品与个人证词往往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情感性因素具有重要作用。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人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代沟”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它是如何出现的?萨维奇指出是18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的经济和政治的骚动改变了人们对“青年”这一概念的理解,在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中颁布的《人权宣言》重申了美国《独立宣言》的思想,于是“在一场由年轻人主宰的大革命中,其意义再清楚不过了:代沟产生了。”(13页)然后,“这些事件的影响贯穿整个19世纪。在新生而激进的平等政策的支持下,年轻人一方面代表了希望和未来,另一方面也是不稳定的危险分子。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年轻人参与了各种革命运动,比如人民宪章运动、效仿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些都表明了这一代人的觉醒转变成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可能威胁到社会秩序。”(13—14页)很显然,具有真实价值和重大意义的“代沟”首先是政治性的,是由政治觉醒与革命行动造成的。法国大革命之后迎来的是极为动荡不安的世纪,君主制与共和制轮番登场,青年人所投入的所有抗争的核心都离不开“自由还是专制”的抉择,于是有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我们所熟悉的德拉克洛瓦创作的《自由引导人民》,还有被安放在巴士底广场的七月革命青铜纪念柱顶端的“自由之神”雕像都是这段历史的证明。
在研究中,总有些年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青春、生命、理想甚至牺牲都在那些特殊的年份中放射出异样的光彩。比如法国的1968年,萨科齐在当选法国总统后说,为了解决国家道德危机,必须“一劳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莫里斯·迪克斯坦说,“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真正有意义的“幸存”产生于与遗忘斗争的过程中,作为历史记忆的“幸存”也不仅仅保存在学者的书斋中,而是在当下的生活中继续燃烧。萨维奇通过少年诗人兰波的眼睛和感受表达1871年巴黎公社给青年一代带来的精神印记,那种关于反抗与解放的精神价值。“1871年4月到5月的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无政府主义者占领了首都,年轻诗人们控制着警力。数以千计的年轻流浪者如飞蛾扑火般奔赴革命的巴黎,兰波就是其中的一个。……亲身经历使16岁的他了解了解放的意义,并决心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23页)于是他的诗歌沿着浪漫主义、爱伦·坡和查尔斯·波德莱尔的轨迹一路走来,“1871年后,他的诗作中充斥着革命骚乱、反中产阶级的谩骂、异教徒的神秘主义和狂热的预言,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形成坚固的宇宙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观点预告着世界末日:‘是爆发的时候了,海洋已经沸腾,地下也已爆炸,整个星球都在急速旋转,接下来的确是要灭亡了。’”(23页)兰波曾为公社写了《巴黎战歌》等诗歌,公社惨遭镇压的时候他写信给中学老师伊桑巴尔,说:“我一腔狂愤,心向战斗的巴黎,众多劳动者正在那边死去……”约翰·梅里曼的《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刘怀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告诉我们,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后对公社社员大开杀戒,有些人仅仅因为打扮像工人或言谈举止的特征而被逮捕甚至枪杀;由于公社在最后的抵抗中曾被迫纵火烧毁一些建筑,军队士兵在大街上滥杀任何携带可疑容器上街的女子,曾一次枪毙了13名女青年;梯也尔在凡尔赛宣称他们是正派的人,惩戒是在法律范围内、以法律的名义;公社被镇压后出现了约300种支持官方的书籍,以证明血腥镇压的合法性;公社流亡者让·巴蒂斯特·克莱蒙特把在1866年写的《樱桃时节》献给勇敢的公民路易(Louis):“我将永远热爱这樱桃时节。/我会将这一时刻,藏在心间,/那撕裂的伤口。”促成约翰·梅里曼写这部《大屠杀》的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一幅这样的历史照片:“优雅的上流社会的巴黎人,在军队镇压公社的1871年5月21 日至28日的‘血腥一周’之后回到法国首都。他们为自己的国家镇压了追求自由的巴黎人这一恐怖行为鼓掌。”(283—284页)那么,可以想象少年诗人兰波当年是何等的悲愤莫名。然而,在过了145年之后,2016年11月29日,法国国民议会依据《宪法》34-1条款通过第907决议,由议长克洛德·巴赫托洛纳签署“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不是又一次新的“赦免”,不是对悲惨历史的怜悯,而是还历史以真相——“此举旨在给那些为自由不惜被立即处死和受到不公正判决的妇女和男子以荣誉和尊严。”
同样悲壮的是纳粹帝国时期的青年反抗组织“白玫瑰”。萨维奇说他们在表达对政权的敌对情绪之外还提出了实际的建议:“消极抵抗,抵抗,不管你在哪里,趁还来得及阻止这蔑视神明的战争机器继续蔓延……”(416页)“白玫瑰”在1942年夏初又制作了三种传单,抗议对30万波兰犹太人的屠杀、苏德战争的惨痛代价、在“恶魔的独裁政治”中自由的丧失,“总之,有尽头的恐惧总比无尽的恐惧要好”。1943年2月,“白玫瑰”的一份传单直指问题的核心:“以德国青年的名义,我们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归还我们的自由,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他用最可鄙的方式骗走了我们的自由。”(416页)十几天之后,汉斯和索菲在学校散发传单的时候被捕了。“等待行刑的日子里,汉斯和索菲保持着他们的尊严,非常平静。……当索菲被问及如果她知道会有此后果是否还会这么做时,她回答:‘下次我还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是你们,而不是我的世界观有问题。’他们留下了两封遗嘱:在起诉状的背面,索菲潦草地写下了‘自由’;在被关押的小房间里,汉斯写下了引自歌德的一句话:‘坚决反对一切专制。’”(417页)他们被执行了死刑,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仍在反抗。
黑塞在给一个年轻的《梦系青春》读者的信中说,“没有革命的经历是形成不了人的”。而“革命”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心中又意味着什么?郝舫的《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告诉我们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比那些表面的“革命”姿态更能表明列侬和“披头士”对革命的真正态度的,是他们那首遐迩闻名的《革命》。因为《革命》引起许多激进青年学生的强烈抗议,约翰·霍伊兰发表了有名的《致列侬的公开信》:“我们所反对的是压迫性的罪恶的权力主义制度,一种非人的不道德的制度……它必须被无情地摧毁。这并不是冷酷,也不是疯狂,这是一种最热烈的爱……不与忍耐、屈辱和压迫抗争的爱是无力和落伍的。”(102页)
法国著名剧作家让-克劳德·卡利耶尔的回忆录《乌托邦的年代》(戎容译, 商务印书馆,2010年)这样描述1968年的巴黎青年:“与美国那些笑眯眯的、飘逸闲在的嬉皮士相反,巴黎的青年们正在掀起一场暴动。鲜花之后,是街石之战。十九世纪市民暴动的纯法国传统被继承了下来,拉丁区的街道都被街垒截断了,‘街垒卫士’们轮番站岗,与警察抗衡。大学生们的医疗救护、食品供应和宣传方法都已经安排有序。索尔邦大学的教室改成了病房,医学院把未来的医生们派去,为那些从夜战中撤下、用担架抬来的伤员们治疗。后来,大学里还设了一个托儿所,为正忙着撬街石、筑街垒、改天换地的父母们带孩子。”(45页)在圣日尔曼-德帕蕾的地铁站里,乘客们的手里都攥着一条手帕擦眼泪,因为催泪弹滚进了地道;“革命”这个词从每一件印刷品的每一个段落里涌现出来,四处流传。“青年一代突然在夜间把我们一把拧醒,自豪地声扬着他们的‘欲望’,叫我们睁开眼睛。别睡了!你们身陷泥潭,无以自拔了!有人把你们捏在手里左右着,还用催眠术在蒙骗你们!快醒醒吧!……你们难道没觉得什么事件到来了吗?难道不觉得这怒火中的春风是一件大好事吗?”(51页)
说到底,许多运动中的激进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某些青年的灵魂无法与之和解的东西。这正是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的真正主题。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的结尾处写道,那孩子已经永远地游到河里去了,“我”的内心被强烈震撼∶“我现在只能说一点——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不管世界上有什么在等待我们,只要有人出生和死去,真理将永远存在……”这段话我曾经在文章中引用过不止一次,我不知道还要引用多少次,才能让我感到足以抚慰那个孩子纯洁、正义的灵魂。我想到的是,应该追问究竟什么是“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艾特玛托夫通过小孩(青年)向我们提出一个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吗?——这个问题还用想吗?难道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岁月静好?
诗人杨子有一首题为“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们”的诗:“蜡烛不会一直燃烧,/如果我们的心灵一直潮湿,/如果我们的心愿变成古怪的三角形。//我们的祈祷已经失去效力,/我们的祈祷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我们的嘴唇已经干枯,/我们的藤蔓在虚空中飘。//风是热的水是咸的,/而我们什么都不能拒绝。//我们说过的话堆成垃圾山,/我们流出的泪成了滞销品。// 唯有孩子们是清澈的在他们变得古怪以前,/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们,/在我们被神圣的尺度变成垃圾以前。”(杨子《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们——杨子诗集(1990一2018年)》,15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7 月)所谓“清澈的孩子”,不就是在内心有着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吗?不就是在内心保留着神圣的尺度、敢于拒绝某些东西、敢于让蜡烛一直燃烧的孩子吗?这是值得期待的浴火重生的青春元年。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