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孙一洲评《哈贝马斯传》︱公共知识分子中的战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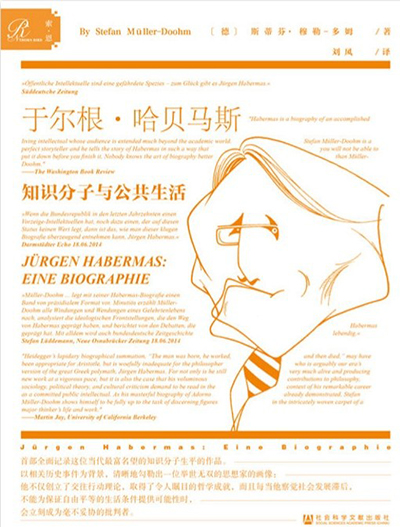
《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德]斯蒂芬·穆勒-多姆著,刘风译,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639页,98.00元
传记一般出现在传主身故之后,因为树碑立传总含有盖棺定论的味道。而且对生命中的各项事件,作为当事人的传主即使不享有最终解释权,声量也比任何记者都更洪亮。况且,总有一些主观情感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作祟,这是多少客观材料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改编不是胡编”,在一个为逝者立传都要遭受其精神后人加诸非难的时代,为生者作传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哈贝马斯的传记却是一本众望所归的“在世者传记”。因为传主本人的争议早已积水成渊,根本不在乎这点毛毛细雨。在其学术生涯中,他曾与波普尔、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马尔库塞、库尔特·松特海默(Kurt Sontheimer)、伽达默尔、施佩曼(Robert Spaemann)、尼克拉斯·卢曼、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罗尔斯、德沃金、德里达、福柯、布迪厄、利奥塔进行过论战。几乎把战后有点名头的西方思想家都单挑了一遍,养活了数以万计的学术从业者。这可能还只是他小巫的那一面,毕竟他的《学术论集》有五卷本,《政论文集》却有十二卷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还都是短小精悍的专栏。
在左拉为德雷福斯案仗义执言之后,知识分子就强调对公共话题的政治介入。战后德国的哲学家长期“不务正业”,动辄在报刊媒体上指点江山。哈贝马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参与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至少2010年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德国公共讨论,堪称公知中的战斗机。作为当事人,他以一己之力就能串起整部德国的战后思想史。麦茨勒出版社(Metzler Verlag)权威的个人理论手册系列一般以逝去的思想家为研究主题,却也早早出版了《哈贝马斯手册》(Habermas-Handbuch,2009)作为八十岁寿礼。在他九十岁仍笔耕不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忤逆他的意愿,在为时太晚之前,进入他的生活。
纳粹父辈,高尚子辈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这个年份就非常微妙。纵览十九世纪末以来思想史,代际冲突和家庭矛盾几乎是标配。如果传主没有和家人发生过什么争执,作者对材料的掌握程度就很值得怀疑。具体到哈贝马斯这一代人,代际就不够精确了,年份本身可能就是其问题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出生就意味着在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时只有十六岁,还没有成年,而成年对一位日耳曼男性来说几乎铁定意味着参军入伍、保卫元首,即使战后幸存下来,也背负了纳粹的原罪。在此和哈贝马斯对标的是两位1927年出生的德国文豪: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与毕希纳奖得主马丁·瓦尔泽。两人都有为第三帝国服役的经历,尤其是君特·格拉斯,他在2006年出版的回忆录《剥洋葱》公开承认了自己在党卫军的经历,引发了当时的舆论声讨。他的回忆虽然不能说深情款款,但总有一些岁月的滤镜。免于服役的哈贝马斯自然也不会有这样的人生污点需要遮掩和洗刷。

于尔根·哈贝马斯
当然,成长在第三帝国的哈贝马斯不可能完全与纳粹无涉。随着二战战争烈度的增强,盟军对德国本土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和轰炸,这些快成年的青年人——也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们——都被从学校抽调到当地的防空部队执行勤务,所以他们这代人又被称为“防空高射炮的助手一代”。哈贝马斯尤为特殊,他早年患有先天性唇腭裂,后被安排到青年团负责急救训练,鉴于战场医疗人员可以被算作非战斗人员,哈贝马斯只能说是勉强与纳粹摘清关系。鉴于战争后期很多狂热的纳粹分子都幻灭了,用格拉斯的话说,他们这代人“要成为纳粹还太小,被纳粹所塑造却足够大”。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出生的德国人,纳粹的历史罪行基本被认为与他们完全无关。
这种细微而敏感的差别体现在一桩发生于哈贝马斯晚年的莫须有事件。就在君特·格拉斯发表《剥洋葱》引发争议的同时,《法兰克福汇报》的一位专栏历史学家和政论作者费斯特(Joachim Fest)在自传《我没有:童年与青少年时代回忆》(Ich nicht: Erinnerungen an eine Kindheit und Jugend)中,不点名地传播了一则关于哈贝马斯的谣言,说他曾吞下自己在希特勒青年团时的一张活动记录。记者于尔根·布舍(Jürgen Busche)如获至宝,大加发挥,在《西塞罗》杂志撰文,宣称他经过调查考证,证实哈贝马斯毁灭其纳粹罪证确有其事。在终其一生的数次论战中,哈贝马斯尤其喜欢给他的论敌扣上法西斯主义的帽子。他骂过右派是法西斯主义者,也骂过左派是法西斯主义者。他被视为半个世纪内德国舆论的言论警察。人们戏称,哈贝马斯每天逐页翻阅《法兰克福汇报》,看看谁的报道又犯了右倾主义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比证实他本人是一位如假包换的纳粹分子更抓人眼球的新闻了,更何况是以吞下肚子这种戏剧性的方式。
随着事态逐渐扩大,哈贝马斯的故交维勒作为当事人不得不出面辟谣。这是一则七十年代的旧事:维勒在六十年代翻阅自己战争期间日记时,偶然发现了一张当年青年团团员活动的表格,内容是催促团员们参加哈贝马斯组织的救护培训,并附有后者的签名。维勒一时兴起,把这张纸片寄给哈贝马斯。后来,两家人一起度假时,他向哈贝马斯的太太乌特追问这张纸的下落,乌特风趣地回答:“你还不知道于尔根啊,他把那张纸吞了呗。”这句调侃被以讹传讹,成为哈贝马斯隐藏过去罪证的写照。事后,哈贝马斯通过律师要求出版社销毁了费斯特的自传,并得到了《西塞罗》杂志的书面和口头道歉。他本人后来澄清,如果没有人参加他的救护课程,他反而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常规军事训练。
虽然哈贝马斯的清誉得以维护,但驱动这次诽谤的代际矛盾却客观存在。曾与哈贝马斯交恶的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九十年代末面对哈贝马斯施压时就曾说过,“纳粹父辈、高尚子辈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纳粹父辈、高尚子辈”这八个字,形象地说明了从五十年代到两德统一五十年间,纳粹这个问题如何成为德国的公共讨论中那头房间里的大象。对德国更年轻的世代而言,他们会觉得这笔债不应该“子子孙孙无穷匮”地偿还下去。所以战后德国思想界一直存在一股暗流,就是尽力与纳粹拉开距离——所谓暗流,并不是说这一主张未被明确表达出来,而是说前后持这一立场的知识分子是在不同时代以不同面目出现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继承关系,但这背后的思想驱动力确实是一致的。哈贝马斯一生与之搏斗的,就是这样一股暗流。
反海德格尔作为方法
相比上一代德国人注定风雨飘摇的一生,他们这代人是战后社会的顶梁柱,人生虽然不无波澜,但总体还是吃到了战后发展的红利,坐享太平之福。知识分子尤甚,哈贝马斯和他们的同辈人大都职业生涯都顺遂,发展如入无人之境。因为很多同龄人都死于战火,而在知识界的前辈很多又因为历史际遇问题不便做高姿态。比如哈贝马斯的博士生导师、波恩大学的哲学教授罗克哈克(Erich Rothacker),他作为1932年最早公开支持希特勒的五十一位大学教员之一,是老资格的食死徒。战后虽然没有被清算,但自然也不便公开发声。而新一代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就垄断了话语权威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到九十年代仍然活跃在公众的视野里。时代剧变造成的人才断层,新一代精英面对巨大的历史空白,享有空前绝后的社会资源。这样巨大历史灾难后的天之骄子,中国人想必不会陌生。
哈贝马斯在思想界的崭露头角,是1953年发表于《法兰克福汇报》的《以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Mit Heidegger gegen Heidegger denken)。他长期敌视尼采、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中的所谓“非理性传统”,这不是秘密。这不仅是立场上的天然对立,也有偶像幻灭的私人动机。像很多九十年代入职的中国哲学教授一样,他在读大学时也是海德格尔的粉丝。而当他在1953年底读到了新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对其中海德格尔的政治投机与反民主思想感到震惊,尤其是海德格尔在成书十八年后的死不悔改,完全无视这期间巨大的人道灾难。海德格尔的纳粹支持者身份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一桩思想史公案,借此也可以一窥战后初期德国的政治气氛。因为德国人民充分反省历史罪行的印象在中国深入人心,尤其定格在了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在犹太纪念碑前的“华沙之跪”。德国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自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这也只是长期历史进程中左右派互搏后的结果。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反思是否充分,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战后执政的阿登纳政府是一个保守主义政权,试图以反共来铸造新的社会共识,而且吸纳了大量前朝余孽,尤其是任命了参与纽伦堡种族法案的格罗布克(Hans Globke)为国务秘书。德国当局也试图以支付赔偿来堵受害者之口,把多场战犯审判拖延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战后的西方政权都有类似的威权残余,戴高乐也面对过类似的指控。哈贝马斯的文章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击,指责他在搞猎巫和文字狱。我们可以参考《窃听风暴》中那位剧作家的遭遇。片中,他在两德统一后见到当初下令监视他的前东德高层,后者仍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甚至用监听到的私生活细节刺痛当事人。在新政权中留任的前纳粹分子可能没有这么跋扈,但仍然是新瓶装旧酒的利益团体。这个德国仍然饱受反民主之苦,左派知识分子当时反对的法西斯主义也不止是一种捕风捉影的思想倾向。
到六十年代时,保守主义的阿登纳政权也走到了尽头,但1961年柏林墙的筑起标志着冷战的激化。冷战升温导致的反共气氛也渗透到学界,战后一些学者也开始将他们的学说刻意“非激进化”,尤其以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任职时的上司和前任霍克海默为代表。长期的流亡经历让这位犹太学阀尤其缺乏安全感,他战后在法兰克福大学执教二十多年,官至校长,却一直没有在德国置业,而是选择在永久中立国瑞士和阿多诺比邻而居。哈贝马斯吐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过的是行李箱上的日子,随时可以打包走人。霍克海默还封存了他在二三十年代主导的一些左翼研究,包括工人运动和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当时的大学生想要读到霍克海默的作品,主要得依靠市面上的盗版。
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六十年代最重要的思想事件自然是学生运动,德国学生运动则发端于高校改革的倡议。哈贝马斯也是德国最早呼吁高校改革的学者之一,五十年代末就参与了大学生政治态度的调查,并在1961年发表了《大学生与政治》(Student und Politik),为大学生介入政治的激进姿态铺路。战后的巨型大学不仅导致了学生的下沉,也引发了教授的贬值。这种贬值未必是待遇上的,却是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上的。传统大学是熟人社会,不同科系的教授之间联席当家。而战后大学的扩张让每个院系都无比庞大,迫使管理层必须采取垂直的企业化管理,大学的学术共同体自然也无从谈起。仅仅作为教学雇员的大学教授自然也很难在社会中发挥其他影响力。大学实际上是战后各个社会组织利维坦化的一个缩影,个人所能扮演的角色愈发无足轻重。哈贝马斯认为,为了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能,大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霍克海默担心哈贝马斯激进的态度会诱导左翼学生采取暴力行为,多次去信要求阿多诺辞退哈贝马斯,这完全低估了哈贝马斯的审慎。1967年6月2日,新左翼运动学生在西柏林的歌剧院抗议前来访问的伊朗国王巴列维。游行示威遭警方驱散,二十六岁的大学生欧纳佐格(Benno Ohnesorg)被一名便衣警察射杀。政治精英在媒体的遮掩下为警暴辩护洗地,群情激愤,全德各地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悼念。这件事成为德国六七十年代左翼恐怖主义的导火索。6月9日,牺牲者在老家汉诺威下葬后,当场举办了一场题为“高校与民主——反抗的条件和组织”的报告会。哈贝马斯是四位受邀到场发言的教授之一,可见他在学生中的号召力。他呼吁采取公共抗议手段来抵制“威权主义绩效社会”,但也告诫说切勿采取暴力的激进行动。这话在当时听起来有点讽刺,因为当事人就是在抗议中被射杀的,所以遭到了学运领袖的反驳,认为不该排除暴力手段,并指责哈贝马斯用“空洞的客观主义消灭了解放主体”。哈贝马斯没有立刻回应,会一直开到午夜,他本打算离开,走到停车场后,又折回会场,说了一句:“我个人觉得,1848年人们所称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在如今应该称为‘左翼法西斯主义’。”
这句话算得上哈贝马斯个人的历史时刻。他尤为可贵的一点就在于,虽然名义上是意见领袖,立场却是高度个人化的,坚持独立思考,不为某种政治激情所裹挟。他随后理所当然地遭到学生团体疏远,甚至助手也撰文反对他。德国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也很激烈,间接导致了阿多诺的死亡,但总的来说比较不像法国五月风暴那样一边倒。最明显的原因在于,德国此时还是一个分裂中的国家,处在冷战前线。比如在柏林射杀学生的那位便衣警察卡尔-海涅茨·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在2009年被证实是一名东德情报机关的线人,于1964年秘密加入东德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虽然没有证实射杀行为是受到斯塔西上峰的指示,但这人的保守主义倾向是一以贯之的,生前接受采访时仍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他捅了这么大的篓子后还能全身而退,很可能也受到了当时柏林警方高层的庇护。
也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德国知识分子在公共讨论中的话语权逐渐降低,抗议游行逐渐成为德国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表达方式,电视也开始接管报纸的政治报道职能,民众不再那么需要知识分子以抽象理论为他们代言。战后德国社会的抗议式民主的发展趋势,最终表现为绿党在八十年代的开花结果。将哈贝马斯称为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并不是附和长时间以来文化界孤臣孽子、兔死狐悲的悲壮气氛,而是一个媒介的概念。既然知识分子起于左拉在报纸上的振臂一呼,是否会终于社交网络上的千头万绪?哈贝马斯长期敌视电视论辩,强调追求民主的公共讨论必须诉诸笔端——可是,刊载见报难道不是少数作者的特权吗?网络、播客和视频,二十一世纪繁花似锦的新媒介早就拉低了发言的门槛,虽然也带来了必然的嘈杂。哈贝马斯是否会喜欢这个时代,殊未可知。他的形象有太多重影,连研究者都辨认不清:一位在理论上、政治上亲西方的学者,一位好斗的公知,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认同与否,他身上都标识着战后德国社会的成就和局限。新一代德国人是否还愿意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些历史包袱,令人怀疑。不过,至少他们还能心怀感激地为九十高龄的哈贝马斯献上祝福。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