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返向内在世界:一场“精神奥德赛”
文 / 张曦(学者)
我在此前几篇专栏文章中已经说到,“做伦理学”致力于“自我”的诊疗和救治,是一种朝向内在世界、聚焦主体能动性重建和精神生活质量提升的哲学尝试。所谓“内在世界”,就是“自我”的精神意识世界。返回内在世界,不仅是为了从理论上克服“主流”哲学伦理学的教义化缺陷,更是要重建伦理知识与生活-经验世界之间的实践关联。那么,“自我”为什么要返向“内在世界”来寻求这种救助?“内在世界”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资源,能够救治自身?这是我们接下来要通过若干篇文章讨论的大问题。
还是从柏拉图开始。《理想国》以这样的剧情开幕:苏格拉底从雅典城高处“下降”到地势略低的比雷埃夫斯港,在那里观看异邦人举办的华丽宗教庆典。回城路上他巧遇朋友珀勒马科斯,珀勒马科斯力邀苏格拉底在港口逗留。于是,半推半就的苏格拉底就留了下来,并在其后十卷篇幅中,乘机为他的朋友们呈现了一个“理念的城邦”。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 / 著
顾寿观 / 译
岳麓书社 2018-10
有见识的学者早已发现,这段开幕剧情与高潮部分的“洞穴神话”、结尾处的“厄尔神话”一起,构成了含义深刻的解释学整体。对此本文无法详察,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品读原著。此刻,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角色和他的动作,以及剧情所发生的背景环境。就角色来说,苏格拉底当然代表了“哲学”,但“哲学”为何要“下降”到比雷埃夫斯港?喧嚣热闹的比雷埃夫斯港又有何象征意味?
就历史本身而言,不管是苏格拉底还是他的学生柏拉图,都生活在后希波战争时代。希波战争的本质,是希腊自由城邦联合起来抵抗波斯侵略。为了战胜波斯强权,捍卫自身的自由和独立,零落分散的希腊城邦自愿结合成提洛同盟,由雅典领导。在领导提洛同盟挫败波斯侵略的过程中,雅典逐渐发展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希波战争后,与其他城邦相比,雅典拥有了显著力量优势。陶醉于这种力量及其所带来的物质好处的雅典,决心依靠这些优势在战后尽可能多占甚至独占财富红利,从而走上了一条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最终落入今人生造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雅典帝国主义”的来历。
帝国的本质,就是利用物质优势制造有利于自身的生产-分配格局,确保自己始终占有超额利益。雅典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政策路线,也是一种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奉行这种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后果,就是全神贯注于物质世界的利益积聚和分配,尽全力赢取最大化的单边利益。帝国化的雅典,不仅对外奉行一套侵略性、不公正的军事贸易政策,而且帝国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注定会从内部改变雅典城邦本身。试想,紧盯眼下物质盈亏以及由此而来的想象性荣耀的灵魂,不可能关注到自己精神的渺小卑微;制定不公不义军事贸易政策的暴政,不可能在制定城邦内部政策时陡然成为天使;城邦统治阶层的僭主化、寡头化,不可能不在最深处对公民尤其是年轻公民有关“美好生活之道”的理解和想象产生影响;一个每天都在犯罪的政制(regime),不可能不依靠诱引人民不断参与自己的罪行来巩固自身。
从领导提洛同盟捍卫城邦自由独立,到独步帝国化道路谋求单边不义优势,雅典城邦的政制在形式和质料两个层面急剧发生变化。尽管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伯利克里于公元前429年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仍然发表了一篇有关雅典精神的正气浩荡的讲辞,但讲辞中那个被伯利克里骄傲地宣布为“全希腊的学校”的雅典,实际上早已开始经历精神上的朽败和死亡。柏拉图和他同时代人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亲身体会什么是“城邦的死亡”、什么是“灵魂的堕落”的一生。但柏拉图的幸运在于,他的体会只停留在“观摩”和“明察”的层面,几乎不曾缠绕到雅典帝国化的实际进程中,始终在精神意识上与“无知、邪门和贪婪”但却充满“统治的热望”的僭主保持清晰的距离,从而逃脱了随雅典精神一同坠入黑暗的危险。
在柏拉图的时代,这份幸运只能独属于那些立志“成为苏格拉底”的雅典青年。因为在那场起于贪婪、终于贪婪、无人受益,并最终导致希腊世界解体的巨大人性悲剧中,唯有苏格拉底以哲学的方式,始终与光明为伍,拒绝在雅典精神的急剧坠落中参与犯罪,并将自己精神探寻的体会以最深刻的方式(“助产术”或“辩证法”)讲了出来。
比雷埃夫斯港,就是被帝国精神所捕获的雅典的象征。希波战争后,雅典人修筑长墙将城邦与港口连在一起,作为维系海洋霸权的战略通道。比雷埃夫斯港的逐渐兴盛,恰恰标志着雅典日益从自由独立城邦转向帝国性霸权存在。这个背景,是理解《理想国》开篇的基础。在开幕剧情中,苏格拉底“下降”到港口的观摩,本质上也是哲学“下降”到帝国雅典的观摩。在喧闹的城邦中,大部分人的精神意识早已在毫无防备和觉察中随雅典一道沉沦。只有苏格拉底,或者说只有“正确的哲学”,才有能力在异邦人华丽无比的庆典和人群的嘉年华狂欢中,看到这场庆典和狂欢的本质:对于帝国雅典来说,这场庆典不过是一幅伴随精神衰败和腐坏而升腾的人工幻象。
因此,当苏格拉底决意在比雷埃夫斯港逗留时,他并非真的屈从于朋友略显逼迫的挽留,而是意在顺势向年轻的雅典公民传递一则重大讯息:在一个外在环境已经无可避免地朽败的社会世界里,唯有向内探寻、向人的精神意识的深处探寻,才能发现一种也许只有“哲学神话”(philosophical myth)才能恰当加以表达的知识。它关乎我们灵魂的秩序,必须花费整个人生去尽力探求。它是“美好生活之道”的基石,人唯有依靠它、听从它,才能区分“好”与“坏”,辨别高尚与低劣,选择过“更好的”而不是“更糟的”生活,从而摆脱盲目命运的折磨,不仅成为自己的朋友,而且成为众神的朋友,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过正直无畏的个体生活和庄严公义的共同生活。
这种知识告诉我们,个性的迷乱和政制的失序,归根到底都源自精神意识的某种内在紊乱。一个残暴的人和一个残暴的城邦,本质上患有同样的病症——“灵魂的疾病”。关注物质积聚和财富最大化的雅典,与迷恋男童肉体的僭主一样,都是被困在物质性的“可感世界”之中,意识不到自身需要救助的可怜虫。要将个性和政制从迷乱中解救出来,最根本也是唯一有效的道路,是返向精神意识的深处去体察永恒的、非物质性的东西。因为,只有那些东西隐藏和表征着整个宇宙的本质。苏格拉底式哲人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在社会世界的喧闹和迷乱中,抛开一切幻觉和“似是而非”的东西的束缚,与自身的心灵交流,走一条朝向高处、朝向本质的精神生活之路,去体察人、城邦、众神以及宇宙所共同分享的理念性本质(essence)。
因此,对苏格拉底来说,“返向内在世界”并非为了逃脱堕落的社会世界。相反,苏格拉底深信,内在世界中隐藏着某种有关人与城邦、社会与自然、时间与空间的整全真相。只有依凭这个真相,人才能觉察出社会世界堕落现实的幻觉和假象性质,才能找到这种幻觉和假象,重新找到走正确之路,因而也是真理之路的门径。对苏格拉底来说,“返向内在世界”,其实就是一场属于苏格拉底式杰出之人(“爱智者”)的“精神奥德赛”。内在自我的精神意识世界,或者说“爱智者”的自然化“心灵”,本质上只是这场“精神奥德赛”通向终点的旅程中的一个驿站,而非终点本身。但这个驿站的秩序状况,意义非同小可。它究竟是混乱不堪,还是和谐均衡,对于踏上旅程之人至关重要。只有栖息在一个和谐均衡因而洁净有序的“心灵”驿站中,人才有望窥瞥旅程终点的奥秘。
对一个人来说,要进入这个驿站十分不易。他要能从社会世界的外在喧闹中抽身,觉察到返回内在世界的必要性。换言之,他得意识到,礼俗、荣誉、财富这些只有在社会世界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幻象性遮蔽物,遮蔽了一个人与永恒真理的联系。他得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意识到自己在何为“好”“坏”的知识方面绝对匮乏。然后,他才能在苏格拉底式杰出之人的帮助下,发现内在灵魂秩序的秘密。
这场“精神奥德赛”无比艰难,旅程中必会饱受无尽的艰辛,唯有真正的“爱智者”才能担负得起。但更大的悲伤莫过于,即便最终窥瞥到真理之光,“爱智者”也绝没有机会在这个驿站中永恒停留。属于凡人的肉身之累,终归要将其重新拽回尘世和大地。可一旦带着奥秘回到尘世和大地,“爱智者”就再也不能假装自己像先前一样“无知”,只能扛起医治无穷无尽个比雷埃夫斯港的负担。
在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精神奥德赛”背后,站着一个容易被现代人斥为“迷信”的古代目的论宇宙观。这种宇宙观相信,“逻格斯”或者“理性”弥散在宇宙秩序的各个方面。人是小宇宙,宇宙也是最大的人。正因此,“返回”内在世界并不是朝向一个与外部世界切断了联系的封闭“自我”,而是以“返回”这样的动作姿态,朝向一个远高于个体自身的根本性生存真理(existential truth)。我们必须记住“生存真理”这个今天并不太容易理解的古老观念,它意味着转向“心灵”的那种寻求“美好生活之道”的“精神奥德赛”,本质上是一种朝向更大、更真实的整全真理的努力。
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精神奥德赛”之路,在基督教兴起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改造。这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思想贡献,由希波的奥古斯丁完成。奥古斯丁用基督教的“上帝”替换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宇宙”观念。内在世界与永恒真理世界所共享的和谐秩序,被重新解释为基督的天意。尽管经历了奥古斯丁复杂而深刻的改造,“返向内在世界”作为探求“更高的存在”的道路却被有意保留下来。区别是,在奥古斯丁的基督教观念里,“返向内在世界”不再是一段朝向灵魂和宇宙秩序的真理之旅,而成了一条通往基督和天国秩序的真理之路。路依然是“向上的”,但其根据已完全不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也不再是寻求灵魂疾病的诊疗和救治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爱智者”,而是亚当的子嗣、“原罪”的继承者。于是,“返向内在世界”之旅中的人,不能再依靠苏格拉底式“正确的哲学”,而只能依靠“圣爱、信心和恩典”,通过一刻不停地在自己的“内在世界”中与“原罪”引发的各种“肉欲之爱”战斗,才有望回忆起上帝印刻在他内在世界深处的神圣印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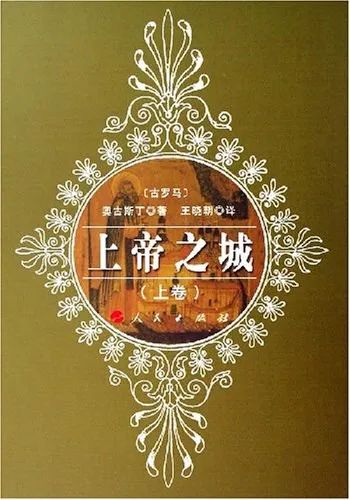
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 / 著
王晓朝 / 译
人民出版社 2006-12
无论是对奥古斯丁,还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来说,“心灵”始终是通往“更高”的东西的一个驿站。这个驿站或许提供了窥望灵魂和宇宙真理的放大镜,亦或许本身就印刻着上帝遗留在亚当身上的神圣印迹。但无论如何,它都不是寻求人生意义(“美好生活之道”)之旅的终点,而被视为一段更为艰辛的求真、求善、求美的坚实之路的真正起点。
人对世界的想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与自身的关系、人对“美好生活之道”的想象。在奥古斯丁之后的一千多年里,至少在西方文化内部,上述宇宙观及其对“内在世界”的理解,都相对比较稳定。但伴随东西文化交流,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一个想象世界的全新方式开始出现——机械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将宇宙理解为一个有着自身运行规律的东西。这些规律恒定而重复,可以被理智生灵所观察甚至理解。但它们对人类事务漠不关心,人也不能去干扰它们。从伽利略到笛卡儿,一种全新的有关人与宇宙、自然与社会、时间与空间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自然世界与人类事务从根本上是“脱钩”的(disengagement)。如果自然世界拥有秩序,这种秩序只是理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表象。而人类生灵的“内在世界”,究竟是杂乱无章还是秩序井然,从宇宙的观点看,都漠然无谓。
这场机械宇宙观革命,不仅奠定了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唯物主义世界的基础,而且将人的精神生活之路带入了一场空前危机。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返向内在世界”始终意味着朝向寄居于杰出之人的个体“心灵”之中的某种根本性生存真理。“自我”和他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是充实的、实质的(substantial)。某种客观、稳固、不可移易的精神意识标准,始终在“更高”的地方指引踏入这趟“精神奥德赛”之旅的人,不断告诫人“何为美好生活”以及如何才能过这种生活,并因此成为他们在精神生活的现实洋流中克服必将遭遇的惊涛骇浪的压舱石。现在,既然宇宙和自然已经与人类事务“脱钩”,那么自然化的“心灵”就不会再内在地蕴藏“好”与“坏”的道理。如此一来,“返向内在世界”,在什么意义不是返向某种空洞和虚无?人的精神生活究竟还有没有标准?世间的生活方式还有没有好坏之分?谁,根据什么道理,还能告诉一个精神错乱、狂悖妄想但拥有一切的现代僭主,他究竟为什么比伽利略或笛卡儿活得“更糟”?而我们每一个人,又有什么样的确凿根据,告诉自己,即便面对无法理喻的社会-历史悖谬,也依然有信心和有决心地,去走一条“向上的路”?
500多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文明。伴随着现代化的展开,欧洲文明的生存逻辑逐渐成为现代世界的生存逻辑。这些曾经的“他们的问题”,也因此逐渐成为“我们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悬挂在时间的前端,而且当你点开新闻网页浏览国际新闻时,甚至会惊讶地发觉,它们恰恰也是当下这个时代最紧要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37期,注释略,原标题为“返向内在世界”。)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