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丨一周书记:巫师、毒药与……闹钟

《巫师:一部恐惧史》,[英]罗纳德·赫顿著,赵凯、汪纯译,广西师范大学丨新民说,2020年9月版,476页,89.00元
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潮州菜中的卤水拼盘,鹅头、鹅肝、鹅掌翼等拼于一碟,浇上特制卤水,大快朵颐。有趣的是,读书时偶尔也会有无意中的拼盘之乐,如近日快递送来的一包书,打开一看是巫师、毒药和死亡闹钟。匆匆翻了一下,发现这份无意中的“拼盘”有共同之处:都是在不同角度的叙事中谈论记忆、迫害、恐惧与死亡。这三部书是:罗纳德·赫顿的《巫师:一部恐惧史》(原书名 The Witch: A History of Fear,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赵凯、汪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涩泽龙彦的《毒药手帖》(余梦娇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和朱利安·巴恩斯的《没什么好怕的》(原书名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 ,郭国良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死亡闹钟”是该书中的重要概念。从性质上看,前两部是典型的人类学与文化史的著述,后一部虽然是个人回忆录性质,但实际上是一部以死亡为主题的思想录。巫师、毒药与死亡,都是很严肃的研究主题;作者是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毒药学家,他们在无意中被汇聚在一起,似乎是为了在同一时刻举证邪恶、谋杀与死亡。
罗纳德·赫顿在《巫师:一部恐惧史》的“导言”中说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了解与巫术有关的信仰,以及由巫术信仰引发的近代早期欧洲的巫师审判,接着介绍了英语学界与欧洲大陆学界在学科视角之间的变化与差异,强调本书试图将两种方法体系结合起来。该书的中心问题是古代及中世纪早期的巫术观念究竟与近代早期的巫术信仰和巫师审判在模式、性质等方面有何相关性,而研究的视角则是由三个逐步收缩的视角组成:深度视角(全球语境、古代语境和萨满语境下的巫术)、欧洲大陆视角和不列颠视角。译者在后记中对该书的基本内容也作了概括性的表述:“本书涉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多个领域,既广泛引用了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至中世纪、近代的大量文献,又采用了大量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各民族人群的研究成果,对巫师文化做了全方位长时段的扫描。它介绍了埃及法老、罗马皇帝、北欧人是怎么看待巫术的,也探索了魔法咒语、德鲁伊和家养小精的定义和来历,最重要的,它从文化、历史等多个层面追踪了近代早期欧洲大规模猎巫和巫师审判的过程,并做了可信的对比、分析和研判。”(452页)
这项以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为中心的巫师研究并非与今天的现实生活无关,虽然作者没有展开论述,但是也提到了直到今天,在整个非洲大陆要说服普通人放弃巫术信仰仍然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教育和执法运动;在今天的西方国家的非洲民族社区,对巫术重新产生了强烈的恐慌,如英国警方调查了八十三起涉嫌巫术的虐待儿童案,还有很多这类案件没有得到充分报道,伦敦警察厅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来处理这类问题。在另一方面,恐慌导致驱魔行为的复活,不少人相信 “西方社方社会藏匿着一个国际性的魔鬼崇拜团体”,许多社会工作者、教师和警察开始相信其真实性。他们虽然不相信世间存在着撒旦或魔法,但是相信确实有组织良好的撒旦教团在进行反社会和犯罪行为,所以必须要对其揭发、镇压和惩罚。这种观念带来一些可怕的司法误判,后来经过仔细调查发现这种撒旦教阴谋论完全缺乏证据。因此,“本书试图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种形象的信仰根源以及在欧洲语境下的发展过程,显然并不是为了唤回这种恐惧和仇恨,而是为了消除它”。(440页)
该书虽然没有全面、深入地讨论巫师审判,但是对于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在西欧出现的大量异端审判案作出了直接的判定,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审判:“对巫术的声讨和对魔鬼崇拜的政治审判,这两个事态的不断升级发展都伴随着对撒旦力量日益增长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早就存在,但肯定在这一时期因为大规模的异端和仪式性魔法的出现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61页)在十四世纪早期,教宗约翰二十二世认为仪式性魔法本质邪恶,更将私敌指控为恶意魔法的操控者,以此罪名为由烧死了一名主教。1326年教宗颁布法令,魔法终于被直接视作异端,将魔法作为政治指控的做法在邻近国家的王室中死灰复燃。“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重新出现的政治不安全感使魔法指控重新成为高层政治斗争的肮脏手段,并使魔法指控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下。”(256页)到了1398年,巴黎大学重申了“仪式性魔法得到了恶魔的协助,因此属于异端”的理论,立场不同的知识分子展开了论争和相互谴责。值得注意的是,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学者在1405至1425年间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以恶魔理论为将魔法作为政治指控服务。(258页)这成为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行动的开端, 从1424年的比利牛斯山和罗马开始,一直持续到1782年瑞士最后一次巫师审判告终,因所谓的巫术罪被依法处死的人数据称在四到六万人之间。虽然真实的数字可能不到一半,但这场大审判的性质非常恶劣,对统治者来说,消灭巫师只是实现基督教政治理想中的一环。

《毒药手帖》,[日] 涩泽龙彦著,余梦娇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版,216页,39.80元
涩泽龙彦的《毒药手帖》正如作者所言,是一部以逸闻轶事为中心串联起来的毒药文化史,读起来当然要比《巫师》轻松得多。不过,要把“毒药”这个主题从久远的古埃及、古希腊贯穿到今天,而且要把毒药、制作与使用毒药的人以及所有相关的知识、逸闻都收罗在十来万字的篇幅中,把“毒药”这一主题编织而成“一张小小的文化史壁毯”,也实非易事。更何况,在毒药文化史的背后其实就是人的历史和“神”的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对政治、伦理、宗教等领域中的人性的另类研究,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使毒药史所呈现的面相显得更为扑朔迷离。
早在古希腊时期,毒药就是人类故事中似乎必不可少的戏剧性情节的主角,是不祥的命运之神的象征,也是宫廷内斗中最有吸引力的武器。但是涩泽龙彦也从审美的视角为毒药涂抹上文艺的色彩,他在全书开头就说:“‘毒药’这个词,总是强烈牵引着罪犯以及浪漫主义犯罪小说爱好者的心。人们认为它拥有某种魔幻而魅惑的余韵。”(第3页)现实中的毒药案虽然没有这么浪漫,但是施毒方法的想象力还是很惊人的:将粉末状毒药藏在戒指的宝石部分;把毒药撒入准备端给对方的饮品中;将液体状毒药涂在针尖上,趁握手时刺入对方的皮肤;在对方会接触到的卡片、钥匙上事先涂抹毒药;手套、长靴、衬衫、书籍都可以染毒;蒸气也经常被用于投毒;还有把毒药藏进灌肠器里的做法;古代埃及法老会将长期食用微量毒药的女性作为礼物送给敌人,对方在接吻后必死无疑;甚至连生殖器也可以传播毒药。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劳就是因生殖器感染情妇体内的毒药而惨死……。(第6-7页)一个很明显的但不难理解的事实是,投毒者以女性居多,统计学的结论是百分之七十为女性,更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使用毒药的女性经常是出身贵族、容貌姣好、才智出众、举止优雅,对于许多男性来说这无疑带来更大的恐惧和战栗。这些投毒的女性一般会主张自己受到了迫害,无奈之下才犯下罪行,更有意思的是,她们常常会在法庭上装作突然激动而不省人事,或者被神经症折磨,以求给法官留下一个无罪的印象。(第9页)
到了二十世纪,这是一个有计划地进行集体屠杀的时代,毒气开始在现代战争和纳粹迫害犹太人中大规模使用,毒药的杀戮规模与邪恶性质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随着科技的发展, 杀虫剂、氰化物、病原体(病毒)和医药品等完全现代化的毒药给人类带来的危害甚至未被研究和开发它们的人们所清晰知晓。正如涩泽龙彦所说,“如今在现代文明之下的我们,全部的日常生活都如受了诅咒一般,暴露在多种多样的毒药危险当中。”(1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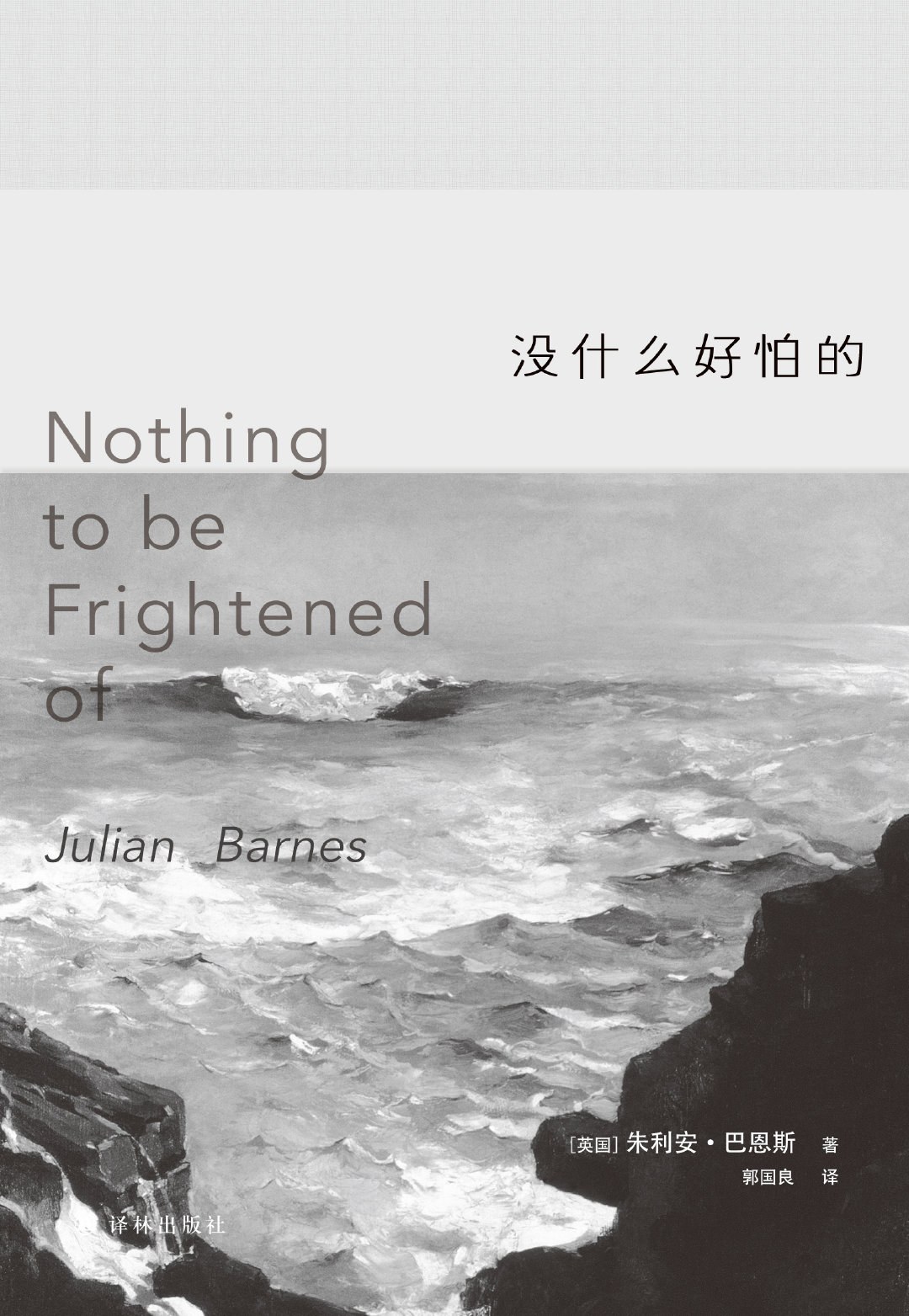
《没什么好怕的》,[英] 朱利安·巴恩斯著,郭国良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版,298页,49.80元
读过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石雅芳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5月)和《10 1/2章世界史》(林本椿、宋东升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3 月)的读者对这位后现代文学家的实验性写作风格应该不陌生了,但是他的这部《没什么好怕的》仍然会让我们有意外之喜:它似乎毫不炫技,让一切归于平淡,剩下的只是出奇的睿智和坦诚。关于该书,他说这不是“我的自传”,也不是在“追忆父母”。说到记忆,他哥哥质疑记忆的根本真实性,而他则是质疑人们渲染记忆的方式,这是两个关于记忆的很好的议题。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哥哥坚信记忆是会出岔子的,谁都不可信。那么记忆到底是什么?年少的时候往往认为记忆都是很真实的,就像储存于某一寄存处的行李,只要拿出票据就能取回自己的行李。成年后多了估测、善变和怀疑,“为了驱逐怀疑,我们不断复述那熟悉的故事,以顿挫营造刻意的效果,假装叙述的可靠性能成为真相的证据。仿佛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精准影像,而不是经过加工和渲染的摹本”。(44页)
毫无疑问,“死亡”是这部书的核心主题。从目睹家人的死亡、如何处理遗体、如何办理后事,谈到一家人的死亡观念和在现实中面对死亡的态度,在对遗物的清理中,对往事的发掘和对亲人的重新认识成为家庭记忆的论坛与答辩会,可以说是一部独特而真实的家庭死亡思想录。然后扩展到朋友和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以及各界名流, 把哲学、宗教信仰、政治伦理、文艺审美等等领域的死亡观全都煮在一锅里。
关于信仰,巴恩斯反对任何的宗教信仰。他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存在这么久,不仅仅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更是因为它被统治者和神父强加于人,成为一种社会统治的手段,还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所谓肩负崇高使命、反抗压迫者等等。(66页)他哥哥对童年时参加过几场正规的教堂礼拜的记忆令人吃惊:“我依稀记得我很困惑,好像一个小人类学家夹在一群食人族中。”他说自己没有失去过信仰,因为从未有过信仰。九岁那年他就意识到所谓的信仰其实不过是一派胡言,是因为在1952年2月7日早上九点,小学校长埃贝茨先生宣布国王去世了,“他去往天堂与上帝共享永恒的荣耀与幸福了”,全体学生为此戴了一个月的黑臂章。巴恩斯当时六岁,和他哥哥同在这间学校读书,但是他说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他只是由此谈到令自己最终完全放弃宗教信仰的青春之歌:“在家里卫生间里弓身俯在一本书或杂志上,我常对自己说,上帝不可能存在,因为如果说他是眼睁睁看着我自慰,这就太荒谬了……为何我认为上帝——如果他的确在看着我——一定不赞成我如此泼洒我的种子呢?为什么我没有想到,上天看到我乐此不疲地自渎却没有塌下来,这兴许是因为上天并没有判定它是罪孽?我也未曾想象,我已逝的祖先们同样也在微笑地看着我的所作所为:继续呀,孩子,你拥有的时候就尽情享受吧,一旦变成空洞的灵魂就无福消受了,所以,为了我们你再来一次吧。”(17-18页)上帝死了,你可以纵情地创造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本质”。于是“‘我是个快乐的无神论者。’之后什么也没发生——没有!”(21页)巴恩斯高兴的是以琐碎的小事为理由就放弃了宗教信仰,“我哥哥是因为怀疑乔治六世根本没有进天堂,我是为了不想在手淫时心有旁骛”。(53页)
不过,还有一件与信仰有关的比较严肃的事情。德国籍的新教皇宣布废除“地狱边缘”这一概念,巴恩斯由此想到的却是“这些年来,连地狱都已每况愈下,简直不像地狱了”。(95页)接着还想到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教皇国,牧师和秘密警察掌控一切,任何“思想家”都被视为危险阶层,所有非中世纪的东西一概不被信任,于是禁止铁路和电报侵入教皇的领地。教皇庇护九世在1864年颁布的《谬论举要》中宣称教会应全面掌控科学、文化和教育,禁止人们信仰其他宗教。他的结论是“宗教往往走向独裁主义,正如资本主义倾向垄断”。(97-98页)1789年,罗伯斯庇尔因抨击天主教会的腐败而举国闻名,他在三级议会的一场演讲中敦促全体神职人员通过出售其所有财产并把收益分给穷人这一方式证实自己的没有忘记初衷,他还表示“假如教会感到为难,法国大革命乐于相助”。(98页)从信仰联想到艺术,巴恩斯显然也有过很思考的深刻。“假如把艺术比作宗教,那么,它无疑不是传统的天主教(上面是教皇专制,下面是忠顺的奴役)。恰恰相反,它更类似早期教会:思想活跃,混乱,宗派林立。有一个主教,就有一个亵渎者:有一则教条,便有一个异端。如今的艺术和从前的宗教一样,假先知和假神灵比比皆是。……一群谄媚妥协的艺术家,像政客一般玩弄伎俩,骗取选票(和钞票)。”(90-91页)
上帝死了,但是死神还活得好好的。因为没有上帝、天堂、来世,因此死亡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巴恩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有了死亡意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每天都起码思考过死亡的问题,每天醒来后就会想到死亡。于是,就有了“死亡闹钟”。法国批评家夏尔·杜博斯造出了一个很有用的词:le réveil mortel,翻译为“死亡闹钟”。听起来有点像酒店叫醒服务,译作“死亡知识”“死亡觉醒”又太德国了。巴恩斯觉得还是“死亡闹钟”好——在陌生的酒店房间里,闹钟时间还是前一位房客设定的,你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被重重地抛入黑暗、恐慌之中,残酷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租住的世界。(27页)还有比这更形象的“死亡觉醒”吗?
巴恩斯在书中写了各种喜欢讨论死亡的群和朋友圈。福楼拜、屠格涅夫、埃德蒙·德·龚古尔、都德和左拉都是无神论者或者坚定的不可知论者,他们友好而不失条理地讨论畏惧死亡但不逃避死亡,福楼拜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口中念念有词,俯视着脚下幽幽的墓穴,以此保持镇静。”(29页)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既恐惧死亡,又恐惧死后复活,末日审判经常出现在他的音乐中。有一次他和诗人玛丽埃塔·沙吉娘及她母亲谈论死亡,边谈边吃着咸开心果,突然他停了下来大笑道:“吃了开心果,让我的恐惧都消失了。你们知道它上哪儿去了?”(30页)这我相信,在喝着啤酒、吃着芝士龙虾的时候谈论死亡,恐惧会消失得更快。正如巴恩斯说的,“对我来说,恰恰是死亡以骇人的事实定义了生命:除非你时常意识到死,否则你不可能懂得生命的真谛:红酒会氧化,玫瑰会在发臭的水中凋零,包括盛花的花瓶最终都将永远被丢弃,当在你走向坟墓的路上,除非你明白并感受到鲜花美酒的时光是有限的,否则其中毫无愉悦和趣味可言。”(150页)
巴恩斯很推崇的作家毛姆曾是一名医生,曾多次目睹病人死亡,他说在他们的临终时刻,我从没看到有什么可以预示他们的灵魂将会永存,“他们的死和一条狗的死没什么两样”。(106-107页)这没有什么不敬的,身在巴黎的莫扎特知道伏尔泰死的消息后写信给父亲说:“你大概已经知道了,那个不敬畏神的游手好闲的伏尔泰死得像条狗一样,像畜生一样——那就是他的下场!”巴恩斯接着说,“像条狗一样,没错。”(133页)巴恩斯知道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的死能够摆出更优雅的姿态,因此也越来越怀疑蒙田所列举的那些值得效仿的死亡:在临终时展现尊严、勇气以及对他人的关切,留下告慰人心的遗言……等等。他在二十多年前写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当人们谈及死亡时,他们只是信口说“这没什么可怕的”,现在我们再说一次,慢慢地强调“这没什么可怕的”。儒勒·雷纳尔曾说:“这世上最真实、最精确的词,就是‘没什么'。”(119页)是的,根本就“没什么”!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这没什么可怕的”,巴恩斯在《10 1/2章世界史》中对描写的那个面对风暴的船长就有这样的象征意义:他不停顺着传声筒往下发出命令,其实甲板下什么人也没有,引擎从来就没有安装,船舵在几百年前就断了。船长知道这一切,知道能否脱险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风暴与暗礁。他知道希望与奋斗就其面对的未知而言都是虚妄的,但仍然是必须的。就像对爱情一样,即使、尽管、因为爱情令我们失望,它仍是我们的唯一希望。“我们必须信奉它,否则我们就完了。”对于历史,巴恩斯的后现代历史观说我们都是历史的受害者、编造者和解读者,不管我们对历史如何失望,仍然应该相信历史不会对邪恶善罢甘休,因为“历史有的是时间”。(258页)因此,回到巴恩斯的《没什么好怕的》,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只要在生活中有令人感到害怕和恐惧的事物,就需要有这种安慰和鼓励的声音。“没什么好怕的”,不管是巫师还是毒药,已经拧上发条的死亡闹钟总会响起来,唯一的问题就是最后的“丧钟为谁而鸣”。
关于“最后”,我们似乎很难会想到巴恩斯说的那种最后——那么自然、真实和冰冷的“最后”。他说任何作家到最后都会只剩下一位读者,那位读者最后也终将死去,而且关于这位读者还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他没有向任何人推荐过你的书。最后,“正如每一位作家都会有最后一位读者,每一具遗体也都会有最后一位祭拜者”。(296页)其实,这个“最后”的意思就是任何人最后都会被彻底遗忘,地球上总有一天再也没有人知道你的书和你曾经存在过这样的事实。巴恩斯只是说了一个太简单的常识:根本没有永恒这回事。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部书的最后是怎么写的:“我希望,写下‘别了,自己‘还为时过早;我希望,涂抹监牢墙上的那句话‘我曾经也来过这儿’也为时过早。但是,写下列两个字并非仓促之举,我明白这两个字以前我从未放入书中。至少放在这儿,放在最后一页: THE END 。”(297页)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