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中):破除“别无选择”的魔咒
【主持人语】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已快2年,科学技术在疫情应对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彰显,但为抗疫所采用的诸种技术治理措施也引发不少争议和担忧。这引起了专门研究科技问题的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新冠疫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来自中国、美国和德国的3位技术哲学家对全球疫情技术治理展开合作研究,阶段性成果论文《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较》发表在《科学·经济·社会》杂志2021年第1期上。[电子版参见:https://www.nomos-elibrary.de/10.5771/9783748910961-301/editorial-der-kontroverse?page=0]他们的观点受到国际技术哲学界的强烈关注,9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技术哲学家发表了针对性的意见。整组笔谈以英文和德文发表于德国的《技术哲学年鉴2021》(Alexander Friedrich等主编,德国Nomos出版社2021年出版)上,所有作者均为国际技术哲学界声誉卓著的资深学者,内容涉及科学技术与疫情应对关系的各个方面,对于新冠疫情反思颇具启发。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刊发这组笔谈。整组10篇文章现分为上、中、下三篇,本文为中篇,包括三篇回应文章《公民自由主义的政治科学序言》《破除“别无选择”的魔咒:社会技术进步的集体概念》《病毒是催化剂,社会本身才是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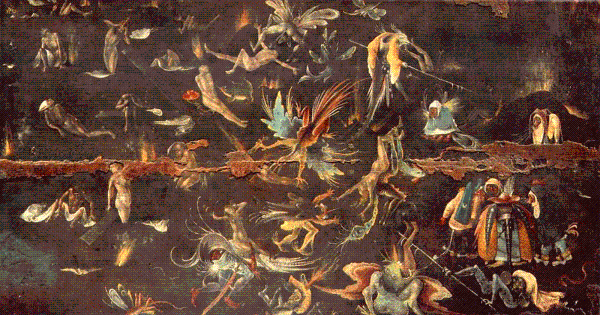
公民自由主义的政治科学序言
作者:史蒂夫·富勒;译:彭家峰
作者简介: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英国华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STS和社会认识论研究。
由于新冠病毒在第一年就演变为全球性疫情,人们对病毒传播过程中真正的科学不确定性与有效的政治沟通和政策制定的需要之间的笨拙应对(awkward fit)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际上,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相当不同的实验中充当小白鼠,这些实验基于大致相同的科学,只是被应用于不同的地理、政治和文化条件下。此外,虽然各国政府采取的行动显然会对其正式管辖范围之外的人产生影响,但并没有商定的标准来对应对此次疫情的“成功”作出跨国性判断。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每一次宣布(如果假设存在这种普遍标准),最后都会让世界上的一个或几个地区感到恼火,认为这是一种指手画脚(backseat driving)。
在20世纪初的德国,关于Volkswirstschaft(国民经济)中“Volk”含义的争论是一个有用的参考,尽管有些新奇。一方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韦伯兄弟(Max and Alfred),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Volk”视为一个大致相当于国家文化的概念,被理解为一种随时间演变的有机体。在任何时候,它都从与实际生活在国境内的民众那里获得其半自主式(semi-autonomously)存在。另一方是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创始人伯恩哈德·哈姆斯(Bernhard Harms),他将费迪南德·唐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招入他在基尔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哈姆斯对“Volk”的定义是: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民族国家的实际居民,以及他们为促进国家利益所带来的能力。[1] 这种对“Volk”概念的区分让人想起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之际,受过德国教育的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在他所谓的关于物种性质的类型学和人口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之间所做的区分。[2]对迈尔来说,概念视野中的这种“元科学”的转变是达尔文的最高成就。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们最终谈论的不过是一个由中世纪学者在“内涵”定义与“外延”定义之间做出区分的更新版本[3]——哈姆斯的“Volk”和达尔文的“物种”被外延地定义为一种表型体的种群(population of phenotypic bodies)。
我认为,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在论及应对新冠疫情时偏向于“Volk”的人口方面,而世界各地的责任政府则更倾向于类型学的方向。至少,当他们描述流行病学人口思维的“大方案优化”方式时,这两个概念都发挥了作用,这与作为特定知识社会的文化成就的创造性“拼凑满足”方案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人们可以超越这种二分,想象特定的文化可能将人口思维内化为集体自我理解的一部分。接下来便是对这一前景的探索,我称之为“公民自由主义的政治科学”。
当前政治言论的一个普遍论调是,政府必须平衡民众的健康和经济的稳健。当然,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声称他们正在取得适当的平衡。然而,当人们的文化自我理解包括强烈的公民自由意识时,也就是说,当一个群体把自己看作是自由个体的集合体时,这项任务就变得更加困难。美国、英国和瑞典在这场疫情中以各异奇趣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我将概述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不同方式,包括一些理论上的评论,它们最终将为这场疫情提供了一个哲学上的清晰视角。
与美国应对措施有关的大多数媒体和学术焦点都集中在唐纳德·特朗普对疫情严峻性的几近否认的态度上。这忽略了公民自由主义在美国文化中的根深蒂固。毕竟,美国是一个联邦共和国,这意味着各州州长对如何处理其管辖范围内的事务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对疫情的处理方式相当分散,其中对疫情更加重视的州则各自实行不同措施,但往往都是欧洲式的封锁措施。这就限制了任何中央政府对全国性的,更不用说全球性的疫情所能做出的有效反应。英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其特点是在任何危机中都应付了事。值得称赞的是,与特朗普相比,鲍里斯·约翰逊在其言论和行动中对其国家的公民自由主义传统更加自觉。虽然英国媒体的讨论非常关注“生命和工作”,但英国政府的目标是采取更成熟的方法。它鼓励而不是强迫人们做正确的事情,在政策执行前(如果能执行的话)宣传几天,以便人们能够习惯它们。令人震惊的是,反对党(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并不呼吁政府倒台。事实上,英国工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政府的努力,抱怨的也主要是信息传递的不清晰。在英国,同美国一样,无论谁在疫情期间执政,对公民自由的关注都是持续的。
瑞典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因为它在早期就公开认可了对疫情采取“群体免疫”的方法,而英国则以更低调的措辞呼应——但不久官方便收回了这一做法。起初,群体免疫和公民自由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明显。然而,从流行病学的人口思维和瑞典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自我理解来看,它将人们培养成负责任的个体,然后根据提供给他们的信息和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感,单纯地让他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在一次关于儿童权利的会议上,瑞典记者亨瑞克·伯格伦(Henrik Berggren)用 “长袜子皮皮”的故事阐明了这种意义,在这个故事中,国家代表皮皮逃离的父母,但他们给皮皮留下了一箱金币,用来管理她的事务。[4] 皮皮则以鲁莽和慷慨的奇妙组合迎接挑战。
这里所隐含的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可以作进一步讨论。它最终反映出公民自由主义中隐含的神学,也就是伏尔泰所嘲笑的“逃离的神”(deus absconditus):从第一个犯罪现场逃离的神圣罪人,以及创世(Creation)!这种有神论在美国的开国元勋者身上表现明显,他们认为人类管理者不应该比被管理者所信仰的神灵拥有更多权力。这是他们对霍布斯挑战的公民自由主义的回应,霍布斯认为上帝应该被一个世俗的国家所取代,在社会中拥有垄断性的武力。在他们看来,即使上帝不在了,人类无论多强大,始终都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容易看出这如何影响到启蒙运动中概率推理和统计人口思维的出现,更具体地说,它如何提供了冒险的动机,我称之为“主动行动”(proactionary)的态度。[5] 这就是“皮皮的金箱”,不过它现在由福利国家提供。它为她提供了鲁莽和慷慨,而这正是福利制度旨在培养的天生的自由主义者的标志。[6]
那么,这对当前的疫情意味着什么呢?
在最基本和看似微不足道的层面上,它意味着国家可以依靠充分提高其人口,使其在需要就民众行为发出任何进一步指令时信任国家。正如耕种作物和饲养牲畜的农业隐喻所表明的那样,国家所提供的是一种广泛的反应潜力,也许有点类似于创造性的“拼凑满足”。这就产生了失败的风险,而且会出现失败的情况。老年人和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会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死于感染新冠病毒。可以肯定的是,人口统计思维意味着——正如凯恩斯提醒我们的那样——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去。这是否等同于对那些无论如何都可能很快死亡的人采取的漫不关心的态度,无论是否存在新冠病毒?公民自由主义的政治科学并不允许对拯救所谓神圣的生命有太多的回旋余地。无论谁来负责,都会有血光之灾。
注释:
[1] See Dieter Plehwe and Quinn Slobodian: “Landscapes of Unrest: Herbert Giersch and the Origins of Neoliberal Economic Geography.”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6 (2019), pp. 185–215.
[2] Ernst Mayr: “Typological versus population thinking.” Evolution and anthropology: A centennial appraisal, ed. B. J. Meggers, pp. 409–12. Washington, DC: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1959.
[3] See Steve Fuller: “Our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humanity. Review of D. Chernilo, Debating Humanity,” Distinktion21/1 (2020), pp. 67–73.
[4] Henrik Berggren: The autonomous child and the moral logic of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6), unpublished.
[5] Steve Fuller and V. Lipinska: The Proactionary Imperativ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6] 同上, p. 76.
破除“别无选择”的魔咒:社会技术进步的集体概念
作者:克里斯托弗·科尔南;译:王誾
作者简介:克里斯托弗·科尔南(Christopher Coenen),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技伦理和技术评估研究。王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21级博士生。
这篇短文非常复杂,充满了各种想法,以至于想要回答所有相关的问题可能需要写几篇文章。因此,在这里我只讨论3个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技术哲学的作用相关,或者涉及多学科的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科学技术研究)的更广泛领域。关于这三个问题,我曾备受如下评论的鼓舞:
“这三种方法也有不同之处:“大方案优化”回到国家的行政实践、热力学、气体定律、统计人口科学(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特别是19世纪的情况,也回到一种特定的知识/权力统治制度,将克里斯蒂安·德斯顿、安东尼·福奇以及钟南山这类科学家提升到国家名人和权威专家的地位。从科学技术研究(STS)、建构性技术评估(TA)、共同设计(co-design)、开放科学(open science)和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的角度来看,令人震惊的是,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虽然公民和“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的贡献在“拼凑满足”和“实时响应”中显现,但这并不根源于关于在21世纪社会中广泛动员分配能力之最佳方法的讨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从具体到一般,从内部到外部:从这些学科和领域如何才能最好地促进“分散力量的广泛动员”这一更实际的问题出发,经由一个关于我们自我反思的问题——上述学科和领域自己的一些模型,它们已经被研发了几十年,本身并不显得过时——到这些研究领域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可能扮演的新角色问题,这可能正是我们的关键任务,使技术行动作为政治行动变得更加显见易懂,同时有助于破除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虚假的客观约束和别无选择(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魔咒,尤其是通过对于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的批判。
1. 公民STS
正如三位作者所言,这次疫情感觉更像是一场考验,人们的确可以认为,社会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比以往更多地暴露他们的问题和性格”,包括“社会技术世界的居住方式”。
这场疫情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一种趋势愈演愈烈,即许多人越来越公开地在阴谋论的意识形态中寻求逃避现实挑战的庇护。然而,这个避难所不再是一个安静的壁橱,而是一个由无数安静的壁橱组成的数字反公共场所,这些壁橱正逐渐失控,并越来越多地单独出现在街道上(通常地标性场所),就像它早已在议会和政府中所做的那样。然而,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这些现象,但这一趋势本质上是由无数技术(信息和通信)行为组成的,这些行为在不断增加,因为人们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少,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迫切希望创造意义。原先的日常生活在疫情爆发之前,很容易使公民在政治上墨守成规,在生活中秉持消费主义。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断所造成的压力下,各地的公民都不得不思考科学、技术和医学问题,以及各种与科学和医学有关的治理问题。
此外,正如我们从(大量)STS学术从业者组织的许多技性科学活动的公共参与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在围绕这些主题而展开的交流中的主要问题不是关于科学事实或技术选择的疑问,而是对科学内涵的根本误解,即科学思维以及科学与技术政治经济学。在一个一方面是“匿名者Q”[1],另一方面是对科学的老式和过时的尊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误解)的世界里,公民是STS方法的专家,了解科学、创新和卫生系统,以及科学如何运作,与参与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公民研究人员相比,我们更需要前者。技术哲学家可以在教育公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使尽可能多的人实践“公民STS”,从而使社会更好地抵御阴谋论意识形态的诱惑。这可能促成“21世纪社会中广泛分布的能力”的真正动员。
2. 疫情中的科学与后真相
然而,技术哲学家和其他学术STS专家真的能够承担起在这些问题上帮助公众启蒙的角色吗?STS领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三位作者所说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似乎与政治领域和公共价值观的讨论脱节,并与之对立”——在其核心技术哲学受到反技术治理和反科学主义推动力的强烈影响。弗兰兹·塞弗特近期撰文写道,在STS中,科学权威的瓦解传统上与科学的民主化同时进行,因此与进一步的“民主的民主化”同时进行;并且,他也提出了该领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延续过去几十年的这些范式的问题。[2] 根据塞弗特的分析,“真相之战”中的演员群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记得史蒂夫·富勒更早期提出的观点。塞弗特认为,对科学的怀疑(至少是作为一个系统)以前被视为民主化民主的机会,现在似乎对一个民主构成了威胁,而这个民主正受到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否认者的攻击,甚至是更绝望、更激进的现实否认者的攻击。塞弗特认为,现在就是这批人,他们正利用对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的(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怀疑来影射进化论、工业引发的气候变化,疫苗的功效或冠状病毒的危害,并且也正是这批人,他们是许多社会中最有发言权和最明显的反制度团体,目前只有反种族主义活动家与他们抗衡。塞弗特认为,这场疫情以及美国毫无希望的两极分化的政治局面(有人会说,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表明,对真相的基本共识的瓦解可能会成为民主秩序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塞弗特也不相信对科学的社会方面的批判性分析与科学与权力的交织是无关的,甚至两者交织在一起本身就是危险的;然而他强调,如果理想的科学民主化仅仅意味着废除和相对化科学权威,这最终将科学专业知识(包括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与日常思维等同起来,无论其“技术性”如何,任何决策过程将完全取决于政治利益,并且在公开辩论中扼杀任何基于事实的辩论。正是基于他的这种观点,对科学真理进行积极的、建构主义的批判之局限性由此变得清晰起来。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塞弗特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他对当前科学敌人的描述。事实上,这些人往往是理性和人性的法西斯之敌。然而,这些人攻击的不是技术治理思维定式。例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乐见自己的虐待狂冲动被欧盟境内的强制措施所满足,而这些强制措施皆出自于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势。
在反科学的阴谋论思维的重锤和近年来日益受反民主右翼势力控制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治机构的铁砧之间,那些被三位作者称为“通过承认技术上的必要性来实现团结的‘理性的’人”,可能会因为没有对科学和真相的概念采取明确和强有力的立场而被击得粉碎。最近,某些环境保护运动重振了一种非常过时的科学信仰——但它只是从几十年前的学术和社会运动话语来看是非常过时的,而它本身是基于一种更古老的技术哲学。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的、往往是超人类主义者的技术未来主义对科学抱有类似的坚定信念,然而与之相伴的却是对技术进步所持同样过时的信念。这两种运动,以及当前其他的非法西斯的学术和政治运动,似乎正在向一种共识靠拢,这种共识将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与文化进步理念(就迄今为止被边缘化和受压迫的社会群体的成功身份政治而言)以及或多或少的生态技术治理解决方案结合起来,以应对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性统治。
我们的确可以(不仅仅是在当前疫情之下)“将我们的技术治理状态描述为一种被流放在国内、对现在失去耐心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失去未来和过去等于失去了政治”,并且“剩下的只是一种对必然规则的反抗”,或者我们可以说是,选择“礼貌的沉默”。
20世纪的技术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反应了技性科学的社会崛起、随之而来的技性科学自身的危机以及与之相伴的现代人无家可归的问题——现代人固然都是“在世”的,然而,由于与过去另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或“超越”的世界纠缠在一起,他也是被流放的。由于目前科学思想的公众理解的下降以及理性敌人的崛起——与两次大战期间不同——至少对北美和欧洲的所有社会,特别是古典自由民主国家产生了显著影响,科学正在失去其指导社会制度的特性。公民科学和公民STS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然而,倘若没有产生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替代当前的社会秩序,那么技术哲学和STS必将很快发现自身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除了帮助重塑科学的权威之外,无法做任何合理或明智的事。有一个可疑但非法西斯的信仰作为一个人代表理性的人采取行动的动机,总比完全没有这样的动机要好。
3. 关于行动
作为一个结论,我在这里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个粗略草图,它勾勒出我们的领域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可能扮演的新角色。在自由民主的一日(光阴)结束时,破除虚假客观约束(Sachzwang)和“别无选择”的魔咒将归结为可能存在怎样的资本主义替代方式的问题。除了将(其他)公民引入我们自己的领域,不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或业余参与者或替补专家,而是作为创造此类替代方式的同志,STS的一个主要目标可能是与理想主义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像某些环境保护运动结成新的联盟。为了发挥这样的作用,技术哲学最杰出的任务之一必须是再次阐发社会技术进步的综合概念,以使我们的技术星球真正地、可持续地宜居。谈及道德反思,至关重要的是,要将其置于已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并避免任何基于可疑假设的争论,这些可疑假设都均出自于一种“规定的”资源稀缺(例如,在当前关于“分诊”的讨论中,该术语的使用与许多国家针对卫生系统发动的经济战争相呼应)。
为了能够真正有助于“打开客观约束的黑箱”,STS需要重新发掘他们自己的领域。如果成功的话,这样的再发掘也可能让技术哲学在重新获得我们“为自己想象出另一个世界的能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注释:
[1] 译者注:“匿名者Q”是一种极右翼阴谋论,其认为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个反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支持者的深层政府。这个理论最早于2017年10月出自4chan讨论版中的一个署名为Q的匿名用户,“Q”这个名字出自美国机密许可中的最高级别“Q级许可”。(参考自“维基百科”)
[2] Franz Seifert: “Die Grenzen akademischen Zweifels”, science@ORF.at, 14.10.2020, https:// science.orf.at/stories/3201963/ (2020年12月18日访问).
病毒是催化剂,社会本身才是疾病
作者:兰登·温纳;译:王誾
作者简介: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技术哲学和STS研究。
伴随新冠疫情的发展,寻求在其上升、蔓延和最终结果中吸取教训无疑需要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政策制定者、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的共同努力。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和人口应对疫情爆发及其带来的严峻挑战所采取的不同方式。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一些初步的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今后的思考。
在许多重要方面,SARS-Cov-2不仅被视为与Covid-19感染相关的众多物理疾病的原因,而且成为广泛分化社会的反应与策略的强催化剂。一开始出现的突出问题有以下这些:谁将在确定关键问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有哪些可以被设想和尝试的选项?多快采取行动?因此,将采用什么方法来监测病毒的传播?应该部署哪些预防和治疗感染的措施,实施范围有多广?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将如何回应科学家和政治人物提出的倡议?重要机构会以何种方式改变其基本形式和运作方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提出了关于公民文化特征以及如何比较不同特定文化的基本问题。
鉴于到2020年2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可能爆发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因此有可能识别和比较一些基本的应对模式。一些国家很快就理解了它们所面临的基本挑战。出于各种原因,其他国家在认真对待这一威胁方面表现得相当缓慢。一些人很快制定并实施了切实可行的战略,而另一些人在关于哪些理论可以解释大流行即将到来(或想象中的消失)的争论中犹豫不决。凭借可信赖的医学专家和政治领袖,一些社会能够就“在当前情况下最有效”的政策达成相对不正式、广泛的共识,特别是在没有疫苗或有效药物的情况下,将社会响应——封锁、隔离,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等——作为唯一的实际措施。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政治分歧严重,无法采取广泛的、协商一致的社会措施的国家——在合理反应和适用战略的问题上犹豫了数周、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在我们等待更可靠、更长期的信息来源时,一个合理的策略是将那些在遏制病毒及其影响方面做得相当好的国家和地区与那些疫情防控显然没有那么出色的国家进行比较。因此,似乎有几个地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新西兰、韩国、冰岛、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偶尔会出现起伏不定的情况)成功地将病毒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另一些地方——包括英国、阿根廷、巴西、西班牙和美国——从总病例和死亡人数来看,情况非常糟糕。
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比较涉及台湾地区和美国的战略。我们知道,双方领导人在2020年1月都收到关于该疾病的可靠信息。当时,台湾地区建议采取系统性整体措施,涵盖医疗专业人员、公职人员以及岛内全体民众:严格控制出入境,检验和追踪感染病例及其传播的,保持社交距离,严格限制社交场所(学校、餐厅、酒吧、办公室等)的活动,日常佩戴口罩的要求等。这些措施很快就在岛内受到欢迎。台湾人充分意识到2003年SARS爆发的类似恐慌,齐心协力采取了有限但有为的实际措施,结果一开始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1]
相比之下,拥有3.31亿人口的美国在2020年初面对新冠病毒的威胁,曾冒着严重困难来制定出一套连贯有效的计划。但是,经济不平等的差距持续扩大,部落主义的政治分歧不断加剧,政策斗争愈演愈烈,种族冲突此起彼伏,总统领导层动荡不安,包括对于科学专家的公开不信任,国家在一系列零散的、不集中的措施中步履蹒跚,而将责任推给50个州的州长,也推给分散的、基本上不协调的机构的自行选择,以及全体人民的突发奇想。面对需要普遍佩戴口罩的专家建议,许多人(尤其是唐纳德·J·特朗普的支持者)认定佩戴口罩是(1)一种不具吸引力的时尚行为,(2)侵犯个人自由的侵权行为。特朗普本人曾通过谴责并拒绝佩戴口罩来强化这种信念。这个国家的其他混乱迹象包括:不佩戴口罩人群的经常性集会,与“开放经济”相关的聚会,以及公开宣扬宝贵的公民自由,这些事件最终被认定产生了“超级传播者”,增加了新冠病毒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速度。虽然还有其他社会和生理因素与之相关,但该国反应严重不集中造成了可怕的人员伤亡。
当然,对台湾地区和美国的疫情进行统计比较是一件冒险的事。两者在地理面积和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个是相当小的岛屿,另一个是广袤大陆上的一片开阔陆地。它们在各自的人口、经济、政治制度和基本公民文化方面也拥有相当不同的背景。当然,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特定紧急情况下倾向于做什么的决心都特别坚决。尽管如此,一些简单的、显而易见的计算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差异。美国的人口大约是台湾地区人口的14倍。按照人口数字比例进行简单计算,如果美国疫情应对效果与台湾地区相同,那么美国死亡人数会很少,而不是2020年底的估算一百万人。[2]
曾帮助我找到基本数据并进行对比的台湾地区学者陈信行也分享了一个备受认可并十分有趣的特征,即台湾地区如何能够将病例数量和死亡人数控制在如此微小的水平——“在我们的街道上,在公共交通和公共建筑中,人们可以看到小老太太走来走去,她们会对任何不戴口罩的人大喊大叫,晃动雨伞!” 因此,台湾地区的病毒防控策略的日常运作包括一种强硬、高效(或许出乎意料)的社会强制手段。唉,当前美国缺乏如此广泛接受、有效的理解以及合作的策略,将这个国家从新冠疫情的严峻现状——已经占据整个国家视野的疾病、死亡、悲伤与社会毁灭中解救出来。事实上,美国公民宁愿在教堂、酒吧、餐馆、运动场等场所举行熟悉的聚会,也不愿(保持合理的距离)聚在一起,以避免致命的感染。面对最可怕的后果,许多美国人仍然拒绝承认有必要采取个人行动来保护自己同胞的福祉。随着尸体一天比一天堆得高,强调“这对我来有啥意义”在大部分应对新冠疫情的全国性反应中仍占据上风,这是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白宫强烈支持的一种疯狂的狂热。
对全球范围内其他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比较无疑会揭示出对新冠病毒的各种应对以及截然不同的后果。我在这里的评论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探索,从字面上“揭露”了一个国家的困境,这个国家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资源最充沛的国家,但在与微小微生物的到来作斗争时彻底失败了。一个合理的诊断将在美国公民文化自身的条件下找到大流行的最终根源。
注释:
[1] 译者注:作者举台湾地区为例,是为了与美国形成比较。此文撰写时情况与发表时差别很大,当时特朗普还在任。但笔谈坚持发表时保持收稿状态的原则,以看看作者的观点最终会得到多少印证。台湾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并没有保持住初期的良好态势。截至2021年秋,台湾地区累积近16,000例确诊病例,其中死亡828例。一方面说明疫情防控任务的复杂与艰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台湾地区的疫情防控后来出现了问题。
[2] 译者注:按照当时的疫情估算至2020年底美国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将达到100万,实际上截至2021年8月美国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64万多例。
作者介绍:
斯蒂夫·富勒(Steve Fuller),世界著名STS学者,英国华威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认识论孔德讲席教授。富勒最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和匹兹堡大学接受历史、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方面的培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他在“社会认识论”领域的基础性工作,这是由他于1987年创办的一份季刊的名称,同样也是迄今所著25本书中的第一本。近年来,他的研究一直关注“跨”和“后”人类科学和文化趋势下的人类未来,以及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未来。富勒的最新著作是《后真相:知识作为权力游戏》(2018)、《尼采的沉思:超人类时代黎明时不合时宜的思想》(2019年)、《后真相状态玩家指南:游戏名称》(2020)。
克里斯托弗·科尔南(Christopher Coenen),具有国际影响的科技伦理学家,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技术评估与系统分析研究所(ITAS)“生命、创新、健康和技术”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自2013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纳米伦理学:新技术与新兴技术研究》期刊主编。他拥有政治科学的背景,在技术评估方面的工作重点是新技性科学发展的伦理、社会嵌入、政治和文化相关性,研究、开发和创新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以及乌托邦传统语境中的跨人文主义的哲学和历史方面研究。他目前在KIT-ITAS的任务包括协调欧盟ERANET-NEURON跨国研究项目FUTUREBODY。
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世界著名技术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专注于围绕现代技术变革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作为科学技术学系的教授,他拥有纽约特洛伊伦斯勒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托马斯·费兰讲席。2020年,他被科学社会学研究学会授予约翰·德斯蒙德·贝纳尔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鲸与反应堆:在高科技、民主与技术的时代探索极限》(第二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