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工作”简史:人类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不是稀缺,而是餍足
我们将气候变化失控的时代命名为 “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命名已经告诉了你一切关于我们人性的悲哀。人类显然是贪得无厌的消耗机;我们正在以我们的方式吞噬着生物圈。人类世这个表述似乎在暗示,过度开采石油燃料带来世界经济的不断扩张,使人类世这个概念成为可能——这样的扩张方式已经被刻入到了人类的基因里。从这个角度来看,试图扭转全球变暖方向很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可是,难道无休止的经济增长真的是我们人类的决定性特征吗?
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既没有经历过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没有担心过其消失。我们的天性并不是每天劳作很长时间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东西,而是做最低限度的必要工作以保证较好的生活。
这是南非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的新书《工作:从石器时代到机器人时代的深刻历史》(Work: A Deep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Robots)的核心主张。他在书中问道,我们是否可以学会像我们的祖先那样生活——也就是说,重视自由时间而不是金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踏上了穿越人类生存30000年历史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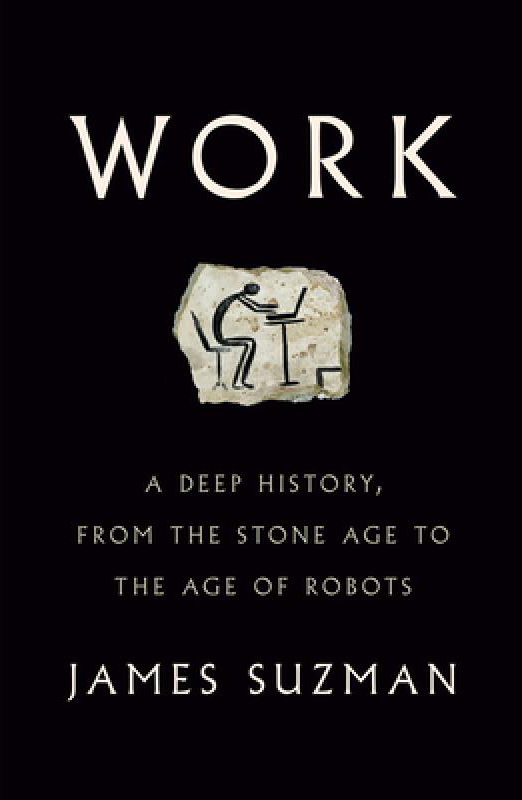
在探究过程中,苏兹曼充分地运用了他自20世纪90年代自己与纳米比亚东部(Eastern Namibia)的布希曼人(Ju/'hoansi Bushmen)共同生活和查阅相关文献的经历。布希曼人的祖籍在非洲南部的喀拉哈里沙漠(Africa's Kalahari Desert)。布希曼人是世界上仅存的一些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s),尽管现在只有很少的布希曼人还在坚持使用传统的觅食方式。
苏兹曼在《工作》一书中对他在钻石开采公司戴比尔斯(De Beers)担任企业公民事务总监以及后来担任全球公共事务总监的岁月提及较少。他于2007年担任该职务。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博茨瓦纳政府将布希曼驱逐出喀拉哈里沙漠,以便戴比尔斯公司在那里进行采矿作业之后,为了回应公众的抗议,该公司将其对一个矿床的所有权卖给了竞争对手GemDiamonds(GEMD)公司,后者于2014年在布希曼以前的狩猎地开了一个矿。该公司后来关闭了该矿场,后在2019年又将其出售,据报道说该公司在这个项目上损失了1.7亿美元。
苏兹曼受雇于De Beers公司,该公司花费巨资进行广告宣传,使世界上的中产阶级相信,钻石属于最稀缺的宝石之一,尽管钻石是一种最常见的宝石。虽然苏兹曼很少提及他的工作,但是其工作经历也可能在书中会有所体现。苏兹曼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现有建立在市场上的稀缺性经济学(scarcity economics)的支配地位“,从而让人类逃离“因稀缺感而带来的无休止的经济增长需求”这一思想陷阱。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思想介入,它也揭示了现代经济学和人类学在作为思考气候危机导向时的限制。
我们30万年的人类历史,有95%的时间里,人类都是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生活,饮食包括水果、蔬菜、坚果、昆虫、鱼和一些野味。自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以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想当然地以为,对于我们的祖先以及后续像他们一样生活的狩猎采集者来说,保持生存是一项耗费全部精力的活动。苏兹曼解释说,近代的觅食者似乎“长期处于饥饿的边缘”,“被持续的饥饿所困扰”。
这样贬损采集狩猎者生活的观念在西方旅行叙事题材小说以及后期民族志研究中找到了广泛的支持。探险家们将现在的狩猎采集者认成了活化石,并将其视为是早期时代的工艺品。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狩猎采集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试图在相反的历史条件下极力生存。像殖民帝国和后殖民国家一样,不断扩大的农业社区以暴力的方式将大多数觅食者赶出了他们长久以来的家园,迫使他们进入更边缘的地区。西方的报道让人们误以为这些被剥夺权利的难民的生活就像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的生活一样,而事实上他们的生活通常要艰难得多。
一些持不同想法的思想家为这一通常充满蔑视的主流观点提供了一个持续的替代方案。例如,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认为觅食者是现代人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不是我们不堪回首的起源故事。在20世纪,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继续这一传统。他们反驳了种族主义者和基于阶段性的人类进化理论,表明觅食者拥有复杂而智慧的文化。这些思想家是苏兹曼观点的重要先驱,但是在《工作》一书中,他并没有采用他们的想法。
相反,苏兹曼关注的是相对较新的 “狩猎之人”会议("Man the Hunter" conference),这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等共同组织的会议。这次1966年的会议标志着人类学家将觅食者作为经济元素进行思考,这是决定性的转变,而也这正是苏兹曼想强调的一点。李一直对非洲南部名为“孔”(Kung)的布希曼人进行研究,这是一个Ju/'hoansi布希曼的旁支民族。李表明,“孔”人只通过 “适度的努力”获得他们的食物,使他们比西方先进工业社会的人拥有更多的 “自由时间”。他认为,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也可能是这样的。
这个研究结果可能暗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对李的同事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说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一直持错误的观点。使用现代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家已经证实李和萨林斯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他们可能低估了觅食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对于早期人骨的化学分析已经确凿地证明,早期人类并非一直在饥饿的边缘徘徊。相反,尽管工具环境简陋,他们吃得还是很不错。那究竟是什么给予了早期人类这样相对舒适简单的生活环境呢?苏兹曼解释说,早期历史的转折点在于人类学会了使用火的能力。这就给予他们“几乎无限的能量供应”,从而减少了他们的劳作。
火使食物变得容易消化,当我们烘烤一头猛犸象,或者一堆胡萝卜,烘烤过程中产生的卡路里量远高于生的食物。获取这些额外热量的能力使人类在进化上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有优势。黑猩猩几乎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觅食,而早期人类每天只需几个小时的觅食就能获取他们所需的热量。
对火技术炉火纯青的使用帮助人类从根本上增加了自由时间。苏兹曼主张,正是因为自由时间的增加,所以后期才塑造了人类文化的进化。在闲暇之余,人们可以长时间与他人一起玩耍,这帮助了语言、叙事和艺术的发展。同时,我们知道了要照顾那些“老得无法养活自己的人”。这是我们与其他少数物种共有的特征。
火的使用同时在其他方面帮助我们变得更有社交性。近期出土的证据表明,早期人类并不像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长期以来认为的那样,在其生存的整个过程中一直生活在小群体中。相反,当食物资源相对匮乏时,人们会彼此间保证足够的距离,从而更加容易的确保食物的获取。相比之下,当食物资源丰富时,早期人类会大量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短暂的社会形态。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山丘上(Göbekli Tepe),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由复杂圆环和巨石组成的巨石阵。在一万年间,石阵被数次掩埋并重建,且建造时间是农业社会出现之前。
种种发现支持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论点,这颠覆了我们对过去人类深层历史的所有看法。狩猎采集者并没有长期食不果腹,也没有使自己工作到筋疲力尽还没能获得持久的安全感。相反,他们的后代,农业时期的人类才是这样度过的。与猎人相比,农民的生活方式用托马斯·霍布斯的名言来说,就是“肮脏、野蛮且短暂的(nasty, brutish and short)”。正如苏兹曼所解释的那样,我们对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民的相对财富的理解的变化使得在使用火之后三个主要的转变——(在苏兹曼看来是)农业、城市和工厂变得更难解释了。它们的出现不能被讲述为一个人类摆脱经济贫困的进步故事。
要知道为什么关于人类起源的辩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你只需要翻开任何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页。这里你便会发现“稀缺性假设(scarcity postulate)”,即人类有无限的需求和愿望但资源数量有限的理论。每当你打开你的银行app,发现你只能负担你放在网上购物车中的一部分东西时,你就会体验到这个原则的真实性。这就带来了一系列无休止的计算。为了拥有这个,你必须放弃那个。
经济学将自己定位为研究我们在稀缺性的限制下做出的选择,即,如何促进我们的生产能力的分配。经济效率的每一次提高都会使这些限制松动一点,所以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在不剥夺其他人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的情况下多满足一些自己的欲望。为什么少数富人能够在世界穷人实现基本的经济安全水平之前满足他们的许多奇思妙想,这一直是经济界的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但经济学家向我们保证,无论如何,全球贫困的唯一长期解决方案是更多的经济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一个漫长的经济扩张的故事,好像我们作为人类的任务一直是而且永远是挣扎着摆脱贫穷从而获得更多的东西。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会给我们思考气候变化,以及威胁人类福祉的生态威胁,如过度砍伐和捕鱼,带来极恶的影响。如果面对这些威胁意味着使用更少的东西,那么在经济学家的眼中,这种限制只能是人性的倒退和反叛。
支撑这种标准经济学观点的人性论述,正是苏兹曼的人类学证据所允许他拒绝的。在现实中,稀缺性假设只适用于人类存在的特定时期。在我们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都认为自己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家庭将满足这些需求的工作进行分工,当工作完成后,他们就收工了。
当古人们发现自己拥有丰富的资源时,他们通常不会把这些资源看作是为经济扩张服务的,而是用于举办大型的聚会,就像在哥贝克山丘上(Göbekli Tepe)或者在巨石阵上发生的那些事一样。在许多文化中,在节日里赠送甚至以仪式性的方式毁掉自己的财产,是彰显自己财富的一种常见方式。而世界各地的人们继续把他们微薄的收入花在精心设计的婚姻庆典和葬礼上,这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是反常的。

哥贝克山丘巨石阵
对苏兹曼来说,人类学对我们前稀缺时代(pre-scarcity)的洞察力为经济学中的后稀缺传统(post-scarcity tradition)提供了支持,他将这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研究联系了起来。凯恩斯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在经济衰退期间,国家应该进行赤字支出,而不是平衡预算。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提出这一论点时,凯恩斯不仅希望稳定西方经济,还希望经济有所超越,从而进入一个后稀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经济困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人类的意识中消失。凯恩斯断言,要想设想这种替代方案,经济学家就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学的本质。
如果你试图盘问人们的偏好来弄清楚他们为什么想要他们想要的东西,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会认为你极度可笑。正如苏兹曼所指出的,凯恩斯并没有那么草率。他对人类欲望本质的见解在人类学中极为精明,他把欲望分为两种类型,他称之为 “绝对” 需求("absolute" needs)和 “相对”欲求("relative" wants)。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绝对的需求可能包括像清洁的水、公寓、跑步的衣服和公交车卡。而相对欲求指的是那些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东西,如奢侈品和高端的教育。我们不可能都是上层人士,就像我们不可能都高于平均水平一样。基于社会地位带来的欲求不同,欲求可以是无限的,而绝对需求是有限的。
实际上,长期以来的技术进步已经使我们有可能花费少量的工作时间去换取绚丽的方式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凯恩斯预言,到他孙子的那一代,我们将拥有大量的建筑、机器和技能,以克服任何真正的资源匮乏,从而满足我们的需求。(包括像21世纪人们对智能手机这样的新需求)。
当然,我们的许多愿望可能仍然没有得到满足。但在凯恩斯看来,愿望大多是对地位的渴望,而不是对财产的渴望。给每个人一双Gucci休闲鞋也无济于事,因为一旦每个人都有一双,它们就无法作为地位的象征品。只有减少不平等的程度才能缓解整个社会的地位焦虑,因为每个人的地位将相对变得不那么重要。凯恩斯认为,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绝对需求的满足,人们将减少庞大的工作量同时不再对生活感到沮丧。取而代之,人们将把多于的精力用在各种“非经济目的”上。从而,凯恩斯认为,在未来的后稀缺社会中,人们可能很享受工作,并且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
对苏兹曼来说,他认为凯恩斯关于未来工作市场的见解是机缘巧合。当凯恩斯 “第一次描述他的经济乌托邦时”,苏兹曼指出,对采集者社会的学习只是在新兴社会人类学学科中的冰山一角。直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去世后的20年,我们才开始了解到,在我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实际上每周工作时长仅约15小时。凯恩斯对后稀缺性未来的愿景,更像是对稀缺前历史的复苏。人类的 “最根本经济问题”根本不是稀缺,而是餍足。
苏兹曼2017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不富余的富裕》(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提出了一个令我们深思的问题。一旦日常工作不再是证明我们身份的核心,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那里学到什么?
而续集《工作》一书主要关注的是一个相反的问题。尽管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没必要那么努力去工作,但为什么我们仍然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工作身份?在凯恩斯自己假设的孙子们(因为他没有直系后裔)长大、变老、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很久,我们还在继续长时间工作,消费越来越多,我们对生物圈带来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苏兹曼写道:“人类,‘显然’还没有准备好申请其集体养老金。”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用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换取更多的自由时间?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中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他在1958年对战后美国经济进行了研究。研究中,他提出,凯恩斯低估了我们可以被操纵从而把相对欲求视为绝对需求的程度。这样的转变主要是通过广告,像戴比尔斯这样的公司在我们身上创造了我们以前没有的欲望,然后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满足这些欲望,我们必须购买他们的产品。由于我们购买像钻石这样的贵重物品主要是为了保持或提高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 “跟上琼斯家的步伐[keep up with the Joneses]”),但一旦有太多的人获得这些物品,它们就会失去神秘感。然后,新的、更难获得的宝石必定会取代已经失去光泽的旧宝石。
对于加尔布雷思来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写作中提出,我们选择这种非理性的、无限的生产政策的原因很清楚:重点其实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无论如何,大多数需求都是制造出来的),而是为了保持工人就业和工资增长。换句话来说,扩大生产服务可以分散人们对经济再分配这一棘手问题的注意力。只要每个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我们就不会太担心谁比谁拥有更多。
但在一个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不平等加剧的时代,加尔布雷思的解释显得不再有说服力。苏兹曼解释道,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开始看到 “大脱钩”现象,既富人的收入在加速增长,而其他人的收入增长则急剧放缓。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应该被富裕的国家政体视为问题所在,然而我们的平均工作周并没有缩小——事实上,在美国,它已经延长了。
苏兹曼借鉴了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解释来补充加尔布雷思的叙述。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书中,格雷伯详细介绍了充斥在经济中的大量无意义的工作。比如只用按按钮的人,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的人,种种这样的工作并不会给经济带来实质意义上的价值。然而,格雷伯认为,我们的经济非但没有剔除这类工作,反而似乎在每个角落都能找到它。格雷伯假设,大量无意义的工作间接导致了经济金融化。随着经济变得更加注重抽取租金而不是新的生产,社会看起来就更像是新封建社会(neo-feudal),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即精英们雇佣了很多无用的下属作为展示他们财富的方式。
苏兹曼对非理性的工作形式为何在整个经济体中激增有自己的答案,但他从一个新奇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农业革命以来,即使我们不需要工作我们也一直在工作,这是因为宇宙的物理规律迫使我们这样做。这个答案非常奇特,因为它从生命本身的背景条件来解释人类社会最近的一个趋势。苏兹曼本质上认为,大自然已经为我们设定了程序,就像它为其他所有生物设定的那样,我们需要用多于的工作去消耗我们机体内剩余的能量。由于有很多可用的能量,但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们就通过工作来释放我们内心的紧张情绪。
苏兹曼似乎是通过以下方式得出这一结论的,既然我们人类的天性是不做超过我们需要的工作,而是把时间花在让我们快乐的追求上——比如和朋友们在一起,做饭和吃饭,唱歌睡觉。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没这么做,一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机制在我们体内起作用,推动我们劳动,直到我们的精疲力竭,而不是把我们的剩余能量用于追求快乐。对于苏兹曼来说,这种更深层次的机制最终一定是定位在生物学本身的层面上。
这些论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关于死亡驱力=的描述,苏兹曼推测“生物系统(biological systems)”很可能同样是自发出现的,因为它们在消耗热能方面比很多无机形式的效率高很多。事实证明,生命体就是一个创造熵(entropy)或产生无序的省力装置,在加速宇宙热死亡的进程中,体能系统便会调用这种装置。苏兹曼认为,生命更深层次的目的正在以多种方式自我呈现,而我们刚刚开始理解这一点,即作为工具为“熵,诡计之神 "服务。
例如,从达尔文的工作成果中,我们已经了解到雄性孔雀壮观的尾羽是它们争夺配偶的一个进化结果。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羽毛更漂亮的鸟类在和羽毛相对差的同类相比时,并没有获得交配优势。苏兹曼断言,像孔雀尾巴这样高能耗的进化特征,除了“消耗能量”,摆脱过剩能量之外,没有其他功能。丰富滋生炫耀。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人类生活中,在某些地质层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 “阿舍利手斧(Acheulean hand-axes)”。我们的祖先显然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长时间用力敲打岩石,把它们磨尖。早期人类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各地制造和丢弃了大量这样的工具。问题在于阿舍利手斧作为手斧来说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根据荷兰人类学家雷蒙德·科比及其合作者的一篇有趣的论文,苏兹曼认为,这些很像孔雀尾巴的斧头的主要用途是为了消耗多余的能量。生物学将我们的程序设定成了这样,就像孔雀,当我们有“剩余能量”,我们"按照墒定律消耗它"。

阿舍利手斧
苏兹曼继续说,同样的热力消耗原则在农业的起源以及后来城镇和城市的建设中同样起到了作用。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告诉我们到某个点就不要再工作了的人性已经被我们更深层的工作到死的本性推翻?
苏兹曼认为这两个原则,就像弗洛伊德的 “爱神(Eros)”和 “死神(Thanatos)”一样,在人类的内心深处争夺着最高的地位。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技术上的突破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生产的完全自动化,这将使大多数人再也不用工作了。这也是我们突破凯恩斯的后稀缺社会的可能性。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的近代政府还在固守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概念。这种执念体现出了更加深层的生物力量,这可能会导致失控的气候将我们摧毁。
令苏兹曼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到达凯恩斯的后稀缺性未来?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两代经济学家。但是,苏兹曼的回答虽然具有启发性,但最终并不令人满意。所有的生命都可能会遵守热力的命令来消耗剩余的能量,但人类肯定可以找到其他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人们甚至可以每天举办派对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继续充当后资本主义的工作齿轮。但是社会必须保持现状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们最好从凯恩斯本人身上寻找答案。凯恩斯远远没有把每周15小时工作制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进化结果。在写完关于后稀缺性可能性的文章后,他把余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释那些阻碍人类到达到后稀缺的力量。
凯恩斯认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不再能快速增长以维持对劳动力的高需求,这种现象被他的弟子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称为“世俗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凯恩斯说,在我们生产出足够的建筑、机器和设备来满足全人类的需求之前,这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将低于平衡私人投资者的风险所需的水平。换句话说,早在我们达到后稀缺性之前,资本主义繁荣的引擎就会让位。其结果不是所有人都减少工作周,而是许多人就业不足,其余人工作过度。
当人们考虑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下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有更多的经济学家说凯恩斯是正确的。由于已经有如此多的生产能力,购买新工厂和设备的回报率已经降为低等级。私人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投资于经济的扩张,所以经济增长率下降,平均失业率上升。
各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让我们停滞不前的经济重新走上正轨。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率,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试图通过放松经济管制,减税,减弱公会的力量来吸引更多私人投资者进行投资。这样的做法不但增加了低质量的工作,同时导致了不平等的增加。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恢复经济增长的引擎却没有什么作用。
凯恩斯认为停滞将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这种想法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他与其他悲观的科学从业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像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样,凯恩斯将停滞视为一种机会,而不是一场悲剧。密尔在19世纪40年代写作时,曾经期待着经济增长的结束。他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人类日以继日的劳累,这是值得怀疑的。” 一旦私人投资的流量降到几乎停滞,穆勒将其称之为“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静止状态的出现可能会最终让社会开始利用其财富来改善普通人的命运。为了创造这样的情况 ,我们需要增加公共投资: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并转变所有权结构,创造一个合作经济。
凯恩斯曾被大家曲解,认为他主张在停滞的条件下,通过政府刺激私人需求,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相反,正如经济学家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指出,凯恩斯把自己列为穆勒传统的遵循者。他称自己为“自由社会主义者(liberal socialist)”。他所想象的是,在经济停滞开始后,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公共投资,这将取代私人投资成为稳定经济的主要动力。这种公共投资的介入不是为了使私人投资更具吸引力,而是为了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直接改善我们的社会。
那么,为什么这种后稀缺性的未来没有实现呢?显然,凯恩斯对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以及改变过于乐观。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世界将更多地通过改变思想而不是物质利益来转变。其他的经济学家对于后稀缺社会的看法则没有那么天真。加尔布雷思谈到了支持生产政治的“既得利益”。穆勒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思想与马克思非常接近,他谈到“所有特权和权势阶级都会为了一己私利而运用他们的权力”。社会精英们绝对不会让经济发展这个引擎停下。也不会放弃他们的公共权力。他们不会让私人投资者掌舵方向盘,除非迫不得已。
苏兹曼还批评凯恩斯认为经济精英将带领我们走向 “应许之地”,然而在他的叙述中,“雄心勃勃的CEO和有钱人”却渐渐从背景中淡出。苏兹曼试图将《工作》写成一本试图覆盖人类经济生活的巨作,然而《工作》一书却忽视了“富人”如何持续拥有比穷人更多的权力这一要点。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经济阶层的出现是与特定的技术突破同步的,譬如农业或者城市生活的出现。苏兹曼引用了一些考古学证据证明了这个论断的不正确性。他写道,许多早期农业社会甚至城市社会仍然是采用“坚定的平等主义(assertively egalitarian)”, 包括 "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类似城市的聚落地。"
然而,在摒除了这些解释之后,苏兹曼继续论证,经济精英的诞生只是另一项科技发明——书写技术的副产品,他认为,随着劳动分工变得更加复杂,文字工作者和商人由于其行业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而获得了权力 。
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对于基于文字的经济精英起源的叙述是不令人信服的。书面文字的发展不可能催生统治,因为文字是统治的主要产品之一。征服者在5000年前就开发了文字系统,以便对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进行财产统计和征税。这些税收反过来让征服者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成为小君主。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古代农业地区,中东的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国家是脆弱易崩溃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不断壮大,征服了全球。
苏兹曼将火、农业、城市和工厂列为人类历史的关键事件。但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一个划时代的过渡,其重要性与其他四个事件相同:从深刻的历史角度来看,“富人”决定国家政治规则的能力,以及阻止“穷人”夺取权力,即使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国家也必须被算作减缓我们走向后稀缺时代的重要力量之一。由于缺乏政治理论,《工作》一书最终几乎完全回避了我们该如何实现这种转变。
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苏兹曼 “建议给予全民基本收入”,“将税收的重点从收入转移到财富”,以及“将我们给予人类和公司的基本权利扩展到生态系统、河流和关键的栖息地。"但苏兹曼并没告诉我们哪里可以找到支持这些政策的选区,或者如何建构为这些目标共同努力的联盟。《工作》中政治的缺失显然与该书处理另一个关键技术变革的方式有关,不是文字的出现或国家的发展,而是生产的自动化。对苏兹曼来说,自动化是解释人类现今经济问题的关键,也是打开通往后稀缺时代的入口的关键。
《工作》的核心理论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已经释放出大量的过剩能量,而这些能量需要找到一个释放的途径。在苏兹曼看来,这个释放口便是服务业的扩张。比如美国,服务业的雇佣率高达90%。这便是能量过剩的事实。即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大量持续的能源过剩,人们(和其他生物)就会找到创造性的方法去解决能量过剩,而方法便是创造工作。苏兹曼认为,自动化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从1980年代开始恶化。当时,“技术扩张”已经在“蚕食劳动力,使财富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苏兹曼援引卡尔·弗雷(Carl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的一项著名研究,声称目前所有工作中的47%将最早在2030年之前被自动化淘汰。
如果苏兹曼所说的是真的,要实现后稀缺时代,与其说需要改变政策,不如说需要一场文化革命。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苏兹曼没有把重点放在具体的政策处方上,而是简单地表达了希望有催化剂这样的想法。如“迅速变化的气候”和“被系统不平等点燃的民众怨气”,又或者如病毒肆虐,这些将会动摇人们的理智。
然而苏兹曼对自动化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没有注意到弗雷和奥斯本的研究的局限性,其作者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该研究没有区分部分自动化的工作和完全自动化的工作,也没有说明工作将被削减的时间间隔(假设它们会被削减的话)。后续研究表明,只有14%的工作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被自动化淘汰,比过去几十年完全自动化的工作还要少。
事实证明,熵对服务业扩张的解释是相对糟糕的。医院和学校的就业率稳步上升并不是为了发泄我们多余的能量,而是因为这些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少出现自动化。我们想提供的保健服务越多,就越需要雇用更多的医生、护士和家庭和健康助理。
只要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人去做,人类就不可能看到工作的完结。要实现后稀缺时代,反而需要我们重新组织工作,使其在更能满足工人的同时,更好地去满足需求。这样的重组必然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并建立民众对专家的信任,还要让他们的建议经过民主审议。我们不可能轻易地按下一个按钮就能抵达后稀缺时代,相反,我们必须通过详细的分工来进行协调。在这方面,我么能从祖先那里学到的东西很不幸是非常有限的。
苏兹曼以及其他人类学家,如括斯科特、格雷伯和格雷伯的合著者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汇集了现有的证据,证明人性与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引导我们去相信的东西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我们人类有能力“缓和我们个人的物质愿望”,但正如苏兹曼所建议的那样,只有当我们解决目前不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水平时,这样得想法才会变得可能。然而,如果像苏兹曼那样,从人类丰富的前稀缺时代寻找鼓舞人心的例子,可能会让我们对实现后稀缺时代的机会更加绝望而不是乐观。
毕竟,作为苏兹曼调查的核心,狩猎采集者主要通过像萨林斯所说的“禅(Zen)”的道路来维持他们的富裕生活。他们将自己的物质财富限制在他们能够携带的范围内。就如在穿越沙漠的长途跋涉中,任何太大、无法随身携带的东西根本不值得拥有。同时,为了维持旅行中的平等地位,采集觅食者会进行“需求分享”。每个人都有权力索要其他人的财物,一般来说,他们都会提出很合理的要求。现今社会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回到那样的游牧生活方式,也绝对不会接受我们个人财产受到如此严格的审查。
最重要的是,苏兹曼在《工作》中所关注的采集觅食者群体是围绕着所谓的 “即时回报 (immediate-return)”经济来组织他们的生活的,他们不为第二天做计划,更不用说明年了。(格雷伯和温格罗所描述的更复杂的“延迟回报(delayed-return)”的采集觅食者社会可能有更多的例子,但却不那么平等)。相比之下,生产我们认为对我们的繁荣至关重要的商品,包括为数十亿人提供供暖、电力和交通,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将需要大量的规划。如果人类学家所记录的前稀缺时期的生活形式是后稀缺时期生活的关键,那么,我们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现有的传统后稀缺性经济学同样在建立未来社会方面有所不足。
在20世纪,有很多人尝试公共替代方案来限制甚至取代私人和利润经济增长引擎。但回看历史,上世纪中期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和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社会主义,两者最终都陷入了世俗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危机中。
铁幕后的技术官僚们试图从中央站点管理他们日益复杂的经济,就像通过遥控器远程控制一样。这样做使后稀缺时代的实现成为不可能,因为它使未解决的紧张局势不断积累,大量的人变得不满。技术官僚收集信息并提供激励措施,从而生产了一些被操纵或忽视的社会角色。由于对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大量的人脱离了工作和社会,或者进行了反抗。在西方,结果是通货膨胀和罢工;在东方则是是经济短缺和人民广泛的不满。
我们不应该试图恢复久远的过去或者让自己与现今的人性理念接轨,我们应该创造新的结构,促进我们去往21世纪的新目的地。我们不应该设定去火星的路线,为了跟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在那里度假,而是应该设定路线通往一个后稀缺时代的地球,在这里埃隆和杰夫的财富被没收并用于更好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克服困扰十分之九的人的不安全感,同时也要减少和改变我们的工作。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要改变投资的功能,正如凯恩斯所建议的那样。要使投资不仅是公共的,而且是民主控制的。摆脱了“稀缺经济学”的束缚,我们将以新的方式为 “诡计之神”热力服务,将多余的能量不仅用于追求效率的提高,或用于制造工程师梦想的任何形式的阿舍利式的手斧,而且还用于为其他各种目的服务,如正义和可持续性,科学和文化,当然,也不能忘了举办派对。
(本文原载The Nation2021年10月4日刊,原标题为“Making a Living:The history of what we call work”,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ociety/james-suzman-work/)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