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边工作边自驾穿越美国加拿大,我找到了一种完美的孤独



我想要在下一个夏天从加州的最南端开到阿拉斯加。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论。上一个春天,我从美国的东岸的最北边开到了最南边。我总是盯着地图,想象自己未来的公路旅行路线。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需要在下一个夏天自南向北穿越美国的西岸,穿过加拿大,再开到阿拉斯加。那么这个夏天我得去续我的美国签证。在思索了几种续签证的方法之后,我决定去加拿大续签证。
这件事是有一定风险的,事情不顺利的话就会被遣送回国。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希望我和我的爱车周爱民待在一起。我决定自驾穿越美国到加拿大续签证,暑假的时候我在美国东岸的马里兰州。我想先从马里兰开到温哥华,在温哥华等签证,再开到多伦多,最后开回波士顿。这意味着我要先横穿一次美国,再横穿一次加拿大。
上路的第二天,我回到了上大学的地方。这种感觉很奇妙,我走在这个我熟悉的小镇上,我渴望被什么人认出来。不过一起念书的大家基本上都离开了,所以我一个人走在街上。
我回到原来上班的奶茶店,我在麦迪逊的朋友在店里等着我。
他们好像永远都在那里。早上十一点的时候店里会开门,从这个小镇上最繁华的街道往窗户里望,木地板上有拖把留下的细密水珠,店里会散着红茶、黑糖珍珠、还有鲜切水果的香气。大概晚上九点的时候,我们会把写着“OPEN”的灯关掉,再把里里外外仔细打扫一遍。
原本我打算在麦迪逊待两天,在认真地考虑过很多因素之后我打算待三天。我的事情很多,工作上和学习上的。有的时候一边开车会一边焦虑这些。然后前一天一点睡下的我会神奇地,精神百倍地在清晨六点醒来。我不再责怪自己睡得少,感觉清醒的时候就醒来,困倦的时候就停在加油站,再用我色彩斑斓的渔夫帽遮住脸睡一觉。平时睡七个小时就足够了,现在对于体力的消耗更大,得多睡一点儿。

我开过了俄亥俄州,开过了我念过大学的威斯康辛州,回到了以前打工的奶茶店。离开威斯康辛的时候,像家人一样的朋友对我说:
“要常回家看看啊,吉普赛姑娘。”
接下来的一周,我都会睡在车里。
我穿过了明尼苏达州,经过清澈的密西西比河上游却没有时间下河划船。夜半时分,风力发动机成群结队地出现,我仿佛闯入玫瑰星云。风力发动机上的红色灯光颤动,宇宙向我眨眼睛。离开了朋友家,离开了朋友的孩子们,我到了荒芜的南达科他州。在7度的清晨,我抱紧我新买的学校卫衣。天亮之后,我开过荒地和石滩,仪表盘上的气温显示100华氏度(约37摄氏度)。我开到了恶地国家公园,它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面前,白色的岩石上有肉色,米色和粉红色的条纹。我摇下窗户,大声播放摇滚音乐。我应该就是方圆两百公里最聒噪的亚裔青年。不对,别说亚裔了,这里连青年都没有。九月的国家公园没有孩子,只有结伴出行的老夫妻。我提着自己的三角架一直走,沙漠花栗鼠和我一起躲避阳光。
不知道从第几天开始,我连营地都不想订了。
我坐在驾驶座上,喝一些被阳光晒得温热的茶水。我大概有几天没有洗澡,也没有找到可以洗澡的货车休息站。犹豫一番后,我决定省下三十美元的营地钱,寻一个野地睡觉。我开过观景公路,石山那一头的夕阳是紫色的,小鹿时不时出现。离开威斯康辛的时候,奶茶店的朋友塞给我很多面包,有我喜欢的肉松面包,脏脏包,还有芋泥麻薯面包。在紫色的夕阳下,我狼吞虎咽下被书包压扁的芋泥面包。我找到高速旁边的免费露营地,小心地开过地上的坑。我在层层叠叠的巨石之间搬出了我的红色露营凳,在温柔的夕阳下读黑塞写的爱情故事。我钻进我的睡袋里,疲惫似满月夜的潮水,浸润身体和床铺的接触面。我高举着ipad在车里读书,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出行的第六天,我穿越了美国的两个时区。在山地时区舒展开来的我,在美国东部时间两点三十一分醒过来。车的后挡风玻璃上结了霜。我用手掌的余温把它们抹开,清亮的星星出现在休眠的加热丝之间,那是一个夏末的梦。我的车停在悬崖旁边。山谷底端传来一些比傍晚风声要温柔一些的鹿鸣,我身旁的帐篷们被风吹得呼呼作响。我拥有一种被荒芜温柔地包裹着的孤独。漫天星星陪着我,但我却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我渴望把星图铭记于心。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学,但是也还有四份兼职工作要做。每天的节奏大概在开车,工作,还有睡觉之间摇摆。清晨我在悬崖边醒来,睁开眼的时候太阳刚刚掠过山头,一个红色的世界等着我。我抱着毯子,听见隔壁的邻居在讲西语。我从车窗中探出头和他们问好:

“Quieres cafe? Quiere pan?”(要喝咖啡吗?要吃面包吗?)
他们烧好了热水,咖啡和牛奶粉末飞扬在九月的荒地里。之后得到一杯美味的墨西哥咖啡。他们问我要去哪里,对未来有什么计划。我问他们墨西哥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离开的时候,墨西哥阿姨紧紧地抱着我。我无以为报,在车里翻出了一包日本水蜜桃硬糖。
“总有一天我会开到墨西哥的。”我说。

“那我们就墨西哥见了,孩子。”墨西哥大叔说。

如果今天你得了一种罕见的心脏病,一周只能工作两个小时,你会用这两个小时来做什么?
这个问题来自于我很喜欢的一本书《一周工作四小时》。
在旅行的过程中,我同时在做四份工作:学校的求职中心学生助理,一个关于社群研究的数据分析和写作工作,学校写作课的助教,还有一份在哥伦比亚炸饺子公司的质检实习工作。很多时候也没有那么糟糕,我只是在跳舞,在工作和游戏中跳舞。
我不大知道每一天是星期几,只是大概知道什么时候要完成工作。住在露营地的我拥有很多个没有网络但是可以随时拥抱星河的夜晚。每天我都会起的很早,然后去最近的星巴克或者沃尔玛(*注:美国的沃尔玛有Wi-Fi)。某一些日子我在处理炸饺子公司在美国农业部的注册信息,或者是给炸饺子算微积分。有一些日子我在写关于美国最大的蔓越莓企业的简介,之后学校会把这样的文章放在求职中心的网站上。也有一些日子我在统计美国堪萨斯州的不同农业和食物救助非盈利组织的改善内部架构问卷。处理完这些,我会短暂地端坐在星巴克永远也垫不平的咖啡桌前做一些简单的瑜伽。处理完工作后便是不间断的驾驶。
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刚刚到了黄石公园的营地。
我那天开了九个小时,从南达科他的坏地国家公园到怀俄明州的黄石国家公园。我穿过三十五度的西部酷暑,眼前只有荒地。穿过茂密的针叶林,穿过山脚下闪闪发光的湖泊,穿过红色的高地和绿色的农田组成的色彩拼盘,穿过那些只能被茶色墨镜所识别的蓝色山脉。不知名的高耸树干像是毛竹做成的屏障,黄石里面的湖泊是黛色的,是刚刚好的粉红色。小镇拦住我的去路,野牛拦住我的去路,我的心里记挂着未完成的工作。我幻想着未来无数种工作的可能性,只要我能开车就好了,能开车就好了。

我到营地的时候太晚了,淋浴已经关门了,我匆匆吃完晚饭。我想,我只剩下一点力气了。星星,树木,烟雾,还有荒地里的响尾蛇都认可我的疲倦。我认可自己的疲倦。计划中的工作做不了了,营地里也一点信号没有。困倦倒在我的肩头,像是要压断我的锁骨。
但是,如果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两个小时,我一定会用来写作。我无法放任脑海里的想法就和睡袋外世界的热量一样飘散开来。哪怕耗尽了能量,我也想把眼前的图景记下来。我不晓得这有什么意义,不过也允许自己不追求意义。

早些时候我坐在营地澡堂的门口,那是整个营地里信号最好的地方。我拿出我的红色露营凳,准备整理一些工作上的数据。网不是很好,电脑也慢慢悠悠的。
我闭上眼睛倒数五个数,回想那一天的旅行。
昨天我很害怕,到黄石的时候天已经要全黑了。我害怕自己又撞上什么动物,开进山里的时候前面的房车很慢,硕大的野牛出现在高速上,大家也都慢慢地开。
过了一会儿,前面带路的房车消失了。我一个人继续开。我不敢开远光灯,我记得我上一次撞鹿的时候,远光灯下鹿闪闪发光的眼睛。
我盯着我的导航,还剩四十分钟。
有的时候我很喜欢晚上开车,因为我只会看到我需要看到的。但是国家公园里,我希望我能看到的更多,我希望在动物撞上我之前我就知道他们在哪里。
松,松,松。
我对着自己讲。
我能够看到的,就是我需要看到的。
五秒过后,我睁开眼睛看电脑有没有反应过来。任务正在一点一点地完成,我好像奇妙地变得更有耐心了。
一个亚裔大叔看见坐在营地门口用电脑的我,他问我,营地里有没有信号啊?
我反应过来大叔是中国人,于是我用中文回答。
大叔看到我麻省的车牌,问我是不是从麻省来的。他和他身旁的阿姨两人一起公路旅行,他们从匹兹堡出发。我们都要去温哥华,不过他们的行程不像我的这么赶。
我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去温哥华,说自己以后想开去阿拉斯加。
“我们去过阿拉斯加了,两次!”大叔非常自然地用手指比了一个二。他回答了一些我对于阿拉斯加的简单问题,他说路况不太好,但是车是承受得了的。他说,虽说阿拉斯加加油站不多,但只要在看到加油站的时候把油加满就不成问题。
“你睡在哪里?”大叔问我。
我总是很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睡在车里。
“我们也睡在车里的!”
我走向他们的车,那是一辆本田CRV。他们的车和我的车一样,后面是一张床垫。不过在他们床垫下面还有一块木板。SUV的车型没有一个隔出来的后备箱空间,床是可以平铺开来的。我的后座放下来之后,床垫会被垫在一个非水平面。他们车后门的窗户安上了漂亮的黑色纱窗。车的穹顶和门的边上整齐地夹着各种储物袋。通常我睡觉的时候,我会把后面的窗户打开一点,然后套上蚊帐。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自己未知的旅途充满了安全感。
我原本完全不是今天这样的人。我的驾照翻来覆去地考了四次。曾经的我,每天都在反复地检查邮件和日程表,为井井有条的生活而感到自豪。我反复翻看自己的日记,咀嚼自己留在相册里面的会议,反刍每一句我听到的话。在我跳离了一段稳定关系后,便开始用所有我想得到的手段来抵抗稳定性和规律性。

最近几天我每天一清早就开去离前一天晚上睡觉的荒郊野岭最近的星巴克工作。有的时候我会去沃尔玛,不过沃尔玛比较难找凳子。我在电话这头和老板讲这个数据点是写成0还是1,我旁边就有咕噜咕噜的购物车摩擦地板的声音。我很幸运,没有人问我在哪里。我现在可能也不大愿意说了。
所以我的上班路就变得尤其得有趣,山间粉红色的落日,凌晨还没有睡醒的河谷,在镇子上的挖土机游乐园游戏的驼鹿。那些失重感和野性,自五十华氏度的风涌进我的脑颅。驾驶的时候,我只悬浮在现世的中空。
我终于要开到太平洋边了,出发前我和朋友说,我准备那天开十个小时的车去大西洋边看日落。下午的时候突然很想给朋友们打个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我在海蓝色的哥伦比亚河边,水纹复杂如同色的万花筒,红色的浮标如渔人的小舟。我停在某一个观景处,问路人能不能给我照一张照片我好发给我妈。
在那一个瞬间,我想念所有人。
我继续上路,给妈妈打电话。信号不太好,我无法在争吵的时候回嘴,只能安静地照单全收。我和我妈解释了一下我的路线。她顺带地变成了美国地理专家。
“为什么离开怀俄明州不直接从蒙大拿州开到西雅图?”
“因为我要去波特兰看海。”
“开完这一次就不要开车了好吗?”
“我要怎么不去过现在这种生活呢?我觉得我没有选择。”
距离目的地十分钟,小镇雾气弥漫,我还在山间。哪里有一点海的样子呢,别提我想要看的日落了。小镇上的旅馆门口闪烁着灯,写着“No Vacancy(没有空房)”
我没有力气失望了。我和我都不说话了。我开到了海边停车场,那里没有别的车。暮色降至,我的大灯打在停车场的告示牌上。牌子上写着:Day use only (停车场仅供白天使用)。我走下车,长时间的驾驶让我的双腿发软,我差点摔了一跤。我没有拿三角架,没有拿露营凳。我往沙滩方向跑,我甚至不知道沙滩在哪个方向。我穿过枯草和常绿树木后的沙丘,我看到了雾气弥漫的太平洋。
没有日落呢。
我闭上眼睛,想着这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我在大陆的表面轻轻留下一道划痕,就和以前的人一样,就和未来的人一样。这是人心里的火,非把心里的枯草地烧尽了才好。
我想我得在天黑之前尽快弄明白自己晚上该睡在哪。我似乎没有什么时间在海边自言自语。我踉踉跄跄地跑回车里,给附近其它的营地和酒店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想开去营地碰碰运气,同时记下看起来比较安全的紧急停车处。我开到营地,不用戴眼镜也看得见:No Vacancy.
我走下车,走到营地管理员的办公室。
“真的没有位置了吗?”我在等待一个我已经知道的答案。
“没有了。”同时大叔递给我一张附近的营地和酒店清单。
“我都打过电话了…他们要不倒闭了,要不就没有位置了。”
大叔看着我。“你一个人?睡帐篷里?”
“我就睡在车里。”
“哎…我有一个给管理员的位置。本州车牌三十刀,外州车牌四十四刀。你想怎么付钱?”
我看着他,不知如何反应,机械地把银行卡递给他。
“哎虽然我觉得这也没什么的,我也没有朋友可以分享这一切。但是,但是,我从美国的最东边开到了最西边呢!”我对忍不住对他说。
大叔稍微抬抬头看了一眼我的车牌,“你开了很远的路呢。”似乎那是一件最平常的事情。
我想,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他问了我之后要去哪,又有什么打算,然后把营地地图和挂在前视镜的牌子递给我。
“Have a good adventure!(祝你探险愉快)”大叔笑着看着我。
雾气弥漫的太平洋边,水汽停留在我的皮肤表面。
我想,让我洗个热水澡再好好睡一觉,我就可以继续上路了。

签证比想象的顺利很多。对方没有问我为什么在美国大学开学之后我还出现在加拿大的原因。也没有问我为什么要续签证。我站在柜台的这头,耐心地等待关于签证批复的答案。我的眼神不敢四处游走,只好定格在她背后的山脉上。我漫游在这个窗外的世界里。数层玻璃把我和山脉隔开,对,只要再忍耐一下,把这个现实世界里的手续完成,我和山脉之间就没有距离了。我想象着我在阿拉斯加划船的样子,某一个冬天再次来到加拿大,去育空省看冰冻雨林的样子。
“你的签证通过了。”柜台那头的女人对我说。
拿到签证之后的那一天我去找了朋友。我们一起去了她念书的地方旁边的海滩。海滩上没有沙子,只有枯木和卵石。加拿大的山脉是紫色的,远处的棕榈树是夏天的影子。我们搀扶着对方,深深浅浅地走。

离开温哥华之后,在卡尔加里的朋友提醒我,如果要去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看湖,最好提前一晚睡在停车场。
九月初的加拿大夜晚已经很冷了,我和朋友哆哆嗦嗦地在停车场睡下。那天是中秋节,宛若铜镜般的月亮高悬空中。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孔雀蓝色的湖泊。
“我们不如去划船吧?”
和所有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表现出我对于划船的过分热情。那天早上大概是4度。梦莲湖的水是冰川融水,冰凉冰凉。夏天穿起来觉得累赘的救生衣现在勉强能起一些保暖作用。其他游客们在等待日出,朋友在等待我把船打好气。
划船的时候,没有一种可以保证自己身上干爽的方法。我让朋友坐上船,然后我走进冰冷的湖水里,把她的小船推向远方。
清晨的梦莲湖太冷了,我的手指和脚趾都没了知觉。我们离开了湖泊,我花了大概一小时的时间把一切整理好,换掉湿漉漉的衣服,再把车里能够找到的所有厚衣物、毛毯还有睡袋裹在身上。朋友打开行李箱,我打开我的大号旅行提袋。我们迅速地在脑海里计算了一下怎么样套衣服才能让两个人既不会太臃肿又能保暖。车载的烧水壶烧得很慢,我们在等待一次沸腾,在等待身体恢复知觉。
开学后,总是没有办法毫无负担地玩。我在摇晃的船上读墨西哥、美国、还有加拿大的营养法规区别;我在落基山脉间读美国营养法规近5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在坐满老年夫妇的度假胜地里的咖啡厅里听老师讲海地的妇女为什么不喜欢用母乳喂养;我在青绿色的梦露湖边读人道主义救助行业的种族歧视。我见缝插针地玩,也用尽所有力气地兼顾驾驶,工作,还有学习。
之后的几天我们在卡尔加里的朋友家和班夫国家公园来回开了几次。某一天我们早上六点起来,准备开两个小时去班夫国家公园。我习惯性地起得早,我去叫朋友起床,推开她的房门,钻进她的被子里。
“你真的想去吗?我好累,我真的好累。”
“去吧。”
我们原本计划在我一点的课之前爬五个小时的山,去到之后找不到车位。只好把车停在距离露易丝湖一小时步行距离的停车场。最后我们在路易斯湖和停车场间走了两小时,在湖边走了一小时。
走在高速公路边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到底在干什么。这个时候我不是应该坐在学校里上课的吗?偶然会觉得格格不入,会觉得自己距离原本的轨迹很远很远。我和Jiwon坐在高速公路边的露营地休息,吃一些在美国买的牛肉干,还有加拿大的特产,番茄酱味的乐事薯片。
然后我们见到了路易斯湖,那是像仙境一样的婴儿蓝色湖泊。划船的游人也是景,我们也是景。高山下的湖泊,还有似乎离家非常非常远的我。那一刻我也看起来不像刚来北美的我:我穿着本科学校的加绒卫衣,粉红色的紧身裤,还有褐色的登山鞋,戴着我的心爱的湖蓝色毛线帽。这是我刚刚来北美的时候最反感的白人打扮方式。我似乎躺在一副陌生的身体里,做着我最想要做的事情。


我告别了朋友,一路往东开。
在班夫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里,我看到加拿大各国家公园的地图。原本我没有做什么在加拿大的行程计划。八月初的时候,我勉强自己做了一个计划。我有一个公路旅行用的excel计划表格,如果一天能开五到八个小时,我是可以在二十天里横穿加拿大的。沿着这一条线路,我找到了几个国家公园。
朋友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们也去爬山。她开玩笑说,如果我们看见一头鹿和一头熊,我们就是加拿大人了。
我开到了Saskatchewan。那里有一个草地国家公园,等我在附近的城镇上完我的人道主义救助课再到国家公园的时候,天已经近乎全黑了。六月初的时候,我一个人去西马里兰州坐观光蒸汽火车,把脑袋伸出窗户的时候,我一低头把我的眼镜摔到了手里,镜片也掉了出来。我勉强把镜片装了回去。等到这次旅行,在八月底的时候,我在爱达荷州某处野温泉边上订满的露营地里找到了一个容身之地。欣喜若狂的我一低头,眼镜又掉到了我的手里。镜片也脱落了出来,落在我杂乱的车里,到今天我也没有找到。不过我的近视并不严重。
之后我又带着我的半瞎眼镜开车。在草地国家公园的黄昏里,我一边大声唱歌给自己壮胆,一边眯着眼睛开车。在今年七月初我自己去西弗吉尼亚州的时候,我撞上了一头鹿。那个下午的五小时驾驶里,我看到了三十头不同的动物,从大角鹿,到驼鹿,我叫不出名字的野牛,还有受惊的浣熊。我还处于一个非常害怕动物的状态,于是草木皆兵,看起来像陆上香蒲的野草看起来也像是小鹿的角。和那一只我早前撞死的美国小鹿不一样,加拿大的鹿似乎比我更害怕,它们看到我向它们开去,也都远远地跑开了。
我开到了一片荒地里。就和过去三周的任何一个瞬间一样。
那是九月初,露营地的水管已经关了。那个晚上估计没有什么可能洗澡了。我坐在一片黑暗里,没有人为今天的旅程结束而喝彩。空气里传来一阵焦糖巧克力的味道。远处的车都是巨大的白色房车,再不然是拖着住宿单元的皮卡车。这里只有一辆轿车,这里只有一个人出行。

我忘了自己要去哪里,手机收不到信号了。我翻出副驾驶座下的美国加拿大地图。我在记忆里摸索,今天在撞鹿的恐惧中看到的地名。我试图把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名字拼凑起来,构成今天的路线。我想,接下来我要去Moose Jaw,或者是要往Regina方向走。
我呆坐在驾驶座上,想要把这些恐惧和欣喜摊平,再编织到文章里去。但是,我很累了,我很累了。朋友早上煮了三根玉米给我,我坐在驾驶座的黑暗里啃食一根冰凉的玉米。
好像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完美的孤独了。


雨下了一整晚,半夜我醒来,又醒来,认真听雨滴落的声音。
早些时候我在一个镇子落脚了,我依然在接近天全黑的片刻到达了小镇。我别扭地在驾驶座上摊开,看我不愿意看的课前阅读。我先是半个身子在车外面,用羽绒服遮住肚子。然后我又在驾驶座和副驾驶座间展开。看了一个半小时的书之后,我知道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还要稍微留一点体力收拾车里。我起身,车窗外水波的声音变成虫鸣。我的羽绒服袖子掉在露气很重的草地上,现在它是漂亮的渐变色。小鹿在我身边打转。远处的路灯不知道是谁忘了打包的月光。
继续往东开的时候,我也许会见到了一个我思念已久的朋友。但是我什么也不想说,也不想提。重逢不需要计划。
我开到了多伦多。
我见到了我小时候的一个老师。“年轻的时候要把燃料用光!用光!用光!虽然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但是你还是要做一个战士,随时都要准备战斗。”老师会对我说。
那是我常有的一种想法,我想把自己吃干抹净,然后睡一大觉,第二天早上再起来把所有燃料都用光。这是旅行的时候常会有的想法。
我见到了奶奶(我的多年笔友,和亲奶奶差不多),我在多伦多唐人街转了又转。我记得这个地方,上一次来加拿大的时候我有来:汽车穿过电车轨道,绿橙相间的出租车,满墙满墙的涂鸦,废弃汽油桶里长出许多杂草来。我在野外待了太久,兴许看起来不像个城里孩子了。
在开来唐人街之前,我和朋友去万锦市喝茶。我站在早茶店旁边的好市多停车场里,从车后座印有加拿大特色的,印有驼鹿的,被压扁的蓝色礼品袋里抽出一件来自班夫国家公园的短袖:我给奶奶买了一件,我也给自己买了一件。往常我不爱买这些,但是和奶奶穿一样的衣服会很开心吧。独自上路的日子里我不怎么穿内衣,进多伦多之后要见很多朋友,所以我礼貌性地穿上了我的运动内衣。我站在繁忙的停车场里,把原来的黑色短袖脱下,然后再换上班夫国家公园的衣服。
见到了奶奶,她站在我的住处门口。我们快乐地拥抱。这里要说什么呢,我想,大概什么也不用说。
我和奶奶大概去年就说要见面,甚至更早的时候。去年和奶奶通信的时候我写:我感到我的身体不断膨胀起来,流动起来,穿过波士顿高楼大厦的间隙,穿过九十三号公路,好像离那个下周末要去尼加拉瓜大瀑布的我很近,好像离奶奶很近很近。
要来加拿大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奶奶是重要原因之一。很久没见温哥华的朋友,很久没见卡尔加里的朋友。我站在朋友面前,我要反应很久。我真的真的在这里吗?这一切是真实的吗?欲望和热望比身体走的快。我对漂泊大概上了瘾。路牌比我更明白我要去哪里。在到多伦多的一天前,我看到路牌说,我离多伦多大概五百公里。
我的身体不断膨胀,我无法只是安睡在一处。
我与奶奶约在唐人街见面,晚些奶奶要回到家里。我们谈论很多,讲文学,讲未来,讲过去,讲男孩。我向奶奶解释我是怎么在车里睡下,怎么把蚊帐套在门上。然后我们从唐人街的另一侧绕回去。停车场的北侧楼面上有街头涂鸦画出的迷宫,远处的教堂顶上挂着蓝色的所罗门之星。
“我们怎么走到京士顿市场啦,这是犹太人的市场。”我们在多伦多的唐人街漫游,奶奶对我说。
“要看看吗?”我问奶奶。
“不看了,我在这里住了二十来年也没有来过。”
“也可以去哦,我陪着奶奶。”
她转向另一侧的身子又转回来。
我们一起去吃饭,我再把奶奶送上有轨电车。我隔着玻璃向她告别。
我不想回酒店。迎面走来的女孩画着利落的眼线,穿着黑色的长裙。我是她吗?我穿着我的North Face冲锋衣,刘海油乎乎的,在街边的印度超市里买了两大支水。我的背包鼓得尴尬。
我走在多伦多的唐人街上,冲锋衣的拉链拉到我的下巴上。我走过唐人街爬满涂鸦的墙,还有那长出一片野草森林的废弃汽车。长居在某处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一个地方的气味,嗅到一个地方的颜色,触摸到一个地方的温度。回忆起某处的时候,这些片段像是藏匿在办公室抽屉里的,被串成一串的回形针。在路上太久了,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感知这些东西。我是疲惫的,亟待一张床铺的旅人。某些时候,我渴望抓住虚空里的一双手。
我抱紧自己的双臂,戴上了冲锋衣的帽子,暖流包围着我。
我不晓得自己要去哪,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我不知道明天的行程,不知道工作的交付日期,不明白怎么下笔写作业要交的论文,没有秋天的计划,没有冬天的计划,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到美国。
只是,背着沉重背包,裹着冲锋衣的我突然明白自己是那个最可靠的旅伴,所以我们一起去哪里都无所谓吧。
多伦多的夜里,没有形状的月光飘浮在水雾一般的雨里。
日子推着我走,我唯一反应过来的一点是,我想要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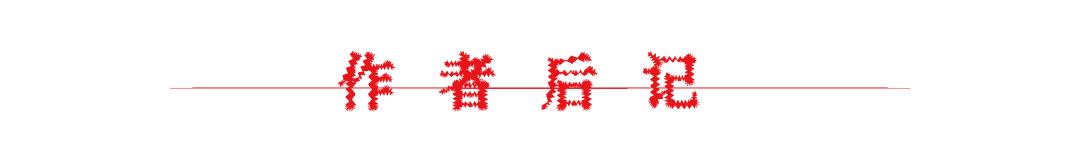
在很多时刻,我都想要努力记录下些什么。但是旅行的大多时候,我都太疲倦了,所以就让灵感自然地消散开了。文章的大纲很久之前就写好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修改它。好像要在钢筋水泥的世界里在经历一些,再多一些,我才有能力和灵感来照顾我写作花园里的这一盆奇花异草。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只是在打一份粗糙的草稿,其余时候,我在等待这份草稿里的世界自己站立起来。其余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其余时候,我希望我在为读者心里的一千个哈姆雷特接生。
那么,和我一起去探险吧。
原标题:《边工作边自驾穿越美国加拿大,我找到了一种完美的孤独 | 三明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