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揭露在美国城市街区中的……驱赶与谋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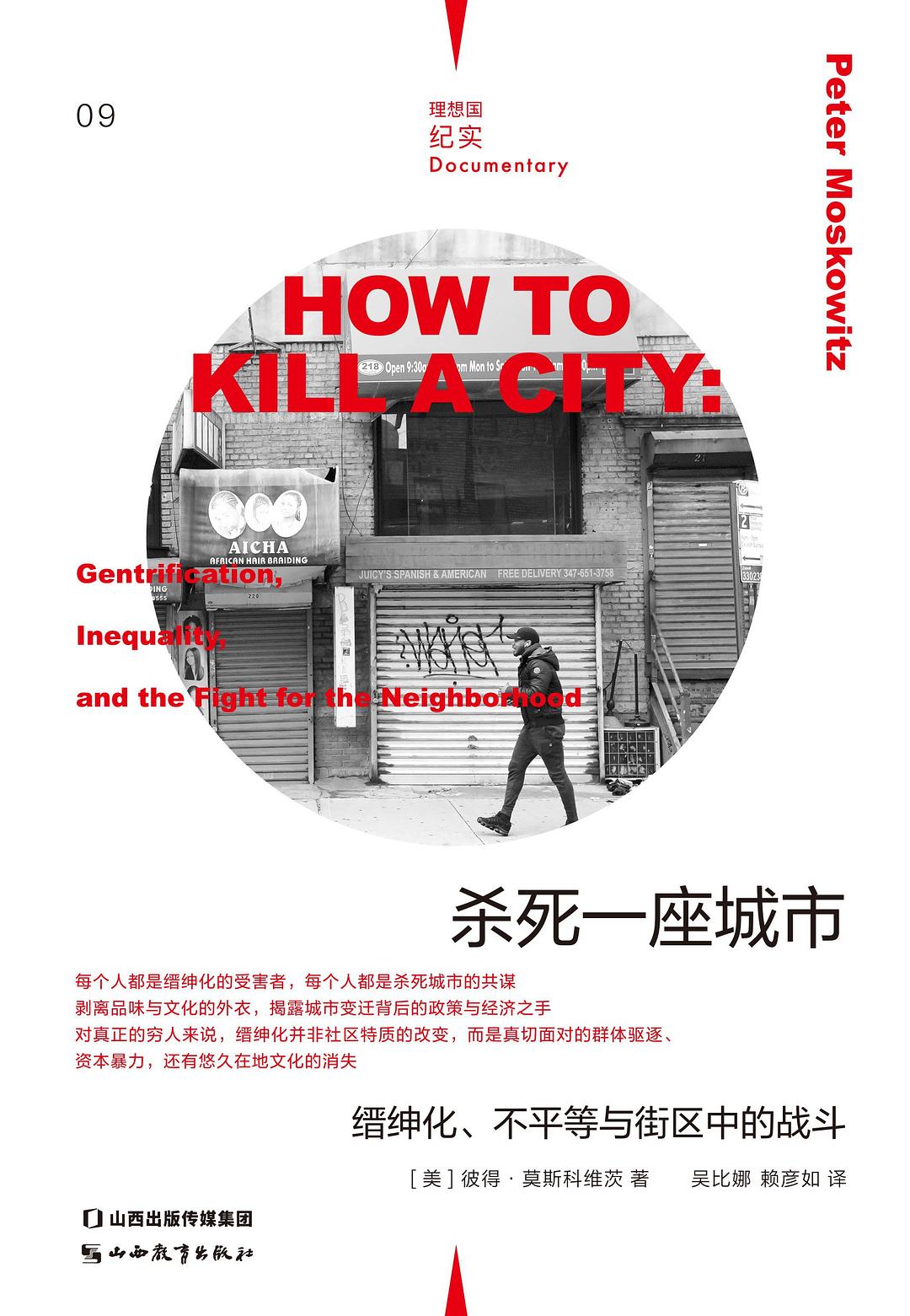
《杀死一座城市:缙绅化、不平等与街区中的战斗》。[美]彼得·莫斯科维茨著,吴比娜、 赖彦如译,山西教育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7月版,284页,48.00元
美国记者彼得·莫斯科维茨(Peter Moskowitz)的《杀死一座城市:缙绅化、不平等与街区中的战斗》(原书名How to Kill a City: Gentrific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Fight for the Neighborhood,2017,吴比娜、赖彦如译,山西教育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7月)是一部相当独特的城市问题研究著作,它不是因 “缙绅化”(Gentrification)这个核心主题而显得独特,而是因为作者所具有的敏锐的思想和正义伦理激情,使这个容易被收编在城市发展规划或城市地理学的学术殿堂中的议题回到社区和街头,书名副标题中的 “不平等”和“战斗”凸显了它的强烈的批判性。
作者彼得·莫斯科维茨的身份不是城市研究专家,而是以城市变迁亲历者的真实感知、新闻记者的敏感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批判精神介入这场有关城市的生与死的讨论。因此在书中没有貌似很专业的城市规划理论空谈,也没有浮在政府机构、议会、社会团体之间的城市规划争论的舆论泡沫之中,而是深扎到城市街区各种社会群体中去。因此全书最后的“致谢”首先就是献给纽约、新奥尔良、底特律和旧金山的受访住民和街头运动的参与者。同时令我感动的是作者对家人的这种感谢:“在饭桌上无数次和我争辩有关政策的种种,帮助我去芜存菁,学着拼凑成有力道的论述”。餐桌上的家庭辩论会似乎是一种平民知识分子家庭的传统,是贴近现实生活的思想与学术交流的温馨平台,也是敏锐而富有伦理正义情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摇篮。作者的这段致谢令我想起多年前我看到一位青年学子在大学入学申请自述中写到“餐桌谈话”对他的影响,我相信这是代际间互相影响的真实过程,是最为自由和平等的思想交流。莫斯科维茨不但感谢父母、哥哥嫂嫂和朋友,还要谢谢他的狗狗瑞米,因为担心它会感到自己被排挤。
该书通过对美国四座大都市(新奥尔良、底特律、旧金山、纽约)重大变迁的回溯和分析,指出所谓缙绅化是在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和政策倾斜的支持下,旧社区在重建后因地价及租金上升,吸引高收入人群迁入,原有的低收入者不得不迁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从而在中心社区聚集更多精英富人,使居住社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贫富两极分化特征。而这一切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个人文化与消费偏好选择,也不是普通个人房产投资者的选择结果,而是当地政府政策自上而下的倾斜为城市的更新改造铺路搭桥,由政府、房地产企业、投资财团等大型机构联手实施。最终结果是街区生活失去了文化多样性和人性化的居住氛围,城市社区失去其历史文化记忆,中心城区只是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而不是普通人的生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说缙绅化正在杀死城市(Kill a City)。
“缙绅化”是该书的核心概念,英文是Gentrification,也可译为绅士化、中产阶层化或贵族化。该词源自英文中的“gentry”,意指中世纪欧洲的一个社会阶级,后来演变为指先天条件优越、在较好的环境中成长并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人。英国社会学家鲁思·格拉斯(Ruth Glass)于1964年在她的书籍《伦敦的改变》(London:Aspects of Change ) 中最早以这个概念来描述伦敦的某些小区因为中产阶级“缙绅”的进驻而产生的扰动与不安。在1969年的美国,“缙绅化”第一次运用于推广一种“棕色石块生活方式”,其倡议人被塑造为“一群善良的城市先驱者”形象,实际上他们在这时已经通过有钱人、政治家、企业家的共谋而从被缙绅化的小区中获利(34-37页)。其实说白了,所谓城市街区的缙绅化进程,就是当地政府为了土地财政而把旧城区地块卖给开发商、投资商,后者必然以百倍疯狂的逐利欲望把在地长住居民和外来打工人驱赶出去,而豪华公寓、高端商业区又把政府官员的“城市名片”擦拭得更为美轮美奂而且日新月异。
必须看到的是,“缙绅化”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而且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缙绅化进程经常还增加了更多的黑箱操作甚至是国家暴力的手段。约翰·里德(John Reader)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们的政府都趋同一致地认为,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启动中心,他们以为这种增长更容易获得外国投资者的青睐。许多国家的发展计划都致力于优先投资建设大城市的环境,力图吸引跨国公司的注意。大量的钱财花在政府办公楼、会议中心、豪华旅馆以及其他面子工程上,而像卫生保健、安居工程、水电供应或适当的下水系统等基础需求,却只得到极少的关注。”(约翰·里德《城市》,郝笑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188页)关于城市居民与政治的关系,里德也说得非常准确:“残酷的现实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居民虽然在人口统计上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没有一点政治影响。”(191页)那么,政府到底是否有权、有正当的合法性、合理性这么做,这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莫斯科维茨同时还揭露了缙绅化也是长期以来在城市生活中存在的种族歧视政策的恶果,呼吁反对这种“新形式的种族隔离”,捍卫立足于社区住房的人权。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或许更值得思考,因为在有些人看来,旧社区在重建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并没有什么不合理,至于社区景观改变得更时尚、出现更多潮人也没有什么不好,说“杀死一座城市”是否会有偏激之嫌?至于说到种族歧视,是否有事实依据呢?作者指出,“美国长久以来的种族化住宅政策,看似跟当今缙绅化现象沾不上边,但这两股力量却殊途同归:假如黑人能够像白人一样,借由房产获致同样的成功,缙绅化就不至于和种族绑在一起。事实上,缙绅化支持者打的算盘,就是要有意地摧毁黑人的城市生活。”(132页)“缙绅化不是由个人的行动造成,它立基于美国数十年来种族歧视房屋政策下的系统性暴力,否定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跟美国白人一样取得房屋、获得同等财富地位的权利。”(第6-7页)话说得很明确、精准。
虽然莫斯科维茨在书中没有深入讨论美国种族歧视中的居住问题,但是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津恩(H. Zinn)所说的,“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知道早在二十世纪初,美国有些城市颁布了地方法令,规定日落以后整个社区禁止黑人进入;在肯塔基州则是规定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住在街道两边。(T. H.安德森《美国平权运动史》,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3页)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城市改造进程中,有市民权利团体(civic right)和自由团体(liberal group)经常反对一项迫使少数种族或者少数民族从他们邻里社区迁出的计划。他们指出在全美最大最出名的斯泰弗森特镇改造项目中,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已经把黑人驱逐出了斯泰弗森特镇;他们反对当时的城市改造法,是因为城市改造法没有反对种族歧视的特别补充条款。R.M.福格尔森的《下城:1880-1950年间的兴衰》(周尚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465页)无疑有更多的美国城市改造项目事例可以证实莫斯科维茨所讲的,美国一直存在着种族歧视房屋政策下的系统性暴力。但是令莫斯科维茨感同身受的是他在访谈中接触的那些被驱赶出原住街区的黑人,因此他才能写出难以从城市研究学者的著作中发现的句子:“对许多被驱离的黑人来说,卡特琳娜使他们身无长物,感到城市对他们的处境袖手旁观,甚至刻意劝阻他们回家,‘殖民’‘侵占’‘种族灭绝’这些字眼,对他们来讲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实发生的事。”(19页)新奥尔良在卡特琳娜飓风过去之后,政府抓住了这个“缙绅化政策实施的机会之门。政客和开发商一举通过以往没有办法轻易通过的法律。在联邦政策的支持下,地方领导人利用飓风的机会,将城市的各项服务都资本化。学校、住宅私有化了,工会瓦解,只要有人愿意投资,就给予免税或种种诱因,几乎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最重要的是,他们尽一切可能确保黑人不会回到城市。卡特琳娜飓风并不是城市第一次试着驱逐它的黑人人口,但却是最成功的一次”(25页)。很多人恐怕不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说在保卫经济机会和种族公平问题上,没有什么比住房更重要。如果你能想象,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人们被驱赶出住房的消息,可能就会读懂莫斯科维茨所讲的,可能就会知道没有什么比住房更重要。
虽然这里讲的是种族歧视问题,实际上与之并存的还有阶级歧视,只不过富人与穷人的利益对立有时显得没有那么触目而已。但是当阶级的怒火一旦燃烧起来,斗争烈焰是同样的炽热。1988年,在纽约汤普金斯广场公园(Tompkins Square Park) 爆发了人民反抗纽约的缙绅化的斗争,群众集结在这里,反对外围建筑被改建成奢华公寓和租屋。在一条标语上醒目地写着“缙绅化是一场阶级战争”。最后整个公园有上百名抗议者和四百五十名警员爆发了一场小小的暴动,纽约市的公民投诉审查会(Civilian Complaint Review Board)接到了一百二十一件关于警察手段粗暴的投诉。激进分子指斥该事件是警方与缙绅化的共谋:当小区开始面临缙绅化的时候,黑人和拉丁人种遭遇来自警察的暴力与羁押事件也开始增加。抗议事件过去之后,市府重新规划公园,用围栏隔开每片草地,把通道弄得弯弯曲曲以避免大型集会;公园里容纳得下抗议活动的开放空间也被指定为狗狗运动区。(202-203页)看来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空间政治学教程都是一个模板的。
学术界对于“缙绅化”的经济学原因当然也有各种解释。美国学者肖特(J.R. Short)认为,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租金差额模型理论试图解释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背后的深层原因:解释高收入群体搬回到城市中心这种行为的因素有多种:高收入的工作机会毕竟还是集中在城市中心的服务业部门,新的家庭类型形成,新的消费类型,年轻的富裕家庭的新住房偏好出现。他也谈到大卫·哈维从前的研究生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资本影响理论,史密斯认为由于许多城市的内城街区都存在着显著的因资本被投入到郊区而出现的投资流失现象,因而造成一种租金差额,从而又为新的投资形式创造了条件。而这种新的再投资形式的净效应就是中产阶级化。肖特自己则认为租金差额理论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不应想当然地到处通用。(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00-202页)莫斯科维茨在书中也认为尼尔·史密斯的“租隙理论”(rent gap theory)是很有学术阐释力的一种解释,但是他更注意到在史密斯理论中的“榨干后再整建”策略,就是开发商先是尽可能不维修房屋,先榨出房屋现况的利润,时机成熟时再以重建踢走旧居。他认为“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阴谋论,但现实却往往与其吻合。”(43页)我认为更有启发的是肖特对美国党派政治与中产阶级关系的分析:“从本质上来说,近来美国政治的历史就是一场争取中产阶级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里根派民主党的出现就是共和党为了赢取中产阶级基础而努力的结果,至少就总统大选而言是如此。政治辩论集中在满足中产阶级期望的问题上。”(《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236页)说到底,所有经济斗争的背后都离不开政治的斗争。
因此,虽然莫斯科维茨在写作该书的时候深深受到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1916-2006)的经典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的影响,在全书的开头就说自己从小在纽约西村(West Village) 长大,离简·雅各布斯写下她的巨著的地方很近,讲述了她在书中的核心观点,但他还是指出“简·雅各布斯的理论缺少关键的种族与阶级分析”(238页)。在我阅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印象中,莫斯科维茨的说法不无道理,重新翻开这部著作就更是觉得莫斯科维茨的批评很有意义。在 “导言”中雅各布斯表达了对处于正统地位的城市规划理论的不信任与不妥协的批评态度,并且表达了对于研究城市如何运作的真实过程的强烈关注。她深恶于城市规划者大权在握、却对真实的城市一无所知,认为他们对城市“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为了牺牲品”(26页)。在当时看起来这或许已经是对于城市规划者最直率的批评,但是实际上她似乎还不明白那些政治与资本权贵们并不是蠢,而是真的坏。她希望让城市拥有多样性和自然萌发的活力,让老建筑在新生活中继续发挥迷人的魅力,让人行道成为安全的、有助于人们自由交往的生活舞台—— 她似乎看不到资本贪婪的目光和政客的关注焦点根本就不会落在这里。
莫斯科维茨接着说:“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想要、需要什么一一更好的住宅环境、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公共交通、更多钱——但他们的公民权却遭到剥夺,无法得到这些资源。所以,要解决缙绅化,不是搞定经济或都市规划就够了,而是与民主相关。假如住在城市里的人、这些让城市实际运作的人,能够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呢?”(238页)这是对雅各布斯的补充,也是向前辈致敬。
但即便是在反抗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中,社区住宅的问题仍然很难成为斗争的焦点之一。作者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缙绅化的抗争有惊人的进展。‘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让警察暴力和长久以来的种族压迫成为每日新闻的主题,酷儿和跨性别运动已经重新将性别(gender)和性取向(sexuality)推到社会正义对话的前线,甚至主流政客们也开始倡导种族和经济正义。然而,说也奇怪,住宅课题还是在这些对话中缺席”(247页)。应该说,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压迫比较起来,城市改造、街区住民迁移的各种因素更为复杂,受迫害个人与群体的利益之间也常常有更多的微观差异性,城市政策制订者冠冕堂皇的口号也更具有欺骗性。地方政府在动迁政策的多变性和随意性中无疑折射出逐利的立场和权力的傲慢,但是也不排除在利益博弈中政府也不乏以寻求实质合理性资源的开拓来应对社会呼吁公平正义价值的压力。“街区中的战斗”的最后结局,有时也是由复杂的因素决定的。在我对城市改造、旧城拆建等城市问题的关注中,曾讨论过一个极为惊人的旧城改造规划:在十年内完成对约几十平方公里的老街区拆迁改造,涉及六十万人口的拆迁,投入超过一千亿元……这样大的旧城改造规模是少有的,其对旧城文化、原居住人口生态等方面的破坏性影响极为深重。后来这个规划没有大规模实施,是因为各种复杂因素所导致的,既非由于发生在“街区中的战斗”,也并非在城市建设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上取得了共识。如果说在读完莫斯科维茨的这本书之后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就是对于“战斗”的持久性和力量博弈的复杂性尚未有足够深刻的论述。
但是无论如何,我很同意莫斯科维茨在全书最后说的那段话:“……现代人对缙绅化的影响更警惕,我们便有机会在下一波资本浪潮袭来之前先做些什么。如同莎拉·舒尔曼所说,不是无时无刻都得革命。1960年代晚期的嬉皮、反战和民权运动扎根之前,许多作家、影像工作者、诗人、表演者、社运者等,数十年来已经打下基础,帮助人们想象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我相信此刻我们已经在奠定基础的路途上,在一个更宽广未来的起点上。是时候起而行了。”(252页)我们的确必须想象和相信在城市中将有着不一样的未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