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朱玉|路易斯·麦克尼斯:“我为什么要回到你身边?”(下)
穿越海峡
麦克尼斯的卡里克弗格斯城堡令人想起另一座古堡——皮尔城堡,屹立在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弗内斯半岛:
我曾与你为邻,你这粗粝的基石!
那年夏天整整四个星期我居于你的视野:
我每天都看见你;从始至终
你的身形睡在如镜的海面。

乔治·博蒙特爵士,《暴风雨中的皮尔城堡》,1806
1806年,华兹华斯在皇家美术学院的展览上看到乔治·博蒙特爵士的油画《暴风雨中的皮尔城堡》,写下这首挽歌。画中,城堡在雷电撕裂的天宇下岿然不动,一艘轮船在咆哮的大海上奋力抗争。人们一般认为这首挽歌写给一年前遭遇海难的弟弟约翰。但许多学者也指出,诗中哀叹的“悲痛”与“损失”也指向另一重回忆:“那年夏天整整四个星期”指的是1794年夏末,华兹华斯曾逗留于城堡附近的兰普塞德村庄,并在莱文沙滩上听闻罗伯斯庇尔的死讯。此前,1792年底,华兹华斯未及见到女儿出生就被迫离开革命的法国。1793年2月,英国对法宣战,更阻断了诗人与法国女友和女儿团聚的道路。因此,尽管挽歌中只字未提法国,城堡周围的景物显然构成他人生中一段动荡岁月的背景,一种涉及法国的生命损失在其中投下巨大的阴影。希尼曾用华兹华斯的案例来说明北爱尔兰少数群体诗人的典型情况:
当英国向革命的法国宣战,年轻的威廉·华兹华斯遭受了一种错位,与现在依然发生在爱尔兰的状况非常相似。这位英籍的大革命支持者怀有法国的政治理想,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华兹华斯将这种困境戏剧化,忆起他在教堂参加为英军成功而进行的祈祷仪式时所感到的孤立、叛变与不忠。华兹华斯说,他的忠心突然裂开一个罅隙,引发令人迷失的巨力,给他的道德自我带来空前绝后的震动与打击。
希尼认为,华兹华斯在诗歌中讲述心灵的危机与复原,北爱尔兰的大部分诗歌也是如此,“写作的最大努力是整合,将全部的文化政治力量重新分配,使之获得差强人意的秩序”(189页)。
1813年,同在弗内斯半岛,华兹华斯写下《黑峡谷之巅即景》(“View from the Top of Black Comb”)。极目远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马恩岛,尽收眼底。在爱尔兰海的那边,他还依稀看到“蔚蓝的山脊”:
那蔚蓝的山脊
是转瞬即逝的云?抑或那里
我们可见爱尔兰海岸的轮廓?
华兹华斯暗引弥尔顿在《失乐园》中的比喻,将爱尔兰海岸(“Erin’s coast”)比作“另一个世界的明亮界限”(“the bright confines of another world”)。但他尚未穿越海峡进入这新世界。1823年,爱德华·奎利南(Edward Quillinan,1791-1851),这位出生在葡萄牙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出版了一本诗歌体书信集《三叶草,或威克洛远游》(Shamrock Leaves, or, The Wicklow Excursion),其中一条注释提及华兹华斯,他未来的岳父。奎利南说,华兹华斯的缪斯“似乎从未提醒他,西部的美景为歌而生却尚未被歌咏;将他自己的浪漫海岸与如同莱德尔、布洛岱尔或阿尔斯沃特(作者按:湖区地点)一样优美的景色分开的,不过是一道狭窄的海峡”。
六年后,华兹华斯终于穿越“狭窄的海峡”,抵达都柏林。华兹华斯的爱尔兰之行有其历史背景。首先,1801年《联合法案》颁布后成立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人对邻近的爱尔兰产生旅游兴趣。华兹华斯曾怀着“极大的乐趣”阅读恺撒·奥特维(Caesar Otway)的《爱尔兰速写》(Sketches in Ireland,1827),希望亲自拜访这个“姐妹国家”。奥特维还赠送诗人两幅丝制爱尔兰地图。其次,十九世纪初英国军事部门发起的地图测绘活动(Ordnance Survey),开启了对爱尔兰地貌的精细测绘。布莱恩·弗里尔的戏剧《翻译》就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同时,1829年4月,英国通过了《天主教徒解禁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确认了天主教徒享有担任教职和参加议会的民事权利。在这些背景下,华兹华斯的爱尔兰之行就不仅是一场旅游,也是一场交游与观察。旅途中,他关注时政,与宗教、政界、科学、文学等各界名士往来,体现了十九世纪初英爱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不禁想问,经历过错位感的华兹华斯能否理解爱尔兰人的复杂处境?
1829年8月底,华兹华斯在爱尔兰皇家天文学家威廉·罗文·汉密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1805-1865)等友人的陪同下,开始了为期五周的爱尔兰之旅。他们游历的许多名胜古迹都将被麦克尼斯写入诗歌的地带。而麦克尼斯故乡安特里姆的鹰也成为这次旅行中唯一进入华兹华斯诗歌的意象——“你也被听见,孤鹰!”(《声音的力量》,1835)站在敦星克皇家天文台(Dunsink Observatory)的制高点,华兹华斯俯瞰利菲河谷和都柏林湾;在三一学院图书馆,他瞻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地图馆藏(the Fagel Collection);造访了1798年起义的重要阵地威克斯福德郡的醋山;游历了未来叶芝的故乡斯莱戈,沿途看到本布尔本山(Ben Bulben)所在的达特里(Dartry)山脉,“一座巨大且轮廓丰富的石灰岩山体浸在深沉的紫晖之中”。两处地方留给华兹华斯最深的印象,一处在威克洛的圆塔,一个爱尔兰女人把孩子的脚浸到圣凯文的湖水中,“为了治疗跛足”。华兹华斯写道,那位天主教女人“如此隐忍,如此虔敬,如此朴素纯一”,她谈起孩子病苦时的温柔,细述孩子走向康复时“那悲伤的欢乐,足以打动最冷漠的人”。大约一百五十年后,希尼从贝尔法斯特移居此地,将所在的格兰摩尔村庄比作华兹华斯的格拉斯米尔,写下《圣凯文与乌鸫》。另一处是前文《诀别》中写到的凯里郡基拉尼,“基拉尼的三个湖泊……胜过我们任何一个湖”;卡朗图厄尔山(Carrauntoohil)“比我们任何一座山都更壮美”。华兹华斯甚至说,他希望与一位技艺高超的艺术家联手,为此地写一本地貌导览。(Brandon Yen, “Ireland and the English Lake Poets”, Library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n.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story/ireland-the-english-lake-poets-trinity-college-dublin-library/RgWxlmqA5vTuIg?hl=en)
但他并没有写。一百多年后,另一位爱尔兰诗人怀着同样的好奇,穿越海峡,来到苏格兰西岸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写下一本游记,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观察岛民,通过认识“他者”而反思自我——爱尔兰。麦克尼斯的《我穿过明奇海峡》(1937)是一部文体松散的作品,融合了日记、诗歌、简史、对话、戏仿和讽刺信件等多种形式,借助历史、地理与政治等多重视角。根据本书编者的观点,这部作品属于两次大战之间流行的岛屿书写,比如爱德华·缪尔的《苏格兰之旅》和休·麦克迪尔米德的《苏格兰岛屿》,但它不同于凯尔特复兴的传统,而是着眼社会经济现实。在这部游记中,麦克尼斯关注的是,在多大程度上,赫布里底群岛能够抵御英国化和商品化这两种不可逃避的趋势。他着迷于岛国自身的独立性,并从这些岛屿中联想到爱尔兰西部,他父亲童年生活的地方以及他父亲的父辈栖居的地方。这是一部求索之作,是希望“发现血浓于墨——我体内的凯尔特血缘将被其同类磁吸到表面”的旅程,尽管这种尝试以徒劳告终。作者以一位局外人的身份开篇:
今年我两度拜访——四月和七月——外赫布里底群岛。去之前,我并未意识到几乎所有岛民都说盖尔语,他们的语言就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懂他们的语言,无法深入他们的生活。因此,我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描写他们——一个对岛屿失望、被岛屿挑逗诱惑的游客,来此仅仅是为了提醒自己,在那片土地上,他永远是一个局外人。(Louis MacNeice, I Crossed the Minch, ed. Tom Herron, Edinburgh: Polygon,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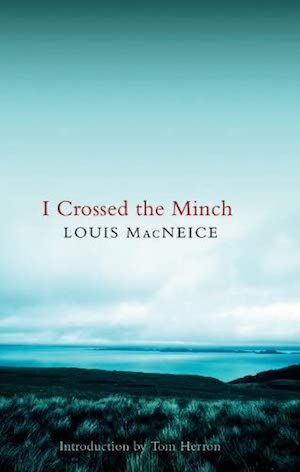
I Crossed the Minch书影
作者自称为局外人,局外人的视角使他在谈论赫布里底群岛时能保持一种平衡冷静的常识,这是他在直接书写爱尔兰时所缺少的。他可以在赫布里底群岛上观察一个微缩的爱尔兰,不带任何痛苦与愤怒情绪,毫无怨恨地思考一个有别于发展中国际秩序的地方与岛屿社区,并认为世界性社会必须是各种差异社区的联盟。麦克尼斯强调自身中的凯尔特气质(“the Celtic in me”),并将这些岛屿和伦敦进行比较:
从血缘上来说,我可能更接近赫布里底人而非伦敦佬,但我全部的成长与教育经历让我疏离自然的(或者说原始的)文化,在不列颠的岛屿中,这种原始文化仅存于凯尔特或落后的边地。我去赫布里底群岛,部分原因是希望发现血浓于墨——我体内的凯尔特血缘将被其同类磁吸到表面。这是感情用事且徒劳的希望。一次,坐在河畔与一些刘易斯岛民喝啤酒,其中一位唱起了盖尔语情歌,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属于这群人,而伦敦沉入污泥。但酒精的信念并不持久。
岛屿即孤立:两者同义。我们以为会在岛上遭遇狭隘的邪行。令人震惊的是,岛屿被大陆的邪恶侵略。
他看到赫布里底群岛受到了商业的侵蚀,堕落到异族手中,但认为要形成一种更加高级的文化尚需漫长的时间。他反思自己初登岛上,曾不近情理地抱怨岛民一脸忧郁,但逐渐认识到,“当地人不会热情地欢迎你。他们会礼貌,体贴,好客,但没有你,他们会过得更好”。麦克尼斯对待外来入侵的态度由此可见。他观察到赫布里底岛民大多行动迟缓,和爱尔兰南方人一样,没有很强的时间观念,但他们的语言或思维并不迟钝,“听他们说盖尔语,你会发现他们的言谈带着火、速度和丰富的戏剧性的”,“给他们威士忌,你会发现天主教和凯尔特气质浮现”。书中也写到自然景色,并将之与爱尔兰的风景对比,不经意间流露出麦克尼斯对故土的微妙情结:
大多数关于高地和岛屿的书籍都把当地景色浸入无法遏制的紫色和金色中并多愁善感地描写当地人民。从我两次的旅行来看,外部群岛的风景并没有不同寻常地丰富多彩,当地人也缺少那种显著的魅力和光彩……我们通常期待在游记和地理杂志有关人迹罕至之处的文字中看到的样子……假如有更多荆豆花,像爱尔兰那样,这里的风景会更加动人。七月野花遍地。我并非花草爱好者,更偏爱宏观效果——祖母绿色的燕麦田埂盘旋在山丘上宛若青蛇,或一片三公顷的草场,开满紫色野生天竺葵。
麦克尼斯还表达了对苏格兰民族主义的看法,借此探讨爱尔兰的政治境况:
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很多人是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我总是嘲笑苏格兰民族主义是对真实政治感到厌恶的聪明青年的宝贵情感,但在岛上,这个概念比在爱丁堡更有意义。苏格兰作为一个整体再也不会重新获得她的统一和独立的自我意识,但对于大陆之外这些讲盖尔语的群岛来说,这依然是一件可能的事。他们的传统语言无需人为培养;他们的人口少得足以维持真正的社区情感;他们的社交生活依然单一(尽管商品化很快就会在其中制造裂隙);最后大海依然将他们与邻居分开。用埃斯库罗斯的话来说,“大海在此,谁会把它榨干?”
他认为让赫布里底群岛实现经济独立是“荒谬”的,然而“为保存岛屿的社会和文化独立而做出一些让步是可行的”,在经济上,“群岛可以让自己配合他们更大的邻居而不臣服于彼”,“我从来不认为,为了保留他们的语言和社区情感,他们就该故意拒绝现代化的优势”。这些内容反映了麦克尼斯在独立与联合、原始与现代之间的思索。他还通过斯托诺韦(Stornoway)的例子说明了英国化的副作用:
地区差异远不如其共性重要,或者全体岛民有别于大多数大陆苏格兰人的共性。也许有一天,赫布里底人失去自己的语言,全方位地与其他苏格兰人或者(也有可能)与世界上所有说英语的种族合并起来,也许有朝一日这是好事。但那一天还没有来。迅速英化的副作用体现在斯托诺韦。农场主进城后,用他传统的节奏和例行方式去换取格拉斯哥仓皇不安的心态和英语公众图书馆里的爵士文化。
两次旅行之间,麦克尼斯也写了一些诗,其中《风笛音乐》通过爵士乐与风笛音乐的对比,反思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在刘易斯岛,麦克尼斯参加了两场音乐会。身穿传统服装的风笛乐队和他们深入脉搏的节奏刺破诗人的记忆,麦克尼斯写下《风笛音乐》,“为苏格兰盖尔语区、为所有传统文化献上讽刺的挽歌”。诗中阴韵(feminine rhymes)暗示风笛的喘息,仓促即兴的气氛也暗示着新的文化无暇与古老的传统歌谣的完全韵(full rhymes)达成和谐。诗中的音乐鲜活凄厉,节奏、副歌和戛然而止的沉重音调都表达了典型的三十年代的绝望(《传记》,212-213页):
不要旋转木马,不要黄包车,
我们只要老爷车和西洋镜。
他们的裤子是双绉,他们的鞋是蛇皮。
他们的客厅铺着虎皮地毯他们的墙上挂着牛头。
“不要……不要……/只要……”是贯穿这首诗的主要旋律,诗人借此思考传统音乐与爵士乐及其代表的“现代世界的混乱”之间的矛盾关系。 诗中的低音和吟唱提醒我们这首诗是关于赫布里底群岛的,但也是全球的。
麦克尼斯如柯尔律治笔下的老水手始终漂泊于迷航。从冰岛(“北方始于内心”)到明奇海峡,从美洲到希腊群岛(拜伦与民族独立战争始终是旅行的背景),晚年他还作为BBC记者前往喜马拉雅——“印度洋颇似贝尔法斯特湾”(1955年11月5日书信)。无论在哪里,爱尔兰始终是他的参照系。在广播剧《疯狂的岛屿》(The Mad Islands,1962)中,爱尔兰与苏格兰在象征层面融为一体,诗人关于明奇海峡的认识也变得更加清晰。他在剧本前言中写道,“我写这部作品,因为我始终对古代爱尔兰航行传说感兴趣”。在航海中,“我们所知的世界仿佛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剧中母亲的一番话尤其耐人寻味:
我没有见过大海——或者嗅过或感受过——已经很多年了。但我曾经住在一座城堡里,北面、西面、南面都是海。哦,那流动的海水和风的装饰音,海藻的气味和成群的海鸥!但我现在不能接近大海,只要那个人还活着并浪迹西部的岛屿。水不像陆地,每一滴连着下一滴;从未间断,没有阻隔。我脚上的一小滴浮沫,或者我脸上的一小朵浪花,都让我觉得凶手在触摸我。只要他还在那里航行,整个大海都被染污。你要去使大海恢复洁净。(Louis MacNeice, The Mad Islands and the Administrator: Two Radio Plays, London: Faber & Faber, 1964, p.9)
《秋天日记》:“我为什么要回/到你身边,爱尔兰,我的爱尔兰?”

Louis MacNeice, Autumn Journal,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2
《秋天日记》是一场由秋入冬的自传性旅程,作于1938年8月至12月,记录了二战前夕诗人的心境。创作之初,麦克尼斯就和艾略特谈起这部诗歌:一部“长达两千至三千行的长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但记录了那段时期我的精神和情感经历”。全诗“包含二十四部分,每部分平均约八十行。这种划分给它一种戏剧性”,诗行长度错落变化,诗句本身“富于节奏且避免抑扬格”,是“迄今为止我最好的作品,既是一幅全景画也是信仰声明”(Louis MacNeice, Selected Letters of Louis, edited by Jonathan Allis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p.312)。艾略特收到稿件后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已经读过《秋天日记》,我认为确实很棒。时常深受感动,更难得的是,对一部长诗来说,整个阅读过程中,我的兴趣始终丝毫未减。部分原因在于你擅长变换韵律,同时,我认为,也在于诗中的意象皆是活生生的意象,而非仅为诗性暗示(poetic suggestiveness)而选取的意象。(《传记》,223页)

“费伯诗人”,左起:麦克尼斯、泰德·休斯、艾略特、奥登,斯蒂芬·斯彭德,费伯出版社,1960年6月23日
此前,麦克尼斯在《今日诗歌》(1935)中赞颂了奥登诗歌的时政性和预言性,并指出从今往后“纯诗歌”(pure poetry)将越来越少,“心理诗和政治诗”与“长篇作品(史诗、小型史诗、散文诗和自传体诗)”将越来越多。在《现代诗歌:个人随笔》(1938)中,麦克尼斯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呼吁不纯粹的诗歌(impure poetry),即受到诗人生活及其周遭世界影响的诗歌。”他接着说道,诗人“既是批评者也是娱人者(除非他令人愉快否则他的评论将毫无效力)。今天的诗歌应在纯娱乐(‘逃避的诗歌’)和宣传性言论之间把握中道”(Louis MacNeice, Modern Poetry: A Personal Ess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当他创作《秋天日记》时,这部作品将“以纪录片的形式容纳世界的不纯粹,经验的涌流,看似完全自发,实则精心设计——如胶片上的图像——在一种无形的想象力的指引下。”(《传记》,228页)
《秋天日记》的前言表达了麦克尼斯的诗学主张,尤其是“诗歌首先要诚实”。艾略特也认为,这部诗歌之所以如此感人,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诚实。这篇前言值得全文引用:
我知道这部诗中有夸张的成分——比如涉及爱尔兰、牛津补选或我私人生活的部分。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果我写的是说教诗,那么我有义务去修正或删除这些夸张和矛盾。但我写的是我称之为日记的东西。在日记或私人信件中,人们写下当时的感受;要尝试达到科学的精准将是——这是悖论——不诚实的。抒情诗的真实不同于科学的真相,这首诗介于抒情诗和说理诗之间。鉴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说理诗的倾向,我想这其中含有某种“人生批评”或暗示一些不仅仅属于个人的尺度。我的写作跨越1938年8月至新年,我没有根据写作结束后发生的事情来更改任何涉及公共事件的段落。因此关于巴塞罗那的部分写于巴塞罗那陷落之前,如果我以后视的眼光,根据自己对后来事件的反应来修改之前的段落,我认为是这不诚实的。我也没有试图提供如今众人对诗人的要求——最终的裁决或平衡的判断。这首诗的性质既非决议也不平衡。我的一些信念,我希望,能在诗文的过程中浮现,但我拒绝使它们抽离于语境。出于这个原因,我会被一些人称为骑墙派,被另一些人称为感伤的极端主义者。但我认为诗歌首先要诚实,我拒绝以诚实为代价的“客观”或明确。
L.M. 1939年3月
麦克尼斯的传记作者将《秋天日记》比作三十年代的《序曲》(248页)。但笔者也想到济慈的《秋颂》和雪莱的《西风颂》,两位后革命时期诗人对艺术与现实的思考。1936年11月6日到1938年5月,麦克尼斯住在汉普斯特德的济慈故居(4 Keats Grove),并写下《花园里的阳光》等名篇。济慈在1818年至1820年间居住于此。1819年9月19日,济慈沿着汉普郡温切斯特的伊钦河散步,写下《秋颂》,虽咏秋景,却是对彼得卢屠杀的回应,是关于死亡的沉思。麦克尼斯创作《秋天日记》时,也是刚从汉普郡度假回来,诗的第一句就是“夏日将尽在汉普郡”,诗中也表达了战争前夕的沉重思绪。而雪莱的“枯叶”意象也在诗中反复出现(如第一首、第十一首),甚至雪莱的名字直接出现在第十五首首行首词。也就是说,如同《西风颂》,《秋天日记》也思索毁灭与新生的问题。全诗语气诚恳,情感真挚,节奏急促,一气呵成,亦不无辛辣。其中第十六首直接谈论爱尔兰,如火山爆发。
“我又恨又爱”(Odi atque amo)。精通古典文学的麦克尼斯在这部分结尾引用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84-54BC)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他对爱尔兰的矛盾情感,为第十六首诗定下基调:
我们该用生锈的匕首把这个名字刻在树上?
她的群山依旧青绿,她的河流
汩汩涌过巨砾。
她是讨厌鬼是坏女人
第十六首诗的首行仅由三个单词组成:“噩梦留下疲惫。”“噩梦”启动诗文,并使之在个人化的梦境/回忆与爱尔兰的历史/现实之间交错展开,激烈而哀伤。首先,睡梦者“嫉妒行动者”,“他们睡去醒来,谋杀暗算 / 毫不迟疑,毫无畏惧”。“行动者”也包括“我毫不妥协的同胞”,“他们开枪杀人从不 / 见遇难者的脸变成他们自己”。这里可以听见麦克尼斯对叶芝的回声,在“嫉妒”行动者的同时,也质疑他们的行动。麦克尼斯从莫德·冈写到胡里痕的凯瑟琳,反思将爱尔兰女性化的问题:
胡里痕的凯瑟琳!为何
一个国家,如同轮船或汽车,必须永远是女性,
母亲还是甜心?一个女人走过,
我们只见她走过。
走过如一抹阳光在阴雨的山上
然而我们永远爱她并恨我们的邻居
而每个人都在他的遗嘱中
延续继承人的仇恨。
诗人没有作答,而是在一阵鼓声中追溯了爱尔兰的动荡历史,感叹自己的疏离,反思爱尔兰性,追问“为何我们喜欢做爱尔兰人?”这次,诗人给出了部分答案:
这就是我的国而我觉得自己
离它很远,上学、定居都在英格兰,
但她的名字始终如洪钟
回响在水下钟楼。
为何我们喜欢做爱尔兰人?部分因为
它让我们这些以仙水受洗的
一个莫须有世界中的成员
在感伤的英国人中找到支点;
部分因为爱尔兰够小
足以给人家的感觉,
因为汹涌的波涛
使她远离更商业的文化;
因为人们觉得在这里至少可以
做地方工作而不受制于世界
且这小小舞台上的幸运儿
或有望实现具体行动的目的。
然而,诗人话锋一转,坦言“这当然是自我欺骗;/ 这座岛上也没有免疫”。他批判“建在烂泥上的城市;/ 建在利润上的文化”,控诉一系列教育、经济、环境、失业等问题,反思自由邦的孤立主义政策以及南北分治后反映在文学上的民族主义。“纸上墨迹这么黑/三叶草也不能覆盖”。但在一连串猛攻之后,麦克尼斯以“我的爱尔兰”颠覆了此前的斥责,最终表达了“血浓于墨”、超越理智的深切情感,是《秋天日记》最动人处:
格里菲斯,康诺利,柯林斯,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哪里?
我们自己!就让圆塔卓然屹立
在硝烟四起的世界!
让学童们笨手笨脚地摸索
于一种半死的语言;
让审查者忙于检查书本;拆毁
乔治风贫民窟;
用盖尔语竞技。
让他们种甜菜糖;让他们
在每个村庄建工厂;
让他们把被害的魂灵分为
绵羊和山羊,爱国者和叛国者。
而北方,我童年生活的地方,
依旧是北方,饰以格拉斯哥的尘垢,
成千上万的人们找不到工作
站在角落里,咳嗽。
而流浪儿童在潮湿的路面
玩耍——跳房子或滚弹珠;
而每个有钱的人家都有一张松垮的球网
在松软的草坪上,在湿漉的灌木旁。
冒烟的烟囱暗示
街角的繁荣
但他们用外国纤维制造厄尔斯特亚麻
而赚来的钱又花出去赚更多的钱。
建在烂泥上的城市;
建在利润上的文化;
言论自由被扼杀于萌芽,
少数派永远有罪。
我为什么要回
到你身边,爱尔兰,我的爱尔兰?
*****
海德莉·麦克尼斯(Hedli MacNeice,1907-1990),拥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歌手,曾在奥登和麦克尼斯等人的许多剧作中歌唱,1942年至1960年间成为麦克尼斯的妻子。在《路易斯盖的房子》(题目戏仿传统儿歌《杰克盖的房子》[“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Hedli MacNeice, “The Story of the House that Louis Built”, in Studies on Louis MacNeice, Cae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Caen, 1988, pp.9-10)里,她描述了一座“厚砖墙的漂亮房子”:“西面的窗户望向康尼玛拉、梅奥和大海。南窗环视多塞特、唐斯丘陵和莫尔伯勒——北窗俯瞰冰岛,东窗面向印度。前门宽大并永远敞开。”这样的布局使我们想起开篇提及的五塔阵,再次证明了麦克尼斯向多元(“incorrigibly plural”,《雪》)敞开的态度。
路易斯的房子里,前厅门庭若市,往来皆是权贵,“那些认为路易斯害羞、傲慢、礼貌、难以接近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他”。第二间屋有一扇坚固的门,敞向一个大房间。路易斯常靠在那里张望,期待兴奋的消息。进入这里的人包括远方归来的记者、诗人和演员。下一道门只对少数人开放,屋内家具破旧,有舒适的椅子和炉火,到处都是书。在这儿,麦克尼斯和三两知己自在相处。这间屋后还有一间很小的斗室,只能容纳两个人:他和迪伦·托马斯或W. R. 罗杰斯。他会拿着手稿和他们讨论创作,“只和他们”。在这之后,一条通道引向另一间屋子,透过玻璃拱顶可以仰望星辰,“在那里,路易斯与上帝独处,或按他的说法,与那些伟大的精神,希腊或罗马,或者但丁,邓恩,斯宾塞和伊丽莎白时期的作家,更近些的叶芝、艾略特和奥登”。通过他们,他谦卑地衡量自己的成就。楼上有两间屋,第一间空荡荡的,他在那里接待偶尔的女性来访。第二间有画有花有琴,他生命中的五位女性在那里徘徊……门楣上写着“爱、忠诚、孤独与幻灭”。“1963年9月3日,他一边说着‘我要死了么?’,一边悄然关上他盖的房子的门。”
此处应该有本杰明·布里顿(多次与麦克尼斯夫妇合作)的《战争安魂曲》(1962)。

麦克尼斯百年诞辰时,希尼在麦克尼斯墓前凭吊,Carrowdore, Co. Down,2007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