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40年40人|黄仁伟:中美关系从未间断是两国根本利益需要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作为来自于上海的专家,黄仁伟能够从历史的维度挖掘上海悠久的美国“烙印”;作为国内著名的“美国通”,他与多位美国资深的“中国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看来,认识和研究美国的捷径就是不断向“对手”学习——对他来说是如此,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在研究美国以及和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黄仁伟还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中美无论是敌是友,双边关系从未间断,保持接触和联系是受两国根本利益驱动的。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对中美未来形势的判断能够更加从容,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也始终抱有信心。
从黑土地走向美国研究之路
澎湃新闻:1972 年尼克松访华,您当时在黑龙江逊克县插队,听到这个新闻后是什么反应?
黄仁伟:197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年份,“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而我在中苏边境的北大荒插队。当时中苏正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这个状态也是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历史性条件。那年冬天,我在一个深山里看守一个县里的战备军火库,一个人很孤独,我就听收音机。收音机里能听到的电台不多,当时我从苏联的电台里听到说,尼克松要来北京了。我以为这是苏联“敌台”造谣,根本不相信,但后来我从深山里出来回到自己的连队后,果然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握手,这才恍然大悟,那时候已经是3、4月份了。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走向研究美国之路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对您的研究事业有何具体影响?
黄仁伟:我1977年参加高考,后来一直读到硕士、博士,学的都是美国史,可以说这个阶段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美国。学成后我来到上海社科院工作,当时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美之间最重大的问题是“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海社科院就让我改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转变,因为两个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经过3年的研究,我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从历史的美国转到了现实的中美关系。因而可以说,是中美关系改变了我的专业的方向,也是因为“最惠国待遇”问题,使我比较深地“卷入”到中美关系前沿的争端问题上来。
到了90年代中期,台海形势恶化,台海问题变成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这时候我遇到了人生中重要的导师—汪道涵先生。他当时是海协会会长、中央对台领导小组成员,又曾是上海市长。在台海问题上,当时大陆讲“一国两制”,台湾方面讲“一国两县”“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实体”等,就是没讲“一国两制”。当时我们对除了“一国两制”讲法以外的东西全部否定。我就这个问题,在1993年写了一篇题为《一国之下XX都可以谈》的长报告,汪老看到这篇报告后很感兴趣,就把我请到康平路去谈。他认为我应该把这个问题继续研究下去,加之我又是研究美国的,所以汪老让我把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之后的几年里,我基本上都是在汪老的指导下研究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澎湃新闻:近40 年来,从研究生、学者到智库专家,从研究史料、旅美访学到交美国朋友,您对美国的认知是如何变化的?
黄仁伟:读书时认识的美国和现实中同美国打交道是很不一样的。而且从与美国打交道逐渐上升到本质上认识美国,又是一个不断地深化和提高的过程。
要讲具体的认识,我认为有四点:第一,美国有她的独特性。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其历史条件、制度因素、自然禀赋以及人才优势,这些都是别的国家难以同时具备的。所以,不是说各国效仿美国也可以成功,因为这是学不来的,美国成功的条件是独一无二的。第二,中美关系从未间断。我们同美国不管是成为敌人的时候还是成为朋友的时候,双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不间断的。即使是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时期,中美还是在联系、在接触,因为中美的接触是两国根本利益的需要。接触可以上升为合作,合作可以再上升为长期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不是凭空而来的,一定是通过接触与合作形成的。第三,我们需要长期向美国学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可否认我们要比美国的发展程度低,很多方面还有欠缺,所以向美国学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前面我说学美国是学不来的,现在我又说必须学美国,这是两个概念。所谓学美国学不来是指照搬美国不会成功,必须学美国是指要把美国研究透,只有把美国的方方面面都掌握了,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第四,在与美国互动时,我们既要自信也要保持清醒。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对比,不是简单的GDP对比,而是对比科技的创新能力、制度的成熟程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以及社会的多元性等。
立足上海看中美
澎湃新闻: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这40 年来在推动中美经济关系发展中做出了哪些贡献?
黄仁伟:上海能够站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沿有三个历史条件。第一,上海与美国有深厚的经济与人文纽带。仔细想一想经济上的纽带,解放前的上海曾经有许多美国企业,例如友邦保险。友邦保险最早不是建立在美国,而是建立在上海,解放后企业搬回了美国,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初,它又回到了上海。它重回上海后是最早享有国民待遇的外资企业之一。人文纽带包括在上海的犹太人,其中有很多人后来去了美国,他们对上海至今都怀有特殊的感情。我们往往在研究现实时就忘掉了历史,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痕迹,上海就不可能在中美关系中扮演重要作用。第二,《上海公报》在上海签署。《上海公报》是使中美关系重新走向正常化的历史性文件。《上海公报》的签署就使上海在中国外交史上,特别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作用变得不可替代。有了《上海公报》后,就可以把上海定位为中美关系发展的起点和基石。第三,浦东开发开放提供机遇。浦东开发以后,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大量的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了上海,这是上海能够成为中国国家级金融中心的重要条件。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国家,美国的金融机构不进上海,上海就不可能成为国家级金融中心,今后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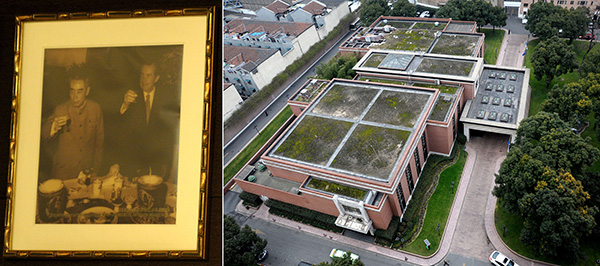
澎湃新闻:特朗普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且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中美之间博弈的烈度是否已达到历史的新高?
黄仁伟:中美关系走到今天,必然会形成这样一种战略竞争。如果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并不觉得这有多么可怕,关键是双方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要允许美国对中国有一些想法、有一些不适应;反过来,美国也要允许中国对美国有一些想法、有一些不适应。
对于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新定位,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这个战略,或者说这个定位是不是美国所有对华政策参与者的共识?实际上,美国国内还有很大一部分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通”还没有发声。为什么?因为美国国内现在形成了一股潮流,即讲中国好话在美国就站不住脚,但这股潮流不会久,因为它不符合事实。第二,如果是共识,那么这个战略在经济、军事、文化软实力上要耗费多大的成本,才能搞倒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经济第二位的大国?对于衰弱中的俄罗斯,美国都已无力应付,更何况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俄罗斯的8到10倍。因此,即使美国有战略,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这个战略的实现。第三,再退一步,如果这个战略能够基本实现,那么结果是什么?是美国也一塌糊涂,美国的利益、国际地位和领导权都会受到致命的损失,而世界也会彻底混乱。所以,这个战略的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会输。那么,既然上述三条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不如同美国讲,我们还是要合作。
“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澎湃新闻:您在15 年前就出版了专著《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 后又参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建构。如今美国又将中国视为事实上的崛起大国,您认为今后中国的和平发展应在哪些方面发力,对冲来自美国的压力?
黄仁伟:我2000年左右开始研究“中国崛起”,2002年写了这本小册子。到现在为止,这本小册子中的所有观点都没有过时,所有观点也都被证实了。当时我有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中国不能重蹈德国、日本、苏联崛起的覆辙。事实证明,他们的道路都是失败的,其最大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崛起过程中挑战头号霸权,而且是用军事力量进行无限扩张,与整个国际体系相撞,这条路中国不可以走。
第二,中国和美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相对而言,现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要比2000年的时候还要多得多。中美的共同利益大于中美利益的分歧,而且共同利益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基本趋势,只要有这个基本趋势在,“修昔底德陷阱”就不可能成为现实。过去历史上敌对的大国都没有这么大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分割、隔断的,人和人也不来往、文化也不交流,只是在军事上相撞。中美之间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第三,中美需要“合作加危机管理”。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中美关系会有一段冲突上升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特别需要双方用智慧、用技术、用制度来巧妙地处理和控制冲突的程度,这就需要“合作加危机管理”。我所说的“危机管理”是广义而言的,包括南海、台海、朝鲜半岛等地缘政治问题,也包括经济,尤其是金融、汇率等议题,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冲突、反恐、流行病等都需要危机管理。因而,就双边来说是危机管理,但就全球层面来说就是全球治理。
上述三点概括起来讲就是“不走老路”“共同利益”和“合作加危机管理”。理解这三点就基本上能够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时间性”与“空间性”?这一倡议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黄仁伟:“一带一路”的空间范围远远超出中国本土,甚至于超出欧亚大陆。如果我们观察“一带一路”的走向,可以说它正在改变着世界市场的格局。在当前世界经济的版图中,欧亚大陆中间是“塌陷”的,如果这块区域不发展起来,它就没有真正地进入世界市场。而“一带一路”正好串联起欧亚大陆两端,能够把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拔高,甚至使这片区域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高地,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世界市场新版图。当然,美国对“一带一路”有看法。担心“一带一路”会使其盟国体系、势力范围和控制小国的方式都被改变。但是,如果“一带一路”是符合世界经济规律的话,而美国又放弃与“一带一路”的结合,那么美国就会脱离世界市场。这样的话,美国的领导地位何在,而且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也会动摇。现在的全球化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全球化,“一带一路”顺应了这个潮流。如果美国选择放弃这个潮流,那么对美国而言就会继续走下坡路。
“中国通”和“美国通”
澎湃新闻:您和几代美国的“中国通”都打过交道,与他们“亦敌亦友”,您如何评价这些美国的“中国通”?
黄仁伟:我自1994年跟随汪老一起做中美关系到现在快25年了,和许多美国的“中国通”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就没有唇枪舌剑甚至是“口诛笔伐”。双方为国家利益不肯让步和双方作为私人朋友推心置腹,这两种状态经常是同时出现的。邓小平曾就做美国工作说过这么一句话,“朋友要交,心里要有数”,意思是不要交了一位美国朋友后就变成什么都听他的了。如果你讲的话与这个美国朋友一样,那么你在这位美国朋友眼中也没有什么价值。这些美国朋友们虽然有他们的价值观,有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是他们在中美关系的很多关键时刻,却是想办法要把中美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点,把中美之间的合作尽可能地维持和发展。
我举几个例子:首先是傅高义。1996至1997年的台海危机之际,他曾率领一支“梦之队”来到中国,队伍里包括十几位共和、民主两党顶尖的“中国通”。他们当时定的调子就是“与中国共存”(living with China)。回国后傅高义就写了《与中国共存》一书,后来这本书也成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蓝本。
其次是兰普顿。他从90年代初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到现在,一直在帮助中美双方加深理解。2015年,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召开的“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上做主旨演讲。也是在那场演讲中,他提出了“中美关系进入转折点”,事后也印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他当时非常担心、非常忧虑,在整场演讲以及演讲完和我见面时,都是一种沉重的心情。
再者是包道格。包道格是老布什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东亚事务主任,后来还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他在台北期间正好是陈水扁的任期,陈水扁全力以赴想要推动“台独”。包道格当时明确地压制陈水扁,不允许他搞“台独”,他甚至在公开场合批评陈水扁。正因为此,美国的“亲台派”对包道格非常怨恨,台湾民进党的一些“台独死硬派”也记恨包道格。2016年“南海仲裁案”成为热点的时期,包道格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和平研究所为我们同美国战略界对话搭平台,他也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还有李侃如。1998年上半年,李侃如到上海来参加我和王缉思共同主持的第一次中美关系专家高层研讨会。这次会议最终把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以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的“三不”原则写进共识文件。这年6月底,克林顿访华,李侃如当时刚刚进入白宫担任东亚事务主任,陪同克林顿一起来中国。据说克林顿在北京飞往上海的途中问李侃如,我到上海讲什么?李侃如说就讲这“三不”。结果,克林顿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中,将这“三不”原则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还有一位好友已经去世了,就是奥克森伯格。他是1979年中美建交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是当年中美建交的具体策划和执笔人之一。奥克森伯格对中国非常了解,他甚至在已经身患癌症的情况下去了三次西藏。那时候达赖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他就和汪老讲西藏问题,分析我们存在哪些问题,可能会和达赖方面发生什么问题,建议我们怎么做,等等。
澎湃新闻:您对中国新一代的“美国通”有哪些建议?
黄仁伟:现在的新一代相比我们当年有诸多优势。一是他们已经对美国不陌生,有丰富的渠道获得关于美国的信息;二是他们从最初阶段就可以接受美国的训练,能够比较快地了解美国的思维方式;三是他们进入国内的决策圈或者是战略高层的讨论圈的通道都比我们当年多得多,比如参与一些课题的研究等等。
对培养新一代的“美国通”,我有四点建议:
第一,青年研究人员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判断。部分研究美国问题的青年研究人员分不清什么是国家利益,或者说分不清美国做的事情哪些是由其国家利益决定的。如果美国把它说成是普世价值,会有人相信,难道美国做的事情只是为了普世价值吗?这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现在研究美国需要的不是“写意画”,而是“工笔画”,也就是说研究要做到细、专、深和具体。如今大家都在做笼而统之的大研究、大战略,做具体研究的人很少。但反观美国研究中国的研究人员,他们对中国是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研究。所以,我们的青年研究者要做“美国通”,一定也要有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做“精准”的美国研究。
第三,新一代“美国通”不仅要懂美国,也要懂中国。现在美国人到中国来,他不和你讨论美国怎么样,而是讨论中国怎么样。如果“美国通”不会讲本国的事,那么当美国人拿他们自己的事向你出牌时,你就没有牌可打。所以,“美国通”首先要是“中国通”。
最后,新一代“美国通”要到实务部门去走一走。美国的“中国通”都是在美国的在华企业、使领馆等一线磨炼过,而后再在智库或大学的中国中心、国务院中国处等机构工作,可以说是有一整套成长培养方案。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国青年学者,有机会也要走进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或者从事涉外工作,深入到基层与美国人打交道,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美国。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