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第174517号囚犯
普里莫·莱维,奥斯维辛幸存者,第174517号囚犯。同时,他也是化学家,被誉为意大利国宝级作家,是二十世纪重要的知识分子,备受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卡尔维诺、安伯托·艾柯等文学大师推崇。他是历史的见证者,并用笔写下良心与美德的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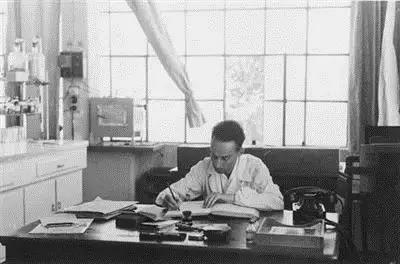
在集中营里,我是那么强烈地希望讲述这些故事,从而在那里开始描述我的经历,当场记录,在那个充满刺骨的寒冷、战争和警惕的眼睛的德军实验室中。
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无法保存这些随意而潦草写就的笔记,而且我必须立刻扔掉它们,因为如果它们被发现,会被当作一种间谍活动,让我送命。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奥斯维辛或集中营的那段历史,莱维曾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真诚回答引人深思:

莱维:我本人的性格并不倾向于仇恨。我认为仇恨是野蛮而粗鲁的,而恰恰相反的是,我情愿我的行为和想法,应该尽可能是理性的产物。因此,我从未在我的思想中孕育仇恨,无论是对复仇的渴望,还是对我真实或假想的敌人施加痛苦的意愿,或者个人的深仇大恨。我更不能接受将仇恨指向整个民族群体,比如,所有的德国人。如果我这样做,我会感到我在遵循着纳粹主义的教条。而纳粹主义正是建立于国家和民族仇恨的基础之上的。
我必须承认,要是让我直接面对那些岁月中的某个迫害者,面对一张熟悉的面孔,面对一些古老的谎言,我会受到仇恨和暴力的诱惑。但正因为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党徒,所以我会抵制这样的诱惑。我相信理性和讨论是最重要的进步手段,而因此我甚至约束自身的仇恨:我更拥护法律制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描述奥斯维辛的悲惨世界时,我有意运用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而不是受害者那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者那激怒的口吻。我认为,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们。
无论如何,我并不愿意将我避免轻率判决的做法与不加区别的原谅混为一谈。
不,我没有原谅这些罪犯,我也不愿意原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除非他证明(通过事实,而不是言辞,而且不要太迟)他发自真心地意识到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与错误,并决定谴责它们,把它们彻底消灭。只有这样,我,一个非天主教徒,才准备依从犹太教和天主教原谅敌人的教义,因为一个发现自身错误的敌人不再是敌人。
德国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莱维:在欧洲的中心地带,灭绝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而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西方人所生活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弱点和风险,但是与那些压制民主思想的国家相比,或者与那些压制民主思想的时代相比,我们的世界有着巨大的优势:每个人都能够知道关于每件事情的一切细节。
当今的信息产业是“第四权”:至少在理论上,记者、新闻报道人和摄像记者能够自由出入任何地方。没有人有权力阻止他们或把他们赶走。
一切事情都很简单: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收听或收看自己国家或其他国家的电台或电视台的广播节目。你可以去报摊选择你喜欢的报纸,本国的或外国的,任何政治倾向的报纸—哪怕这个国家与你的国家不睦。
你可以购买和阅读你想阅读的任何书籍,一般不会招致“反国家犯罪活动”的控告,或政治警察对你的房子的搜查。避免一切偏见当然并不容易,但至少你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偏见。
在一个独裁国家并非如此。在独裁国家中,只有由上层所宣示的唯一真理。所有报纸都差不多,它们都重申着相同的唯一真理。电台也是一样。而你不能收听其他国家的广播节目。首先,这是一种罪行,你会冒着进监狱的危险。其次,你的国家的无线电台会在适当的波段发送干扰信号,将他们自己的信号叠加在国外信号之上,从而阻止你收听它们。
至于书籍,仅有国家喜欢的书可以得到出版和翻译。你必须在国外找到其他书籍,并自己甘冒风险把它们引进国内,因为它们被视为比毒品或炸药还要可怕的危险品。而如果警察发现你拥有这些书籍,它们会被没收而你则会受到惩罚。国家不喜欢的书籍,或者不再喜欢的书籍,会在城市广场当众焚毁。1924 年至1945 年间,意大利就是这样的独裁国家。
而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统治之下的德国。当今,仍然有许多国家奉行独裁主义,其中我们不得不悲哀地算上某个曾经英勇地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在一个独裁国家中,政府可以更改真理、编造历史、扭曲新闻、掩盖真相、宣扬虚假。宣传取代了信息。
事实上,在这样的国家里,你不再是一位公民,一位权利的拥有者,而只能做一名顺民。而作为一名顺民,你必须狂热地忠诚并消极地服从于国家(以及代表它的独裁者)。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可能(尽管并不总是轻而易举,深切地侵犯人类的天性永远不会是轻而易举的)掩盖大量的事实真相。在法西斯意大利,对社会主义政治家马泰奥蒂的暗杀是相当成功的。
几个月后,这个案件就被封锁在一片沉默之中。而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控制和掩盖真相时又比墨索里尼技高一筹。
然而,向德国人民隐瞒巨大的集中营设施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且,从纳粹的角度来看,这也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在他们的国土之上营造并维持一种模糊的恐怖氛围构成了纳粹主义的部分目标。这也让人民知道反对希特勒是极为危险的。
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实行纳粹主义最初的几个月中就被投入集中营: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天主教徒。整个国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并知道集中营里的人们遭受着折磨且濒于死亡。
尽管如此,大批德国人的确并不了解集中营里后来所发生的最凶残暴行的相关细节—以百万计的规模,成系统的工业化的灭绝,毒气室,焚尸炉,对尸体卑鄙的掠夺。这些并不为人所知。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很少有人了解这些事情。为了保守这些秘密,纳粹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
比如,在官方用语中仅仅使用小心翼翼而玩世不恭的委婉辞藻:人们不写“灭绝”,而写“最终解决方案”;不写“流放”,而写“转运”;不写“毒气杀害”,而写“特殊处理”,等等。
不无理由,希特勒害怕这个骇人的新闻,如果它得以泄露,将会损害这个国家对他盲目的信仰,也会损害战斗部队的士气。此外,如果盟军知道这件事,也会把它作为宣传材料。这种情况的确出现过,盟军电台多次描述了集中营内的恐怖现实,但由于这些罪行过于罪大恶极,大多数人反而不敢相信。
德国人对集中营有哪些了解?
莱维:除了它们存在这个具体的事实之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在今天,他们也所知不多。
严格保守这个恐怖系统的秘密细节的手段,被证明极为有效。这些手段,让那些痛苦变得含义不明,因而更为复杂深刻。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的,甚至很多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们将犯人投入其中的集中营里发生着什么。绝大多数犯人对关押他们的集中营的功能及所采用的手段也缺乏准确的了解。
而德国人民又怎么能知道呢?任何走进集中营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这是对保密工作的力量和效能的最好证明。
但是……但是,甚至没有一个德国人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或相信它们是一些疗养胜地。很少有德国人没有某个亲属或熟人被投入集中营,或者说,很少有德国人不知道有这个人或那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所有的德国人都目睹了各种各样的排犹暴行。
在犹太教堂遭到纵火焚烧,犹太男人和女人们被迫跪在街上的泥浆里,遭受羞辱时,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就在现场,带着冷漠、好奇、轻蔑或完全幸灾乐祸的快乐。很多德国人通过收听国外电台知道了集中营的情况,还有很多人接触到在集中营之外工作的犯人。很多德国人都曾经在街上或火车站里遇到过集中营囚犯那悲惨的队列。
在1941年11月9日德国警察和安全部队司令部发给所有……警官和集中营指挥官的一则通告中称:“尤其是,必须注意到,在徒步转移的过程中,比如从车站到集中营,相当多的囚犯会在途中崩溃,因衰竭而昏倒或濒于死亡……不可能向民众隐瞒这些事情。”
没有一个德国人不知道事实上监狱中已经人满为患,而全国各地都在不断执行死刑。数以千计的地方法官、警务人员、律师、神父和社会工作者普遍知道事态非常严重。
许多商人作为供应商与党卫军打着交道。一些企业老板请求党卫军的行政和经济部门把集中营里的囚犯拨给他们做奴工。这些商人、企业主,还有那些办公室里的职员,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许多大公司正在压榨奴工的劳动力。
有不少工人在集中营附近或者就在集中营里工作。各个大学的教授在希姆莱设立的药品研究中心共同工作着,很多公立医院的医师以及私人研究机构的医生与这些专业的杀人者合作。很多空军成员被调任到党卫军所管辖的部门中,而他们一定知道那里发生着什么。
许多高级军官知道在集中营里对苏军战俘的大规模屠杀。甚至很多士兵和宪兵一定也清楚地知道集中营、犹太人隔离区、被占领的东欧国家的城市和乡村中所发生的可怕内幕。而你能否认这些事实吗?
在我看来,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我们必须再补充一条,从而让整个场景趋于完整—尽管信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但大多数德国人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
因为,事实上,他们希望不去了解。当然,国家恐怖主义肯定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非常难以抵抗的武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德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没有尝试抵抗。一条特殊准则普遍存在于希特勒的德国:那些知道的人不说,那些不知道的人不问,那些问的人得不到答案。
通过这种方式,典型的德国公民赢得并捍卫了他的无知。而他的无知,似乎让他对纳粹主义的支持有了充分的理由。闭紧自己的嘴巴、眼睛和耳朵,他为自己营造了一种“不知道”的错觉,并借此为发生在他门口的罪行而洗刷了自己的同谋罪。
知道或让自己知道,是一个人远离纳粹主义的方法之一(基本上并不那么危险)。我认为德国人民在整体上,并没有求助于这种方法。我相信他们完全应该承担蓄意忽略的罪责。
有囚犯从集中营里越狱吗?怎么会没有大规模的反抗?
莱维:这些是年轻的读者们最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因此,它们一定源自于某些特别迫切的好奇心或需要。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当今的年轻人感到自由是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特权之一。
结果,对他们而言,监禁的观念立刻与逃跑或反抗联系在一起。此外,许多国家的军事条例都规定着,战俘应该尝试逃跑,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借此恢复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地位。而《海牙公约》规定,不得惩罚试图逃走的战俘。浪漫主义文学(还记得基督山伯爵吗?)、流行文学和电影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在这些艺术作品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
把囚犯那不自由的境遇视为某种不正常的、不适当的事情—就像一场疾病,只有通过逃跑或反抗才能治愈—这种看法也许是好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观念完全不符合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
比如,只有几百名囚犯试图逃出奥斯维辛,而在这些人中只有二十多人成功越狱。逃跑是困难而极度危险的。饥饿和虐待让囚犯身体虚弱,而且意志消沉。他们被剃光了头发。人们可以立刻认出他们的条纹囚服。
而他们的木鞋让他们不可能快速、安静地行走。他们没有钱,而且,一般都不会说当地的语言:波兰语。他们在当地没有关系,也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
最重要的是,纳粹对越狱事件会进行残酷的报复。任何试图越狱的人如果被抓住都会被当众绞死,在点名的大操场上,常常在死前遭受可怕的折磨。要是一场越狱被纳粹发现,逃跑者的朋友都会被当作同谋,关在禁闭室里饿死。其他所有囚犯则被迫站上24 小时。有时,甚至会把“罪人”的父母抓起来,关进集中营。
党卫军哨兵如果杀死了一名试图越狱的囚犯,可以得到特别假期。结果,党卫军哨兵往往枪杀并非试图越狱的囚犯,只是为了获得假期。这一事实人为地夸大了试图越狱的囚犯人数的官方统计数字。正像我前面说过的,真实数字很小,几乎都是一些雅利安血统(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非犹太人)的波兰囚犯。他们的家乡离集中营不远,因此,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而且可以肯定群众会为他们提供保护。在其他集中营,情况也基本相似。
至于说集中营中缺乏反抗,这并不完全符合真实情况。首先,我们必须铭记那些发生在某些集中营中的起义: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布尔(Sobibor), 甚至比克瑙,奥斯维辛的附属集中营之一。这些起义的规模不大,但正像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起义一样,证明了起义者杰出的道德力量。
这些起义都是由具有某些特权的囚犯所计划和领导的。这些囚犯因此比普通犯人有着更好的身体和精神条件。这并不令人吃惊—只是从表面看,它似乎有悖于“受压迫最深的人奋起反抗”的观念。即使在集中营之外,斗争也很少由“下层无产阶级”发动。穿破衣服的人并不反抗。
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或政治犯占大多数的集中营,这些政治犯搞阴谋的经验被证明极为有用,而且常常导致相当有效的保护活动,而非公开的反抗。不同的集中营,不同的时间,他们的手段也不尽相同。
比如,他们成功地敲诈或贿赂党卫军,控制他们那任意妄为的力量;或者暗中破坏德国军工业的生产;或者组织越狱;或者通过电台与盟军联络,向他们通报集中营里骇人听闻的情况;或者改善患病囚犯的治疗条件,用囚犯医生替代党卫军医生;或者“引导”筛选的进程,把那些间谍和叛徒送进毒气室,而拯救另一些囚犯的生命(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囚犯的性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随着战线逼近,准备—甚至以军事方式准备,抵抗纳粹对集中营的大清洗(事实上,纳粹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犹太人占大多数的集中营,像奥斯维辛地区的那些集中营,无论积极或消极的抵抗都特别困难。这些集中营里,大多数囚犯都缺乏最基本的组织或军事训练。
他们来自欧洲各国,说着不同的语言,因此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残酷,也因为他们往往在犹太人隔离区经历了长期的饥饿、虐待和羞辱,所以他们比其他囚犯更饥饿、更虚弱、更疲劳。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在集中营里那可悲的生存期非常短暂。总之,他们是流动的人口,一面不断大批死去,一面新的囚犯不断到来。在这样一种退化而流动的人类群体中,反抗的种子难以生根发芽是可以理解的。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那些刚刚下火车的囚犯不反抗,而是等几个钟头(有时甚至要几天!)后走进毒气室?除了我刚才已经介绍的,我必须在此补充一点,那就是德国人已经完美地创造出一套如恶魔般的狡诈而灵活的大规模屠杀系统。在大多数时候,新到达的囚犯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纳粹以冰冷的效率接待他们,却并不凶残,邀请他们脱掉衣服“淋浴”。有时,他们会分发肥皂和毛巾,并答应在淋浴后提供热咖啡。
事实上,毒气室伪装得就像一间淋浴室,有水管、龙头、换衣间、挂衣钩、长椅等等。要是囚犯们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知道或怀疑他们即将来临的命运的迹象,党卫军和他们的爪牙就会运用奇袭战术,以极端的残暴进行干预。这些纳粹党徒叫喊着、威胁着、踢打着,甚至开枪、放狗。这些狗经过专门的训练,可以把囚犯撕成碎片。而这些囚犯则是困惑的、绝望的,因为五到十天在封闭车厢中的旅行而变得虚弱不堪。
事情就是这样,而有时被人们提起的说法—犹太人因为胆小懦弱而不反抗—却是荒唐而带有侮辱性的。没有人反抗。有一个例子足以证明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忘记,奥斯维辛的集中营经过300 名苏联战俘的考验。这些战俘年富力强,经过军事训练和政治灌输,而且没有孩子或妇女拖累,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反抗。
还有最后一点,在今天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的观点:人们在压迫面前不能屈服而应该反抗,在法西斯主义横行的欧洲,却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尤其是在意大利。它是政治活动家那狭小圈子里的产物,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立刻孤立、排挤、恐吓和摧毁了他们。你一定没有忘记德国集中营的第一批成千上万的受害者。
事实上,他们正是反纳粹政治党派的骨干成员。缺少了他们的贡献,敢于反抗和敢于组织反抗这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理念要在很久之后才开始出现,而这主要归功于德国在1941年出人意料地撕毁了1939年9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之后,欧洲共产党人投身于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中。
总之,指责集中营里的囚犯不反抗,主要是一个历史视角的错误,要求这些囚犯具有当时仅仅属于精英阶层的政治意识,尽管它在今天几乎是人们的共识。
本文节选自莱维作品系列之《休战》后记,中信出版社,2018.11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