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市与城市:明清以来杭州的“天竺进香”
关于传统中国的进香活动的研究,近年来国内涌现了若干优秀论著,如叶涛关于泰山香社的研究,梅莉关于武当山进香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继承了顾颉刚先生等人的传统,特别重视相关民间文献,尤其是进香碑刻的搜集,试图以此重构明清以来中国各地的进香图景。作为进香的“重镇”之一,杭州的进香活动值得深入探讨,明清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的发展繁荣离不开每年进香群体的定期光顾。本文节选自王健著《多元视野下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力的互动:以明清江南为中心》(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有删节,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杭州进香是明清以来非常重要的大范围朝山进香活动之一,其中尤以上天竺寺为最。“天竺”本指杭州城外天竺山之上天竺寺,该寺据说始建于五代的吴越国时期,创建者则是吴越王钱俶,据《咸淳临安志》的记载,当时钱俶“梦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寤,乃即其地创佛庐”,始称天竺看经院。到了宋代,寺中观音逐渐受到了上自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的崇信,其寺名也在宋英宗时改为“天竺灵感观音院”,成为江浙地区著名的观音道场。
围绕着这一寺庙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庙会活动,不过至少到南宋时,当时的主角似乎仍然是杭州本地绅富。只是到了明清时代,江浙民众才大量远赴杭州进香,以上天竺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香会、香市文化,它既体现了传统时代中国民众“朝山进香”的一般特征,同时也有着较为浓郁的江南地方特色。
不同群体的进香活动
明清以来杭州进香的繁盛,其实是由不同的群体共同造成的,上至帝王,下至农民,均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
首先,毫无疑问,在明清以来的杭州进香史上,农民始终是最重要的进香群体。其进香活动往往在年初即由香头组织,“于元旦日发帖邀人,至二三月间成群结党,男女混杂,雇坐船只,出门烧香”。正如范祖述在《杭俗遗风》中提到的,嘉道间苏松嘉湖“各乡村民男女坐船而来杭州进香者,……早则正月尽,迟则二月初,咸来聚焉。须于看蚕时返棹,延有月余之久”。自二月初至看蚕之五月初,这段时间自然也是相对的农闲时间。
关于农民之所以热衷于到杭州进香,铃木智夫有过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一方面与上天竺观音道场的形成有关,为求蚕稻丰收,农民十分笃信于观音大士,另一方面则与杭州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路途近,风光美,自然会成为江浙农民乐于前往的地方。
其次,则是广大女性信众。早在明代小说《型世言》中就有关于苏州昆山县妇女周氏等买舟前往杭州进香的描写:
(周氏等)预先约定一支香船,离了家,望杭州进发。……一路说说笑笑,打鼓筛锣,宣卷念佛。早已过了北新关,直到松木场,寻一个香荡歇下。
光绪间洪如嵩补辑的《杭俗遗风》中也说:“一至立夏节,烧跑香皆归家饲蚕。继来者,大率嘉湖市镇及苏申之富有家妇女。若辈举止阔绰,不惜金钱。”
与普通民众相比,明清时代士人的进香活动则往往更具冶游之意,在进香时间上也更为随性,有意无意地反映了士庶之间的区分。
如明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便载其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初八日“肩舆至天竺进香。午至飞来峰冷泉亭,观新瀑”。而成化四年秋后杨守陈进香天竺寺所记则直接将进香称作“游佛”,更能说明士人进香之悠闲:
杭多名刹,天竺为称首。久欲游佛,……与山僧同至下天竺,见泉无跳珠者,访流杯、翻经诸亭台,但芜址耳。中天竺荒寂类之。于是尽所谓九里松者,始到上天竺,诣观音殿。启椟阅象,宝光奕奕射人。僧为口数手执以示客。小朵轩面石壁峻峭,松萝垂荫。天香室对乳窦、白云诸峰,若屏障前拱,空翠欲滴。寺之胜止此。
另外,在清代嘉兴文人张廷济的日记中亦有其道光二年七月廿八日前往天竺进香的记载,花费轿钱六百。
还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杭州进香风习之盛,与一些统治者的支持、提倡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清代前中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作为观音道场的上天竺寺为例,根据清代刊刻的《天竺山志》记载,清前期,康熙在南巡途中曾经五赐临幸上天竺,并时有经书、碑记颁赐寺中。而另一位崇佛的帝王乾隆则更是曾经九次临幸上天竺寺,并将其改名为法喜寺,同时还大量赐钱赐物。
正是由于帝王的喜好,因此在清代前中期,浙江、杭州地方官员对于天竺寺更是青眼有加。“(二月)十八日,文武百官,自抚台以下,亲往拈香,一切执事,城门口即便打落,不敢开锣喝道,其敬畏有如此者”。而天竺寺本身在清代中期也得到了多次的修缮。因此,正如乾隆中期所修《大昭庆律寺志》所言:当时“香客之至倍盛于前”。
普通民众进香之路线与行程
1882年,《申报》的一篇文章在谈到杭州香客时,曾说“香客皆在江苏府州县境,本省则惟有嘉湖两属之人”,这样的说法自然比较片面。不过,杭州以北的苏州、上海等地香客在进香者中比例占多,大约还是事实。这从西湖香市的布局主要位于西湖以北也可以看出来。如明末张岱述及西湖香市时便曾说“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清初康熙《杭州府志》亦言当时香市之盛:“自北新关至松木场,舟车衔接,昭庆以至天竺,摆列器物玩好等物,俱成市肆”。
明清时代江南民众赴天竺进香的惟一交通工具当然是舟船,清代道光间所撰《吴郡岁华纪丽》也列有“杭州进香船”一条,描摹每年二三月间苏州城乡妇女坐进香船前往杭州的情景:
吴郡去杭四百里。天竺灵隐香市,春时最盛。城乡士女,买舟结队,檀香柏烛,置办精虔。富豪之族,则买画舫,两三人为伴,或挈眷偕行,留连弥月。比户小家,则数十人结伴,雇赁楼船,为首醵金之人曰香头。船中杂坐喧嘈,来往只七日,谓之报香,船上多插小黄旗,书“天竺进香”四字”,或书“朝山进香”字。
直至近代,每至二月间杭州香会之时,江浙一带甚至还有一舟难求的景象出现。如1876年2月,便曾有人因为要将家眷从上海送回常州,“第值天竺进香之时,船只极少”,因此向盛宣怀“求赏借红船一用”。
那么,这些船只又是循着怎样的路线去往杭州的呢?富豪之家以画舫出行,其行程较为随意。但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出于时间和成本的考虑,其进香线路相信是比较固定的,但普通的资料对此并无详细描述。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册《上天竺进香舱中结缘宝卷》抄本,该宝卷并未记载从苏州出发去杭州的行程,但却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从杭州出发,经由水路如何返回苏州的行程,根据以下引文,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大致了解清代苏州普通的进香团体是如何往返于苏杭之间的:
松毛(木)场,又来了。北新关,滔滔过。……摇到塘栖天色晚,太阳将近落山抛。香客上岸痧药买,开船就到铅粉桥。三十三里的菱河多野断,两边插挞在关好。也有摇垣并兵和,亦有宣卷木鱼敲。念佛太太缘来结,船中香客闹喧喧。……新市街上多闹热,又要过一条伯姆三条桥。连市街上滔滔过,帮梢伙计换班摇。珠藤棚搭拉街当中,香客在望岸上膘。蚕山顶上一只庙,清明胜会戏台高。乌镇街上船来歇,香客叙会闹噪噪。又个太太上岸来买货,又个太太船中就把佛偈念。……七十二里兰溪摇得哮哮吼,帮稍工要换班摇。鹦墩河,一只庙,急水要过画眉桥。平望街上船来歇,香客上岸买窑糕。帮稍要买铁塔柄,开船一路直妙妙。八尺塘背纤穿梭过,吴江宝塔七层高。一路滔滔来摇过,还有狮子摆带桥。帮稍便把点心吃,今朝要过蜜驼桥。安里桥急水滔滔过,霸基桥前就推稍。东准望西吊桥过,望北齐门马路桥。洪泰河头船来歇,香客上岸闹噪噪。有个要到虎邱去,有个要望城里去。山塘景致真闹热,灯笼店相对了山塘桥。南濠街上不必说,渡僧桥造得果然高。……

上引文中的松毛(木)场是苏松等地香客赴杭州进香者一个非常重要的泊舟场所。据《天竺山志》记载:“松木场在钱塘门外,凡吴郡士女,春时进香天竺,必泊舟于此。吴农祥有诗云:松木场边春水生,绿杨红树隐高城。上方钟磐珠帘迥,十里笙箫画舫明。芳草雉媒娇夜雨,妒花鸠妇说新晴。武林车骑如流水,闲傍清溪听笑声。”
另外,从以上引文可见,该进香群体在回程中一路经过的较大市镇有塘栖、新市、连市、乌镇、平望、吴江等,如果将这些市镇排列起来,比照以地图,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其进香的路线。

值得指出的是,明末商书《士商类要》中曾记载了苏州由杭州府至南海普陀山的水路路程:“苏州阊门,四十五里吴江县,四十里至平望,九里大船坊,九里乌龙浜,九里钱马头,九里师姑桥,九里十八里桥,十八里至乌镇,二十七里琏市,十八里寒山,十八里新市,三十六里至塘棲,十里武林港,二十里谢村,十里北新关……”这与上述宝卷中所载路线是基本相符的,可见自明末以来这便是一条从苏州至杭州进香的重要线路。
至于进香团体在往返途中的主要活动,我们也是可以想见的,主要就如《型世言》中所说“打鼓筛锣,宣卷念佛”,类似《上天竺进香舱中结缘宝卷》这样的文本本身也就是因着这些需求而产生的,宝卷中的大量篇幅便是在劝人行善积德。
而如《吴郡岁华纪丽》所言,一般的进香团体来往苏杭之间“只七日”,那么,这七日是如何分配的呢?分析以上《宝卷》,似乎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据该宝卷记载,进香群体到杭州后,第一天到杭州后,先在天竺山上“安歇房头香来进”,“拜子菩萨下山跪”,之后再到灵隐寺,当天晚宿天竺山上。“明日最(再)把回豆(头)香来烧”,随后一路下山,前往岳王坟、玛瑙寺、昭庆寺、雷峰塔、城隍山等处,并进城采买货物后便回程,因此,在杭州大约花费两天时间。
除去在杭州的逗留时间,他们在路上又须花费多长时间呢?宝卷所述不明,我们不妨可以稍作推测。根据《士商类要》的记载,从苏州到杭州北新关的水路里程约为300里,而明清江南一般的舟行速度约为一昼夜百里左右,因此往返所需时间约为5-6天。
这在一些小说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清末民初小说《九尾狐》中也描述到了天竺进香的情景:海上名妓胡宝玉有意前往天竺进香,便“吩咐相帮往船行中雇定了一只双夹弄的蒲鞋头船,并不用小轮拖带”,第一日傍晚“管船的烧了神福,放了一串鞭炮,进来讨了赏封,一班水手们方始解缆撑篙,筛锣开船,船上扯著天竺进香的旗号,一迳向杭州而去”,“今朝一百里,明朝七十里”,结果直到“第四日午后”,方才“舟抵武林城外”,费时约三日,在没有轮船拖带的情况下,这应该是比较正常的速度了。
同样的,胡宝玉等人亦是在天竺山上“落下房头”,“明日清早上疏拈香”,据其观察“庙中地方宽阔,房屋甚多,即就东跨院一带而论,各香客的房头已有百余间之夥,其余如佛殿僧房、经楼宝阁、丈室斋堂,以及客厅厨厕、与西跨院一带香客房头,不计其数”。可见,接待香客正是天竺寺的一桩大买卖。
与以上行程相比,当然也存在更为紧凑的进香安排。1930年代,时任之江学院教授的北长老会传教士队克勋(Clarence Burton Day)曾经在其著作中留下了一群来自桐庐的香客清明期间在杭州进香的宝贵记录。据其记载,这些香客顺钱塘江而下,黎明时将船只停泊于江边六和塔旁的码头上,从那里出发,在短短一天内连续参拜了虎跑寺、大仁寺、六通寺、玉泉寺、灵隐寺、龙井寺、理安寺等,到晚上则重又回到船上返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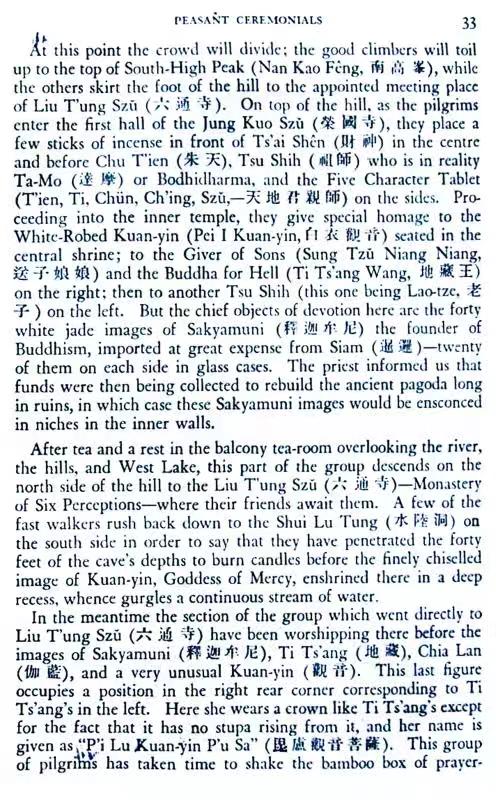
队克勋记载的珍贵性是在于给我们留下了杭州以南民众进香的记录。来自杭州以南的桐庐香客为求方便而将其船只停泊于西湖以南的六和塔旁,这当然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考虑到在这周围未能形成另一个香市,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地区的香客在杭州进香史上扮演的角色是有差异的。另外,根据队克勋的记录,这群香客并未前往上天竺进香,而对于苏松嘉湖的民众来说,上天竺则为非常重要的进香目的地,这究竟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需要作进一步考察。
最后,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明清及至近代苏松嘉湖赴杭之进香沿线亦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太平,而是常有盗匪出没,我们在近代《申报》上便经常能看到类似的记载,如1871年的一份《申报》上便载有吴江某商人携妻赴天竺进香,船至王江泾,被盗贼抢劫一空的新闻。这或许也是进香者往往会由香头组织,集体行动的原因之一。
进香对杭州城市之影响
明清时代,一年数月的天竺进香活动吸引了大批江浙民众前往杭州,因着信仰的缘故,这样大型的活动一方面固然促进了杭州佛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则无疑对杭州乃至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明末杭州诸生邵重生《上竺论》中对天竺与杭州之关系才会有如下之论断:“杭城灵竺,岂但相为表里,而又相为盛衰;岂但盛衰相为,而实相为存亡者耶。”以下我们试分析之。
首先,大规模的进香活动促进了杭州佛寺道观的发展。对此,范祖述《杭俗遗风》中有具体的描述:
其进香,城内则城隍山各庙;城外则天竺及四大丛林。……又以黄布、白布,或数匹、数十丈不等,扯长间段,牵拽而行,名为“舍幡”,其实白送和尚。香则檀香、线香两种,檀香数百十斤,线香千百古,略为烧点,余亦送与和尚。故天竺之香、布两物,虽市店亦不敌其多;至于点残蜡烛,仓中散放,不知其几千万斤也。所以天竺和尚、吴山道士,白手求财,吃着不尽,各房头均有嫡派子孙,相传剃度,外人不得而与也。
那么,寺庙究竟可以从中得到多少利益呢?一些资料中也稍许为我们透露了端倪。乾隆四十三年,浙江布政使徐恕在一篇奏请云林寺兼管天竺寺的奏折中曾经提及“天竺、云林均系杭城古刹,两寺各有荒瘠山地三千六七百亩,花息无多,惟三春香火较盛。今细加查核,云林寺岁入地租香火布施,约有二千余两;天竺法喜寺岁入地租香火布施,约有五六千两”。由此可见其收入之丰。
1920年代的一篇杂文在谈及杭州烧香时,也专门提到知客僧对太太奶奶们的“趋承恐后”,为的就是要让她们题写缘薄,出资“装塑金身”。
其次,天竺进香繁荣了杭州城市的商品经济,促进了市场流通。明末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曾列“西湖香市”一条专述明末杭州香市的盛况: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邦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酝。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波纹如绫,温风如酒’,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颌笙之聒耳;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从以上叙述中可见明末香市之盛况,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岳王坟、湖心亭、陆宣公祠、昭庆寺,各色商品,应有尽有,真个是“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不仅明末如此,清代亦如是。康熙《杭州府志》记清初香市之盛,亦云:
(二月)十九日,上天竺大士诞辰 。三吴士女买舟进香,不可亿记……自北新关至松木场,舟车衔接,昭庆以至天竺,摆列器物玩好等物,俱成市肆,数十里不绝,一月有余,穷民赖以为生。
范祖述《杭俗遗风》记道咸间香市之盛,也说“三百六十行生意,一年中敌不过春市一市之多。大街小巷,挨肩擦背,皆香客也。余坟亲李玉堂,居住留下,其房分有业竹篮者,每逢春香,一家要做千余串钱生意。即此而推,各色生意,诚有不可意计者矣。”
由此可见,明清时代,香市在推动杭州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是一以贯之的。进一步的,我们还注意到,此类传统时代的长程进香活动对于进香沿线市镇经济发展的影响相信也是存在的。如上文所引《上天竺进香舱中结缘宝卷》所载,这些进香人群不仅会在杭州城内购买土特产品,在往返途中往往会在一些市镇歇脚,采买物事,如塘栖、乌镇、平望等地,结果“苏饼物件多买到,出稍装,蛮蛮高”。
再次,杭州香市的兴盛还给很多人提供了谋生之手段,就业之机会。早在明末,《杭州上天竺寺志》中就曾提到:“灵竺既无沃壤。山浅附郭,不容故家。居民止以香客为活,谓之锅头种田。交易三春为一年之计,谓之柜上田。”
《杭俗遗风》记“天竺山饭店,自三天竺至灵隐寺山门内,有一二十家,惟陈三房最有名。所卖之饭,每碗四文,口大者,只须一口就完。……春香一市生意,要安享坐吃一年也”。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交通的方便,杭州进香“一年盛一年”,它对于杭州城市经济发展之影响自然也得以延续。一方面,轿夫、黄包车夫、船夫、小贩继续对“香市有很大的希望”;另一方面,一些较大型的商店,如“方裕和的南货、翁隆盛的茶叶”等也都“为香客们所信用”。
不过,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民国时期,随着杭州逐步向旅游城市转型,所谓进香的人群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杭州逐渐成为了上海新兴中产阶级的后花园,而烧香则越来越与旅游结合在了一起。
今上海图书馆藏有一份民国年间印行的《武林进香录》,其中内容十分丰富,“凡进香者如何借寓,何处上栈,如何雇轿、乘车、驾船,一切价目如何,便宜较省如何,进香次第日期如何,进香挨次路程有几座庙寺,各寺庙名称及火车来回价目时刻表,杭地西湖出品物件莫不应有尽有。书中再有各大寺院,各名胜山景,统用照相拍出印入”。
同时刊印该《进香录》的商户还宣称提供香烛异地支取业务,客人只须出资购买联票,该商号便可在三日内“照票代运到杭”,同时还可以将香烛分包,并在各包上写明“何寺何庙所用,内分名目,何对之烛是烧大殿,何对之烛是烧内殿,何对之烛是前殿,后殿的是何神仙”,“只需挨次取出随烧,决不致乱失次序而手慌脚乱”。
从以上说明及提供的服务来看,这部《进香录》所面对的对象显然不是普通的农村香客,而是来自大都市的中产阶层,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杭州、天竺的寺庙文化,但进香却实实在在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前往杭州休闲的理由,因此才会有类似《武林进香录》这样的刊物与相应的服务出现以迎合其需求。不过,对杭州城市而言,这就已经足够了,因为香会文化的底蕴已经为城市的转型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图3-6)
谭钧培禁烧香
在明清时代,从法律上讲,民间烧香活动,尤其是妇女烧香并不被允许,但这样的法律事实上却很少得到认真施行,除了在一些特殊时期,而清末或许就是这样的时期之一,杭州的进香活动便曾在这一阶段遭遇过较大规模的申禁。
清末江南对朝山进香活动的禁止是由光绪初年曾任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的谭钧培发起的。光绪六年(1880),上任护理江苏巡抚不久的谭钧培发布了禁止进香的命令,《申报》以《护抚新政》为名,对此进行了报道:
苏郡每逢春二三月复有各处香会,或赴茅山,或往天竺,往往雇船买棹,男女相杂,船桅高扯朝山进香旗号,帆樯相借。各船户皆乐于装载,以其人数众多,船价既可从丰,而逢关过卡亦可稍宽稽查也。此次中丞出令不准有香头香会名目,并令大小船行各具切结,不得揽载各路香会之人,如敢违禁,定即严行究办云。
至于为什么要严禁香会,《申报》在稍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进香之举在当时有纵奸,纵盗,酿寇,漏捐四患,故不得不严禁:
吴中二三月间,男妇纠会,出境烧香,每一关卡日所过之船日以千计,其中弊窦凡有数端:妇女出门,家长必查其所往之处,至于烧香则俨然份内之事,见其夫若父甚为有词,而男女杂沓眠食,蓬窗起居,究非所便,若有私约者因是以遂其欲可也,故纵奸一也;连樯对舻,衔尾而来,舟必数十人,人必数金,而年轻者亦与其中,有产者亦在其列,珠翠盈头,鲜衣夺目,宵小窥伺,得便而劫之,而地方官从此多事,故纵盗二也;船插黄旗,担扛巨烛,列队而进,鸣锣以示先声,且某会有某会之标识,一帮有一帮之衣履,且气象宛似营伍,不肖之人由此生心,假以结联羽党,即不难为伏莽之戎,故酿寇三也;大则舟由舻千里,小则三两野航,高竖旗帜而曰进香,则关卡不屑过问,假令会中有私携货物,或船伙贪受其庇,夹带税物者,卡中放过矣,故漏捐四也。有此四端而谓可以任之恕之,则亦何不可恕哉。
分析以上提到的四患,纵奸、纵盗历来是地方官员指责民间信仰活动的重要理由,而酿寇、漏捐却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即经过太平天国战乱的清政府,对于民间利用香会之名“结联羽党”有很强的警惕性,另外,战乱后百废待兴,急需资金,因此地方官员对于偷逃关卡捐税也十分敏感。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才直接导致了上述所谓“新政”的产生。
那么,这样的政策究竟有没有得到具体执行呢?从相关史料看,在其发布之初,应该还是严格实行过一段时期的,如当时上海县令便曾奉命向本境保甲人等发放谕单,以防止“无赖之徒,先期纠敛”,“中途拿办,利已入己”,同时也确实有香船在关卡处被中途截回,故“此风顿杀”。而且事实上,该禁令发布后一时间也确实对进香者起到了震慑作用,1882年初,《申报》一篇文章在谈到当年的天竺香客时,便曾说道“香客皆在江苏府州县境,本省则惟有嘉湖两属之人,去年谭苏藩宪护理抚篆,曾经出示严禁,并谕令各卡严行查禁阻截,一时各属闻风,凡欲进香者皆嗒焉意丧。今岁谭公虽卸抚篆,仍居藩任,令出必行,难保不申明前禁,以故香客犹皆迟疑,而天竺之热闹殊不及曩昔也”。
本来太平天国后,杭州“大吏发帑,富户捐募,天竺、灵隐、吴山各庙渐复旧观,而下乡蚕丝,以外洋销售价昂,亦复家给人足。杭州香市,应可渐渐复原”,但谭钧培的政策一时却打断了这一进程,对杭州城市商业的繁荣无疑是有影响的,导致杭州香市“日衰一日,如范祖述所云者,不及十分之一”。而光绪初修纂之《杭州府志》也曾言及“近年吴中大吏有悬厉禁者,乡民裹足,于是杭城内外,市面交易为之骤衰”。
不过,总体而言,这样的情形似乎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1881年,谭钧培卸任护理江苏巡抚,仍任江苏布政使,尽管他在年初依然发布了禁止进香的告示,但实际上由于“行事类皆掣肘,从前锋厉之气亦以稍杀”,因此已稍稍弛禁,“沿途各卡不奉严札谕禁,则虽连樯而至,亦听其往来,不为阻止。以故三月初旬以来,纠集进香之举已渐有人焉。况近日天气晴和,四时之中所不可多得之景正在此时”,“杭州松木场以及茅家埠一带其热闹情形必已日胜一日,而通城生意当为之生色矣”。
至1882年初,苏州等地更是“此禁大开,十九日为观音大士诞辰,举凡荒刹古庵,莫不会启无遮”。虽然仍然有地方官员出示申禁,“苦口婆心,谆谆告诫”,但民间却早已“故智复萌”了。
在历史上,对于民间信仰活动的悬禁,即使要取得部份的成功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清初汤斌在江南的毁灭五通神,便是一方面得到了康熙的大力支持,同时还有地方士绅的配合,才暂时取得了一些成果。与汤斌相比,谭钧培对朝山进香的禁止更多的只是一时兴起,既没有得到最高层的支持,同时由于天竺进香在江南不仅仅是下层民众的一种信仰活动,也得到了达官贵人的青睐,因此这样的行动根本也无法取得地方士人的支持。再加之谭钧培光绪初年一时骤贵,在苏州立足未稳,官场同僚亦并不配合其行动,正如《申报》论者评说的,“同官之中渐与不洽,有临其上者,而其事不能果行,有与之并者,而其志且不能遂,于是意兴阑珊,渐蹈模棱泄沓之习,而先后迥判两人”。所以,由其倡导的这次试图与地方传统相较量的角力也就注定只能成为数百年“天竺进香”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小结
中国传统的进香活动与西方的“朝圣”相类似。“在任何宗教中,总有一些被视为特别利于同超自然力量建立联系的地点和时间,而在绝大多数的文化中,人们总是会前往这些地点以求建立此种联系”。这就是所谓的朝圣(pilgrimage)。1978年,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通过对基督教文化中朝圣现象的研究指出,朝圣具有一些通过仪式的中介性,对于朝圣者而言,朝圣这一行为的意义在于通过脱离日常的社会结构,而获得某种提升(体验)。从这方面来看,朝圣与进香自然有相通之处,即两者都寻求对日常生活的解脱而进入一种非日常的状态。
但对中国进香现象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显然是不够的。1992年,韩书瑞(Susan Naquin)等人出版了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一书,其中收录了相关学者对泰山、五台山、普陀山、妙峰山朝山进香问题的若干研究论文,试图以中国的实例丰富关于朝圣的理论,同时也提醒人们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书瑞在导言中曾将中国的“进香”称为pilgrimage-like behavior,显见已经意识到它与西方朝圣现象的区别。但要深入理解中国的进香活动,则只有浸淫其中,正如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等人对妙峰山庙会所作的调查那样,仔细研究各地进香的对象、组织、行程、活动等具体内容,才能有所明了。
本节正是通过对明清以降杭州进香活动的初步研究,借助于对某些细节的揭示,初步表明了在江南社会生活史上,杭州进香作为一项持续了数百年的民间俗信活动,因着各方面条件的作用,成为了江浙地区各阶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并保持其强大生命力。同时,杭州作为进香目的地,也大大受惠于此,明清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的发展繁荣离不开每年进香群体的定期光顾。而官方对这样的活动也往往是明张实弛,即使是偶尔的悬禁,也很难获得成功。当然,以上所作的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探讨,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进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