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冠疫情背后,逝后又重生的中国人

在大街上的人来人往中,与你擦肩而过的某个人,或许将在以后的某一天,用自己的身体撑起别人的希望;又或许,其中就有人带着别人的捐赠,正在继续着余生的旅程。
生命终将离场,一曲终了,悲欣交集。

时间倒退1小时,上海支援金银潭医院的医生群里收到了一则消息:
5床家属同意尸体解剖,已签字。
从上海来武汉金银潭医院支援防疫的医生查琼芳回忆说,5床是位老先生,印象中他一直比较烦躁,从15日下午开始指标都不太乐观。
查琼芳原想请示教授调整用药,但当她换下防护服走到楼下,就听说老先生离开了。

接到张定宇电话后,刘良迅速安排团队成员,一同前往金银潭医院。
其实,早在1月22日,刘良便已经通过社交媒体多次呼吁对新冠患者遗体进行解剖。
病理是医生的医生。
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如果治病救人没有病理支撑,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为什么会无痰干咳?
为什么咽拭子核酸检测会出现假阴性?
到底该不该使用激素治疗?
……
尸检之前,医生们对许多问题都很茫然。

钟南山院士也曾致电刘良,满心焦急:“我们前线的医生,就等你的的结果了。”
只有把“黑箱”打开,才能知己知彼。
随着首例新冠遗体捐献者的出现,2月16日凌晨1点尸检正式开始。
暴露在高浓度的病毒之中,负责主刀的刘良就像站在了核辐射最核心的地方,他必须尽最大努力缩短操作时间,才能降低自己和同事被感染的可能性。
但是,当一行人进入临时搭建的负压解剖室,却没有立即投入工作,而是鞠躬。

“第一步是鞠躬,长时间的鞠躬。”
“非常感谢他和他的家人。”
刘良的半张脸被口罩遮住,看不清表情,但是庄重的语气中透着诚恳和回忆。
他是法医,也是一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行走在生命两端的人更懂得:
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亡?

刘良家一共姐弟4人,其他3个孩子都应许了,但刘良的心理工作,父亲做了三、四年。
为了得到刘良的认可,父亲甚至找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来劝说儿子。
而刘父之所以如此执着地征求儿子的意见,除了情感上的尊重,还有流程上的必要性——进行遗体捐献,必须要征得所有直系亲属的同意,否则就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夙愿。
遗体捐献,对于治愈罕见病和医疗教学都有极大意义。与之相互关联,器官捐献也将更多人与死亡的距离,拉得更远了。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2月29日,中国器官捐献(含遗体捐献)志愿登记人数为1876168人。

但是,中国的器官捐献成功率却非常有限。
捐献成功率最高的西班牙为百万分之四十七,而中国只有百万分之一点六三。
因为当志愿者达到捐献条件时,只能由家属完成医疗决策。
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说法。
因此,许多人对器官捐献“闻之色变”。

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器官移植需求和患者家属意愿之间的巨大缺口。
也成为了中国器官捐献事业的一大痛点。
由此,诞生了一个特殊的职业: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份工作没有工资,需要24小时的待命,因为无论对于捐献者还是受捐者,每一秒都有可能是最后一秒。
器官捐献协调员最常出入的地方就是医院的ICU病房,他们中许多人的本职工作就是医院的医护人员。
他们犹豫地走向一个又一个病人家属。选择合适的时机,慢慢开启这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因此,每当他们出现,便会有人说:“死神来了。”
甚至有人会说,他们是守在将死之人身边、等待啄食内脏的“秃鹰”。
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份职业的误解也显露出中国器官捐献事业举步维艰的原因。
作为中国第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15年来,高敏遭遇过无数白眼、误解、谩骂,甚至推搡。

她总是背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她所负责的所有器官捐献志愿者的资料,她说,那是世界上最沉重的两样东西――生和死。
有人称高敏是“劝捐员”,但她总是不断地纠正这个称呼。
当家属表达明确的拒绝意向,她便不会“劝”。
“那是不人道的。”
曾经有一位捐献女儿遗体的父亲,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捐献器官的时机,事后埋怨高敏为什么不多劝劝他。
高敏说:“你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得尊重你的想法。”
与亲人永别的痛楚,她见证过成千上万次,当父母失去孩子、当孩子失去父母,如果她过度劝说,无疑是一种绑架和伤害。
所以,每当她调整呼吸走向下一个亲属的时候还是会有些手足无措。
生死这件事,经历得越多,越是无法习以为常。

一边是死神,一边是天使,但高敏自己称自己是生命的摆渡人。
一头是死亡,一头是重生,当捐献者的生命长河无法挽回地到达尽头,她的职责就是把生命之舟摆渡到另一个人的生命长河。
在她所负责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中,有一个妻子因煤气中毒被送到医院。
丈夫为了完成妻子的愿望,紧急联系了高敏。
但就在高敏赶往当地途中,电话再度打来,这位妻子心脏停跳了,她所在的是基层医院,器官无法得到很好的维护,未能达到捐献标准。
她的老公很伤心,说:“我不光把她弄丢了,现在连她的遗愿也没能帮她实现。”
这样的事,高敏不止一次遇到。
每一次,她都会拍拍家属的肩膀,陪着他们送亲人最后一程。

“能做这个决定,都不容易。”
对于家属来说,做出决定,捐献亲人的器官,或许已经耗尽半生的爱与不舍。

起初,焦兰珍说:“这次不哭了。”但当王述成开始读信,她便转身抽泣。
三个月前,他们的儿子焦俞去世,年仅25岁。
2015年10月25日,因脑肿瘤,焦俞从成都紧急转往上海华山医院。
经过院方组织多名专家会诊认为,病情十分复杂,暂时无法下定论,必须尽快进行穿刺手术。
由于普通病房紧缺,只剩下高级病房,心急如焚的夫妇俩四处筹钱,终于在10月29日让儿子住进了华山医院总部的重症监护室。

然而,就在焦俞住进病房后不到两个小时,就突发昏迷。
转入重症监护室后,家属只有每天下午的15分钟时间探视。王述成、焦兰珍夫妇和女儿、女婿抓住这点宝贵时间,轮流在病床边呼唤,希望焦俞能够醒来。
晚上,一家人就在病房门外,通宵达旦地守候,半步也不愿离开。
但是,年轻的儿子最终没能醒来。
11月2日晚,焦俞的病情恶化,被确诊为脑死亡。
很艰难,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
“能够救人的器官都捐。总比他火化了,剩下的全无,就是一捧灰,要好得多。”王述成哽咽地说。
并且,他们同意医院对儿子的头部进行解剖。
“儿子在世的时候,没能查清楚病因,直到死都没有定论,我们对这个疾病非常仇视。一定要把病因查清,不让更多人因为这个病而失去生命。”
焦俞的姐姐靠在墙边放声大哭:“我们这个家庭非常痛苦,所以我们不想其他家庭再遭受。”
但是,当履行程序的时候,王述成犹豫了。
医生再次确认脑死亡,需要王述成签四个字:放弃治疗。
这是最揪心的一刻。
写完“放弃”,这个父亲无法继续下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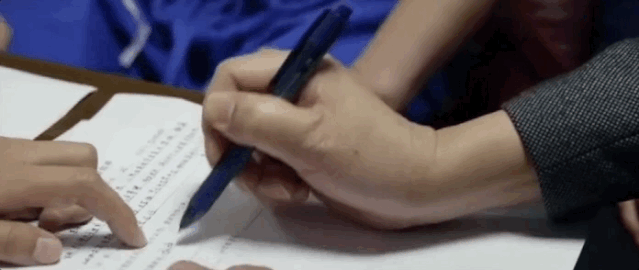
无论医生怎样解释,王述成都写不下去。
器官捐献对家属的残酷性,就恰恰体现在这:它要求患者家属必须在短时间内就作出这个决定。因为器官太脆弱了,一刻都等不起。
最后,是妻子焦兰珍下定决心,劝慰丈夫,但是当手续完成,下一秒,她便拉着医生痛哭。
签完字,王述成茫然地离开座位,摩挲着双手,灵魂好像被抽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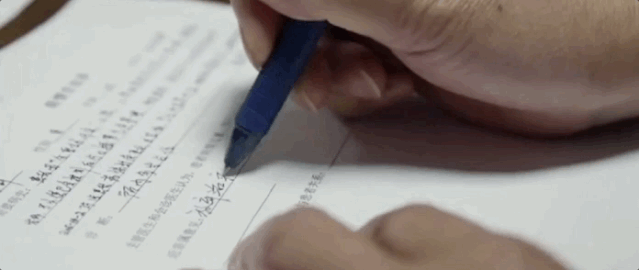
几乎每一个成功捐献的家属在做出决定之后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后悔和不安。
华山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蔡国玮表示,曾有捐献者家属感到愧对逝去的亲人,“就像是做了件亏心事”。
在华山医院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秘书长张明看来,这是因为人言可畏。
曾经有一个江西农村家庭,男孩十八岁,在外打工时出车祸抢救无效,家属做了捐献器官的决定。

村里不相信有人会做这么伟大的事情,传言他们把孩子的器官卖了,甚至有精确的数字,说一共卖了一百万。
在很多人心里,器官捐献是“一命抵一命”。
囿于这种观念,妈妈每次出门都会被人指指点点,每次躲在家里哭,丈夫都会守在他身边,怕她做傻事。
得知此事后,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宣传部负责人张珊珊邀请男孩的父母来参加活动。
在一次上海的宣传活动上,他们被请上台领了一座水晶纪念杯,并且和相关负责人合影。
妈妈激动地说:“现在回去,我就可以把我跟领导的照片摆在我家里,告诉他们,连国家都已经认可了,我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你们不能再说我了。”
红十字会会为进行器官捐献、遗体捐献的逝者树立纪念碑,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悲伤的故事,和更多人的重生。

但是,有些家属会要求器官协调员严格保密自己的捐献行为,纪念碑上也不留名字。
问及原因,大部分都是:怕被人戳脊梁骨。
或许,对于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来说,比起被歌颂,他们更需要的是——你我的理解。

这被称为“莫比乌斯环”,中国人更熟悉的说法则是:因果。
在中国短暂的器官捐献史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莫比乌斯环。
2015年10月20日,矿工刘福(化名)的妻子摔伤,医生宣布其脑死亡。
器官捐献协调员赶到刘福家中,询问是否有捐献意愿,如果选择选择器官捐献,将可能有3个人获得重生。

刘福犹豫了。
前后5个小时,纠结、纠结、反复纠结……
“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亲人搞得支离破碎。”
他想,如果不捐,可能有3个人很快就会告别人世;
如果捐,妻子还可以以另一种形式继续活在人世。
再加上,彼时刘福已经与尘肺病相伴近二十年,同样也是受尽病痛折磨的人。
于是,他选择签字。“但愿来世她的命能好些。”
当他费力地喘息着,用颤抖的双手写下名字的那一刻,不会想到2年后,自己竟也成了器官捐献的受益者。
刘福年轻的时候有个说法:地下的钱比地上的钱好赚。指的是井下采矿。
为了谋生,他17岁起就在各个矿井中辗转。
今年钨矿,明年煤矿,无论在哪儿,炮眼总是轰地炸响,矿块迸射的瞬间撒下无数粉尘,把人都湮没了。

1998年,28岁的刘福被确诊为尘肺病,人佝偻着,一呼一吸就像拉着风箱,“呜—呜—”。
“只要让我好好呼吸一天,死了也甘心。”
刘福曾经对妻子说:“你走吧,我拖累你了。”
妻子,是刘福一辈子的痛。
为了给没有劳动能力的刘福治病,妻子一边在工地打工,一边照顾丈夫。
那天妻子摔下楼梯,浑身瘫软的刘福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
绝望让他丧失求生的意志,他想过跳楼自杀,但是爬楼对他来说难于上青天。
妻子走后,他活不了,也死不成。
2016年底,医生对刘福说:只能回去了,医治也拖延不了多久了。”
回家的路上,刘福让儿子买了副棺材,一道拖了回去。

了解到他的情况后,红十字会将他转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进行救治,并免除了大部分治疗费用。
但对于晚期尘肺病人来说,所谓的治疗只是减轻痛苦,除了肺移植,别无他法。
医生告诉刘福,等待肺源一般需要3个月左右。
同病房的病友,没有坚持到那一天。
器官捐献,是一场群体性等待。
一旦有捐献者,医生会同时通知几个等待移植的病人空腹抽血,然后带着他们的血样连夜赶到捐赠者所在地去做配型,于此同时,这两三位候选者会进行手术的准备工作。
但只有相关指标匹配程度最高的患者才会能获得捐赠。
器官配对的概率,只有两种结果:要么百分百,要么零。
第二天一早,病房的电话铃会响起,接听的护士会宣布谁是中标者,然后推着他进手术室,对没能中标的人来说,就是空欢喜一场。
刘福一天一天地数日子,等待命运的宣判。
第49天,死神没来。
2017年4月28日早上,主治医生告知他不要吃早饭了,恭喜你等到肺源了,质量非常好,是一个16岁的少年。

闻讯,刘福蒙在被子里大哭。
他心里,除了庆幸,还有感激。
“一个16岁的男孩啊,还没我儿子大,我也是一个父亲。”
同为捐献者家属,他知道做出这个决定所要经历的切肤之痛。
术后清醒,刘福呼吸到一口新鲜空气:“好舒服。”
“好”字,他拖了很长的音。
他看到墙上的挂钟:03点45分,那是他重生的时间。
身体恢复后,刘福很想当面感谢少年的父母,但是出于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指捐赠和受赠双方互不知晓对方信息。),他只能通过红十字会转达。
“重生”之后,刘福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秒都会数着过。
“多一个小时都是赚的。”
他会尽己所能做些零工,赚到的钱不多,但他会委托转交给少年的父母。
孟风雨是全程跟进刘福器官捐献的90后协调员。
为了给捐献者父母安慰,又不违返“双盲原则”,她专程找到包括刘福在内,叶沙器官捐赠的7位受捐者录下感谢音频。
刘福把录音稿拟了一遍又一遍,总是问孟风雨:“我这样表达会不会让他的父母伤心?”
2019年2月23日,WCBA全明星赛,出现了一支特殊的球队,他们受邀与职业女篮打了一场表演赛。
他们不是球星,但观众却致以最热烈的掌声。
台下,姚明起身向他们致敬。

他们说,他们是“一个人”的球队。
他们,都接受了一个名叫叶沙(化名)的少年所捐献的器官。
其中,那个矿工就是刘福。
早在半年前,5个人就录制了一个短视频《“一个人”的篮球队》。
2018年9月20日,叶沙的母亲段念可(化名)在器官捐献志愿者群里看到了这则视频。
一个多小时里,她把这段视频看了数十遍。她看到5个穿着“叶沙”球衣的陌生人,知道叶沙的器官正在他们体内鲜活地跳动。
后来,她把视频转给了丈夫叶俊杰(化名)。
或许,这段视频和7个受捐者(另外两位没有出场)就是夫妻俩后半辈子的牵挂。
协调员孟风雨说:“我们不仅摆渡患者的希望,也摆渡家属的念想。”
2020年2月26日凌晨,叶沙的奶奶唐红英离开了人世。
生前,叶沙的父母告诉老人家,孙子获得了大奖,被保送到美国读医学院去了,要读很多年,学成归来再来孝敬奶奶。
奶奶满足地说:“一定要守着孙子回来。”
“母亲直到最后,也不知道叶沙已经走了。”
临终前,奶奶选择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捐献角膜和遗体。

湖南省红十字器官捐献中心承诺,一定会让祖孙二人在纪念陵园团聚。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潘爱华教授说:“自2017年4月27日起再未见过面的祖孙俩,终于以另一种方式相见了。”
2019年,带着叶沙的肺,刘福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表示,他和儿子也都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高敏接到了其父姚峰的电话,老两口愿意遵循女儿生前的愿望,捐献眼角膜。
按照他们的要求,其中一部分眼角膜捐到了姚贝娜的家乡——武汉。
后来,高敏每次回想起姚贝娜,都会想到那双美丽的眼睛,“像两汪湖水”。

姚贝娜有一首歌《心火》:

村上春树说:“人一旦死去,就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
古人云:“死去元知万事空。”
死亡,本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的终点,也可以是生命的起点。
在大街上的人来人往中,与你擦肩而过的某个人,或许将在以后的某一天,点燃别人的希望;
又或许,其中就有人带着别人的捐赠,继续着余生的旅程。
君子在外,远父母兄弟;擦肩而过,皆同胞手足。你我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别人梦里都想见到的人。
生命绽放,终将离场。于是,有人选择在自己的生命燃尽之后,照亮别人的往后余生。
一曲终了,悲欣交集。
部分参考资料:
1、新民晚报:《敬佩!两位新冠患者逝世后捐献遗体,供解剖研究》
2、《三联生活周刊》:还原首例新冠肺炎逝者尸检前后
3、《人间世》第一季 团圆
4、《和陌生人说话》第二季第8集
5、《新青年》演讲第69期
6、剥洋葱people:《“一个人”的篮球队》
7、每日人物:《“我女儿救了五个人的命,她还活着呢”
8、读库:《我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看生命延续生命》
9、梨视频:《法医刘良再发声》
图片来源:网络、视频截图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