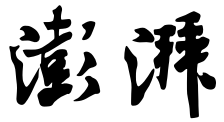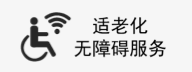- +1
杨宽诞辰110周年|杨宽史料整理思想探析
近代西方史学观念的流入,及本国新史学思想的发展,科学研究历史渐上轨道,其中尤为注重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蔡元培言:“史学基本是史料学。”傅斯年亦曾言:“史学便是史料学”,因而史学家的职责便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此史料学观念即认为一份材料出一份货,材料整理完善,事实自然就显明。杨宽亦受此影响,指出:“原夫史学之研究,基于史料,无史料,斯无史学也。”然而所谓史料,杨宽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解。其在《史学研究法讲义》讲:“史料者,即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遗迹,为今日吾人所得见者。”又言:“史料乃过去人类思想行为之遗迹,前人思想行为之留存于今者不多,而遗迹之能千古不灭者尤寡,古籍之因天灾人祸之散佚者尤比比皆是,无遗迹之留存,即无历史之可言,故无史料,即无历史。”人类思想行为之遗迹均能当做史料,则史料范畴超出文字记载的古籍,此则极大超出传统史料考察的范围,颇具现代学术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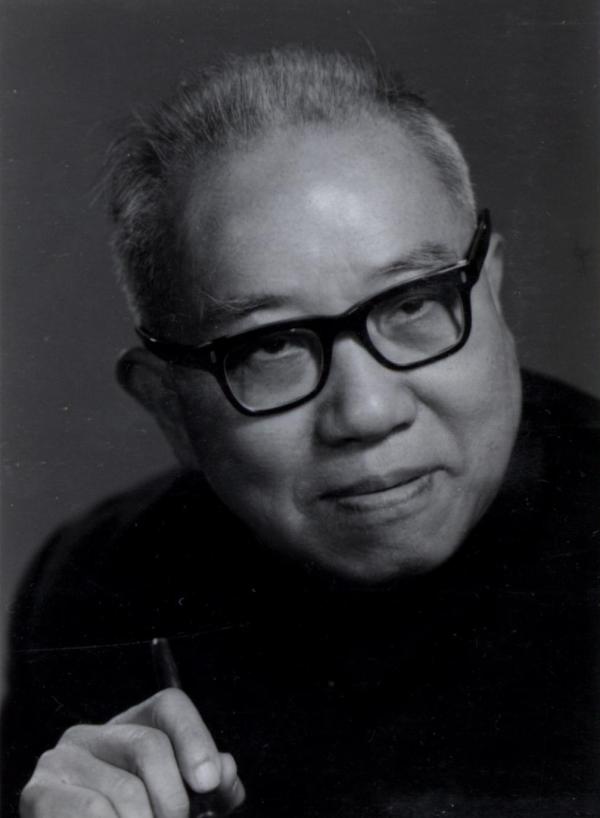
杨宽先生
目录学:搜集史料门径和求学法门
1937年夏,杨宽受聘于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初为人师其所编《史学研究法讲义》,即指出:“凡历史之著作,必先以史料之搜罗咨访。”因此,史学研究其第一要务便是搜集史料。
搜集史料和求学门径须从目录学始。学术研究不先全面搜集史料,就难以正确认识历史真相,而中国典籍又浩如烟海,头绪难寻。幸而自刘向、歆父子撰《七略》,中国目录之学历久不衰,学术源流清晰可观。清人整理古籍,校释诸书,颇看重目录学之应用。王西庄曾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王氏将目录学视为窥探学术的门径,称之为学问第一要事。张之洞《輶轩语·语学》通论读书条,指出读书得法则事半功倍,因此他特意推荐《四库全书总目题要》,认为:“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析而言之,《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张氏于其《书目答问·略例》亦有相近语调。从此可知,目录学确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求学基础。杨宽《史学研究法讲义》中将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相比较,指出史料搜索“吾国则有目录学”,版本则有“吾国则有校勘学”,并画出研究图示:初基知识—目录学—搜罗咨访。通过目录学加之搜集咨访以全面掌握史料,此为历史研究的初级阶段。杨宽感慨:“如果缺乏搜集史料的本领,不能详细占有材料,就可能发生片面的认识,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因而“史料浩如烟海,要寻找到需要的史料,要详细占有材料,不通晓目录学是不行的”。此点在其《怎样学习春秋战国史》一文再次申明,杨宽可谓深谙传统学术的法门。具体而言,目录学的头绪应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加以掌握。杨宽认为:“譬如研究古代史,就得注意古代史籍的目录、近人著作的目录、考古资料的目录和史学论文的目录。”古代史籍的目录,杨宽举出《四库全书总目题要》《中国丛书总综录》《书目答问补正》等,此与古人读书与搜集材料之法并无二致,只是杨氏受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新史学思想影响而史料搜集则更为科学。
史料搜集和整理的旁通意识。近代学者强调历史研究的“四把钥匙”,即目录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和官制史。所以杨宽虽然把目录学作为史学研究的初步,但同时更具科学和综合研究的意识。杨宽《中国古器物学讲义》研究古器物学的方法:“第一搜集材料要完备,第二科学方法去比较分析。”因此,凭借目录学通晓中国传统学术源流,进而掌握读书的门径和史料搜集的方法,但更需科学和综合分析的眼光。通过目录学占有史料“同时历史记载,离不开时间、地点和人的活动,政治历史事件的记载又离不开大小官吏的活动,因此解释和利用史料,就非懂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和官制史不可”。此将史料的收集和运用相结合,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依据年代学建立清晰的时间序列;凭借历史地理学构建人类活动与地理相互影响的空间序列;辅助以官制史将组织结构同人事活动的调配相结合,展现“活的历史”。不惟如此,“四把钥匙”的内容是传统史学,杨宽为深入历史研究,解决历史中的复杂问题,就势必超出“四把钥匙”的传统局限。因而,历史研究不仅需了解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历史问题有关的史料著作和论文目录,还必须“明白过去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过程及其已取得的成绩,看清进一步探索的重点及其途径”。基于此,研究者为探讨历史上经济政治的复杂问题,就须学会考察历代典章制度的方法,历代制度的沿革演变可翻阅《十通》,考察一代之制度则有历代《会要》;探索各时期生产发展的情况,则须具备科学技术常识,例冶金技术史可参阅《中国冶金简史》《中国古代冶金》等书;了解各时期经济发展的情状,掌握户口、田地、田赋的统计数字,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可参考;计算各时期田亩面积和生产产量,则须具备度量衡变迁的历史知识,此方面可阅读《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中国历代度量衡图录》。正是此种现代学术史的旁通视野,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突破史料搜集的限制,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打破学科的局限,致使杨宽的历史研究能够左右逢源。
史料分类:凸显原始性和价值性
史料分类民国学人实已了然于胸。关于史料分类,民国时期国内外学者已多有著作,杨宽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史料详加分判,并形成自身史料学思想的特色。
史料分类首重其原始性和价值性。史料之所以分类,其目的在于充分挖掘史料价值,从而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增强史料应用的充分性、准确性,进而赋予研究结果的权威性。杨宽依据史料的内容、形式和来源详细将史料区分为不同层次。史料以内容分,有属原始史料和孳生史料,其史料价值则原始史料较孳生史料更近真实;史料以形式分,则有遗物和传说之别,文字记录和非文字记录之别,其价值则文字记录以外,实物较为原始;史料以来源分,有“有意传沿”和“无意传沿”之别,其价值则无意流传较有意更可信。通过史料类别分判史料价值,进而考察史书的范畴及其运用。因此,史料运用中应首重其原始性。例如《战国策》与《史记》史料价值相论:“拿史料价值来论,《国策》和《史记》里同样的叙事,自当以《国策》为据,因为太史公那些列传,就是根据《国策》之类的短书杂记的,而太史公却不免有许多润色的地方。”杨氏注重史料价值的原始性,由此即可知史料运用的次第。关于我国传统三种体裁的史书即正史(纪传体,政书同于“志”)、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三种体裁的史书其史实记载无非理乱兴衰(即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典章经制(即正史志书和政书)二类,即相当于今日政治史和文化史。杨宽考察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所载的范围和价值,指出:“吾人于最初步应用时,自以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为便,然正史史料较为原始,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三体,往往以正史改作,故最终仍非根据正史不可也。”从此可知,四种体裁史书以正史史料最为原始且价值最高,研究也自然以此为依据。
此外史料分类过程中又注重其价值性。如上文所言,杨宽运用现代学术视野以科学和综合分析史料,其在看待古史书价值尤其如此。稗史小说、野史及杂史古代街闾巷闻的记录,传统史家对之不屑一顾。《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载:“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街谈巷语自然真伪难分、良莠不别。《隋书·经籍志》杂史条载:“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大抵传统史家看待稗官野史等均以其难登大雅之堂。赵瓯北曾说明其原因:“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不敢遽诧为得间。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赵氏所言,野史等记录不甚整全且与正史记载多有抵牾,又未尝对材料甄别考证,因此传统史家多不敢信用。此固然是野史等之缺点,但杨宽指出:“其所记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知一家之私记,要皆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昔日以稗官野史荒诞不经而鄙弃不用,今日又以其能记录遗文旧事而弥足珍惜,这不能不说是时代学术视野转变的结果。然而,杨宽学术观念的转换,史料观点的转变,将传统史家不甚注意的材料纳入史料的范畴,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这就延展了史料学的视野,拓宽了史料的维度。
“六经皆史”的史料观之承袭与发展
六经皆史说其来渊源有自,隋朝王通曾道“三经亦史”之说:“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王通认为六经中《尚书》《诗经》《春秋》皆为圣人所述之史,因此提出三经“同出于史”的观点,此为三经皆史说的滥觞。明朝王守仁扩展“三经亦史”之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史,《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又“《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劝诫”。王守仁昌言“五经亦史”的命题,并提出存史的目的在于存道,所谓“事即道,道即史”即是此理,而其价值则在“明善恶,示劝诫”。此后王世贞提出:“天地之间无非史也。……六经,史之言理者;编年、本纪、志、表、书、世家、列传,史之正文。”此时王世贞已提出“天地之间无非史也”的论断,经书亦即史书之一种,“六经,史之言理者”正是王守仁“事即道,道即史”的注脚。尤可注意的是王氏将世间文章、著作多统归于史的范畴,突破传统经史观念,其眼界实开傅斯年等人昌言“史学即史料学”的近代先声。李贽《经史相为表里》言:“经、史一物也。……故《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异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李贽仍然秉持王守仁、王世贞辈史以经明理,经因史而彰的理路,经史为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又认为道理屡遭变移,则需史阐明其所以然,首次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及至章学诚提出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因此“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氏从源头处论证经、史最初没有分别,均为史官保藏和整理的典籍,六经的内容是记载先王政典史事,章学诚将“六经皆史”说的命题论述更为系统化、理论化,有其突出的含义和价值。
正是基于突破传统经史关系的局限,加之现代学术观念的转变,杨宽在史料分类上承袭“六经皆史”的余绪,又能拓宽史料的范畴。关于六经,杨宽同意章学诚援经入史的思想,甚至赞同章氏《论修史集考要略》言纬书、《逸周书》、《春秋后语》“具与古昔史记相为出入”的观点。具体言之,《周书》中《吕刑》《康诰》《多士》等篇为西周作品,是较为原始的材料;《诗》三百篇纯粹史料至多,例《玄鸟》《长发》等述商周开国史迹;《易》之卦爻辞,亦即殷周之际绝好史料;《周礼》是战国史料。二戴《礼记》是周末汉初史料;小学类,如《尔雅》《说文》等书,可由文字起源于训诂以推索古代社会情状。杨宽摆脱传统经史观念,甚至超越执著于经书体裁和年代问题的局限,挖掘史料本身所能反映的时代价值,例《周礼》可探求战国史事,小学类著作可推证古代社会情状。关于伪书,杨宽理解比较深刻:“所谓‘伪书’只要考出他的来源和真相,也就可以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上应用,因为有些‘伪书’并不是全出凭空杜撰,其中有些部分也是有所依据的。”因此,民国诸人认为《周礼》之伪,但却不影响其反映战国时期之制度的史料价值。此正如陈寅恪所言:“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材料真伪乃相对而言,考察材料的时代及作者,进一步据此材料所反映本时代的思想与课题,如此材料的范畴和价值则大为显见。基于此,战国子书的成书特点,杨宽言:“所有著作,或为一人所作,或为一家之说。各家著书立说,往往引证历史故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用作立论根据,甚至作为学习榜样。”战国诸子多托古论辩,其所引据的文献基本不是严谨考证的结果,但诸子“儒、墨、道、法诸家,其为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之主要材料。又如天算、医学之书,其为科学史之主要史料”。因此,杨宽将子学所涵盖的内容和体现的思想,均可作为不同学科的文献史料。
两周史史料特点与运用
两周史史料特点与运用。先秦史乃杨宽古史研究的重心,尤其在两周史的研究中取得重大的成就,因而杨氏关于此段史料的观点十分重要。传世西周史料保存甚少,且真伪繁杂,因此三代以上,史迹真相难以寻觅。
现存西周主要史料的特点,杨宽指出:“即儒家作为经典的《诗》、《书》、《礼》、《乐》,都经过战国时代儒家的编选和修订,有其家派的局限性。第一,儒家所传西周史料,大多是开国文献,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史料。……第二,儒家所传西周的礼书,都不是原始资料,已经儒家按照其政治理想重新编定。”现存西周史料不仅存量稀少,且时段分布不均;此外史料编定也是按照门派各自的有意选定,结果即很难建构起完善的西周历史。然而,面对现存传世西周史料的特点和缺陷,其史料本身并非一无是处,研究者并非手足无措,借助后人的著作对前史作一番深入的探究,仍可以从中寻找出西周历史的真相。杨宽指出古人所谓礼制不仅包含典礼仪式,更含有许多重要典章制度:“因为古代的典章制度经常贯串在各种仪式的举行中,从而得以确立和维护的。经学家一向把礼书的分析研究作为重要的课题,……今天我们要探讨西周的典章制度,还是有必要把古书所载各种重要礼制,结合当时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制度,系统地探索其源流变化,从而揭发出西周时代典章制度的真相来。”因而,传世史料经过综合、科学的运用,仍然可以对前史作出比较有效的研究。依据杨宽《西周史》所举七项史料,除儒家编定史料外,仅剩四项。第三项中,《逸周书》具有《周书》的逸篇性质,数篇保存有西周的历史,但“《逸周书》原是战国时代兵家所编辑”。其特点和缺陷与儒家编定的史料相同而过之。此外《国语》《周易》不过只言片语保留西周史料,均难以构筑某一时期的西周历史图景。第四项中,《古本竹书纪年》本即战国魏国的编年史,且原书宋朝时期已散失;《世本》成书战国末年,原书宋代散佚;《穆天子之传》战国时期类古小说性质,神话成分严重。实则这些史料不仅不是西周史的原始史料,即便其书也深受怀疑。第五项中,《史记》《汉书》《后汉书》其所载史料多源自经书,或是后世史籍的抄录,是否能真实反映西周史也难以言明。日本学人白川静曾指出《周本纪》:“它不过是拾缀《诗》、《书》及其他古传说而成,仅只附记了周王系谱及一些神话,很不充分。”进而说明《诗》《书》“这些原始史料的可靠性,直至今天仍然有许多应当作为分析的对象”。白川氏此言的依据是金文的出土,可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此点杨宽意见类似:“既然儒家所传的西周文献有其局限性,又缺乏西周中期和后期的文献,五百篇以上的西周金文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我们研究西周史,很有必要以西周可靠文献,结合西周金文,参考儒家所传礼书,作综合比较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杨宽所列西周史料第六项即“西周金文”。西周史研究除了利用传世文献作必要的探索外,唯有金文史料的应用才能丰富和扩展西周史的研究领域。
春秋时期史学发展迅速,中原各国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史官制度,国家历史的记录和保存都较为发达。《国语·晋语七》:“羊舌肸习于《春秋》。”又《楚语上》:“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此说明春秋时期已有《春秋》作为教本供官宦子弟学习。《墨子》言:“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墨子称述诸国皆有《春秋》史籍,此点《史通·六家篇》引墨子语:“吾见百国春秋。”因此,春秋时各国皆有国史,墨子之言不污。《孟子·离娄》言:“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此又为春秋诸国皆有国史之证。因此,诸国重视国史编订能遗于后世的材料较多,研究春秋史可凭据的史料相对丰富。春秋史料及史学的特点与其史官制度相联系。杨宽指出:春秋的历史文献都出于当时史官的记述;史官原是当时天子和诸侯的秘书;史官的历史记述为贵族的政治服务;当时史官又是历史文献的保藏者。基于春秋史料与史官制度密切联系的特点,春秋史料的体裁及其目的相映成趣。杨宽指出:“史官记载有记事和记言之分。记事的叫做‘春秋’,记言的叫做‘语’,还有记宗谱的,叫做‘世’或‘世系’。当时史官编写史书,目的在于吸取贵族统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便进一步巩固和维护贵族统治,以供统治者作为借鉴,并用作贵族子弟的教材的。”正因此,春秋史料的缺点也很明显,“现存的春秋时代历史文献,虽然不少,但是大都是出于当时史官的记述,原来是用作为贵族的政治教科书的,不仅有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而且局限于贵族的一些活动,局限于他们认为可作经验教训的言论和事例。”可知春秋史料的记述范围和对象均是贵族阶层,史料的狭隘程度不言而明。具体言之,《春秋》一书经孔子整理修订,基本上还是依据史官记载,并继承当时史官传统。《诗经》之《鲁颂》是鲁僖公时告祭祖宗、颂扬武功的诗;《商颂》是宋襄公是祭商先祖、称颂君德的诗。《国风》中《鄘风》的《定之方中》是歌颂卫文公迁到楚丘重建卫国的诗,《载驰》是翟灭卫后许穆夫人所赋的诗,《卫风》的《硕人》是卫人歌颂庄姜的诗;《王风》是周东迁后的诗,《郑风》是郑国的诗,《唐风》是晋国的诗,《齐风》《秦风》《陈风》《曹风》是齐、秦、陈、曹等国的诗。虽然,春秋史料除官方编定典籍外,不乏有《国语》《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墨子》及《礼》书等对春秋史事的记载,但或记述范围及对象与当时史官编定典籍的性质相同,或只言片语不成系统,或各家凭据己见修订,故而传世文献的范畴、可信度还需进一步考释。因此杨宽注重出土材料和文献对春秋史的研究,“解放以来考古挖掘上的重大成就,大大补充春秋文献的不足,使得我们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了解。”正是出土文献扩大了研究范畴及其视野,超越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使春秋史研究更加全面和科学。
战国时代文化繁盛出现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但现存战国史料却未呈现出完整的史料序列,战国史较之春秋史的研究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战国史料存在的问题,杨宽于其《战国史》一版早已言之:首先,春秋战国间的史料缺乏;第二,史料的年代紊乱;第三,部分史料所记的历史事实缺乏真实性;第四,史料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杨氏在其1980年二版《战国史》中仍重述战国史料存在的问题及其需克服的困难。杨宽概观战国史料的特点言:“因为现存的战国史料,残缺分散,问题很多,年代紊乱,真伪混杂,既不像春秋时代的历史有一部完整的编年体的《左传》可以凭信,更不像秦、汉以后每个朝代有完整的历史记载。”然而就战国史料的时段分布及其记述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战国初期之史料已大多散佚,……及战国中期以后,史料增多,但所记大事尚甚简略,年代颇多错乱,大多为纵横家所记述之计谋、权变与游说故事,或为长篇游说辞,或为献策之书信。其中有真实之历史记载,有著名纵横家真实之作品,亦有夸张扩大,随意附会,甚至假托虚构者。亦或记载有出入,传闻异词者。”幸而战国史料存在的问题,前人实则已作出整理和考订。宋人吕祖谦《大事记》、清人林春溥《战国纪年》和黄式三《周季略编》等对战国史事详加考证,务求建立完善的战国纪年序列和较为完整的事件编年。但正如杨宽所指出,这些编年的战国史书仍然存在相当缺点:(一)未能全面改正错乱的纪年;(二)未能作“去伪存真”的鉴别;(三)未能全面搜集史料加以考订。从此可知,杨宽对战国史的研究及编纂和著述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充分汲取前人的成果和借鉴前人偏失的基础上而取得。具体言之,杨宽对战国史料的认识和价值挖掘也是不断深入研究的结果。例《史记》的运用及其史料补充,“本纪”“世家”是帝王和诸侯的编年大事记,“列传”则为大臣和历史人物的传记,“书”记载典章制度,“表”则附事件于纪年之中与本纪、世家等记录相表里。所以《秦本纪》《始皇本纪》东方诸国《世家》《六国年表》以及战国时期诸列传,已可概观战国史事,此为研究战国史最权威的文本。但即便如此,《史记》仍然有诸多可弥缝之处。《汉书》之《百官公卿表》《地理志》《食货志》《艺文志》《西南夷列传》等篇,其记载战国史事可补史记之不足;《后汉书》之《西羌传》《南蛮传》等篇所述战国史事亦可补《史记》的不足。正史补充《史记》之外,《战国纵横家书》提供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内容,可纠正《苏秦列传》的错误;云梦秦简《编年记》所载战国后期史事是研究战国末年和秦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可补《史记》的不足,纠正《史记》记载的错乱和混乱;《古本竹书纪年》其中战国部分,不仅可补《史记》的不足,还可用以纠正《六国年表》记载魏、齐等国的年代错乱;《华阳国志》中记述西南地区远古到东晋的史迹,其中述及战国史事,可补《史记》的不足;《水经注》引用《竹书纪年》等书说明战国历史情况,其中述及楚方城、魏长城、齐长城、燕长城以及郑国渠的经历情况,这些是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可补《史记》等书的不足。从此一列可知,《史记》中战国史料的补充就传世文献而言已有较大空间,战国史料运用以《史记》为主干,仍需对前后文献史料尽量搜索以扩充和补订《史记》记载战国史事之不足。此外,出土文献对于《史记》的订误和补充同样不可小视。所以,面对现存战国史料的特点,杨宽极为注重考古新史料:“由于原有战国史料的分散残缺,年代错乱,真伪混杂,考古发现的新史料因此显得特别重要,不仅可以补充原有史料的不足,而且可以纠正原有史料的错乱,并用作鉴别真伪的标本。”先秦史研究中,杨宽从始至终非常重视考古新材料对研究历史的价值。
总结
综之,杨宽史料整理思想,一方面承袭传统优秀史学思想,另一方面受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和本国新史学潮流的学术影响,开辟出自身史料学的研究特点。杨宽重视目录学对于初基者的为学门径和史料搜集的法门,同时注意史料搜集和整理过程中的旁通意识。而文献史料的分类中尤其凸出史料的原始性和价值性,依据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扩充史料的范畴。杨氏承袭传统“六经皆史”的史料观而发展,突破文献体裁和年代问题而注重挖掘史料本身价值,扩充子书乃至其它一切文献可资运用的史料。先秦史研究尤其两周史研究中,注意不同时段的史料特点,就传世文献中深入分析及综合整理运用,再依靠考古新材料的补充以求各段历史史事的完备,自觉形成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相结合的研究路径。由此可知,杨宽史料整理运用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将史料搜集、分类、扩充及运用科学化、系统化,转换史料运用的观念,扩充史料运用的视野,形成较为完善的史料整理思想。此对于后学研究古史尤其先秦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与意义。
(原文注释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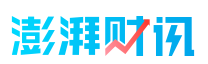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