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讲座|朱岳:“内向世代”
在纯文学不被重视的今天,一个在中国台湾地区已经隐没的文学流派,可想而知很难获得读者的关注。这个流派便是大陆读者都很陌生的“内向世代”。这个概念怎么来的,有哪些代表作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家、后浪文学主编朱岳最近在寻麓书馆·传灯人讲座跟读者分享了这些话题。以下为本次分享内容的文字整理。

朱岳,曾是律师,后转行做图书编辑,业余时间写作,出版短篇小说集《蒙着眼睛的旅行者》、《睡觉大师》、《说部之乱》
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地区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变革,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议题大讨论,但与此同时在文学上出现一种相反的倾向,就是深入“内向”的探索,回归心灵和文学性本身。被归于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有:黄启泰、邱妙津、赖香吟、骆以军、袁哲生、黄国峻、童伟格等。他们继承了现代派的传统,并为中文小说创作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内在风景”。但是,在短短时间内,这批作家中有多人或自杀或退出文坛,这不由令人怀疑他们的文学风格与命运有内在的联系,这是文学的悲剧,也是一个耐人深思的谜题。
这一文学流派,因其自身的“内向性”以及几位主要作家的过早离世而为我们所忽视,甚至在台湾,许多文本已经绝版,但他们的作品在深度、技法、语言等方面,均达到极高造诣,是中文文学中的一座宝藏。
从外部世界的喧嚣转向朝内追寻的探索
“内向世代”本身并不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文学流派,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这个概念在日本文学中就存在着,日本战后涌现出来的一批作家被归为“内向世代”,代表就是古井由吉。台湾地区的“内向世代”是黄锦树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估计他可能受到了日本“内向世代”的启发,但在他的文章里并没有关于日本“内向世代”的介绍,所以我们也只从台湾文学本身的历程来介绍这个文学流派。
1980年代末,台湾地区有“解严”的过程,这时候就有很多思潮,比如关于性别、解构等社会议题的浪潮,反映在文学上就有很多争论、争锋。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向一个“内向”的方向发展。它不是紧跟社会热点话题或者议题,并不是以此为中心,而是相反的方向,就是转而对内在世界的探索,或者说是对“自我”进行剖析的过程。黄锦树说,它是一道“潜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明显,但其实又很有力量。
当时的文学是介入当下现实,或者要去提出一个答案、要表达民间的痛苦,或者要替无法发声的人来发声,或者是以一种虚无的态度去解构这些东西,但这种虚无本身也是面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所以后来的“内向世代”和这种虚无其实质还是不同的。
这批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迅速登场,他们的同时代人黄锦树给了这批人“内向世代”的命名。但这些人有些很快就去世了,有的是自己退出了文坛,所以这个浪潮很快兴起然后又很快消失了。
其实我们从“内向世代”的特点也可以看到,它对我们现在文学的走向是有启发的。我们现在的文学也是有两个方向,一种方向就是和时代很贴近,在我写小说和编小说的过程中,都有各种朋友来探讨,小说一定要贴近时代或者反映当下的问题,或者起码是要回应这些东西,小说的态度是鲜明的。但另一种就是“内向”的,也是我前面说的。
内向世代开启者:黄启泰
回到“内向世代”,有几个重要的作者,黄锦树首先把黄启泰归入其中,然后把邱妙津、袁哲生、黄国俊都算进来,还包括比他们小很多的童伟格,依据的是黄锦树的一篇文章《内在的风景——从现代主义到内向世代》,以黄启泰作为“内向世代的开启者”。
黄启泰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家,最近出版了他的一本书《防风林的外边》,这本书第一次在台湾地区出版是1990年,也就是30年前,之后黄启泰等于告别了文坛,去伦敦学心理学,后来回到台湾任教和研究,也是心理学领域。这本书本来在台湾有机会再版,但由于编辑去世,所以被搁置了。它最早的发现者,也可以叫做伯乐,林耀德,也是很年轻就去世了。

黄启泰《防风林的外边》
在我看来,“内向世代”的作家每个都很厉害,但《防风林的外边》可能是最特别的一本。其中有一篇叫做《少年维特的烦恼导读》,题目好像是和歌德的小说有关系,事实上基本没有关系,是以一个精神分裂患者视角去写的“元小说”。当然它又掺杂了很多同性恋的压抑、乱伦、倒错。黄启泰可能当时就涉猎过很多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当然他不是直接用这些知识,而是完全把读者的视角带进那种精神分裂者的视角。
我记得有一种说法叫做“人写鬼”还是“鬼写人”,就是说,有些写鬼的,你一看就是人写的,但有些看起来平常的故事,写法却阴森森的,就是“鬼写人”。《防风林的外边》不是正常人在写精神分裂,而是本身就能达到很逼真的模拟精神分裂的状态去写了这部作品,但是他又高度自省,很好地驾驭了这样一个视角,他本身控制得很好,表现力很强,自己完全没有失控。当然我这样形容大家可能不容易理解,真的需要看一看作品。
黄锦树把《防风林的外边》放在“内向世代”的首位,可能是因为作者较早隐退,也象征了这个流派的宿命,但也是因为这部小说的冲击力实在很大,很可能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受到一定冲击。当然黄锦树其实并没有着重去谈精神分裂这种精神变异,他是从“内在的风景”这个角度去谈,这也是黄启泰自己解释作品的时候,对小说的一种说明。这种说明后来就被用在对“内向世代”特点的解读上。他说,正因为我把故事建立在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模糊的边界,忽略了许多外界正在进行的有意义的事件,过度专注于内在世界的呈现,而不从社会政治历史等朝外的观点来剖析世界,而且由于这种建构故事的方式主观成分非常强,使得文本本身变得不够透明化。他很清楚地说出了他的文学主张就是“内在的风景”。其实王国维那里就区分过“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可能所有的文学都可以归类到这两种。所以“内向世代”是很明显的“主观之诗人”,他是从“内在的角度”作为切入点。黄锦树老师归纳了几个特点,第一就是他主观性特别强,第二是外部现实被转化为“内在风景”,第三就是诗化,语言是像写诗一样的语言。平时说到外部世界,比如当前的热点事件,你可能只能用一种直白的语言,这是一种透明的语言,你不会让大家注意你的语言,而是要大家注意到你表达的事情本身,比如说“哎呀,着火了”,你不会修饰它。但一种不透明的语言会像诗歌,让你注意语言本身,而不是让你注意语言所指向的那个世界。“内向世代”的语言特点也是这样,它是不透明的,而是诗化的语言。第四个特点就是,我变成他人,然后真诚地面对自我。无论是黄启泰,还是袁哲生、童伟格,都有这个特点。
袁哲生与他的《寂寞的游戏》
我们(后浪)从2017年开始,比较系统地来做华语文学出版。台湾地区第一本就是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戏》,这本书后来影响较大,前段时间有部电影叫做《阳光普照》,里面一个角色讲了一段话,那段话也是从《寂寞的游戏》里引来的,那个编剧好像也很喜欢袁哲生的作品。但一开始大家对“内向世代”和台湾文学都没有了解,接受起来很困难,所以我们做纯文学是很累的,不像那种有刚需的书,教辅教材就不说了,还有很多是读者想获得知识的,大家其实阅读是为了获得知识,而很多人读小说都是为了消遣,如果小说看着累,让你没法消遣,那很多人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买这些小说来看。《寂寞的游戏》是借助了影视剧这种途径才有了更多的受众,当然这本小说本身也很有意思。

袁哲生《寂寞的游戏》
袁哲生在39岁就自杀了,非常可惜。他写小说的时间不长,出道没几年就去世了,期间很短暂。《寂寞的游戏》很多都是白描手法,如果你看的话,会觉得是很抒情的故事,比如有一篇是夫妻两个躲在山里,与外界没有什么联系,有天他们做了一个约定,说我们都来拿一个罐子,各自写一句话给20年后的对方,然后把罐子埋起来,20年之后再打开看彼此说了什么。他们就各自埋了一个罐子。然后很快妻子去世了,丈夫有一天就想看看妻子写了什么,虽然还没到20年,他就提前把罐子挖出来了。他挖出妻子的罐子,里面什么都没有,那是个空罐子。而丈夫其实在埋罐子的时候什么也没写给妻子,就放了一张白纸。丈夫想,肯定是妻子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把他的罐子挖出来,看到丈夫埋了一张白纸,就把自己写下的真心话拿走了,所以那个时候妻子的罐子已经空了。他的故事都是一种你说不清楚,有一种很玄妙的感觉,当然也有一种很深的情感,就是看了可能心里很堵得慌的那么一种感觉。但是在这种白描式的抒情背后,又有一个很强的逻辑结构。我刚才的这种叙述,可能就把这种逻辑结构说出来了。其实他的整个描写很优美,很梦幻,但他的逻辑结构很硬,你能感觉到这种清晰,就像一场博弈似的。而且,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我”。
袁哲生的小说,在形式上有一个主题,就是“镜像结构”,我叫它“镜像主题”。关于“镜像结构”,有一个故事很鲜明:一群小孩捉迷藏,主人公“我”躲在树上,一个小孩来到树下抬起头,但并没有发现“我”,目光完全“穿透”了“我”,就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我”就惊呆了,因为对方看着你就像什么也没看到一样,那就说明你已经没有形象了,从对方看你的目光,你看到了自己的隐形。这就是“镜像”,通过别人看到自己,对方正像你自己的镜子一样。袁哲生的很多小说都有这样一种镜像结构。还有一部小说,是一个小孩没有父亲,另一个小孩也没有,他们一起玩耍,但你能感觉到这两个小孩是互为镜像的,虽然一个是“我”,一个是另外一个人,作者始终没说他们就是同一个人,然而你却感觉到他们就是一个人和自己的镜像。
介绍过这两个作者,你们可能已经感觉到内向世代的特点是什么了。
黄国峻:内在的战场并不比直接参与社会轻松
我再来介绍一个小说家,叫做黄国峻,他在32岁就自杀去世了。他和袁哲生也是很好的朋友,他去世后,袁哲生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叫做《偏远的哭声》。我最喜欢的黄国峻小说集叫做《度外》,他26岁写了《留白》这篇小说就获得了当时的文学大奖,张大春说他是自有一股不与时人弹同调的庄严气派。其实这也是当时的背景,大家还是很关注社会议题,但是“内向世代”的风格就很超越,对自我的关注,可能更切近每个人的内心,并不是远离现实,而是从这种外向投射的现实转向对内在现实的关注。黄国峻去世之后,袁哲生写的文章里也谈到,其实他们是同一个战壕里战斗的兄弟,他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进行一场战斗,这种战斗也很痛苦,并不比直接参与社会关注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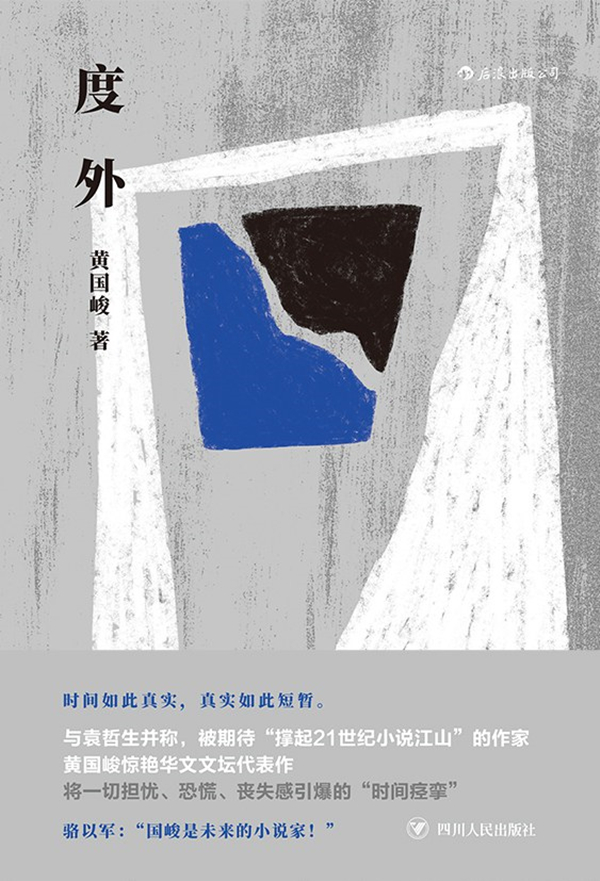
黄国峻《度外》
我觉得黄国峻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种内在的形式感。他讲了一个故事,一场台风之后,一家四口从各自的视角写了台风之后的经历,以一种回旋的方式来构架小说,整个故事没有太多情节,就是一个主观视角之后换成另外一个主观视角,不停地在四个主观视角之间切换,而一股旋风的形式感就通过这个作品显现出来了。他的形式感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他讲的是人和人终极的命运的结构。
还有一篇小说叫《送行》,一个儿子被捕了,被押上火车,主人公“我”和父亲两个人去送哥哥,讲的好像是一个很温情的故事,但是送行过程中车上的人来来去去,然后他哥哥被带走了,他和父亲也告别回学校了。在这个故事里你就看到这种人和人的聚散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是自然呈现出来的,你会感到所有的人都是一种路人的关系,他通过这种聚散离合的形式,最后让你感觉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管血缘多么亲近,他们各自就像撞球一样,一弹就都弹回到各自的轨道上去了。如果放大的话,你也能看到全人类之间也是这样一种关联。
这些小说并不直接切入去谈论人类世界,但是它是把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用一个很自然、很故事性的表达传达出来,甚至作者都不一定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形式,可能是无意识的。他们可能就是把自己内心的风景表现出来了,但这个风景并不是一盘散沙,它有一个很强有力的逻辑,是很深邃很本质性的东西。
他们的后继者,就是在这些人都去世之后,现在还活跃在台湾文坛的作家童伟格。黄锦树认为童伟格是“内向世代”的集大成者,他的语言更加精纯,叙事方法更加丰富。
黄锦树与泛华语文学
最后我再介绍一下命名“内向时代”的黄锦树,他是马来西亚作家。我们把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称为“马华文学”,这一支文学很特殊,它相对于我们也很遥远,可能有少数人知道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就不错了,更少有人知道马来西亚还有一批华人在拼命写纯文学小说。所以在这样一种处境下,我觉得黄锦树可以说是用以一人敌一国的力量去从事他的文学事业,他不仅批判了马华文学里很多他觉得落后的东西,而且把台湾文学很精华的“内向世代”也总结得很好,同时他自己又是一个研究者,一个很了不起的小说家。
华语文学,不仅包括内地,也包括香港的、台湾地区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写作,除了这些地区或群体,其实还有很多地区的海外华人在从事纯文学创作。我觉得我们就缺像王德威那样的学者,视野能涵盖到这么大的范围,但真正关注到他的文学评论家很少,整个批评界的声音很微弱,台湾地区可能还要好一些,但他们读者其实也很少,据说在台湾地区,黄锦树的小说集印了2000本,卖了20年都还没卖完。
我特别推荐一本他的小说《雨》。这本小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光怪陆离的故事,它的主体是一家四口,父母兄妹,在一个雨林的小屋里生活。大家看“雨”这个字就好像是一个小屋里头有四个人,这四个人不停地以各种方式死去,轮流地死去,在第一个故事里死去的,在第二个故事里可能没死去,就在很封闭的雨林这样一个幽暗的环境下,以各种神秘诡异的方式,一会儿这个死一会儿那个死。

黄锦树《雨》
我觉得黄锦树没有把自己归到“内向时代”,是因为他还是有一个外向的指向的,他没有完全回到对自我的剖析或者是完全上升到一个形而上学的角度。但是他也是用一个高度形式化的结构去表现人的灾难,他选的这四个主人公都是替身,遇到的各种灾难象征着马来西亚华人遇到的各种灾难,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代表全人类,既有抽象的那一面,又有很具体很实际的外在的指向性,他把内向和外向统一起来了,有社会议题的那一面,又有探索人的存在本质结构的那一面。所以《雨》被我讲得好像很抽象,其实是有血有泪的。
好的小说语言
最后我想说一下语言问题,怎么才叫一种好的语言,这个很难判断。我其实读了很多翻译小说,可能很多喜欢文学的人都是读翻译文学,语言受到翻译文学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觉得应该找到一种更属于我们的语言,我注意到日本文学,觉得它更接近东方人的美感和节奏,但它还是一个外国的文化。后来经过同事的指点,我终于知道香港、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华人在中文写作的探索上走得很前卫。……他们接触西方的现代派写作又相对要早,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多长处,语言很值得我们借鉴。像有些成语我们可能都闻所未闻,但是在台湾地区可能小学生、初中生就掌握了。从这个语言角度来说,我们大陆当代纯文学之外的那些文学,也是很重要的补充和借鉴。我们整个的视野不应该局限在现在的这种作协系统的纯文学,要多看看我们忽视的其他地区先进的中文写作,能对我们有一种激发。把更有活力、更丰富的华文文学引介进来,也是我们现在想继续坚持的工作。
Q&A
Q:感谢朱岳老师的分享,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怎样去看这些“内向世代”主力军最后走向自杀这一点,包括邱妙津?
A:自杀的事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当时很多人选择自杀,可能有自己的身体或者心理的原因,并不一定和写作有关系。他们的写作比较倾向于内向,比较倾向于自我探索,可能正是因为身心有一些问题,所以才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当然,写小说的人还有一点是很难被人理解的,我觉得现在我写小说,还有包括我做原创文学,其实都是这样的,你很难遇到理解你的人,同时你如果光靠写作又无法生活,就只能去干很多也不太愿意干的事,这样很累也很痛苦。有时候痛苦能激发灵感,但是如果你依靠痛苦去激发灵感,会越陷越深。这几点因素可能会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偶然的,不是说有一种很必然的联系。
Q:您之前在访谈中提过袁哲生在描写一种状态而非情节,想听您解读这一点。
A:我确实觉得小说的情节包括桥段、套路,如果说的不好听就是烂俗,很多写作课就教人这种桥段、套路怎么去写,但是真正很动人的情节,往往不是虚构出来的,是你看新闻突然看到一个事儿,可能那个情节比任何作家想出来的都要神奇。所以很多作家不是以情节取胜的。所有作品有智力成分或者说智性的成分,它才可能流传久远,除非你是个山歌,如果没有这种智力成分,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智力的成分又不一定是体现在情节上,可能在很多方面都蕴含着智力成分,包括你的一字一句,比如你调动巨大的数据库去用一个词。
Q:会长好!我很喜欢“内向世代”这个命题,《寂寞的游戏》里袁哲生写人天生喜欢躲藏,主人公热爱捉迷藏,实际上很想被人看到,我觉得这和后现代很多人的困惑相通,包括台湾“内向世代”的写作者们,知道彼此处于困扰之中,虽然可能理解这种痛苦,但没法挽救任何个人,我觉得会长关于镜像的想法很有趣,这种向内挖掘的文字,探索的结果只能接近塌陷吗?
A:我觉得黄锦树老师对“内向世代”也是有一个批判态度的,他不是完全认可这种向内挖掘的路数,这也是我觉得需要再继续思考的一件事。“内向世代”的“自我”并不是很强大的自我,很脆弱,它把人和人、人的存在看得很透,出离心很强,这个世界可能没有什么能抓住他们了。当然这完全是我的一个臆测。为什么儒家还要讲关怀天下,你还得有一个外在的东西让你去改变它。这两个面向是要达到一个平衡,你要不时地回到很内在的探索,同时你又不能完全放弃外在的努力,我们还是要尽量地去把这个世界变好是吧?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