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惠男评《最后的皇族》︱在“新清史”之内或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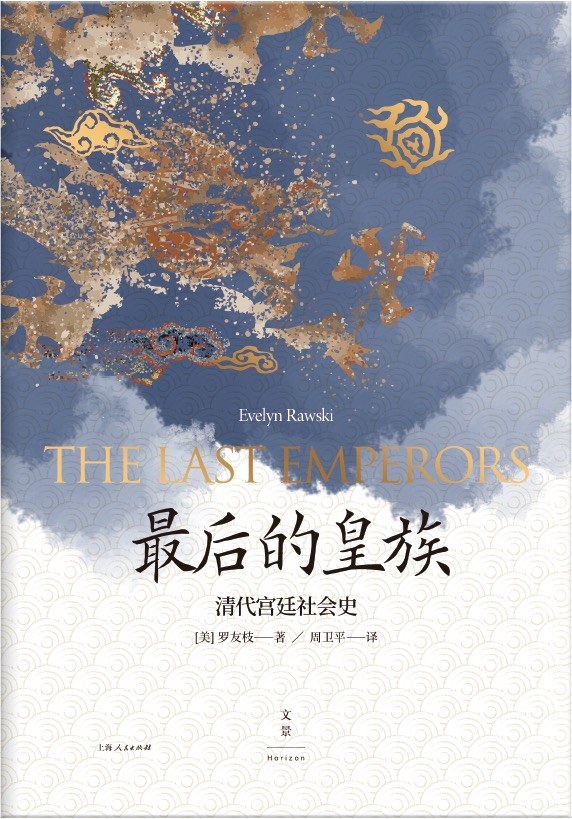
[美]罗友枝著,周卫平译,《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582页,98.00元
如果梳理近四十年来美国的清史研究成就,匹兹堡大学的荣休教授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必定能占据相当的篇幅。除了早年间对明清经济和社会史的贡献以外,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还要归功于她在1996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年会上以主席身份发表的那篇名为《再观清朝: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的演讲。在这篇引人注目的主席演讲中,罗友枝既是号召呼吁般地、也是预言般地指出了二十世纪末北美清史学界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的学术转型——包括并不限于:重新思考清朝何以成功统治中国的方式及由此衍生的统治集团精英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而重新评价清朝的国家性质与历史地位——即现在被称作是“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的潮流。
罗友枝教授于1998年出版的《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是顺应这股潮流的应时之作。史家盖博坚(R. Kent Guy)曾于2002年撰写评述,对本书颇为推崇,展望其未来能和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欧立德(Mark E. Elliott)、路康乐(Edward Rhoads)的同期专著共同成为亚洲研究领域的“满学研究四书”(the Four Books of Manchu Studies),可见其在北美学界之地位与影响力。
《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以下简称《最后的皇族》)首次引入国内的时间是在2009年,距今已逾十一载。因此,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此次再版,无疑是把本书重新带入了学界与大众的视野,对其在中国的普及起到十分重要作用。这篇书评将对《最后的皇族》的各章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并对本书的核心问题作提炼归纳,以期能对新读者起到一定的导读帮助作用,并唤起更多关于本书内容的深入思考。
一
除绪论、结语以外,《最后的皇族》共分为三部分,分别冠以“清代宫廷物质文化”“清代宫廷社会结构”和“清代宫廷礼仪”之名。
第一部分“清代宫廷物质文化”由单独的一章组成,即《宫廷社会》。
在本章中,作者通过探究宫廷的物质文化,指出清朝的宫廷社会是数种文化传统的“折中融合”(eclectic blend)。清朝的君主在决心维持作为满洲人的身份认同时,也将不同的统治权形象(images of rulership)投射到被其视为国家主要成员的汉族和内亚民族的文化模式中。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作者主要以清朝的多都制、宫廷生活的文化政策以及清宫艺术三个方面展开。
作者认同弗雷特(Philippe Forêt)的观点,指出清朝施行多都制度,存在盛京、北京和承德三个首都能够同时承担起清帝作为满蒙大汗、汉人皇帝与藏传佛教菩萨的责任,而这种特殊的体制应当追溯到辽、金、元的政治传统。不过,北京城虽然保留了大量的儒家符号体系,但清朝的统治者仍然做出了属于自身特性的改变,例如自1644年入关以来就实行的内、外双城划分,不仅是辽代就已存在的模式,亦是清朝入关前都城特色的延续等等。从多都城的体制到北京城暨皇城、紫禁城的空间规划,清朝有意地营造了一种折射在不同层面的空间分隔,空间本身就具有相应的政治文化属性,而皇帝来往于不同空间的活动则是帝国文化策略的写照。
除此以外,作者较为全面地总结清朝统治精英集团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满洲文化的坚持,包括语言、姓名、服饰、弓箭骑射、膳食等方方面面,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排斥来自汉族或内亚民族的传统。例如,清朝皇帝在接纳从明朝流传下来的“朕”“用膳”等政治等级词语时,也会要求官员在满文奏折中按照满人的传统尊称其为“圣主”(enduringge ejen)并自称为“奴才”(aha),亦对蒙古人尊奉的称谓“博克多可汗”(boγda qaγan)欣然接受。
在清宫的各类艺术品中,这种文化的多元性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皇帝利用自己收藏的珍宝和画像彰显了放眼天下的宏伟胸襟。因此,作者断言清朝的统治者并没有简单地把自己当作汉人或满人的君主,而是在统治多民族的过程中“披上”不同的文化装扮(cultural guises),并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如此才能成为帝国的唯一中心。
第二部分“清代宫廷社会结构”由四章组成,即第二章《征服者精英与皇室精英》、第三章《家族政治》、第四章《皇家妇女》和第五章《宫廷奴仆》。
第二章的核心内容在于征服精英集团的组成、等级结构以及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作者界定的征服精英(conquest elite)最初是指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成员,而旗人与广大汉族百姓的分野正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分野。随着清朝领土的扩展,包括喀尔喀蒙古王公、藏传佛教的活佛和穆斯林的阿訇也进入了这个集团。
第三、四和五章的研究对象虽然各有不同,却都存在一个共通的核心问题——如何消除宗室、外戚、宦官专权等威胁皇权的政治不稳定因素?面对这些不同难题,清朝摸索出了多套富有针对性的策略。例如,在处理宗室问题时,清朝成功地将“汉族的官僚政治技巧(bureaucratic techniques)与非汉族的兄弟同盟(fraternal alliances)”结合在一起,既允许宗室王公参与政治,又限制他们的自主权,使其成为皇权的支柱而非竞争者。此外,清朝虽然先后涌现出孝庄、慈禧这样能够左右朝局乃至垂帘听政的皇室女性,但她们的政治影响力却是通过与清朝的宗室王公和大臣合作的形式实现的,这与汉朝太后倚靠外戚的专权形成鲜明对比。作者通过对清宫档案的发掘,认为这是由于清朝宫廷隔绝了后妃与娘家的社会关系所致,她们的衣食住行完全受到皇权的控制,成为了皇室不可分割的财产,再加上皇帝对公主婚姻的操控更将皇室与征服精英贵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扩大了皇族的基础,最终得以消弭外戚的威胁。最后,面对来自宦官等奴仆阶层的挑战,清朝则独创了内务府制度以管理宫廷的各项事务并约束奴仆阶层的日常行为。
当然,第二部分不只有以上这点内容。例如,第二、三章还涉及到清朝雍正时期的八旗制度改革、秘密建储、宗室爵位的分封、皇子教育等方面,第四章还提到公主的爵位、妆奁、婚姻礼仪等问题,而第五章还展现了包衣、奶妈、妈妈里(mamari)、哈哈珠子、工匠、艺术家等为宫廷成员提供服务群体的生活境遇。但囿于书评篇幅的限制,本文无法逐一点评到位。总的来说,本书的第二部分向读者全景展示了清朝宫廷内外的人物群像,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

寿恩公主(1831—1859年)
第三部分“清代宫廷礼仪”由三个章节组成,依次是第六章《皇权与对儒家礼仪的实践》、第七章《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在宫廷》与第八章《私人礼仪》。
作者认为礼仪是能够使政治制度合法化的重要手段。皇帝的统治不只依靠强权,还需要通过对特定仪式的实践来获得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支持。1644年后,清朝的统治者把宗教因素融合进了不同的统治权形象中,包括要求满人保持萨满教的传统,在汉人面前打扮成信奉儒家的君主,同时又利用藏传佛教获得了通知蒙古人和藏族人的合法性;即便面对唯一可能不受这种策略影响的穆斯林(异教徒无法充当宗教的保护者),皇帝也通过包容的宗教态度以及官方对清真寺修建的资金投入来取得回疆精英的支持。
在第六章中,作者主要讨论了清朝的儒家国家礼仪。其中,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礼仪中,始终存在着关于权力合法性来源的两种对立观点——“德性之治”(rule by virtue),与理所当然的父死子继式的“世袭统治”(rule by heredity);前者注重君王所拥有的品德,后者无疑更强调天命所归——清朝入主中原后,虽然同样承认“天”的作用,却开始将“德性之治”的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并为此赋予“德”以新的意义,即孝道(filial piety)。清朝皇帝通过对祖宗的“孝”来确定自身的“德”,也就意味着将“德性之治”与“世袭统治”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思想体现在清朝皇帝对于祭祀祖先帝后的热情,以及在祭祀天地等国祭场合中增加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降的祖先作为陪祭对象的开创性举措之上。而考虑到降雨或干旱被古人认为是上天对君王道德的回应,作者还借国家的祈雨仪式说明一味地遵奉“德性之治”则可能会给统治者造成的尴尬,这也使得清朝皇帝不会单纯依靠儒家的仪式,他们还会祭拜民间信仰中的龙神,并号召和尚、道士来祈雨。各类地方神祇由此被纳入国家的祭祀体系之中,朝廷在有意图地促使这些神祇的“灵”为己所用。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选择将儒家礼仪局限于明朝统治者经常祭拜的庙宇之内,虽然一些庙宇后来也在边疆地区设立,但皇帝通常也允许反向操作:藏传佛教和萨满教的庙宇也在北京和各地修建了起来,这意味着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能够超越儒家礼仪的束缚,将帝国的礼治延伸到东北和内亚地区。早自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起,清朝就确立了萨满教的国家级仪式;入关以后,清朝持续在堂子以及坤宁宫举行萨满祭礼,乾隆皇帝甚至还亲自颁布了《钦定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来规范、指导旗人的礼仪实践。关于萨满教对国家构建的意义,作者通过一些民间流传的故事文本的解读,指出萨满教的实践有助于巩固清朝对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和其他共同作为“新满洲”(ice manju)部族的统治合法性。除此以外,作者还认为藏传佛教也帮助清朝皇帝赢得了对蒙古诸部和西藏地区的统治合法性,这些宗教行为包括皇太极在盛京建立供奉玛哈嘎拉(Mahākāla)的实胜寺,以及入关后康雍乾三帝在北京、承德和五台山的大规模修建藏传佛教寺庙的活动,并主持有关《甘珠尔经》等大量佛教经典文献的编纂和翻译工程。清朝在扶植藏传佛教的同时,也对藏传佛教采取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包括用金瓶掣签制度来支配对蒙藏转世活佛的承认权。而谈及清帝本人对藏传佛教礼仪的践行,恐怕无人能与乾隆皇帝相提并论:他不仅向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学习佛教和藏语知识,还接受了后者施予的灌顶;紫禁城的雨花阁,被乾隆营造为私人佛堂;在乾隆的陵寝墙壁上,更是绘满了佛像和梵文佛经。在第七章的最后,作者还注意到乾隆时期绘制的宫廷唐卡御容画像,乾隆将自己打扮成文殊菩萨的形象以面对藏传佛教世界的僧侣,进而赢得对彼此的认可。
在本书的第八章,作者转而关注与国家祭祀、宗教保护无关的私人礼仪活动,即作为家庭的宫廷的礼仪,这也是宫廷生活所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这些私人礼仪包括不限于:皇帝在养心殿的祭祀、在宫中各处佛堂的拈香、在坤宁宫的萨满祭坛和灶神牌位前致祭;正月初一日,要前往乾清宫东侧的孔子像前叩头、在御药房的药神前叩头等等。如果将宫廷档案与《大清实录》的记载相比较,会发现这些私人礼仪是与公开礼仪在同天内交替举行的。此外,作者还通过档案总结了皇室女性参与的更具家庭祭拜特色的礼仪内容。最后,作者讨论了宫廷成员的生日、婚姻、开府、疾病、葬礼、家祭、陵制等生活周期的私人仪式。倘若以整体视角概括所有私人礼仪的特征,清朝的宫廷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集结萨满教、道教、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混合体,各式各样的文化传统的折中与综合已经在宫廷内部渐渐成为现实。

郎世宁《阿玉锡持矛荡寇图》
二
罗友枝究竟想在《最后的皇族》中讨论什么样的问题?纵观以上各章的内容,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罗友枝通过“清代宫廷物质文化”“清代宫廷社会结构”和“清代宫廷礼仪”三个方面,依次展现了清朝的统治阶层不只在吸纳汉人的制度与文化,其宫廷内部也存在大量非汉元素的事实,以此重申对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于1967年的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发表的《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一文的挑战——何炳棣认为,“清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征服王朝,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早期的满洲统治者采取了系统性的汉化政策”(the Ch’ing is without doubt the most successful dynasty of conquest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key to its success was the adoption by early Manchu rulers of a policy of systematic sinicization)——亦如她之前在《再观清朝》中所做的那样。
问题的核心其实仍然在于汉化,或者说“汉化是否是清朝成功统治的关键因素”的旧问题。在罗友枝看来,汉化史观(特别是在美国)所主导的传统研究更多关注了清朝的内地组成部分,但清朝的版图并不只是对明朝的简单继承,而清朝皇帝治下的臣民也绝非只有汉人,所以清朝不可能只凭借单一的汉文化策略来统辖这个体量庞大、内涵丰富的国家。罗友枝认为,清朝皇帝所面临的难题始终是如何统治多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最后的皇族》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以下内容全部摘录自绪论和结语):
清朝之所以成功,原因正在于它不是汉族王朝。清朝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恰恰与汉族统治王朝的政策相反。清朝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在观念上淡化自己与明朝遗民的区别,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满洲认同。当政治上有利可图时,他们就采用汉人的习俗;当无助于他们实现政治目标时,他们就拒绝这些习俗。清朝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它有能力针对帝国之内亚边疆地区的主要非汉族群体采取富有弹性的特殊文化政策。
除此以外,自《再观清代》的发表以来,所有的学术史梳理都将这篇演讲视作北美“新清史”的发端。那么,到底是什么才是“新清史”?至少在学界大众的眼中,“新清史”的一大特色似乎是走到了作为汉化史观背面的“满洲中心观”,这也是罗友枝在《再观清代》中所呼吁的:“满洲中心观对于重新评估清帝国而言极为重要(A Manchu-centered perspectiv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reassessing the Qing empire)。”
然而,如果我们将《最后的皇族》与同为主张“满洲中心观”的欧立德《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进行对比,会发现两位学者的研究取向有一些不宜被忽略的微妙差异性。欧立德的专著几乎完全倒向了满、汉二元论的思维,主张清朝长久统治的秘诀除了坚持儒家道统以外,更重要的举措是维持了满人的“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而《最后的皇族》中每个部分都在事无巨细地分别介绍清朝宫廷的多元文化体系。罗友枝虽然反对汉化论的基调,主张满人并未同化于汉人的观点,但却始终强调清朝宫廷内部绝非只有单一的满或汉的文化元素,亦如《再观清代》所言:
新研究使我们更深入地关注满洲人将不同文化背景的战士与自身的事业结合的能力……我们或许能将女真/满洲人建立联盟的能力归功于他们东北亚故乡的地理历史条件。自蒙古高原起向东延伸、北抵茂密的针叶林带、南至肥沃的辽河平原,东北的三套不同的生态系统致使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农耕民族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基于这一研究侧重点,本书对清朝性质的定义大概就是“以坚持自身满洲认同的皇帝为核心的多民族文化普世主义帝国”。
三
不可不提的是,《最后的皇族》自出版以来其实就颇具争议,许多学者都曾质疑过本书观点的准确性。
举例来说,耶鲁大学的史家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认为汉化的模式仍然不可完全抛弃,特别是在讨论到清朝在西南苗疆的统治时,汉文化反而取代了非汉的文化实践,至于本书对清朝“家族政治”的解读,更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针对本书的清朝文化普世主义的思路,包括清朝的“统治者试图通过使用其治下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词汇与他们打交道”等观点,国际著名的蒙古学家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则以朝廷在面向蒙古臣民时所使用的“恩赏”(kesig)这一政治修辞背后潜藏的中原文化元素挑战了罗友枝的观点。关于清朝通过履行藏传佛教仪式来获得蒙藏统治合法性的问题,艾宏展(Johan Elverskog)的《我们的大清》(Our Great Qing)与清华大学的沈卫荣教授的《大元史与新清史》分别从蒙古学、藏学的角度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而就本书第一章提到的清朝多都制的问题,中央民大的钟焓教授指出,在清朝统治的众多内亚民族人群的心目中,北京才是他们不可替代的唯一首都,承德无论在史料或传说中的地位都远不如北京。对于这些来自中外学界的不同声音,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一并参考。
最后,罗友枝在撰写《最后的皇族》时曾利用了大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务府档案,这对于清朝宫廷文化的爱好者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指引作用。因此,如果你对本书讨论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不妨在阅读之余亲自前往一档馆,去探寻那些隐藏在档案里的深宫奥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