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当代摄影的影像构建与……历史图像学研究

《当代摄影中的影像构建》,[美]安妮·莱顿·马索尼 、[美]马尼·欣德曼著,范筱苑、刘冰心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年5月版,248页,118.00元
安妮·莱顿·马索尼和马尼·欣德曼合著的《当代摄影中的影像构建》(The Focal Press Companion To The Constructed Image I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2019;范筱苑、刘冰心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年5月)是一部论文与访谈集。“在本书中,作者和书中提到的艺术家思考了从1990年代以来当代摄影中影像构建的发展历程。”(前言)这部去年出版的著作的选题和讨论的焦点是后九十年代,有意识地与先前的历史和评论拉开距离,可以说在西方摄影理论出版物中也是相当新和处于前沿的著作。
讲到后现代语境和“影像构建”,该书的作者其实对摄影影像的本质都持有大致相同的后现代观念,即“所有的照片都是被建构出来的”。但是这显然与大多数人对“传统”照片的认识很不相同,因此他们意识到在这项聚焦于“影像构建”的工作和论述中应该与“传统”照片区分开来。书中共分六章,它们既是独立的,也有相互联系的可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当代摄影中影像构建的方法:“构建影像,构建空间”“构建地点”“地方感:艺术家改变环境”“图式化:制作系统”“无相机摄影:摄影的保真和失真”“为相机而表演:后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和行为摄影”。在叙述框架上每章的开篇都是一篇论文,从观念、概念到创作实践和历史回顾等角度论述相关主题。然后在每章中都以图文配合的方式呈现一系列新锐的和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文字内容包括了访谈、叙述和关于作品的讨论。
该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有关当代摄影的影像观念与创作实践的对话文本,对我来说则具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被历史图像学研究作为史料运用的摄影照片很少出自当代摄影的“影像构建”的展场,照片的图像史料学看起来仍然固守在传统的照片档案之中,对于被篡改的或摆拍的历史照片的辨析仍然是在一个物质性的客观对象议题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思考当代摄影作品进入历史学研究叙事的可能性?当代摄影的影像构建与当代历史叙事的构建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当代史研究的前沿如何延伸到当代摄影中的生产媒介、影像建构和传播方式中去?这些都是我在阅读该书时特别希望能引申出来思考的问题。
为了更深入理解该书的当代影像构建观念与我一直念兹在兹的历史图像学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关系,先谈谈两个相对比较外围的思考视角。
首先,当代摄影的即时叙事的生产,在许多事件、运动的场合中往往与现实冲突有紧密联系,其性质是极为深度的介入,成为现实斗争的前沿工具。而当这些照片有朝一日被作为史料,或者说马上就被作为年度摄影载入史册的时候,这种语境以及它的明显倾向性虽然不会仅仅因此就可以抹杀照片的历史价值,但是任何有经验的历史学家和读者都会有更小心谨慎的阅读与接受态度。今年6月5日在国家地理杂志官方网站(NATIONAL GEOGRAPHIC)发表的非洲历史和摄影史专家约翰·埃德温·梅森(John Edein Mason)的文章《抗议的影像呈现:视觉语言中的隐喻和倾向》以极为清晰的现实政治感分析了当时发生在美国的这场种族冲突中的图像的作用。这是基于对美国种族问题的历史由来与现实状况认识的图像解读,当代摄影在在场所具有的说服力似乎会被认为是一种真实的记录,作为史料档案的可能性似乎无可怀疑。但是,在当下几乎所有对新闻摄影与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会意识到所谓的在场不但只能是局部的,而且也是受立场所决定的。因此,图像对于传播信息、煽动情绪的作用明显具有片面性。但是对于明智的历史学家,它的偏激和片面有时恰好是构成全面图景的一个真实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摄影作为历史史料的重要意义也就恰好在于它的极端性,从而为一幅历史全景提供非常有力度的局部。在某些图像中,真相与谎言有时并不是那么截然对立,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某种角度看过去的真相,只要不是在后期技术上对图像进行过有意图的改动。历史图像学对于篡改照片的分析面临更复杂的任务:不是被篡改的图像,而是在多种角度的局部真实之间存在冲突以及不同倾向的呈现。梅森通过分析对比美国近年来经典的黑人抗议运动的照片,提醒身处现实漩涡的读者或者或关注发生在遥远地方的事件的读者注意一个问题:当你试图通过照片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时,蕴藏于图像中的“潜台词”很可能已经为你做出“那是什么”的判断,他提醒我们警惕图像的视觉语言中的隐喻与倾向。文章中有一段话更像是写给历史研究的同行:“我们几乎会本能地寻找一种形象来定义某个特定的事件或历史时刻。例如,想想教科书和纪录片是如何反复借用Dorothea Lange(美国纪实摄影家)的《移居的母亲》来总结大萧条的。经典影像本身也存在问题,最根本的是,没有哪种单一的形象可以概括出复杂的历史现象。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贫穷的母亲们无疑憔悴而又忧心忡忡,但我们不希望我们对那段艰难岁月的理解就此结束。”(https://www.sohu.com/a/404260055_649502)可以说这正是对传统的图像证史研究提出的警惕性启发。
另外,与早期的摄影归类和分类整理的状况相比,当代摄影的归类和分类整理在观念上更为复杂,在依据上有更多的可能性,导致历史图像的研究者在当代摄影展图像检索和性质估计上产生更多困惑。当代摄影面向社会的最有效手段还是以展览图录等摄影书为主的形式,但是“当代”与“摄影”的标签容易使这些摄影书被局限在只是摄影界关注的语境中。在这方面,早期和现代摄影在图书馆系统中所经历的分类已经有过教训,尤其是在对摄影照片的分类整理中,对刊载有著名摄影家拍摄的照片的图书如何分类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些图书因为有著名摄影家的拍摄的照片而归入“摄影”类,有可能会割裂了这些照片图像本来所属的历史或地理、社会等性质。道格拉斯·克里姆特(Douglas Crimpt)对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提出的批评就是一个实际例子: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在成立了摄影部之后,把过去按历史、地理和科学等不同主题来编目分类、包含有摄影家拍摄照片的图书全部按单一的“摄影”类别重新编目分类。克里姆特认为这种新的分类使历史、地理、社会、都市贫民等主题的图书变为艺术和摄影类,严重影响了读者对它们的准确理解和使用。(参见特里·巴雷特《看照片看什么:摄影批评方法》,何积惠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183页)
回到这部《当代摄影中的影像构建》。所谓的“影像构建”,从其观念上说无疑是对历史图像学研究中把摄影照片作为图像史料的传统研究方法提出某种挑战。玛德琳·耶鲁·普雷斯顿(Madeline Yale Preston)在该书第一章中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摄影经历了一场对其意义的全面重新评估:“当下存在大量关于摄影的论述,它们质疑摄影先前对原创性的主张及其作为证据媒介的地位,对观念艺术批评中首次提出的‘摄影对象的非物质化’概念进行了扩展和修订。……互联网和数字文化的迅速崛起,加之模拟影像制作的过时,引发了人们关于摄影物质性以及如何在其流通中构建意义的新思维模式。这一不断扩大的关键领域反映了摄影本身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复杂、分层、有时甚至是经常违反特定本体论分类的混乱的存在。”(19页)从我们至今已经完全接受的当代摄影的生产形态来说,互联网和数字文化中呈现的图像经历了挪用、复制、融入、分享、演绎的后摄影生产策略,所谓的“构建”就如普雷斯顿所说的,“已经被用来描述各种各样创建和改变影像的方法”。(20页)最早对“构建影像”这个概念表示关注的摄影评论家是A.D.科尔曼(A.D.Coleman),他在1976年的《导演模式》一文中描述了当代摄影创作的“摄影小说”或“伪造文件”行为,指出它们与摄影的纪实传统截然不同。历史学家玛丽·华纳·马里恩(Mary Warner Marian)在此基础上的表述是“以导演模式工作的摄影师构思和编造主题,而忽略了摄影从世界视野中寻找意义的传统任务”。(20页)关于什么是当代摄影的影像构建,上述这些论述已经讲得比较清楚。原创与复制的界限被打破,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被冲破,影像不仅仅是对世界的客观复制,而且也可以是在主观引领下的创造性产物。这样的影像还能作为“图像证史”的证据吗?——当然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作为当代摄影的影像构建史的证据。
无论如何,在当代摄影的影像构建中能够产生某种意义是毫无疑问的,普雷斯顿认为当代摄影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物质性的概念,并同样关注如何在图像的内容中产生意义”。(21页)在这些“意义”中,不会缺失与“历史”相关的进程、事件、人物、观念等维度,问题是历史学家应该学会从“图像证史”中拓展出“影像构建”证史的有效方法。普雷斯顿在第一章对于莱斯利·休伊特(leslie Hewitt)、亚当·布卢姆伯格(Adam Broomberg)和奥利弗·沙纳兰(Oliver Chanarin)的作品的分析论述以“重构历史”为议题,提出思考集体记忆和历史观念是如何在摄影装置中实现的,这种论述视角给我们带来启发。休伊特的影像装置作品《明确说明》(Make It Plain,2006)是对美国民权运动的表现形式的有意义的探索,亚当·布卢姆伯格和奥利弗·沙纳兰的合作关注摄影新闻如何纪录冲突、政治和历史事件,探讨了媒体的透明度、档案纪录的主题以及观众在解释和传播摄影意义中的角色,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历史与摄影档案之间的关系。(41页)这些影像构建的创作方法和审美意识使摄影图像重新被处理为图像装置,甚至表现为对原有的图像档案的介入,“他们的项目对历史与文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评论,将摄影的纪实功能打造得更具诗意和艺术性。……如果我们将现存于公共档案中的照片视为是在扮演人类学的角色,那么布卢姆伯格和沙纳兰为‘科学’理解文化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创作性策略。他强调了近期新闻摄影实践的转变,例如公民新闻、业余摄影、新科技形式以及不同的视角叙述方法”。(42页)这些论述虽然在很多地方还语焉未详,而中译的文字叙述有时也让我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的是:当代摄影的构建影像实践打破了传统的档案照片的封闭性和固化性,在影像的重新构建中有可能激发出原先难以想象的视觉经验,从而以一种陌生化的眼光重新观看和凝视图像。当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里为止,所谈论的其实还是当代影像建构的方法论和视觉经验激发我们从更为开放的视角和更有想象力的层面上重新认识作为图像史料的照片,但是这些当代摄影的影像构建作品本身是否能够和如何做到作为证史的图像史料,仍然是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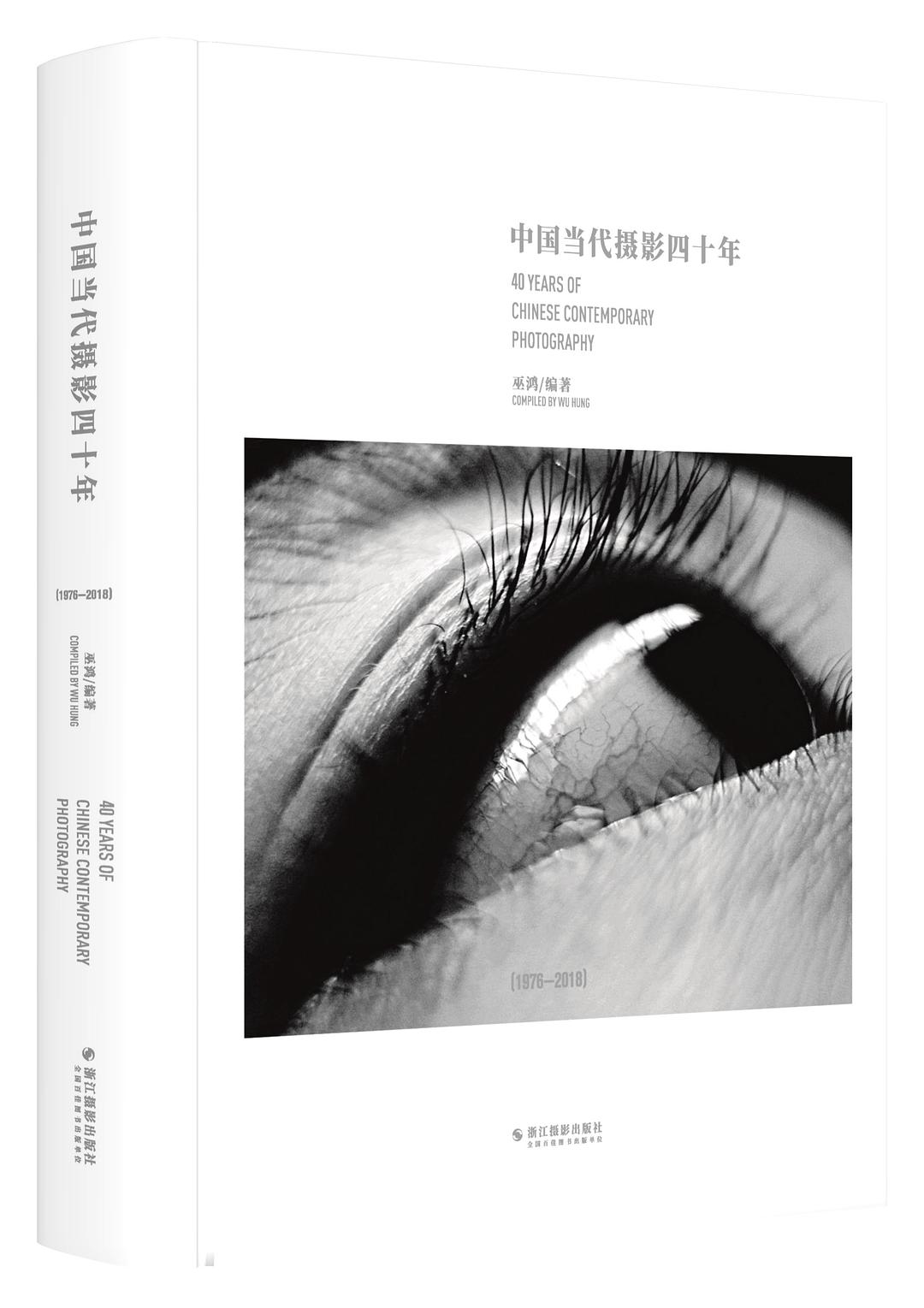
《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美] 巫鸿著,浙江摄影出版社,2020年1月版,376页,398.00元
另一部关于中国当代摄影的历史回顾的著作可以让我们在中国语境中延伸上述思考。艺术史家和策展人巫鸿编著的《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浙江摄影出版社,2020年1月)是2017年三影堂同名展览的摄影图册,该展览是对中国当代摄影的一次整理与回顾,图册收录近两百位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近六百幅作品及艺术家个人简介,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当代摄影历史。策展人巫鸿撰写的“前言: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虽然篇幅不长,但是作者以艺术史家的目光梳理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为我们从中国当代摄影的视野中思考历史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份清晰、简要的学术文本。其中所谈到的历史事件、社会改革潮流、图像文本、公众记忆、团体机构现象等议题既是一种历史性描述,同时在对中国当代摄影的历史回顾中触及到一些连结当代史研究与当代摄影的重要节点。
巫鸿首先谈到了“当代摄影”的概念定义,他认为“‘当代摄影’是一个国际通用但不具备共同定义的概念。有的西方美术馆以历史事件(如二战结束)作为‘当代’的时间底线以建立收藏和策划展览,有些研究者则以摄影技术和摄影观念的发展为基础思考这门艺术的当代性。所有这些成文和不成文的定义都基于特定地区的摄影实践、学术研究和展览机构的历史经验和现状。”(第1页)在这里并没有把当代学术语境中复杂的“当代性”概念作为界定和阐释“当代摄影”定义的语义基础,而是非常直接地为该展览的“当代摄影”概念找到合理性依据——“基于特定地区的摄影实践、学术研究和展览机构的历史经验和现状”。因此,展览以1976年中国摄影的标志性事件和民间摄影团体与民间展览的出现作为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而无需顾虑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摄影事件的核心是纪实照片和普通人摄影行为的自发性和业余性。“被称为‘四五运动摄影’的历史图像保存了人们对这个事件的记忆,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历史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第2页)在这里展开的历史与图像研究仍然属于传统性质的,很难说已经接触到 “当代摄影的图像建构”的当代性问题。然后是从1976年至1979年的民间摄影社团和非官方摄影展览的崛起,前者的民间社团性质反映出“文革”刚结束的时候社会力量的自发复苏,后者表现出在摄影作品的生产与传播中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这些事件作为中国当代摄影的起点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代摄影在中国的诞生与全能政治对社会管控的变化和艺术从政治禁锢中获得最初步的解放紧密相关,当这些摄影者在组织化和唯政治性的摄影生产之外获得行动空间和能力的时候,他们镜头下的日常生活图景和突破政治禁锢的审美意图构成新的影像视觉经验,这一开端的设置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当代摄影在历史叙事中的重要位置。
在接下来的“摄影新潮(1980-1989年)”阶段中与历史图像学研究密切相关的是纪实摄影。“
经过这个学习和吸收西方摄影风格的‘多样化时期’,纪实摄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成为新潮运动的主流。与美国三十年代的纪实摄影运动类似,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作品也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它们的内容、形式和手法服务于摄影家们为之献身的社会改革潮流。……大约同时,由于中国城市的爆破性发展,越来越多的纪实摄影家将镜头聚焦于剧烈变化中的都市景观。拆迁场地的废墟、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涌入、变动中的城市人口和都市生活等等,都成为纪实摄影的常见题材。”(第3页)值得思考的是,与美国三十年代纪实摄影作品早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图像史料相比,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纪实摄影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作用仍有待重视和挖掘。
在这里或许可以插入一个重要议题:当代摄影在某些方面与大众史学(或公共史学)的内在关系。所谓大众史学的关键起因就现代生活与文化的发展使人类对过去历史的认知和思考普及化,与历史记忆的建构相关的许多过程、体验和传播现象再也不是历史学家能够垄断的事情。早在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 ,1873-1945)就提出“人人都是历史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的观念。当时贝克尔还只是更多从个人生活体验与社会共识的建立等朴素的经验层面上论述和强调了这个问题。随着历史知识越来越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对象,学院之外的非专业历史叙事的传播迅速发展,七十年代以后在美国出现“大众史学”(Public History)的史学分支概念和专门的杂志,关于大众史学的研究渐受学界重视。大众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就是随着视觉图像的传播与普及,使历史知识的可视化成为公共文化的典型现象,不仅是以历史读物的图文并茂吸引着大众,更重要的是在大众的历史知识与想象中,视觉图像往往比文献记载更为普及,成为大众的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在今天没有接受过任何历史学教育的普通大众中间,他们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建构和个人记忆往往不是来自文献阅读,而是来自大众文化中的视觉图像,这就是所谓读图时代中的历史教育。在画报、绘本、广告、影视、商标、礼品等等载体上出现的世界古迹、名胜及名人图像成为潜移默化的历史教科书。从历史图像学研究来看,这种现象是“历史的图像叙事”的重要研究论题,包含有图像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等多种因素。
接着下来,从最宽泛的当代摄影视野来看,当代科技、媒介手段不但给与当代摄影家带来摄影观念、图像建构等方面的可能性与空间,同时也给大众带来图像生产与传播的可能性与空间。可以说,今天网络与手机时带来图像制作、传播的大众化彻底改变了图像生产与传播的垄断性,不仅在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图像诞生,而且在无数的突发事件中往往都是由普通人拍摄的图像成为历史现场的第一见证。这是大众史学的突出现象,纪录突发新闻与历史记载融为一体,例如美国“911”事件现场民众拍摄的照片。因此,当代摄影语境中的图像建构其实不仅仅是专业的,同时也是属于大众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摄影与大众史学和历史图像学之间可以建立起真实的联系,历史图像学的开放性、现实关怀以及面向未来愿景的学科目标使它必须认真研究当代摄影中的大众图像生产与传播,也就是说历史图像学的大众面向、当代面向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是交织在一起的。
巫鸿在“前言”中继续谈到在1990-2006年的实验摄影,摄影与前卫艺术的关系极为紧密,这是与西方当代摄影中的影像建构在观念上和实践上都紧密接轨的阶段。从2007年至今,在该展览中被称为“实验性摄影机构的发展”的阶段,突出性标志是当代摄影的大型展事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摄影节以及大量的个展和群展中的实验摄影的迅猛发展,相关图像文本的出版、研究与批评的风气、商业与展示机构的运作等景观表明中国当代摄影“开始从实验摄影家及批评家的小圈子中走出来,参与到全社会的文化生活和艺术教育之中。与这个变化同步,新的摄影展示场地、商业渠道、研究中心和批评研究陆续出现,表明中国当代摄影进入了一个新的、机构化的阶段。”(第5页)这既是摄影史的叙事,实质上也是中国当代史叙事中的一个侧面,从而应该思考的是在当代史研究中不应缺失中国当代摄影的视觉经验,并且应该重视这些另类的视觉经验所带来的“图像证史”的新的或潜在的空间。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