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朱玉|“无数的见识使我成为神”——纪念济慈逝世两百周年

济慈像,约瑟夫·塞文绘,1819,国家肖像馆
约翰·济慈(1795.10.31-1821.2.23),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享年仅二十六岁。他在二十岁出头感知诗歌的天职,遂弃医从文,可惜他的诗歌生涯还不到五年,便因肺结核离世。包括莎士比亚和但丁在内的巨笔在济慈的年纪尚未写出相当水平的作品。哈罗德·布鲁姆教授认为,在六位主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济慈拥有“最健康的想象”。济慈的诗歌对丁尼生、唯美派、史蒂文斯和希尼等后世诗人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在书信中表达的诗歌思想如“消极能力”“诗人无自我”等依然为我们敲响“钟鸣般的声音”。
1820年10月31日,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以及十天的船内隔离之后,济慈和同伴约瑟夫·塞文终于在那不勒斯湾登岸。这一天,济慈刚满二十五岁。来意大利是为了养病,这里有温润的气候和清新的海风,“如果你的眼睛感到烦恼疲惫,/ 就让它们尽飨大海的寥阔”(《在海上》)。对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意大利是精神的故乡,与希腊并称为古典传统的发端,也是文艺复兴的源头,在十九世纪成为欧洲壮游(the Grand Tour)的必经之地。拜伦和雪莱在此度过许多时光。拜伦还在《少侠哈罗尔德游记》中称意大利为“全世界的花园,/ 一切艺术的家乡……连你的野草都美好,/ 你的荒芜富足,/ 你的遗迹荣耀,你的废墟 / 无瑕”(《游记》第四卷第二十六节,为凝练及节奏的气势计,第四至第五行没有完整译出)。

《少侠哈罗尔德游记——意大利》,透纳绘,1827,泰特美术馆
“在广袤世界的岸上”
在那不勒斯附近,济慈看到一幅描绘九位缪斯女神和阿波罗的壁画。已经11月了,路边还有许多盛开的花:桃金娘,月桂,仙客来,俨然潘神的田园。看到这个时节还有玫瑰,济慈颇为惊讶,便凑上前去,却发现已然没有芳香。他感慨道:“失去了芬芳的玫瑰是什么?”在西塞罗殒命之地,济慈想起自己与古典文学的初遇。就连他顺利通过医学资格考试的原因,也被同学归为扎实的古典语文基础(考试内容多为拉丁文),但他最终弃医从文,献身于诗歌的天职。

左图标记着济慈出生的客栈和马厩,伦敦摩尔菲尔德街24号;右图为克拉克的学校,恩菲尔德。1803-1810年,济慈在此上学。
1810年,济慈十五岁,在父亲坠马离世六年后,他的母亲因肺结核去世。作为家中的长子,少年济慈已经感到对弟弟妹妹的重任。但要减轻生存这一“神秘的重压”,他还需要文学艺术的滋养。他老师的孩子、年长他八岁的查尔斯·考登·克拉克建议这个躲在讲台下、不要别人同情的敏感少年去翻译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以便分散注意力,走出悲伤。这部讲述征战、航海与流放的史诗为他心中带来光亮,引领他日后进入更广阔的文学世界。他领略了史诗这一崇高的体裁,视之为诗人的至高成就,并为将来的创作立下宏伟目标。诗中那海上的风暴,特洛伊的硝烟,狄多的深情,埃涅阿斯的冥界之行,似也隐约预示着他的一生。
除了维吉尔,荷马也是济慈早年诗歌生涯的向导。1816年10月25日星期五,晚上,克拉克为了庆祝李·亨特转借给他一本查普曼的荷马史诗,举行了一次“诗歌论坛”。他们一边畅饮,一边朗诵诗中名篇,聆听查普曼铿锵有力的联韵。周六一大早,济慈刚从华纳街回到萨瑟克,就写下了一首十四行诗:
我踏遍许多黄金灿烂的王国,
也博览无数美丽迷人的疆域,
曾置身于西部的无穷岛屿,
那里的诗人们效忠于阿波罗。
我常听说,有一片天地寥阔,
是那蹙额的荷马的领地;
但我无法领会人们的旨意,
直到我听见查普曼铿锵的诗歌。
于是我仿佛一个观察者将重天仰望,
一颗崭新的行星游入他的视线,
或如壮硕的科特兹,当他以好奇的目光,
凝望太平洋,当他的手下全然
彼此张望,玄思狂想——
而他沉默,在达连的山峰之巅。
(《初读查普曼之荷马》)
“仰望”是济慈常见的姿势。在诗歌的国度里,他始终保持谦卑的心态。尽管他会为发现“新行星”而欣喜,但他知道,那有待发现的世界如天宇和海洋一样浩瀚无垠。
大约在1817年3月2日,济慈与海顿、雷诺兹一起去大英博物馆参观。他们几乎穿过整个博物馆才来到临时搭建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像展厅。拜伦强烈反对英国人掠夺雅典万神殿的瑰宝。在《游记》中,他曾斥责埃尔金勋爵和英国政府的强盗行为,“谁若眼见英国人的手掌 / 损毁你的墙垣、拆迁你腐朽的圣殿 /而不哭泣,谁的眼睛就迟钝无比”。当海顿与理查德·佩恩·奈特争论着这些雕像究竟是罗马风格还是希腊渊源时,济慈早已淹没在巨大的雕像群落之中:宁静的马首,残缺的河神,与人马作战的拉庇泰人……大雕塑家菲迪亚斯的珍品令他震撼:
我的灵魂过于孱弱——死亡
沉重地压在我身上,如无意的睡眠,
而每一座想象的绝壁和山巅
都以鬼斧天工诉说着我终将死去,
如病鹰仰望着天宇。
(《观埃尔金大理石雕像有感》)
“病鹰仰望”一句表达着浪漫主义诗人的坦诚和济慈特有的谦卑。虽难以企及古人高超的艺术境界,但他能透过这些残缺的雕塑,以心灵的目光感见亘古之前那“巨浪滔天的海洋——太阳——宏大之影像”。

《人们参观埃尔金大理石雕像的盛况》,阿奇博尔德·阿彻绘,1819,大英博物馆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彼得拉克出现在1817年发表的《睡眠与诗歌》中。这是济慈早期作品中较为成熟的一首,也是他唯一一首完整的长诗,共四百多行。和华兹华斯的《丁登寺》一样,这首诗也追溯了心灵成长和想象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诗歌以十个追问开篇——问句是济慈常用的句式,体现一位年轻诗人的好奇与求索,一颗敞向未知的开放心灵:
什么比夏日的轻风更加和煦?
什么比漂亮的蜜蜂更加治愈?
它在盛放的花朵中停歇一瞬,
快乐地嗡鸣,从树荫到树荫?
……
除了你,睡眠,还有什么?
在祥和的田园背景下,诗人继续追问,还有什么比睡眠更加高超?比天鹅的翅膀、比鸽子和雄鹰更加瑰丽?“我”用什么来比拟它?——“诗歌!”在两次重复“我尚未成为你寥阔天宇的光荣子民”后,诗人表明,“我年轻的灵魂愿为阿波罗献上新鲜的祭品”——“给我十年时间,我将侵浸于/ 诗歌,以便按照灵魂的 / 旨意大有作为”,穿过许多领土。首先,他将穿过“花神与潘神的国度”——天真的境界。然而,诗人自问:
我能与这些欢乐作别吗?
能。我必须穿越它们企及更崇高的生命,
在那里,我将发现人心的苦痛
与挣扎……
“转向人心”使济慈与华兹华斯关联起来,拜伦式的英雄则更喜欢自然而厌弃人类。当诗人作别“冰冷的田园”,一切美妙的幻象荡然无存:
一切幻象都逃遁了——马车遁于
天堂之光,取而代之的,
一种真实事物之感愈加强烈,
如泥泞的小溪,将承载
我的灵魂至于空无。
济慈的诗中经常出现“逃遁”一词,但遁去的是幻象,留下的是现实。诗人重返而非逃离现实。与此同时,当他面对泥泞不堪的现实,他依然铭记那些曾经耀目的神圣幻象,而这些将承载他的灵魂臻于丰盈。唯美如济慈,“泥泞”也是他诗中频现的词语,似每一场午夜梦回而惊觉的真相——“美已然醒了!/ 你为何还不醒来?”在这部长诗中,济慈还谈到诗歌的崇高目的,认为尽管诗歌单纯而无功利性,但诗歌恰如友人,能“安抚忧绪,提升灵思”。
作于1817-1818年间的《恩底弥翁》讲述作为牧人、诗人与恋人的恩底弥翁追求月亮女神的故事,呈现了浪漫主义的求索。济慈本人认为这部作品只是“热切的尝试”,远非成熟。诗中求索的过程体现为从美到爱(唯有爱能消除自私),再与实质结交,最后抵达诗歌的无上境界。当恩底弥翁最终走向山谷,发现身旁的凡人少女就是月亮女神时,他向上的求索与降入人间的过程并行:
如今我已尽尝她甜美的灵魂,
其他一切深度都变得肤浅:实质,
一度体现精神,此刻却如泥泞的沉渣,
只为滋养我泥土中的根须,
让我的枝条举起金色的果实,
融入天堂之华。
从果实到花朵的逆向过程,连同泥泞与泥土等意象,暗示着求索的重心在于此世。后来的《圣艾格尼斯节前夜》和《拉米娅》两首叙事诗同样延续着济慈在《恩底弥翁》中对理想与现实、真寓于幻以及诗歌即“烈度”(intensity)或激情等问题的思索。济慈重视灵魂在俗界的旅程,认为人间乃“铸造灵魂的山谷”。1819年4月21日,济慈在写给弟弟乔治的信中写道:
假设一朵玫瑰有感觉,它在一个美丽的清晨盛开,怡然自得,然后冷风袭来,烈日当空——它无处可逃,无法消灭它的烦恼——这些和它自己一样,都是世界固有的——人也不会更加幸福,俗界的元素同样将捕噬他的心。
那些迷途而迷信的人们管这个世界叫“泪谷”,在上帝某种随意的介入下,我们得救而升天。多么狭隘而僵化的想法!如果你愿意,就把这个世界称为“铸造灵魂的山谷”吧。然后你就会发现世界的用处……我说“铸造灵魂”——灵魂有别于心智。或许,心智或神性的火花不计其数——但它们不是灵魂,直至其获得自己的身份,直至每一个成为个体。……灵魂如何铸成?……除了通过此世的媒介,还有什么途径?……
难道你不觉得一个充满痛苦与烦恼的世界是必要的吗,它能够培养心智、将之铸成灵魂?
当他从那不勒斯出发前往罗马,山谷中的旖旎风光,失去了芬芳的玫瑰,摇摇欲坠的果实,贫困潦倒的人们,是否具现着从浮华田园到滚滚红尘的“沉落”?是否唤起他早年的感悟?
“从圣殿到圣殿,从拱顶到拱顶,/ 穿过钻石铺筑的光辉长廊”
1820年11月14日左右,济慈与塞文在萨提尔雕像的注视下,从拉特朗城门进入永恒之城罗马。诗人觉得终于回到家了。他们往市中心走去,穿过狭窄的圣若望路,途经古代圆形角斗场,残破的拱廊在阳光下显得愈发沧桑。无论那环廊里曾上演怎样惨烈血腥的格斗或怎样勇武慷慨的胜利,此刻都了无痕迹。对街的叫卖声、草地上的嬉闹又为断壁残垣注入生机。

《角斗场》,乔万尼·保罗·帕尼尼绘,1747,沃特斯美术馆
浪漫主义诗人对废墟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对他们来说,残缺、碎片、废墟构成人生的核心。生命本身就不完美。过程远胜于结果,求索的行为本身大于求索的目标,比如雪莱永远攀登那永远攀升的高峰,阿拉斯特梦中的追寻,老舟子和哈罗尔德的漂泊,施莱格尔所说的“追求无限”,施莱尔马赫那“永远无法满足的渴求”。在诗歌形式上,浪漫诗歌中有许多“未完成”,如柯尔律治的《忽必烈汗》,雪莱的《生命的胜利》以及济慈的《海佩里翁》系列,开启了十九世纪初以来相当规模的“片断”诗。或许,济慈也从那些残损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像中获得启示。海顿在日记中写道:
上周一,一千零二位访客参观了埃尔金大理石雕像!大英博物馆成立以来访客最多的一次……我们听到两个相貌平平的体面人互相说道,“它们是多么残缺不全啊,是不是?”“是啊,”另一位说,“但是多么像生活本身!”
残缺即人生。1818-1819年间,济慈创作了两部雕塑风格的史诗《海佩里翁》与《海佩里翁的垮台》。这是济慈继《恩底弥翁》之后的又一次史诗尝试,但却比上一次困难得多,这与他同期的大量阅读和关于“诗性人格”的思考不无关联。两部作品都是片断,前者体现弥尔顿传统,后者则似但丁的《炼狱篇》。根据赫西俄德的《神谱》记载,海佩里翁是十二位泰坦旧神的一员,是天(父)地(母)之子。济慈这两部史诗大致讲述泰坦诸神与奥林匹亚诸神新旧交替之际的身份危机。《海佩里翁》的笔触冷静,没有个人介入,没有道德说教。整体基调不仅折射出1818年滑铁卢之战以后英国的精神状态,更隐含诸多自传色彩,比如济慈对恶疾的不祥预感,自身家世的败落,以及他作为医学出身的诗人的诞生,甚至那些静谧的景物描写也让人想起济慈童年的生活环境。《海佩里翁的垮台》则延续着《睡眠与诗歌》中关于诗人天职的思索。
先来看《海佩里翁》。诗歌始于“悲伤的山谷”。失去天国、坠入尘世的泰坦诸神仿佛失去了“真我”,既不解自己的命运,也怀疑自己的身份:
我消失了,
离开了我自己的胸膛:离开了
我强大的身份,我真实的自己,
处在王位与我在此静坐的
这抔尘土之间
然而,这位绝望的天神依然希冀东山再起,他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反问道:
难道我不能创造吗?
难道我不能赋形?难道我不能塑造出
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宇宙
前两卷的结构和内容让人想起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堕落天使,神格的丧失,并推进着诸神人性化(亦即终有一死)的过程。第三卷残篇则讲述海佩里翁的替代者、新神阿波罗(医学与诗歌之神)的诞生和自我实现:
无数的见识使我成为神。
名声,功绩,暗淡的传说,灾难,叛乱,
王权,君主之声,痛苦,
创造与毁灭,顷刻间一并
涌入我空荡的脑海,
使我成为神,仿佛我畅饮了美酒
或无与伦比的琼浆,
变得不朽。
然后,“犹如在死神门口的挣扎”,或更像一个人“离开那苍白不朽的死亡”,阿波罗“伴着剧烈的痉挛死入生命”。第三卷也在阿波罗的自我认同中戛然而止,仿佛济慈不满于这样的结局,遂以“未完成”的形式制衡着阿波罗的“完满”。尽管这一历程多少也映照着济慈自身“诗人的诞生”过程,但他努力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种超然无我的境界。
在《海佩里翁》创作之初,济慈一直在思考诗性人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一次聚会,济慈终于有机会得遇几位“真正的”文豪。然而,激动之余,他却发现这些所谓的名流都如出一辙:自恋,造作,故作风雅,谈论时髦八卦如数家珍。济慈深受触动,开始反思“一位在文学上有所造诣的人,应该具备什么品质”:
我指的是消极能力,即一个人能够安于种种不确、神秘、怀疑,而不急于求索事实真相和道理的能力。(济慈致乔治和汤姆·济慈,1817年12月21、27日;据《济慈书信集》编注,27日这天存疑)
“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这一词组本身构成悖论:“消极”隐含某种被动性,“能力”则涉及主动性,两者的结合造就了一种特殊的能力。济慈认为,要想在文学领域有所造诣,就需要具备这种“消极能力”。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抛却自己的人格身份,放下对世界的看法,摆脱对自我和事物的执着与成见,我们才有望进入另一重未知的境界,诗歌中的强烈时刻才能诞生。济慈认为,莎士比亚就是这种能力的典型代表。
事实上,在提出“消极能力”之前,济慈在大约一个月前的信里还提到“恭顺能力”(capability of submission):
我必须说起一件近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事,它增强了我的谦卑之心和恭顺能力,那就是——天才之人就像某些超凡的化学品那样伟大,能够在中等智力的大众身上发挥作用——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自我,没有固定不变的个性。(济慈致本杰明·贝利,1817年11月22日)
“消极能力”可以看作对“恭顺能力”的发展。两者都强调自我的谦卑、顺服乃至消解,以便更好地表达对他者和未知世界的共情。济慈传记的作者W. J. 贝特曾这样解释“消极能力”:
在我们充满不测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种体系或一个公式能够解释一切;甚至,用培根的话来说,语言也至多是“思想的赌注”。我们所需要的是一颗善于想象并且开放的心灵,以及对复杂多元现实的高度包容性。然而,这涉及一种自我消解。(W. Jackson Bate, John Kea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63, p.249;另可参考Bate的Negative Capability: The Intuitive Approach in Keats, Contra Mundum Press,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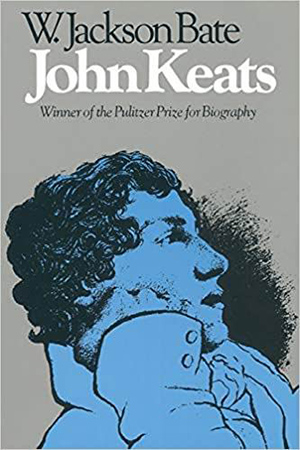
W. Jackson Bate, John Kea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消极能力”的“消极”暗示着一种积极的“自我消解”,这是实现共情、自我超越的前提。大约一年后,济慈在信中提到“诗性人格”,也是对“消极能力”思想的进一步阐释:
至于诗性人格本身……它并非它自己——它没有自我——它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它毫无个性……在所有生灵中,诗人最无诗意,因为他没有自己的身份——他始终在塑造着——或填充入其他某个身体——日、月、大海、男人、女人,这些有冲动的生物富有诗意,因为他们拥有不变的属性——诗人没有,没有自我——他必然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生物中最无诗意的一个。(济慈致理查德·伍德豪斯,1818年10月27日)
济慈关于“消极能力”和“诗人无自我”的思想与海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论人类行为的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Actions: the Natural Disinterestedness of the Human Mind)中提出的“人类心灵之天然无私无我”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十八世纪的“同情性想象”传统密不可分。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认为,海兹利特所说的“disinterestedness”并不排斥所有的私利或功利,而是敞向未知的多元(Hazlitt:The Mind of a Critic,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0)。济慈的思想主要在这个意义上与之发生交集,并将之运用到创作层面。“诗人无自我”的思想在后世一些诗人心中引起共鸣。比如希尼在谈到创作经验时指出,“抒情性写作的一个简单要求——甚至定义——就是自我遗忘”,有意识的写作让位于直觉的释放——“每一首真正的诗歌都是这样诞生的,在发现词语的欢乐中,自我意识让位于自我遗忘。” 越是泯去自我,越能激发诗性的能量。
《海佩里翁的垮台》重返济慈关于诗歌天职的思考,相信受难是炼就诗性人格的必要条件。在这部同样具有自传性质的诗作中,诗人-梦者在死神的门口徘徊,渴望拾级而升,企及诗人的至高境界:
如果你不能登上
这些台阶,那就死在你脚下的大理石上吧。
你的凡胎,那平凡尘土的近亲,
将因为营养不良而枯竭——你的尸骨
不出几年就会销殒,匿迹,
最敏锐的目光也找不到你的半点踪迹
隔着白色的纱幔,女神莫妮塔警告诗人,在树叶烧完之前,你若不能登上这“不朽的阶梯”,没有谁的手掌能翻转你生命的沙漏。在这威胁恐慌之下,“我”以迟缓、沉重而致命的步履竭力登上最底下的台阶,刹那间,生命注入冰冷的脚趾。面纱下的女神再度给出训诫:
你难道不是那梦者的一族吗?
诗人与梦者截然不同,
……
前者为尘世倾洒芳香的油膏,
后者只将世界搅扰。
“不朽的阶梯”或许既追溯着济慈年少时经常光顾的“缪斯圣殿”书店——那里宽大的阶梯引领他走向文学的殿堂;同时似也预告着济慈人生最后的住所西班牙广场(the Spanish steps)26号窗外那通往三一教堂的一百三十五级台阶。这些有形与无形的阶梯勾勒出诗人一生的攀登与求索。

版画《“缪斯圣殿”书店》,伦敦,芬斯伯里广场,1809,大英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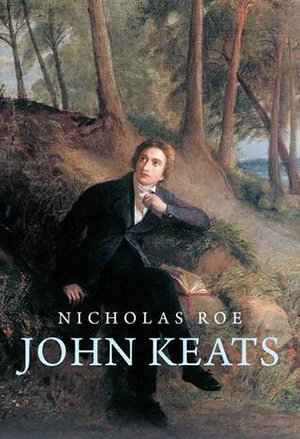
Nicholas Roe, John Keats: A New Lif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本文从这部传记中受益良多。
“成群的燕子在天空中呢喃”
西班牙广场26号曾是一幢玫瑰色的房子,位于一百三十五级台阶的右侧。济慈在罗马的医生詹姆斯·克拉克(1826年回到英国后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御医)为他选择了这处便于休养的住所。阶梯前方是贝尔尼尼设计的船形喷泉,从济慈的房间,可以听到持续的水声。天花板上雕刻着繁复的玫瑰图案,济慈却更喜朴素的英伦花朵。他感到“真实的人生已经逝去”,正过着“死后的生活”,或者,苟延残喘于生死之间。1821年1月10日,塞文将济慈从床上移到客厅,帮他换上干净的衣服。济慈已经虚弱得无法自己行走了。他们促膝而谈,塞文觉得济慈“镇定、平静”下来了,认为他“已经离去”,以“自我的缺席”而存在着。

雪中的西班牙广场26号

贝尔尼尼喷泉
1819年的六首伟大颂歌是济慈最后的作品,其中不乏告别意味。颂歌这种体裁源于希腊,后演绎为品达体和贺拉斯体,乃重要的古典诗歌形式,通常描写庄重的主题,结构复杂而恢宏。浪漫主义诗人大多写过重要的颂歌作品,比如华兹华斯的《永生颂》、柯尔律治的《沮丧颂》和雪莱的《西风颂》。
《夜莺颂》的美酒里有“温暖的南方”。这首黑暗色调的颂歌以“我心痛”三个重音开篇,与夜莺的快乐形成对比;复以四处“离开”(away)和三番“别了”(adieu)表达了诗人欲借助诗歌的隐形翅膀(当然也借助“鸦片酊”“毒药”和“酒”)随不朽的夜莺一起离开痛苦尘世的愿望。“我看不清脚边是什么花朵”以及具体的花卉描述——白色的山楂花,野蔷薇,紫罗兰——既再现着济慈诗中常见的花语,也遥指他后来墓旁朴素的芳华。诗人在黑暗中倾听,“几乎爱上了安适的死亡”,感到“若能在午夜无痛地死去”无异于一种“富足”——这里似有一语成谶之嫌:
我在黑暗中倾听;多少次,
我几乎爱上了安适的死亡,
以许多沉思音韵轻唤他的名,
将我平静的气息散播空中;
如今,若能在午夜无痛地死去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似一种富足,
趁你此时正在如此欣喜若狂中
向外倾泻你的灵魂!
你的歌唱不息,而我有耳无益——
面对你崇高的安魂曲,我化为泥尘。
然而,当他穿过“黑暗的走廊”,他逐渐意识到,夜莺虽不朽,自己却终将化为泥尘,夜莺的欢歌遂成为安魂曲。绝望中,诗人从田园回到“只要想起就充满悲愁的世界”,从夜莺重返孤独的自己,恍然有所悟:“别了!这遐思奇想骗不了人”。音乐远去,诗歌在问句中结束:
这是幻象,还是醒来的梦寐?
音乐遁去了:——我醒着,还是在酣眠?
《希腊古瓮颂》的“瓮”多指存放骨灰的罐子,使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与死亡发生了关联。诗人描绘了古瓮上凝止的画面和无声的旋律——永不落叶的树木,歌唱不休的少年,永未企及的亲吻,永远喘息永远鲜活的爱情——呈现了一种有始无终的“进行时”和超越时间的“未完成”,具有一种捉弄人的(“tease”)表面的永恒,实则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在轻歌曼舞的爱情画面之外,另一幅“献祭”场景则以寂静的街巷和不归的灵魂使画风变得凄凉,最终引出“冰冷的田园”之感悟。最后两句广为人知: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便是
你们在世上所知且需知的一切。
世人曾为这两句的意义争论不休,但这似乎有违诗人的初衷,因为我们只要“知道”就足够了。开放性恰是济慈诗歌的特征。当然,我们也会想起济慈关于想象的说法:“凡想象认为美的,必然真实。想象可喻为亚当之梦,梦中创造了夏娃。亚当醒来发现这是真的,很可能就因为她是美的。” (济慈致本杰明·贝利,1817年11月22日)

济慈-雪莱纪念馆
济慈写下的最后一首颂歌是《秋颂》,作于一次秋日漫步之后:
这个季节多美啊——天空多么晴朗。一种温和的凛冽。真的,不开玩笑,纯净的天气——月神的天宇——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喜欢收割后的田野——胜过春天那清寒的绿意。不知为何,那收割后的田原看起来是温暖的——就像有些画给人暖意……(济慈致雷诺兹,1819年9月22日)
一年后的早秋,他从伦敦南下,于晚秋时抵达罗马。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秋天大多在海上度过。他有没有错过那“重重薄雾和果实圆熟”?《秋颂》是一首如金秋一样丰美的诗。诗的前两节以浓重的色彩描绘出丰收时节的斑斓秋色:累累硕果,姗姗繁花,嗡嗡蜂群,满满粮仓,还有最后榨出的滴滴果浆。其中“收割”与“粮仓”的意象应和着一年半之前那首十四行诗《每当我害怕》中的诗句:
每当我害怕自己将不复存在,
而我的笔还未及收割我丰产的心田,
堆积如山的书本尚未如富足的粮仓,
在字里行间贮藏成熟的谷粒。
死亡的威胁与尚未实现的艺术理想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也许正因如此,济慈才尤其喜爱那收割后的田原,虽然土地上残留着短短的残梗,似乎毫无美感,但没有什么被荒废,也没有什么未达成。第三节则在秋景的基础上配以阵阵秋声,从视觉转向了听觉,一如华兹华斯的《永生颂》,在“辉光逝去”之后,诗人仰赖听觉去感知那精神的浩瀚水声:
春天的歌儿在哪里?啊,在哪里?
别去想春曲,你也有你自己的音乐,
当一道道云霞让渐黯的天色绚丽,
当收割后的田原染上玫瑰般色彩浓烈;
这时,小小的蚊蚋以悲哀的合唱
在那河畔的柳树之间发出哀鸣,
随轻风的起起落落而升升潜潜。
成熟的羔羊在山边啼叫嘹亮;
蟋蟀在树篱中歌唱;红胸的知更
以柔美的高音在花园里歌咏;
而成群的燕子在天空中呢喃。
但蚊蚋的和声是哀悼的。知更鸟也高吟冬的讯息。燕子集结,准备南归。在一切达到丰实之后,自然转向萧瑟。诗在离别中收场,“艺术的终极是平静”(希尼,《丰收结》)。
然而南下的济慈最终没有迎来新的春天。1820年11月30日,他写下最后一封信。如他在信中所说,他不善于告别,“总是鞠下尴尬的一躬”。在此期间,他没有给芬妮写信,也不敢拆开她的来信。他的医学知识让他对自己的症状洞明而悲恐。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陪伴他的是杰里米·泰勒的《神圣生死》。1月28日凌晨三点,日夜照料他的塞文为了让自己清醒,为病榻上的济慈作画。这是一幅不忍多看的肖像:枕头上的济慈阖上了往日那双“好奇的眼睛”,面色苍白,头发凌乱,汗水湿透。他的影子投在墙上,一个黑色的晕影。

《病榻上的济慈》,济慈-雪莱纪念馆
2月14日晚,在不息的泉水声中,济慈告诉塞文,在他的墓碑上刻下这句话:
在此长眠者,曾将名字写在水中。
2月23日下午四点半,死神逼近。直到生命最后,济慈还在为他人着想。他告诉从未亲眼目睹死亡的塞文不要害怕,这一切很快结束。塞文扶起济慈,把他抱在自己的臂弯中。当晚十一点,济慈安详离去,宛若入眠。这一天正是罗马的特米纳斯节,“此地的死者正生向 / 未来”(希尼,《草木志》)。

济慈与塞文的墓碑,罗马新教公墓;雪莱的墓也在这里。
特米纳斯(Terminus)是古罗马的界限之神。希尼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他:
在元老院山上的朱庇特神庙中,罗马人仍供奉着特米纳斯的神像。有趣的是神像上方的屋顶是洞开的,敞向天空,仿佛在说,一位大地上的界限之神需要有途径进入无限,那无限高远、辽阔、幽深的天空本身;仿佛在说,所有的界限都是必要的恶,而真正值得向往的境界是无拘无束的无限之感,是成为无限空间的王。我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正是这种双重能力——一方面, 我们为熟知事物所带来的安全感所吸引;与此同时,我们又难以抗拒那些超越自身的、未知的挑战与惊奇。这种双重能力,既是诗歌的源头,也是诗歌的鹄的。一首好诗让你既把脚放到地上,又把头伸向空中。
在某种程度上,这段文字也可以总结济慈的诗思与人生。痛失双亲,贫病交加,济慈却自幼热爱搏击,毕生喜欢说笑。当他从迷人的田园重返泥泞的人间,他从未放弃对美与真的憧憬。无论他经历了多少苦难,他始终抱持欢乐的希望:
当我从古老的橡树林消失,
不要让我彷徨于梦的荒芜:
但是,当我在烈火中燃成灰烬,
给我崭新的凤凰羽翼自由翱翔。
(《坐下重读〈李尔王〉》)
附记
大约十年前,我也曾穿过同样的城门,来到西班牙广场26号,如今的济慈-雪莱纪念馆。台阶上,很多人在晒太阳。贝尔尼尼的喷泉依然奔涌,只是水声在人群喧嚣中不再那么清晰。楼下一家男装店(27号)的招牌上赫然写着“拜伦”。进入展厅,我是唯一的访客。原先的客厅现在被改造为一间图书馆,陈列着与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有关的八千余册书籍。济慈的卧室在最里面,虽然狭小,却朴素有致。由于济慈死于肺结核,根据当时的法律,为了防止传染,屋内所有物件都要被付之一炬,甚至连墙纸也被销毁了。所以,我们如今看到的陈设都是根据那个年代的风格复原的。站在这里,很难想象他那宏阔的灵魂在这样窄小的床上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我也想起那“鲜活的手,此刻温暖/尚能热忱紧握”(《这鲜活的手》)……窗外,一些人在攀登阶梯,一些人走下来。

窗外

济慈的卧室

原先的客厅,现为图书馆

左图:济慈、雪莱和亨特的头发,欧洲曾流行友人互赠头发的传统;右图:济慈书信手稿
不久后,我攀登了阿尔卑斯山。置身于令人敬畏的山脉之间,我想起多少浪漫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曾登上这“不可丈量的山峰”,看山间万物乃“同一心灵的运作……代表着最初、最后、中间、永远”(华兹华斯《序曲》第六卷)。然而济慈不曾来过这里,他羸弱的身体不允许。他登上的最高峰是苏格兰的本尼维斯山,其次是湖区的海芙琳峰。站在峰巅之上,他感到释然:“我从未如此彻底地忘却我的身高——我活在目光中,我的想象被超越而平息下来。”(济慈致兄弟托马斯,1818年6月25-27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