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对话昨日:秦晖、金雁所经历的大时代与小生活

秦晖与金雁
作者简介:方华康,学人scholar学术观察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以来士绅及知识分子思想史。
每个人的记忆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个人的感情色彩,那些往事之所以积淀在记忆中保留下来,一定是在我当时的认知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荡,个人史的回溯记述其实是“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之间的对话”。
——金雁
近两三年间有一篇题为《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文章讲述的是秦晖(1953—)、金雁(1954—)两位著名历史学者数十年间治学、生活的经历,称他们“在清贫和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我想,如果读者对他们的学问和思想稍有了解,很难不认同这样的评价。他们恐怕的确是中国当代学者中少见的真正配得上“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思想者。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纯粹的学者应当是一群超越功利性,只“以学术为志业”的人。而知识分子与一般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除了专注于对知识的关怀、学理的追寻,他们还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反思能力。换言之,他们与所谓“社会主流”之间永远保持一种疏离感,对其存一分质疑。在旁人看来,他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现状的“异见者”、“社会的牛虻”。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指出:
“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说,秦晖、金雁这样的思想者正是以他们的思索引领着后来人前行的脚步,让更多人摆脱康德所谓“不成熟的蒙昧状态”,敢于运用头脑中的理性,反省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社会的未来可能。

金雁,1954年生于西安,198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专业,获硕士学位。1982年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1994年任职中央编译局研究员。2006年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与以往严肃厚重的大部头学术著作不同,2020年出版的《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是金雁教授的一部散文集,共收录回忆随笔、生活杂感等十余篇文章,文字生动活泼,读来毫无晦涩之感,金雁教授手绘的大量插画使全书更添妙趣。但严肃学者写通俗文章难免招来“不务正业”的质疑。在今天的学术氛围中,遑论发表拉拉杂杂的生活随感,学者即使是写通俗学术作品都往往被认为“掉了身价”。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电影导演姜文曾说,他从来不关心他拍的电影属于所谓商业片还是文艺片,他只负责拍出对得起观众的好电影。文艺创作如此,学术创作又何尝不是呢。对于读者而言,一部作品重要的应该是它的品质是否有保证,能否带来有益的启发,而尽可以不论其体裁、风格。
金雁坦言“我并不在乎如何对这类写作进行定义,只是想把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讲述出来。”金雁教授主要成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她认为那是一个“像黑白照片一样单调”的时代。然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那是一个同样风云激荡的特殊年代。在其兼具温情与理性的笔触下,那个时代的一些图景通过独特的个人经历得以展现。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内容却很丰富。作者在书中谈成长,谈时代,谈治学,回忆青春,怀念亲友。值得一提的是,全书最后有相当篇幅是关于丈夫秦晖教授的生活、治学经历,或令人捧腹,或引人深思,为读者认识秦老师的学养、性情提供了一扇窗口。了解“下蛋的母鸡”对于品尝其所下“鸡蛋”的滋味自然会有所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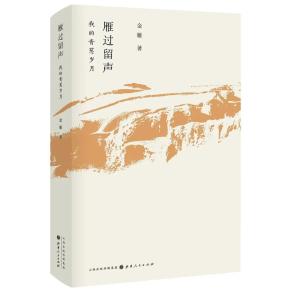
作者试图记录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毫无疑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方面的种种原因,关于它的严肃研究并不算多,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常常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正因如此,金雁教授利用先辈留下的民间资料及自身的记忆回溯那段“激情岁月”的努力才显得弥足珍贵,至少可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在她看来,那是一个“以标准化的模式塑造无个性的时代”,人变成了整齐划一的工具。当时能看到的戏剧、电影都是《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心里始终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

《霓虹灯下的哨兵》
那是一个政治与人性背离的反常时代。作者的爷爷因为是“落后阶级”,在大饥荒时投靠儿子无果而被饿死。在那样的时代里,“整个社会氛围都在有意压低和泯灭物质需要”,实际上,当时社会能提供的物质条件本来限,即使出身一般干部家庭,忍饥挨饿也是常态。
那也是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唯成分论”时代。书中回忆了所谓“黑七类子女”在当时遭受的种种歧视和伤害。作者在书中很少对她所经历的那个时代下直接的断语,字里行间更难见到或愤怒或哀怨的控诉,更多的只是生动、平和的记述。但在这些娓娓道来的故事里,我们依然能读到作者的情感、态度和反思。与作者几乎同一时代的著名作家王小波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对那个时代同样做出了精准、深刻的诊断。他们记录时代的风格截然不同,但都怀着对人的悲悯和关怀,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残酷的浪漫”。作者套用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言写道“时代是共同的,但是每个个体的体验各有各的故事。”这本书既是时代的记录,也是一个关于青春的故事,回顾了作者从“成长”到“长成”的艰辛历程。
关于成长,可以说作者在书中记述的个人经历颇具典型性。她总结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几乎都经历过一个盲从-狂热-碰壁-思索-还原个人的过程”。自小在机关大院里生活,父母都是冲决罗网、投身革命的“觉悟者”,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以及大的时代氛围熏染下,作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期,在思想上都始终保持“左”的基调。因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出身“旧家庭”的姥姥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隔阂。作为“旧家庭”里的“新女性”,姥姥一生历经风雨,对后辈们的教育非常开明。在后来家庭的急剧变故中,作者才慢慢感受到姥姥是一位充满生活智慧、重情重义的老人。
书中提到六十年代作者曾跟随母亲到临潼乡下“整社整风”,真正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困苦。文革开始前一年,作者又跟随父亲被下放到甘肃定西地区。在那里,她学会了自立自强的生活态度。她写道:
“在陇西的这几年,是我对生活最贴近、最理解、感触最深的几年……对‘过日子’几个字有了切实的感受,懂得了社会底层期盼的幸福意味着什么,也开始思索为什么整天劳作的人们连基本的温饱都满足不了”。
上中学时,作者也参与了大串联、批斗会,毕竟那是一个“革命不积极,思想有问题”的时代。七十年代,作者到陇西县一个公社插队,后来又被分配到供销社工作。这段经历一方面使她养成了勤俭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也促使她对社会体制进行了一些反思。文革结束前的1977年,她工农兵学员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老师。阴差阳错之下,虽然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却在1978年顺利考上了兰州大学苏俄史专业研究生。经过在史学园地里多年地辛勤耕耘,终于成为苏联东欧史研究的著名学者。

年轻时的秦晖和金雁
全书还有相当篇幅是关于秦晖教授的治学与生活经历,或许对于他来说,这两者根本就是一回事。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研究托尔斯泰时,提出将知识分子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前者以广博著称,长于发散;后者热衷建立体系,鲜少游离。近来有学者指出,其实以赛亚·伯林本人是一位“在狐狸与刺猬之间”的知识分子(参见段超:《以赛亚·伯林:在狐狸与刺猬之间》,《中华读书报》2020年2月5日)。面对这样的二分法,知识分子研究的大家许纪霖教授称自己是“无法归类的蝙蝠”。按照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分化以来的谱系划分,许纪霖教授和秦晖教授大致都可以被视作自由主义的左翼代表,属于相当温和的一派。
应该说,在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都以“百科全书式博学”著称的秦晖教授同样兼具狐狸和刺猬的气质。一方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其学术研究涉猎的领域之广在当今人文学界鲜有人企及,以至于我们甚至难以武断地称他为史学家。他的研究至少可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初运用传统考据方法致力于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研究;80年代后期运用中外比较方法转向研究中国经济史;90年代以来,结合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推动建立农民学。
其实,秦晖教授数十年间跨时段、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始终围绕的主轴无非是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包括传统社会的形态(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社会诸层面)、现代公民社会的特征、社会经济转轨进程等几个紧密关联的方面。他在著作中反复强调的“秦政”、“大共同体”、“儒道互补”、“尺蠖效应”、“权责对应”“自由优先于主义”等关键词实则包含着对中国如何顺利实现社会转型的深切思索,对如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尊严这一实践命题之不懈追寻。面对梁漱溟之问,我想,他的回答会是:“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好完全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这便是所谓“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而不是任何简单的决定论。
隐约记得之前有人写文章讨论过为什么秦晖教授能提出我们时代的“真问题”。我觉得这本书中关于秦晖的一些片段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个问题得到解答。秦晖教授于1978在兰州大学跟随我国农民史研究泰斗赵俪生教授攻读研究生,而此前的9年则一直在广西农村上“早稻田大学”(参见谢小灵:《秦晖:我与‘早稻田大学’》,《中国贫困地区》,1999年第8期)。或许正是在中国最贫困地区生活的几年让他在学术生涯中始终对普通人的生存状况格外关注,提出“无论中西‘文化’之异还是左右‘主义’之别,都必须以基本的人道为基础,以基本的人权为底线。”
赵俪生教授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声名鹊起,被誉为山东大学“八马同槽”佳话中的“八马”之一。金雁教授在书中回忆,赵先生学问精深,性格率真,讲课艺术出神入化。学生“私下里都称先生为‘最有魅力的导师’。”赵先生被秦晖对历史学的痴狂所感动,对他十分喜爱,“恨不能立马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弟子。”作为学者(此处指“学习的人”)的秦晖教授是真正爱书成痴的“看书科”生物,且“过目不忘”。秦蓓蓓在《我的父亲秦晖》一文中回忆了很多这方面的趣事,称“秦老爹眼睛不好,从小练就两个本领,一是站着看书……第二个本领就是看书时高度集中,可以屏蔽掉一切无用的信号和活动。这个习惯保持至今。”他的好友张鸣说“认识秦晖,最先感到震惊的是他读书的速度……人家拿在手里,把文章贴在眼镜上,拉来拉去,一会儿工夫,看完了。你还别怀疑他应付,因为随后人家能跟你谈的头头是道。”
尽管金雁教授在书中称秦晖教授是“拖沓天王”,实际上,在当今学术界,他的“产量”绝不算低。与对各类知识的痴迷形成鲜明对照,生活中的秦晖教授却在许多方面根本“不走心”。书中所写他在穿袜子、坐地铁、煮牛奶、倒垃圾等日常小事上闹的笑话让人不禁捧腹。他穿衣服随便到连德国总统也改变不了。在这方面,他的学生张宏杰说:“秦晖老师待人接物有一个特点,没有一句客套话。纪录片制片人夏骏和我聊起,他与秦老师以前见过,有一次开会遇到,他叙了几句旧,秦晖老师却一句也不接,一开口就谈学术。他总结说,秦老师‘只有学术思维,没有人际思维’。”正是凭着对学问纯粹的兴趣和好奇心心无旁骛地读书、思考,才使他在论著中旁征博引,抓住我们时代的真问题。
《雁过留声:我的青葱岁月》这本书真正的价值不仅在于通过对个人经历的展现让我们从一个微小的侧面直观生动地认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回顾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借此书可以了解两位思想者面对时代变局如何求索社会的公正自由,关怀普通人的生老病死。过去的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即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恐怕也算多事之秋。谨以秦晖先生在世纪之交许下的愿景结束此文:
“一愿新年道德昌明,经济繁荣,天人和谐,世界大同;二愿新年交易有序,强盗敛踪,人或自利,法不失公。前愿或为乌托邦,但求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倘无强制,乌托邦何害之有。后愿肯定是底线,我想白猫也好黑猫也罢,若不守此,哪一个能辞大咎?”
- 后台回复关键词,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
1.回复『学人书单』,阅读学人独家荐书:
2018.学人书单|36位学人的100本荐书(之 文史哲)
2019·50位学人的200本荐书(知识人篇)
……
2. 回复『学人访谈』,提取学人精彩专访:
萧功秦、方方、王笛、陈志武、周启早……
3.回复『学人专题』,深入了解学人与学界:
木心是悲剧命运代表,但不是艺术大师——致郭文景兄、陈丹青兄
年过九旬,他们依然关心这个世界
……
4.回复『先生之风』,一览略学人风采:
胡适、陈寅恪、蔡定剑、杨小凯、哈耶克……
原标题:《对话昨日:秦晖、金雁所经历的大时代与小生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