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战百年︱7本书让你读懂世界大战
五个星期内,世界大战爆发了

俄国介入保护塞尔维亚客户;德国支持奥地利同盟;法国出兵履行与俄国的协议;大不列颠履行了帮助法国的承诺。五个星期内,一场世界大战爆发了。至少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的《1914年7月:战争倒计时》(July 1914: Countdown to War)详细记录了这几周的大变局,令人不忍释卷。
战争:谁之罪?
战争释放了灾难性的冲突,它比历史上任何系列事件对之后的世界的影响都要大:没有大战,共产主义不会入主俄国,法西斯不会控制意大利,纳粹主义不会控制德国,几大全球帝国也不会如此迅速混乱地解体。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还在探寻它的原因,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找只替罪羊。在战争刚结束时,许多人觉得很清楚:德国尤其是其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奥地利作为帮凶,负次要责任。《凡尔赛和约》将之铁板钉钉,胜利国宣布“德国及其同伙公开挑衅并将战争强加于其他诸国”。这项臭名昭著的罪责条款是为了证明未来的严厉“赔偿”的正当性。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如果胜利方不追究全体德国人的责任,就会瓦解建立一个不受过去污染的全新德国的尝试,甚至许多普通德国百姓也同意这样的观点。

比利时、英国、俄国和法国四个协约国士兵的合影
然而德国人很快就开始挑战历史的判决。他们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战争罪的问题,五年里竟然出版了洋洋四十卷期刊,收集了各种证明德国无辜的材料。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应对:《战争起源的英国文件》十三卷,《法国外交文件》四十一卷,版图大大缩小的奥地利也出了九卷《奥匈帝国外交政策》,为其帝国前身的外交政策辩护。与此同时,新上台的苏联政府则想尽办法揭露沙皇政权的邪恶不公,在所谓的“红色档案”中公开了许多秘密。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各方面慢慢开始对1914年谁该负责的问题有了更平衡的认识。有大量证据表明,所有方面都做过玩火冒险的决定,导致战争越来越近。而且,文学见证人比如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就总结过,整件事是巨大的愚蠢和徒然。第一阶段的反思是意大利政治家、记者路易吉·阿尔贝蒂尼(Luigi Albertini)于1942-1943年发表的长篇学术论著。阿尔贝蒂尼被法西斯政权噤声,于是埋头收集材料,还采访了许多大战幸存者。这使得他的精彩叙述有了一种即时性,表现了个体在现实中所做(或者躲避)的重大决定。当阿尔贝蒂尼的杰作在1950年代被译成英语后,终于产生了影响。在一战五十周年之际,判决似乎清晰了:通向战争之路是极为复杂而拖延的进程,所有方面都有责任。
接下来学术共识又被削弱了,早先的假设似乎在新的视角下得到了巩固。汉堡史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将战争归罪于德国预谋已久的“追求世界霸权”。他在《空想之战》(1969)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德国的战前外交政策,认为威廉二世和他的大臣一意孤行地挑起争端,其中既有扩张的野心,也旨在规训社会主义者以及国内日渐增长的种种不听话元素。这种“费舍尔争议”导致了联邦德国的知识不稳定性,包括在国社党与整个德国历史进程的关系上暧昧不清,并流行用社会经济来解释政治行为。不管怎样,它得出了具有影响力的结论:《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者虽各自心怀鬼胎,但也许并没有大错特错。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大家又开始对战争归罪的问题争吵不休,但因有凡尔赛苛刻条件在前,费舍尔的观点一直有市场。但如果我们看本文评论的几本书,只有麦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的书依然保留了这一观点。在萨拉热窝百年之际,阿尔贝蒂尼胜利了。他胜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些书中对此根本没有任何异议(除了黑斯廷斯之外)。这几本书有很多共性,挖掘海量材料(由作者本人完成,有时候是研究助理完成)时发现了一些新信息,但大体上它们还是检验已有的知识库。这导致阐释的新意很少,但有许多新鲜的细节,通过这些细节将现有的视角带入了跨国界恐怖主义及其对主权国家的侵犯问题。
此外这些叙述都十分有说服力,好像复制了战前世界的文雅,而这种文雅很快将消失在战壕的污秽和野蛮中。它们间接排列了当时的文学作品,比如茨威格和凯斯勒的回忆。但总的来说它们还是在讲述个体的故事:统治者、外交官、政客、将军。它们令我们相信(至少是我们这一代人),大决战倒数的年月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顶层人物的性格。
协调机制是怎样崩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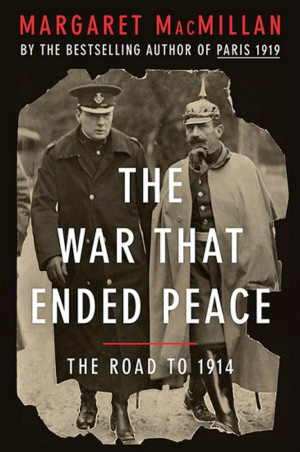
核心联盟是由刚刚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所主导的,人们怀疑俾斯麦曾经的铁腕让位于爱冒险又无法预测的皇帝威廉二世(麦克米伦形容他像个夸张的演员,但其实暗地里对自己的角色缺乏信心)。奥匈帝国习惯性地支持德国,维系中欧两大强国已有的纽带:有些人自以为是地形容奥匈帝国是排在德国之后的光荣老二。但法兰西共和国和沙皇俄国发展出了一种别扭但互相依赖的关系,他们的“约定”(entente)旨在共同对抗潜在的德国威胁,同时法国对俄国的工业转型进行了大量投资。不列颠渐渐从孤立转向了对法俄的谨慎支持,而意大利表面上属于德奥阵营,实则貌合神离。
麦克米伦叙述了几次国际危机的累积效应,其中包括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它们测试了忠诚度,扩大了焦虑,也强化了有控制的边缘政策。大家都爱用“不用明言的假设”,这种心理模式使得战争作为最后一击变得可以接受;军队首脑变得越来越自主,鼓吹进攻策略,正如许多民众也被战争的光荣假象所迷惑,人们开始借用达尔文、尼采、柏格森等不相干的思想来吹嘘战争的好处。1914年5月,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顾问豪斯上校总结了欧洲的情绪—— “疯狂好战”。
两大阵营曾有交锋的两个区域变得尤其危险:北非——法国和德国在1905年和1911年有过两次局部战争,摩洛哥是争夺要地;巴尔干半岛——1908年奥匈帝国不顾地方反对,单方面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亚(首都萨拉热窝),当时老迈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自内崩溃,近邻均对其领地垂涎三尺,奥匈帝国与俄国的争抢尤其令人担忧。到了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区域战争,但是极为野蛮)重新划定疆界,但加剧了紧张气氛,两大帝国剑拔弩张,随时会陷入深渊。
1913:山雨欲来风满楼

爱默生以同样的技巧优美地描述了北美的大都市,从威尔逊执政早期的华盛顿写到纽约(当时的象征性事件是J.P. 摩根去世,当年最高的摩天大楼伍尔沃斯大厦落成),从底特律(T型发动机小汽车生产线于1913年投入使用)到墨西哥城(当时仍处在革命的阵痛中)。亚洲和非洲的孟买和德班的双城肖像引人入胜,作者还尝试复原君士坦丁堡和北京所代表的两个老大帝国。
爱默生的地平线上没有暴风雨之前的滚滚乌云;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13年是最后的和平之年。他明确表达了世界眼光:尝试去展现即将失落、被毁灭的,至少是被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一词是德国人首先使用的,虽然他们比起其他大国并不那么国际化)所重新定向的东西。1913年许多国际间的和平接触网络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爱默生断言,之后它们顶多成了一种期望。

有时候麦克米金想要跟传统成见刻意保持距离,结果走得太远,比如他将弗兰德斯斥为战争小插曲,“没有持续的战略重要性”,或者坚称俄国无需害怕德国军队去东线,而沙俄在坦能堡被彻底击败只是“意外”。大战一百年后我们看到他的定义是“奥斯曼继承权之战”,在多方面重塑了地中海以东到亚洲以西的广大区域。然而在大战的最后酝酿期,它依然是一次欧洲事件:正如一个俄国官员指出的,“去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必要通过维也纳……和柏林。”最终风暴眼从之前远在天边的殖民竞赛挪到了欧洲的巴尔干后院、萨拉热窝市中心的码头旁。
大戏在麦克米金的另一作品《1914年7月》中上演,正如其主人公之一丘吉尔后来所言,“任何戏剧无法超越。”此刻拳击手麦克米金让位于擅长讲故事的麦克米金,娓娓叙述了萨拉热窝事件五周后的高层政治和外交,几乎是以日为单位,挨个探究了各国最高决策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这里有算计、困惑、诚恳、狡猾、愤怒的时刻,也有催人泪下的时刻。这本书中的叙述让前一本书看起来像是诡辩。这里萨宗诺夫不是邪恶天才,俄国的反应恶化了形势,但他们顶多准备来第三次巴尔干战争,而不是一场世界大战。
麦克米金总结1914年7月见证了一系列绝无可能复制的独特事件的串联。这里有无心之失,有故意犯错,也有愚蠢的外交大失误,但并没有主犯。起先德国应负主要责任,向一心复仇的奥匈帝国提供了空白支票,最后又愚蠢地入侵比利时(为了达到德国一直坚信的包抄法国军队以速战速决的目的)。但换句话说,德国是被奥地利人拖了进来。麦克米金严厉批评了奥地利人的不灵活、笨拙和鲁莽,跟塞尔维亚人算账时一拖再拖。接着又有俄国和法国的武力威胁,他们过早进行了军事动员,让德国深信双线作战的噩梦即将来临。
《梦游者》:世界大战如何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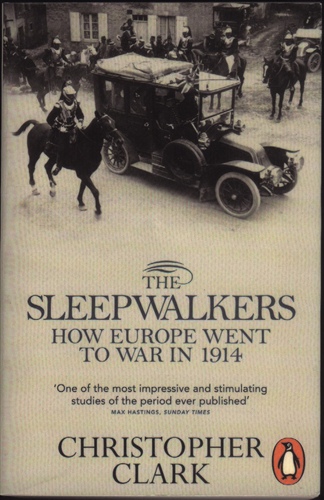
等到战争爆发时,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都成了龙套,7月底威廉二世甚至告诉哈布斯堡皇帝,塞尔维亚边界“只要最低防御措施即可”,而奥地利当时的唯一军事计划就是跨过这边界。此时俄国已经全面介入,克拉克和麦克米金意见相似,认为俄国在玩邪恶威胁的游戏,而法国将巴尔干危机视为最好的保证,俄国定会参战抗击德国。在克拉克的叙述中,法国的回应因个人因素主导、因冒险而变得强硬。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是个强势的民族主义者,正要开始重塑总统权威,这当口正好要去俄国访问。一旦他与萨宗诺夫确定了军事动员,德国不得不去收割他们播下的恶种。到8月1日欧洲大陆已经全线开战。
只剩下英国了。如果英国袖手旁观,事情是否会不一样?更现实地说,应该是如果英国在7月就确认支持法国,那么德国是否会收手?这些书的作者尤其是克拉克,都考查了从1890年起日益增长的英德对抗,海军军备竞赛更是火上浇油,两国高层时常互相怀疑(一个例子是英国方面相信有几千个德国间谍假扮成餐馆服务员潜伏在伦敦各个角落)。战前略有缓和迹象(至少经济和文化关系上效仿和对抗不相上下),大不列颠在制造无畏战舰的竞赛中大获全胜,因为向老百姓征的税更高。
然后德国向比利时发最后通牒,要求比利时让德军通过,这样就威胁到了该国得到国际保障的中立性。德国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真的吗?伦敦的外交政策由乡绅爱德华•格雷爵士暂时掌管,他在柏林的鲁莽冒进行动之前和之后都摇摆不定,而英国政策也会受到议会分裂和内战动荡的影响。也许只有战争能够转移对爱尔兰自治危机的注意力,还可以把本来要送去爱尔兰维稳的军队派上真正的用场。
英国参战的决定几乎是公开的。克拉克极为精彩地分析了权力的形态:君主及其大臣的行动;政府及其外交代表的行动;军事和民事权威的交锁范围;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媒体代表的更广泛观点的关系。媒体一直对政府吹风。1914年法国驻柏林大使朱尔•康邦甚至报告:“说德国民族和睦而政府好斗是不对的,正好是反过来。”不过,国内媒体可以被视作官方政策的前奏,因为决定打仗需要将对手刻画成挑衅者,这是透明但有效的策略,能够对外交和军事措施进行扭曲。所以德国和奥地利在7月的举动是极不妥当的,他们签发了蛮不讲理的最后通牒,接着在军队还没准备好打仗的时候就宣战了。
从萨拉热窝到世界浩劫

当时还有许多假设被现实立刻否定了:德军竟然被不堪一击的比利时军队给耽搁了;奥地利人被塞尔维亚人挡了回来;俄军的东线优势在坦能堡惨败中化为乌有;悲哀的法国人没能夺回他们挚爱的洛林省。最后来的是最大的恶报——人们以为战争会很快结束的预期成为泡影。所有这些前提假设都帮助他们在7月做出参战的决定,而且导致了最初的种种热情迹象,这些热情迹象又被后代大大夸张了。
到了12月,麦克斯•黑斯廷斯所言的“浩劫”发生了;他书中的时间范围从萨拉热窝写到1914年底,主要着眼点是战前各方对战争走向的预期。“圣诞节回家”是一句很受欢迎的标语。那么是什么如此残酷地拖延了战争呢?麦克米兰详细考查的和平运动怎么了?为什么当时的交战国没有严肃地尝试坐下来谈判,哪怕是在未来的毁灭已经十分清楚的情况下?
最明显的是,一旦军队进入战场,军权就被无限扩大了。大部分交战国立刻实施军事管制,开始征召士兵和其他人为战争服务。审查制度立刻猖獗起来,利用一切手段粗野镇压任何潜在的反对意见。还有体制因素:穷凶极恶地污蔑中伤曾经维持欧洲长期和平的大国平衡机制。这种清算帮助塑造了战争决策(比如不参战会让敌对国家更有机会击垮可能的盟友),结果便是无可避免的军事僵局。此外,所有交战方都没有现成的退出机制。战争似乎是要满足一种需要,那就是为已经造成的牺牲找到理由。最终的现实是,听从权威的社会都迅速接受了全面战争的指示。
黑斯廷斯非常擅长描述战争现实——事先缺乏考量,经济立刻陷入混乱,武器生产失常,金融信用破产(不过非参战国可以渔利);掠夺平民,游击战给平民带来的苦难(特别在德国,但英法对逃兵更残忍)成为常态。军队价值在一切领域中践踏平民生活,而在高级军官明显无能时就显得更为刺眼: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将军有忧郁症,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tzendorf)浮躁粗笨,约翰·弗兰奇(John French)是个“胆小鬼”(他指挥的不列颠远征军总和法国盟友差半拍,亏他好意思取名叫“法国”)。媒体上到处是无知而误导的报道,少有真实的信息,很快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最后,交战方放弃进攻,开始僵持,机关枪和重型火炮被拉上战场,用来阻碍敌方前行,西线开始挖掘战壕,海军进入消极防守模式。
1915年起有了新动态。本文所评几本书中,麦克米金的《俄国根源》在1914之后继续下去,强调了土耳其参战后东线和东南线的重要性。他在一些最刺激的章节中写到了沙皇政府煽动西方盟友在土耳其的加里波利采取行动,后来还煽动亚美尼亚人以及安纳托利亚和波斯的其他人,帮助俄国火中取栗。
斯特罗恩的杰作很难超越

1914年的那一个阳光夏日对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来说是多么轻易啊!“我不是罪犯,”他这样告诉检察官,“因为我毁掉的是邪恶。”然而他又放出了多少邪恶。在1914年圣诞节,有些地方神奇地短暂休战,接下来就是坦克和毒气;空中轰炸(德国早就对英国东海岸进行过轰炸);意大利参战后全部战线中最惨烈的阿尔卑斯“白色战争”发生了;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索姆河和凡尔登战役;德国潜艇对美国采取敌对行动——想想威尔逊在1913年的就职演说中只字未提国际事务吧;非洲和亚洲前线;许多交战国中发生了革命和危机;一千六百万人丧生,两千万人受伤。
1914年7月几乎没有人预见这一切。驻贝尔格莱德的俄国大臣尼古拉·哈特维希(Nikolai Hartwig)甚至在萨拉热窝事件后请假,因为近期“看上去没什么重要的事会发生”。然而落落寡合、迟疑不决的爱德华•格雷(没有人把他当英雄)已经意识到了大祸临头。他在乡下大宅里和自然交流时(他是一位鸟类专家,极度喜爱活生生的鸟儿而不是斐迪南大公帽子上的羽毛),已经得出了结论:“如果战争爆发,将是这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大浩劫。”
(盛韵 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