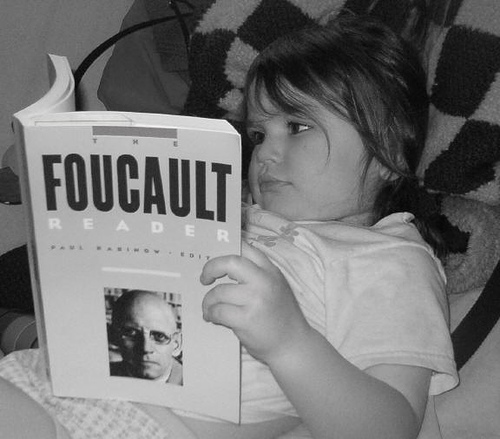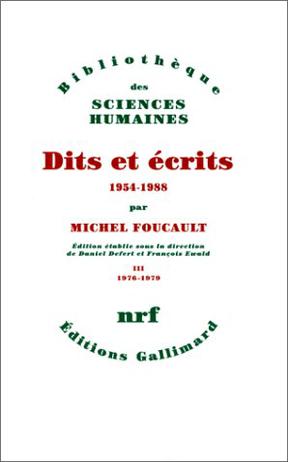【编者按】
作者姜宇辉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二十世纪法国哲学》作者之一,德勒兹《千高原》译者。
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得以缅怀或“追忆”福柯?
首先,试图在那些多变的路径和面具之下重建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挖掘出所谓的“核心”思想,这注定是徒劳的。我们必然要直面福柯向时代和历史所提出的问题。当海德格尔将发问作为其存在论思索的起点,当德勒兹将问题作为哲学思索的原初界域,他们都在强调问题的首要地位之时同时暗示出此种问题之探问的艰难与困顿。它会一次次地将你带回“重新开始”的起点,或将你抛回无所依托的迷惘境地。这时所需要的,除了有思的勇气,还必须有思之决断。
“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福柯的这句名言理应铭刻在每个哲学历险者的孤舟舷侧。也正因此,在这样一个追忆的时刻,我不再想简单重复或归纳自己研读福柯的心得体会,而试图再度追随他回归起点,在思想的发端之处重新体察哲学思索的别样可能。


福柯思索的起点自然是《古典时代疯狂史》。在我的心目之中,它不仅是二十世纪哲学中的一部厚重经典,而几乎可以算得上是西方思想史上最为奇异的思想结晶体。此种奇异不仅在于疯狂这一离经叛道的主题,也不仅在于作者所翻阅和梳理的浩瀚文献。疯狂作为主题并非福柯的独创,而福柯对于历史资料的处理也往往受到正统历史学家的(往往是颇有根据的)诟病。但这部巨著的真正力量并不仅局限于这些明显的方面,而恰恰在于它对于哲学思索的真正起点这一普遍问题的深刻追问。从思想史的演变线索上看,无论将感觉经验抑或内秉观念、乃至体验或启示作为起点,它们都已经内在地蕴含着导向真理的趋向。换言之,作为通向真理的普遍而必然的思想运动的初始环节,它赋予思想以启始的动力,但却注定要最终作为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被纳入到整体性的体系之中。但福柯在《疯狂史》中却恰恰提出了一个判然有别的立场:哲学思索的起点理应在于不可确定的“别处”,异于自身的“他者”,或无法内化的“外部”(dehors)。哲学的思索并非单纯沿循着一条同一性的思辨路径冷静前行,而恰恰是开始于差异性的紧张和焦虑(但又未尝不是一种极致快感(jouissance))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追问“疯狂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终极问题并不切题。无论是自然状态还是文化和社会要素,都不足以界定疯狂的“本质”。相反,疯狂的功用仅仅是揭示出非哲学(non-philosophy)的外部。它既非既定的状态,亦不具有明确的本质,而只是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显现出哲学在发端之处的差异性痕迹。漫过海滩的潮水留下痕迹,但重要的正是透过这些既定的形态去体味其背后的差异性力量相互作用的关系和格局。或者说,当外部力量激发思想沿着某种途径运动、凝聚成某种体系形态之时,它总是以种种暗示、隐含的方式展示出更为丰富而难以穷尽的创生力量。用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的著名隐喻,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可见的仅仅是光亮的痕迹,但在背后所敞开的却是蕴含着无限强度涨落与差异的电磁场域。

但要恰当把握这一要点却并不容易。甚至当加里•古廷这样的资深研究者在详尽辨析《疯狂史》中的种种“历史”难题之时(《福柯:剑桥指南》),也陷入了明显的困境。针对历史学家们所指摘出的书中的种种“硬伤”(证据薄弱,以偏概全,随兴阐释等等),他的辩护也显得苍白。比如,有学者就非常有力的指出,作为全书核心论据的“大紧闭”充其量只在法国的范围之内才有效,至少就英国而言,此种大规模的紧闭运动从未真正出现。这当然是对福柯的历史学论述的有力证伪。固然,福柯的那句半认真半玩笑的反讽性托词(“我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不足为据,但古廷看似言之凿凿的论证性辩护亦远未切中要点。无论是将福柯的论述重新纳入到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之中(在多变而复杂的事实背后重建一种连贯性),还是将福柯的历史论证的普遍性仅仅归结为主观的方面(普遍的“认知模式”),这些都仅仅局限于疯狂之思的“可见”方面。以至于在全文的最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疯狂史》中存在着一个难以协调的差异性张力:即一方面是围绕疯狂所形成的种种可见的话语(医学的,哲学的,政治的,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对疯狂的所谓“直接体验”

然而,无论是经由德里达的批驳,还是诉诸福柯自己的论述,所谓对“疯狂自身”的“直接体验”都是难以成立的说法。诚如福柯在更为激进的第一版序言(后来被完全删除)中指出,更为恰当地说法应该是探寻“界限”(limite)。因而,我们理应在书中所重点关注的,并不是那些连篇累牍的医学知识,或看似荒诞的政策法规,而正是那些游弋于边界,界限或“门槛”之处的痕迹。它们既具有可见的形态,但更是敞开着不可见的隐含力量。界限,并非单纯是划定彼此的鸿沟,而必定已经渗透着理性与疯狂,思与非思,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复杂纠葛的种种印记。
然而,何者方能作为此种界限的恰当形态?首先即是图像或意象(image)。不过,意象在这里不再是注定要被储存于记忆、最终被吸纳于概念范畴之中的感觉材料,而是真正激发思想不断重新开始的外部力量。由此我们方能体会,那些疯狂意象闪现的时刻,也往往是将我们从那些乏味的历史缕述中重新唤醒、保持思之警惕的时刻。阿尔托自肉体深处喷吐而出的谵妄话语,戈雅画布上展现的疯人院的惊心动魄的场景,这些都构成了整部《疯狂史》的真正“入口”。但最为令人回味,值得一遍遍品读而思索的却正是“愚人船”这一不可思议的意象。这是书中第一次出现语言与形象之间的断裂契机,也正是在这个断裂的缺口之处,涌现出思之种种别样可能。


《愚人船》(现有曹乃云先生的中译本)最早指德国作家塞巴斯蒂安•勃兰特创作于15世纪末期的诗体作品。它在文学上的开创性价值不仅令其产生了巨大深远的社会影响,也成为随后众多所谓“讽喻”文学的典范和原型。也正是由此,很多学者也就自然而然地将这部作品与荷兰诡异画家博什(Hieronymus Bosch)的同名作品(Ship of Fools)联系在一起。由此亦衍生出无穷无尽的从文学寓意出发对图像所形成的阐释。比如,画中直竖于小舟中央的桅杆实际上明显是一棵树的形态,而很多论者就基于勃兰特诗作的宗教背景将其理解为伊甸园中的智慧之树,而隐藏于树梢之中的那个神秘面孔也就顺带被理解作诱惑之蛇。类似的解释更是层出不穷,不一而足。但所有此类解释的症结皆在于最终将图像还原为象征(symbol),从而被纳入到更高的意义的层次之中(语言,知识,价值),而这就使得图像本身所隐含着的激发性强力丧失殆尽。图像现在仅仅沦为一个讽喻或道德训诫的符号。诚如博什在另一幅更为直接描绘人类“七宗罪”的作品构图之中所表现的,种种人类的愚蠢和堕落的罪行最终都无法逃出居于中心的上帝之眼的审视。在众多论者看来,博什在《愚人船》之中所描绘的图像也正是在更高的神圣之眼或理性目光的审视之下方才显现出其全部的扭曲与疯狂的“意义”。讽喻,总已经是预设着一种镜像的等级结构,将图像投射于更高的意义层次来读解其意义。就此而言,当福柯进一步从主题(水,船,航行,驱逐等)上来阐释愚人船的那种介于“划分”和“过渡”之间的含混边界的地位之时,他虽然洞察到前人未能洞察到的哲学深意,但最终仍未能摆脱此种镜像的结构。

这也是时时困扰着艺术哲学的一个难题:当我们基于一种自认为颇有理据的哲学立场来对作品进行“解释”之时,到底怎样才能避免固步自封式的自我独白?或更确切说,怎样才能以一种哲学方式来学会倾听作品和图像自身的声音?
固然,另有更为专业的图像学(iconology)的研究强调要回归图像本身,将博什作品置于其创作及艺术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进行考察(比如贡布里希),试图让作品本身来发出声音。但其实这无非是另一种镜像结构,即便它摆脱了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先在束缚,但最终仍然将图像吸纳入种种整体性的结构及其转换关系之中。当我们不无炫技式地将画面上的哪怕最小细节(甚至是盘子中的樱桃,旗帜的标识,桌上的杯子等等)都按图索骥地回溯到某一种图像模式或演变脉络之时,真的还能体察到作品带给我们的冲击强力吗?
与此相对,似乎还存在着另一个迥异的方向。不再是上行至某个更高的镜像,而是下行,坠落至那个更深的本原。如德勒兹在《感觉的逻辑》中对弗朗西斯•培根画作的解读,完全脱离了主题、寓意、背景等等宏大叙事的上升预设,而是转而下降,更为直接地去面对图像本身的生成运动(线,颜色,平面等等),以及由此展现出的肉体与空间之间的力量角斗。同样,在随后的段落中,福柯也从形象爆裂的角度来探索其更为直接和野性的表现强度。就博什的这幅惊世之作本身而言,既然绝大多数论者都认同其主题无非是贪婪(gluttony),那即便一个观者对其中的文化背景、图像象征以及道德寓意并不了解,仍能最为直接地体察到肉体自身的生成欲望的强烈展示。做个不太恰当的比拟,图像中最为鲜明的洞开的嘴巴的形象与培根笔下的嚎叫的教皇又是何等近似。诚如福柯所言,只有当图像挣脱了种种“形式的秩序”,方能在极度的增殖爆裂之中展现其原初能量。
也正是在下降的运动之中,我们窥见了另一种镜像结构。但不再是疯狂和肉体领受理性的审视目光,而是理性在下降的深渊(动物性,欲望)之中窥见了自己战栗的扭曲影像。这也是为何在全书的最后,福柯将疯狂置于人与其自身真理的循环之中。也正是在这最后的部分,戈雅,萨德和阿尔托带着蛰伏已久的疯狂的意象能量再度出现在现代性的边界之处。如是观之,全书的整体结构似乎也同样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镜像结构。
回顾自己这些年的研究工作,虽然从未进行过对福柯的艺术哲学的主题研究,但无论是对图像本身的关注,还是围绕肉体与图像关联的种种探讨,其基调似乎早已隐含于初读《疯狂史》时的震撼体验之中。在福柯的丰富文本资料之中,还隐含着大量尚待挖掘的启示性,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他对宾斯万格《梦与存在》所做的深奥序言。所有这些都诱惑我再度跟随他进行下一次的航行,驶向开放未知的思的汪洋。驶向生命深处那令人目眩的渊薮。“夜的野兽在嚎叫,这是我的道路,黑色的门关上。”(伊夫•博纳富瓦,《一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