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战俘营里的日本守卫:无论多么残暴,都不是恶棍那么简单
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说这是场考验。他十分着迷于一种念头,就是他那一代的男子生得太晚,没能参加大战,也就没能经历强加于他们父辈的那种男性成人礼。1915年衣修伍德十岁,他的父亲、职业军人弗兰克·衣修伍德死在法国战场上。这对他产生了极深的影响。男性气概的考验,对他而言要比真枪实弹的拼杀更重要(因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性至关重要。他常说要冒险才能证明自己。他的同性恋取向披挂着反叛的外衣。倒不是说和柏林街头的猛男乱搞可与面对索姆河的德军机枪相提并论,但至少在衣修伍德心目中,这里面有种细微的关联。
澳大利亚小说家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的书《通往北方的小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刚得了今年的布克奖。他出生于二战结束后十六年,也许时间隔得太久,对所谓考验已经不在意。但他的父亲是战俘,曾被迫修筑泰缅铁路。很难找到比这更能考验人的事了。
这条铁路曾被称为“死亡铁路”,修建的目的是通过泰国把马来半岛的增援和物资送给占据缅甸的日本部队。日本工程师根据崎岖的山区地形推算,铁路至少要五年才能完成。之前的英国人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但是有了六万名盟军战俘可供差遣,还有许多亚洲劳工,日本军方首脑决定,这项工作应在十八个月内完工。

因日本和韩国守卫的野蛮态度,加上热带疾病、饥饿、过度繁重的劳动(尤其是1943年疯狂的“高速”劳动),逾一万两千名西方战俘死亡,亚洲人死亡数可能在十万以上。今天东京的靖国神社依然自豪地展示着“死亡铁路”上开过的第一辆火车的机车头,但实际上当时修筑的铁轨极为粗制滥造,战后泰国人不得不重修大部分轨道。
在“死亡铁路”工作的经历,恐怕很难想象。不过这正是弗兰纳根试图做的:去想象。除此之外,他还试图想象那些监督修路的日本军官的心理。
结果就是,这本小说描述的恐怖,有时让人无法承受。例如:一个名叫达基·加迪纳的澳大利亚战俘,被冤枉消极怠工,先被日军守卫打得半死,然后被淹死在公共茅坑的屎溺中。弗兰纳根的小说也提及了男子气概的考验。从某种方面说,这是对澳大利亚人阳刚之气的探讨,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此书对男性气概的观点阴冷黯淡,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观点,那也是反阳刚的。
很明显,弗兰纳根钦佩那些在泰国雨林的烂泥地里受苦挨饿、被奴役,甚至死亡的人。但他的小说并不是人类战胜逆境的老套故事。故事中弥漫的是一种失败之感——尤其是在极端环境中无法找到意义,也无法得到宁静生活的回报。我们在生命中寻找意义的唯一希望,似乎要依赖于文学和艺术。弗兰纳根的祖辈是强硬的爱尔兰政治犯,他生于以前流放犯人的塔斯马尼亚岛,这里的人们可没闲工夫去欣赏艺术。不过弗兰纳根本人文学修养很高,还是一位精妙的散文诗人。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多瑞戈·埃文斯,是个医生,他总是竭尽全力帮助那些忍受非人条件折磨的病人。据说这个人物有真实的来源,经历和“疲倦的”爱德华·邓洛普(Sir Edward “Weary” Dunlop,“疲倦的”是他的绰号,因与邓洛普牌轮胎的“tyre”的谐音“tired”同义——译注)爵士颇有些相似。邓洛普是运动健将,生来就有领导气质,他是缅甸铁路上的传奇英雄,以公共人物的身份为战俘做了许多好事。要说有任何人通过了阳刚考验,那就是“疲倦的”邓洛普。
但伟大的英雄有时也是很烦恼的。弗兰纳根塑造的多瑞戈·埃文斯是个复杂而痛苦的人物。他在战争中的行为相当英勇,也因英雄气概而为人称颂。但俗世的浮名对他来说意义不大,社会授予他的种种荣誉只会加重他内心的空虚。他和一位美丽心善的女子艾拉成婚,但只是尽义务而已。他有许多情人(大部分是同事的老婆),但没有女人能取代一段战前的回忆,他和叔叔基斯的妻子艾米有过一段不伦之恋,这也是他唯一经历过的真正激情。
他主要的爱好是读书。“睡觉时没有女人没关系,没有书可不行。”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他在一次毫无新意的车祸中受了重伤,躺在医院病床上还轻轻吟着丁尼生的诗《尤利西斯》:“【我决心驶向】太阳沉没的彼方,超越 / 西方星斗的浴场,至死方止。”护士以为他在呓语,事实上,这首诗很应景。多瑞戈的奥德赛之旅,充满了无数塞壬的诱惑,终于到了尽头。他的旅途的意义,不是衣锦还乡,或柴米油盐的家庭生活,而是旅途中的考验。这些只能在词语、文学的语言、诗歌中找到意义或解答。
对那些参加过战斗的人来说,之后的人生时常令人感觉寡淡无味。有什么能比在暴力死亡面前与战友共同奋战抗敌更为剧烈的感受呢?对一个经历过战斗的人来说,在郊区超市里和人挤来挤去买菜太让人失望了。那些死亡营里的幸存者虽没有理由去怀念可怖的日子,但有时他们也会觉得很难从接下来的人生里找到什么意义。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国家,上上下下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着迷状态,编织出大量神话,因为之前从未有如此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以后也很难再有。
弗兰纳根的小说里,有个战俘名叫吉米·比奇洛,他的战后生活要比大部分人成功。对他来说,战争“只不过是真正世界和真正人生的一次间断”。但即便是他,最终也无法彻底逃离回忆。他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了孙子,但逐渐地,他想起战争的时候越来越多,而生命中其余九十年的光阴慢慢分崩离析。最后他很少会想到或说起别的事情,因为他越来越觉得,其他的都像没有发生过。
埃文斯(以及我们可以假设弗兰纳根本人)对战争没有任何浪漫幻想。他不相信受苦是为了让受苦的人学到美德。事实上,埃文斯“痛恨美德,痛恨美德受人敬仰,痛恨人们假装表扬他的美德或是假装自己有德”。他相信,美德只是“虚荣心盛装打扮,等待别人鼓掌”。
这里有一种招牌的男性姿态:一个男人就是要做他应该做的,诸如此类。但埃文斯并不认为他的战时行动是美德。在弗兰纳根的小说里,日本人并不都是魔鬼,包括埃文斯在内的澳大利亚人也远非圣人。他们会欺骗朋友,偷走别人的最后一份口粮;有可怜人累得栽倒在地,脸浸在血染的泥土里,他们就当没看见。但埃文斯依然关心他的病人,哪怕他无力挽救大部分。他们都病恹恹的,长期挨饿,被迫在丛林中日夜工作修筑铁路,日本军官要赶上疯子制定的工期,根本无所谓多少战俘死在铁路上。埃文斯知道苦力们必须互相支撑,因为“一旦活人任由别人死去,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停止了意义。如果他们想活下去,就必须结为一体共患难,现在如此,永远如此”。
也许,正是这种团结之感,这种生命随时会被(疾病、饥饿或是日本人无情的鞭打)夺走的强烈感觉,在回到“正常的”生活后很难再现。弗兰纳根再次为主人公在战后世界的疏离增加了一种文学元素。埃文斯感到了某种东西在枯萎,原本危险重重的生活被乏味的新世界取代了,在这个和平世界的眼中,准备饭菜要比读诗更叫人感动。
诗歌和冒险之间的共生关系并不常见。但在弗兰纳根这本用文学方式处理阳刚考验的小说中,它是如此自然。
令这部小说尤为有趣的是,无论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径多么残暴,他们并没有被简单地描绘成彻头彻尾的恶棍来衬托澳大利亚人的文明体面。日本人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宗教信仰、爱国主义、武士道精神与别人不同,这是肯定的。要说弗兰纳根对日本军人的描写有什么毛病,就是有些太整齐,陷入了无条件崇拜天皇和变态的武士伦理的程式。无疑日本军人被灌输了投降便是极大耻辱的观念,所以对待投降的战俘可以任意蔑视糟践。西方人尤其是个子高的人,有时会被故意当众羞辱,让他们知道在亚洲谁是老大。然而更常见的事实是,马来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境遇更差。
但可怕的日本宪兵队的特长是折磨犯人至死,这可不是武士道传统。事实上,在之前的战争比如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军人对俘虏还相当尊重。但1940年代的日本皇军要比1905年残暴许多,也更不讲纪律。弗兰纳根的神来之笔是写出了日本人的思维过程,比如残忍的劳动营指挥中村少校,尽管他被灌输了各种可怕的观念,但仍然能够与埃文斯那样的人形成怪异的平行。
中村接到上级命令迫使他完成不可能之任务,以至于他指挥的战俘营成了一个活人屠宰场,他在绝望时刻,也会在诗歌中寻找意义。他的上级古田上校是用武士刀砍掉犯人首级的高手。中村需要药物兴奋剂的帮助才能继续执行任务,而古田实际上很享受屠杀他人。一天他们两人谈到战俘营、铁路和战争,中村说:“这不光关乎战争,也关乎让欧洲人知道他们不是高等人种。”古田加了句:“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才是。”在片刻沉默思索之后,古田吟了一首诗:
即便身在京都,
听到布谷鸟鸣,
依然会向往京都。
芭蕉的俳句,中村说道。
松尾芭蕉最有名的一首俳句写于十七世纪末,讲的是旅行,就叫《通往北方的小路》。中村认为,缅甸铁路的目的是让日本军队一直达到印度,这样可以把印度从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在中村眼里,“日本精神的当下体现就是这条铁路,铁路也就是日本精神,我们这条通向北方的小路,帮助芭蕉把他的美和智慧带到更广阔的世界。”
我不太确定这能有多大说服力。俘虏营指挥官的诗歌隐喻也许更多地透露出弗兰纳根的审美趣味,而非日本军官的想法。但这是挺好的比喻。日本是优越的,它发动的战争是高贵的,是战争就要有可怕的牺牲,包括把外国战俘推向死亡,所有这些都在一首十七世纪俳句的凝练语言中表达了出来。
重申一下,中村并不是邪恶之徒。战争结束后,他很和气,甚至谦卑。而正因为他不是暴徒,他得为那些残暴的命令找些看似高尚的虚假借口。他试图把自己想成一个高洁之人,因为他为更高的事业克服了对折磨劳工的反感。但接着他发现战争结束后他和他的受害者一样难以继续生活。战后的日本已经没有天皇崇拜和尚武精神的空间,正是这些把中村这个单纯的工程师变成了杀人犯。
战后,古田为中村在日本血库找了份工作。古田所属的这个机构,现实中就是在东北进行可怕细菌实验的一个前战犯创立的。这样的巧合当然有可能,但也许有点太造作了。还有就是古田在死后被做成一种干尸保存起来,这样他的女儿能兑现他的福利支票。他的床边也有一本芭蕉的《通向北方的小路》。一叶干草书签标记着这一句:“日月是行者的永恒,流年亦然。”
同样,这并非无法想象的场景。但弗兰纳根的叙述有点用力过度的倾向,总要表达一种哲学观点,而且时常用诗性的语言来表述。
弗兰纳根的文学技巧反映了他对诗歌的关怀。他的小说中诗意形象不断再现,好像主导动机。其一是尘埃在光线中飞舞,正如生命一般偶然无常。埃文斯的无爱婚姻让他感觉“如同一百万个飞舞的无意义的微尘般叫人丧气”。他妻子写的一封家书抵达战俘营,通常这是爱意的珍贵信号,叫人珍惜生命。但她的文字“像尘埃般四散升起,于是越来越多的尘埃互相碰撞……”
战后许多年,他突然看见战前的恋人艾米在悉尼海港大桥上走过。他任由她擦肩而过。他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们像“光线里狂飞的粒子,失落已久,正如他知道如今一切都失去了……”
诗意的隐喻在日本守卫身上也适用。中村去北海道拜访一个战友,看到机场的大路边矗着许多冰雕,有哥斯拉、铁甲人和其他怪兽。他听朋友说话时,回忆起了那些战争暴行;它们好像冰雕怪兽,及时冻结了,但随时会突然扑向他。
弗兰纳根向读者展示的寒冬视角,也很接近传统的日本情感,一种源于佛教的生命虚幻无常之感。相信一切都只是幻觉并非没有安慰,至少它能帮助我们度过无法承受之难关。弗兰纳根对泰国的战俘营的描述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
埃文斯在战俘营里有一个小手术室,他竭尽所能弄些最基本的工具,有偷来的瓶子、管子、刀具,去修补那些八成要死的人的残破躯体。他知道这是“神奇想象力的胜利”,他对一位护工解释,“我们只有在幻觉中保持信念,生命才有可能……”
有时,所见所感太痛苦以至于难以忍受时,幻觉能够提供出口。当日本人逼迫战俘们看着达基·加迪纳被竹枝打得皮开肉绽时,丛林中飘来的水果香味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起了雪梨酒和圣诞午餐:
虽然他们会带着达基被打的回忆赴死,不管是六天后还是七年后,但当时他们似乎束手无策,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与石头砸下或是暴风雨来临没有区别。最简单的办法,是找点儿其他事情去想想。
到最后,一切都会过去,甚至回忆。曾经有无数人惨死的缅甸铁路,如今成了旅游景点,泰国的导游会推荐游客去看看。战俘被鞭打至死的地方,现在是纪念品小摊。中村的内心被冲突折磨着,他到底是承担了帝国责任的高尚之人,还是那些挥之不去的冰雕怪兽呢?于是“带着当年在暹罗丛林里的钢铁意志……他决定必须从此以后把自己想成一个好人”。
这也是一种遗忘术,一种有意的幻觉,可能许多施暴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而且不光是在日本。不过有些日本人选择了不去遗忘的畏途。一个叫佐藤的人告诉中村一个可怕的故事,基于真实发生的事件,说日本医生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中村不想听到这类故事,于是总躲着佐藤。
多瑞戈·埃文斯没有忘记过去。但他又对当下的空虚感到痛苦:“他无法承认,其实是死亡给了他的生命意义。”只有诗歌能提供某种解脱。一个日本妇女代表团到塔斯马尼亚去拜访他,为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暴行向他道歉。她们带了一本关于死亡的日本诗歌集送给埃文斯,作为痛悔的信物,埃文斯欣然接受,因为他相信“书有种光环在保护他……”。
其中一首俳句尤其打动了他,这是十八世纪禅僧Shisui在临终前写下的。整首诗只有一个圆,“一个封闭的空洞,一种无尽的神秘,无限的呼吸,巨大的轮,永恒回归:圆——乃直线的反题”。
直到自己临终,埃文斯才明白了这首无字俳句的另一层涵义——跟随幻觉、不顾一切向前行的动力,这样才能继续生命的循环。他的临终遗言是:“先生们,前进,向窗台冲锋!”(小说人物因卧病在床,体力所及之处只达到窗台而已——译注)
然而小说并没有以这些临终遗言结尾。尾声是以闪回的形式完成的。加迪纳被溺死在粪坑后,埃文斯收到了一封妻子的家书,告诉他一个错误的噩耗——艾米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了。尘埃飞舞的意象又一次出现了。埃文斯无助地盯着煤油灯的火光:
他望着光,望着煤灰。好像有两个世界似的。这个世界是隐蔽的,但是真实的,尘埃飞舞旋转,发着微光,任意碰撞,于是新的世界诞生了。
他拿起一本书,讲的是真爱故事。但最后几页没了,大概是被哪个犯人撕下来当了手纸。他放下书,走到暗处的竹林小解。回营房的路上,他发现黑色的淤泥里半掩着一朵绛红色的花。他用油灯照着“这小小的奇迹”,在倾盆大雨中弯下腰细细观赏,然后直起身,“继续走他的路”。
淤泥中的红花这一形象,很醒目,但也有些乏味扭捏。但它与这部非凡的小说的整体语调是协调一致的,那就是对战争绝无多愁善感(只对诗歌除外),更别说什么阳刚考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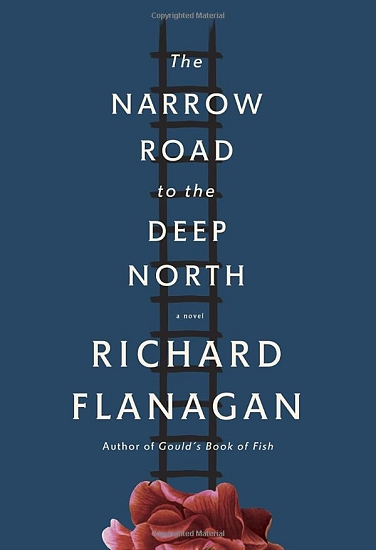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