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性别是条毛毛虫》作者:我们还处于跨性别社群的草创期
【编者按】12月18日,为回应外界的猜测,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博客上宣布自己是异性恋,并已经跟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伴侣同居17年了,“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的Transsexual(LGBT中的T,跨性别者),他所爱的只能是异性恋女人,而不是同性恋女人。”
跨性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凯特·伯恩斯坦的《性别是条毛毛虫》一书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该书中文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凯特·伯恩斯坦是一位先锋跨性别作家、表演艺术家、剧作家和演说家,本书是对伯恩斯坦从一个异性恋男人到一个同性恋女人、从一个IBM推销员到一位戏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之转变历程的叙述。
作者以幽默、坦诚而极富文采的笔触,讲述了一个跨性别女人的故事,她从未停止对我们文化的核心假设的质疑。无论当她详述自己变性手术的点滴细节,还是当她揭露流行文化中暗藏的性别玄机。本文由新星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经过编辑删减。

我着了魔,而就像大多数着魔的人那样,我自己总是最晚才知道事实。我们的文化也对性别着了魔——而一如既往地,文化将是最后一个发现自己是多么痴狂的人。
我们从来不曾适应男性/女性、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的文化二元论。我们是些小丑,是性的客体,是无数小说中神秘不可捉摸的人物。我们是精神病患者,是凶手,是充斥电影的犯罪天才。观众们很少亲眼看到跨性别者的真实面容。他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看不到我们书写的文字。太久以来,我们跨性别者都在玩着一种躲藏的游戏,戴着面具出现在城镇中,并且在被发现真实面目之前逃遁。我们绝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们是谁,因此,我们也从来无法发现彼此。这一切现在即将改变。
仅仅呼吁“出柜吧出柜吧,不管你身在何处”是无法让不计其数的跨性别者真正出柜的。在我们声称出柜是一种选择之前(而我也相信出柜是必然的一步,我们都会有跨出这一步的那天),必须先让跨性别者开始相互交谈。向他人出柜的第一步乃是向自己的同类出柜。
另一个让跨性别者保持沉默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将变性欲望视为一种疾病,一种只能被沉默所治愈的疾病。
还有一个促使跨性别者保持沉默的原因,则是跨性别亚文化本身的一种迷思。这个迷思认为,两三个变性人聚在一起,别人就更容易识破他们是变性人——这样他们就无法蒙混过关了。我可不信这一套。
我认为,变性人相互回避,因为我们都戳到了彼此的痛处。
我们每个人,不论是不是变性人,都从小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以此让我们的经验变得可信,使我们的存在变得合理,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具备的疯狂辩护。不是变性人的大多数人,可以把自己的世界观泊靠在文化的规范之上,而所有的杂志、电视、电影、电子讯息公告栏以及与日俱增的无数传媒手段都会宣扬这种世界观。
而变性人在这个文化中既得不到媒体公正而准确的呈现,也得不到社会的尊重,所以我们的世界观是在孤独中形成的。孤独之中,我们摸索得出自己遗世独立的缘由。迄今为止的所有关于跨性别经验的文献,都无法帮助我们形成一种与其他跨性别者一致的跨性别世界观,因为迄今为止的所有性别理论和变性理论都不是由变性人自己写成的;不是变性人的作者们,无论多么出于善意,也不过是在努力让我们嵌入他们的世界观之中而已。而跨性别者早在幼年就已开始学习如何向自己解释性别了。
多数变性人选择相信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没有中间地带的理论:他们赞成性别体制。曾几何时,我亦如此——我只是知道我必须二选其一——因此,在我的世界观里面,我觉得自己是个错误:一件需要被修理的东西,修好了才可以天衣无缝地放进其中的一个类别里。
变性人自己发展出来的世界观有着非常微妙的差异。只需和几位跨性别者交谈一下,你就会发现,从前看似寡淡无味的性别概念,其实是多么丰富而细腻。
在和其他变性人的接触中,我们带入了对自我存在的独特解释,而其他的变性人也毕生都在建构他们自己存在的理由。相见之时,如果我们的世界观迥然不同,那么我们就会威胁到彼此对这个世界的基本信念——我们会威胁到彼此。所以,与其不欢而散,不如老死不相往来。
在我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了。变性人和其他的跨性别者终于坐在一起,彼此了解,彼此对照——而我们发现,原来是主流文化出了问题。因为共聚一堂,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接纳自己、接纳彼此。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向这个要求我们缄口不言的文化发出抗议。
我们所处的这个文化倾向于牺牲掉经验的个性,以保障一种可被更多人接受的共性。结果,我们有了麦当劳,却吃不到真正可口的食物;我们到处修建度假旅馆,却找不到一个真正宜人的家;我们整天读着《今日美国》这样的无聊报纸,却看不到针砭时弊的时评和社论。如此情形,俯拾皆是。
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跨性别亚文化也正在形成之中;随之出现的,是关于性别流动和性别模糊的一些常见说法。以下便是几例:
1、我们是神的选民。
这是许多群体的观点,而非跨性别者的独创。这个观点让我感到不安,而我通常也会主动脱离任何一个自诩和至高无上的力量颇有渊源或者受其惠顾的群体。
2、我们是正常的男人和女人。
真的存在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吗?我的想法是,只存在人,而人的性别是流动的,但是关于正常的规范使得人们不停地挣扎着去相信一种幻觉,相信自己属于某一种性别。所以,如果有人经历了性别改变,然后挣扎着保持一个新的僵化的性别,那么这个人就正常了。这就是我对此迷思的理解。
3、我们是比原生男人或原生女人更优秀的男人或者女人,因为我们是经过努力之后才办到的。
这个我可不确定——我认为每个人都得努力,才能成为男人或女人。跨性别者可能只是对其中辛苦更加心知肚明,如此而已。认为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优越的想法,根本就不是一种充满爱和包容的想法,而是一种旨在制造压迫的想法。
4、我们罹患了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
并没有。
5、我们被错误的身体所囚禁。
我理解很多人会如此解释自己手术之前作为一个跨性别者的生活经历,但我相信这只是为了符合文化的期待而随手采用的一种经不起推敲的比喻罢了,这并不是对跨性别感受的诚实反映。人们其实短于用喻,所以一旦有个比喻还算差强人意,人们就不再追索下去了。是时候让跨性别者开始追索新的比喻了——这样才能让更多生活在迂腐性别里的人理解我们的生命。
6、我们受尽了各种剥削利用。
说这话的人真是自命不凡,而且不知人间冷暖。我是从一个还没做手术的、中产阶级白人男跨女变性人那里听到这个说法的,此人自己就还是个医生。我猜她大概不了解非裔美国人当中那些少女妈妈的悲惨生活,更别说另外一些处境更惨的族群。变性人确实在这个等级制的社会中遭受着诸多苦难,但也不要井底之蛙地以为我们是唯一受苦的人。
7、存在一个跨性别社群。
有人曾问我,跨性别者的社群是否就像男女同性恋者的社群那样。我说不是,因为男女同性恋社群是基于亲密关系的对象,而跨性别就不一样了:它是基于身份——和自我相关的认同。这是一种更加内在的东西。这群人聚在一起是因为都怀着对自我的追问,这个群体的状态和别的群体很不一样。(戴维·哈里森与凯特·伯恩斯坦的交谈,19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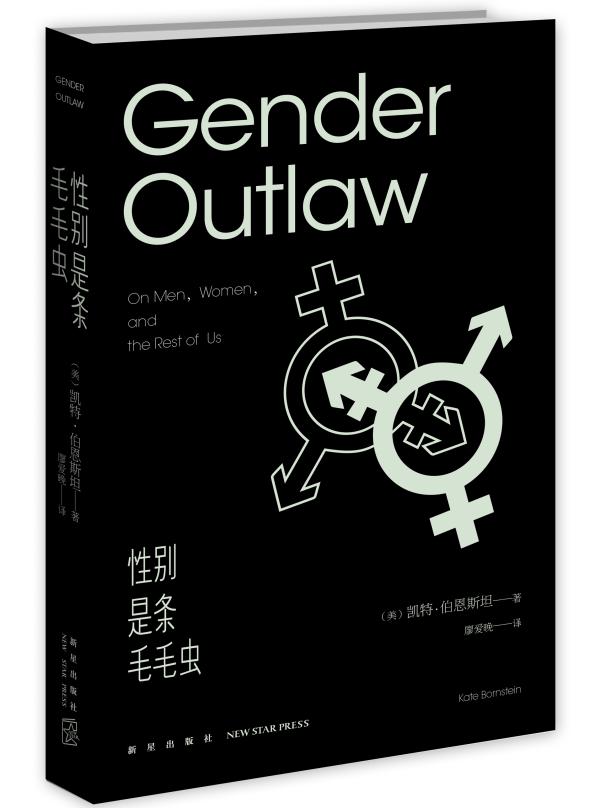
我已经发现在一些男跨女性别逃犯的群体中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这种等级是根据你恰好穿什么样的鞋来确定的——高跟儿鞋还是“锐步”运动鞋。
手术后的变性人(也即那些已经接受生殖器手术,并且全部时间以另一个性别角色生活的人)高高在上地俯视着——
手术前的“易性癖者”(也即那些全部时间或部分时间以另一个性别角色生活,但尚未接受生殖器手术的人)又瞧不起——
跨性别者(也即那些以另一个性别角色生活,但很少或根本不打算接受生殖器手术的人)又受不了——
人妖(我的一个人妖朋友如此自述:“大波,长发,浓妆,再加一根屌”)嗤之以鼻的是——
扮装王后(也即那些偶尔以穿着各式女装为乐的男同性恋者)又嘲笑那些——
公开的易装者(他们通常是些异性恋的男人,公然展示他们自以为是的女装形象)又可怜那些——
尚未出柜的易装者(也即那些无法公开进行变装行为的人)又对手术后的变性人鹦鹉学舌。
与上面这些中产阶级白人的例子相比,女跨男的群体以及一些我所知道的劳工阶层的跨性别俱乐部,似乎在成员身份和出席要求方面都更加宽容一些,在俱乐部的规定和成员的互动方式上,也不那么等级化。但是,几乎没有哪个群体可以呈现性别越界的完整光谱,很不幸地,大家仍然以男跨女和女跨男为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我很乐意哪天成为一个社群的成员。多年来我迟迟没有改变性别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将会成为一个局外人。所有类型的跨性别者在一点之上都有共通之处,那就是我们都违反了一项甚至更多的关于性别的律法:我们的共性在于我们都是性别逃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把我们井然区分的企图(你是易装者,你是扮装王后,你是人妖,诸如此类),无异于把固体的定律强加给液态的物质:正是流动这一特性让我们彼此联结。正是这种不息的流变和持续的涌动,造就了这个日新月异、海纳百川的跨性别社群。
我将会甘愿成为一个社群的成员,但前提是这个社群以这种永恒的变化作为自己的原则;成为一员意味着要遵守更多规矩,但是围绕性别而订立的任何规矩都让我心有不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