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访谈︱台湾社会还没有进化到文化公民的阶段

彭怡平是个很难被定义的人。她在台大读历史,巴黎读电影,学很多门外语,写作、摄影、旅行、策展、拍纪录片,关注电影与美食。最近她做的“女人的房间”纪录片,跨界得“更不像话”。她说自己有偏执狂,知其不可而为之,执著于以自己的方式,带着年轻人去了解文化与艺术,去看外面的世界,“做得挺开心的”——她说自己不信教,“但我相信只有傻子才能进天堂”。她的新书《米其林大厨》,正好把她所喜欢的法国文化、美食和摄影融为一体。
台湾媒体不知道怎么称呼彭怡平,干脆叫她“艺术家”。她自己,则希望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弥补一些社会的不足。她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人都应是文化公民。台湾社会还没有进化到文化公民的阶段。

彭怡平:我留学法国就是因为一颗苹果。当时曲德益——他现在是关渡美术馆的馆长——在“国父纪念馆”旁开了家咖啡馆,他用一颗苹果做了热腾腾的苹果派,调了一杯非常好喝的鸡尾酒。我还是大四学生,去哪个国家还举棋不定。我还记得问他:“法国有多少用苹果做的料理?”他回答我说:“三百多种。”我就非常震惊,想这个国家的文化一定非常细腻。于是毫不犹豫地就留法了。我为什么这么在意饮食?不是因为特别想要吃法国菜,(而是)因为从里面可以学到非常不一般的东西,细腻到尖端。我一到法国就去看跳蚤市场,看他们怎么摆摊,摊上有什么东西。当时我的法文就已经很好了,可以直接和他们沟通。
澎湃新闻:您的法文是怎么学的?
彭怡平:我都是在台湾学的。其实我学语言没什么诀窍,因为当时的学校都很烂,老师都很懒。我那个法文老师特别的法国,课都爱上不上的。每次我打电话叫老师来上课,他都一副吓死了的样子,“怡平,我这次真的生病了,没有骗你”。我算是个蛮主动的学生了,会读很多法文小说,看很多法国电影,算是通过一些周边的东西,触类旁通地学会了。学其他外文,像拉丁文,也都靠自学。
澎湃新闻:您到法国,是在巴黎索尔本第一大学读的电影专业,能谈谈当时的情景吗?
彭怡平:我的入学考试是在巴黎一大一个两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题目一发下来,好多人都不会写:法国的实验电影。一般考电影学院的学生都是学名门正派的东西,我看的东西又杂又偏门,一看这个题目就乐了,下笔如有神。那一年,我是唯一一个考中的亚洲学生。其实是法国用它独特的方式选择了我,不是我选择了法国。我在法国既不想家,也非常的快乐,比在台湾快乐一百倍一千倍。法国大学非常自由,再也看不到台大那种抄笔记,所有学生都非常慵懒,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而且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大学没有围墙。我觉得太棒了,一上完课,走出教室就是社会。它鼓励大学不和社会脱节。我的所有老师都是不同领域的学术权威,比如埃里克·侯麦。我刚上他的课的时候非常兴奋:这可是侯麦耶!可是法国的学生都不怎么鸟他,因为他说话很慢。而我看到了,一个导演怎么用很少的一百万拍出很棒的电影。我现在办展也是要灯光、场地、人员都要投入最小,我一直寻求用想象力代替预算不足,太多预算反而限制我的发展。这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习惯,对我影响也很大。像楚浮(编者按:即特吕弗)和高达(编者按:即戈达尔)后来分道扬镳,就是因为高达越拍越贵。
澎湃新闻:法国教育对您的影响真的很大。
彭怡平:法国很多艺术家都是从一而终,一直走他自己要走的路,非常忠于自己的内心。台湾的教育训练出来的小孩都像变色龙一样,这样经过几十年,你再去看就很恐怖。我现在回看我的高中同学,就像看到我妈那一代人一样,精神状态非常的老,他达到某种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摧毁了自身的很多东西。可能我自己也比较特殊吧,我的父亲现在还是常常对我讲:“小平,我真觉得你是抱来的。”我和家里其他小孩都不一样。我先生也喜欢讲我是抱来的。我的父亲最开始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教育我妹妹,后来他就会抱怨我的妹妹,说她没主见。其实还不是因为大人希望孩子走他希望走的路。所以再说回到法国,我写的《米其林大厨》也好,其他什么书也好,其实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并不是刻意要去表达法国怎么样。我觉得法国某个东西,台湾没有,大陆没有,那么我就要把它写成书。我是想要通过书籍这种最古老的方式寻找知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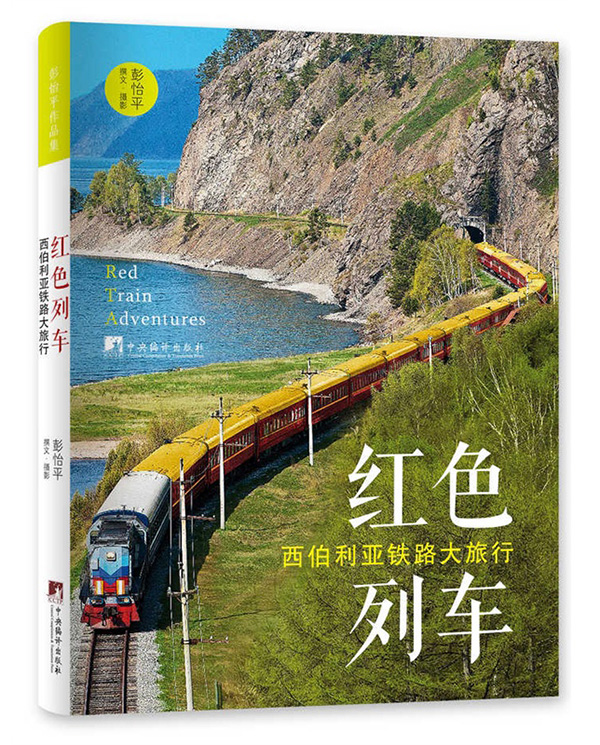
彭怡平:我采访了四十多位大厨。其实也不是采访,我有我自己的方式。他们常常以为我是米其林的秘密试吃员。我一个人去,常常对着菜肴自言自语,做很多笔记,觉得有问题还是把经理叫过来当场批评。这些大厨其实脾气非常古怪,他们通常不会和食客有来往,也很讨厌记者,他们觉得记者都不懂厨艺,性格很傲慢。有位大厨听说记者来了,拔出枪来就要追记者。每个大厨的性格不一样,对料理的理念也不一样,我的目的就是通过和他们沟通,找到他们想说的话。我其实就是一个解答秘密的人。后来不少大厨和我成了好朋友,我看到的不仅是他们的餐厅,更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怎样去构思、去选择。他们也乐意请我去试吃,我觉得自己好像料理的化学分析师一样,可以很快地把某个料理的好处坏处、需要拿掉什么、需要增加什么说出来。
澎湃新闻:您平时下厨吗?
彭怡平:会啊。老公第一次吃完我做的料理之后,觉得我是一个贤妻良母,后来发现我不常做,变得非常沮丧。我大概天生就擅长对味觉的搜索。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不会做菜的妈妈,她一做菜,我就想尽办法不要在家吃这一餐。当然,她会很沮丧,但是我爸会留下来。我爸是一个很喜欢给孩子做料理的人。他是外科医生,非常忙,但是周末他在家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在外面吃到的东西讲给他听,用什么食材,什么味道,怎么做。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在分析料理了。
澎湃新闻:您和法国大厨沟通的方式就像和您父亲一样。
彭怡平:对。其实非常简单。有些味觉的新经验也是我不知道的,我会去不断地研究菜单。法式菜单很好看,里面有很多秘密,我会想办法从里面找到一种思维模式。我很喜欢搜集全球各地的菜单。法国有一个米其林三星大厨叫亚伦·松德汉斯,他跟我一样,他有一间密室,是一个圆形的房间,里面挂满了全世界各地他最尊重的大厨的菜单。这简直是他神圣的殿堂。
澎湃新闻:除了收藏美食菜单,您会关注这方面的书籍和电影吗?
彭怡平:会啊。比如《味觉的生理学》,我简直爱死它了。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就是美食和电影。写完论文之后,我的教授有一年没上课,他也跑去写书了。我的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再修改一下,就成了我的饮食三部曲的第三部。阅读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光是美食的书。我最近在读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太美了,我简直遇见知己了。我还喜欢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骂观众》,让我觉得非常具有反叛性。我也很喜欢大江健三郎。我喜欢的可多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我也很喜欢读哲学,东西方的都喜欢。历史就更不用说了。它们都有一个共性:优雅。有的作家刻意追求粗糙,觉得代表生命的活力,我觉得你可以选择粗糙,但是粗糙里面也要有细致的东西。电影的话,我看得真的很杂,最近在看瑞典导演洛伊·安德森的人生三部曲,我非常迷这个电影,觉得太好玩了。很多人在电影院里会看睡着,我却看得津津有味,这个导演到了七八十岁还可以这样去调侃人生,用影像讲这样一个故事。


彭怡平:所以他们都叫我“艺术家”。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在某些方面弥补台湾社会的不足。台湾社会现在还没有进步到文化公民阶段,文化方面这是最有待进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刺激大量年轻人去创作。我现在还在成立一个文化基金会,我死之前身上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块钱,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投注到文化艺术上面。文化对我来说是毕生所要从事的志业,也是我到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最重视的议题。当你讲这方面的话题时,肯定有很多人还不懂,但我想,文学家、艺术家,就是应该看到大多数人还没能看到的东西。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