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陈雁丨挑战成见:中国妇女/性别史的研究革命
文_陈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妇女/性别史进入中国学界已有四十余年,但关于妇女史与性别史的定义仍有诸多争论。我很喜欢美国历史学家凯伦·奥芬(Karen Offen)为《牛津世界妇女史百科全书》(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Women in World History)所写的“妇女史”条目,她在对妇女史进行定义的同时,也说明了性别史是什么以及妇女史与性别史之间的关系。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Women in World History
Bonnie G.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妇女史包括了男性在内的全人类的历史,但从女性中心的视角处理问题。它突出女性的活动与观点,宣称在讲述人类故事时,她们的问题、观点与成就与其兄弟、丈夫和儿子的共同处于中心地位。妇女史把各性别(sexes)或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置于历史考察的中心,质疑女性的从属地位。它检验了在一种或多种文化中,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建构的密切关系,为其连续性和演变寻找根据。妇女史揭露并遭遇了早先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编纂方式的偏见,质疑为何某些特定的学科与研究主题特别受到偏爱,并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时间上,从史前到现在,空间上,从西方到全球,从事妇女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极大地扩展了妇女和社会性别的研究范围。[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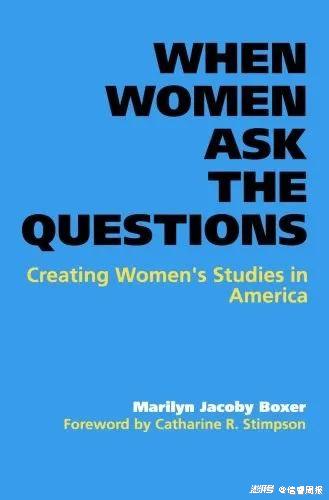
Whe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Marilyn Jacoby Boxe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妇女/性别史研究不只是把研究对象转向妇女,而且从女性中心的视角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为人类漫长的性别不平等历史找到原因,开出解方。美国妇女史学家玛丽琳·J.波克塞(Marilyn J. Boxer)1998年出版的专著,记录了美国妇女学研究从萌芽到发展的历程,书名《当妇女提问时》[2]来自诗人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的诗句——“我们不是别人提出的‘妇女问题’;我们是提问的妇女。”[3]不管是历史学家波克塞还是诗人里奇,都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投身美国妇女运动,也是美国妇女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创立者之一。在她们或学术或文学的写作中,都注重妇女的个人体验和生活经验。半个世纪前,美国学界的性别生态与今日大相径庭,当历史学家关注妇女史,当女性学者基于性别经验提出新的问题、引入新的视角,当妇女能够提出问题,而不只是被当作问题来研究时,新的或以往乏人问津的史料受到关注,新的或修正性的研究范式得以提出,妇女/性别史前所未有地挑战了历史学的一系列成见,并开垦了大量新的研究领域。本文不是对妇女/性别史研究作整体性的学术回顾,而是对中国史研究领域内妇女/性别史学者已经取得的学术革命的致敬。

1928年,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陈东原出版《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开启了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在对传统中国习俗、制度、规范等方方面面对妇女的压迫展开论述之后,陈东原提出了“压迫—解放”这一范式,“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的历史!”陈东原声称要“燃着明犀”,照亮压在妇女头上的巨石,把妇女从封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然后便知道新生活的趋向了”。[4]这一范式多年后被哥伦比亚大学的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称为“五四妇女史观”,如果传统妇女不是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压迫之中,那所谓“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无从说起了。而如果没有解放运动,又从何建构一幅现代的、新中国的蓝图?传统中国社会只有受害、受压迫的封建女性,高彦颐认为,这一分析结论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缺少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考察其所身处的世界,从而造成了将标准规范直接等同于历史发展实际情况的混淆。[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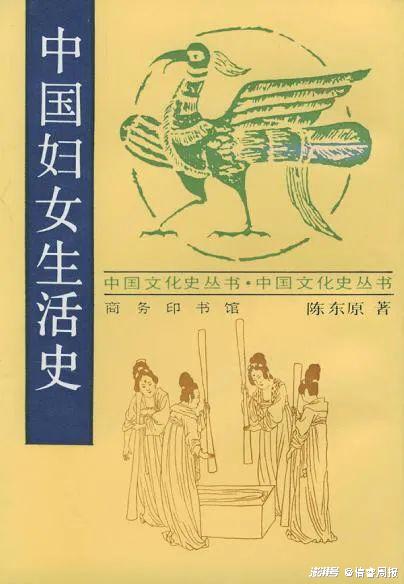
中国妇女生活史
陈东原 / 著
商务印书馆1998
其实对“压迫—解放”范式,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末就已经有过检讨。比如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主任的郑必俊教授,她在检索《四库全书》搜获千篇宋代妇女墓志铭后发现:女人作为母亲在家庭生产、理财和人情交往上都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在家庭之外,她们还是市井文化的传播者、创造者和创作源泉。[6]近二十年来,海外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大量成果涌现。比如,李国彤的著作《女子之不朽》通过大量的文本解读,让读者看到传统中国女教的发展,绝不仅仅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些大而化之的僵化教条所能代表的,即便是男性话语主导的旌表制度、墓志铭等对现实生活中女性角色给予的肯定,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那些被陈东原视为巨石的压迫妇女、摧残妇女的规范教条。[7]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利用大量女性写作完成的《张门才女》一书就旗帜鲜明地提问:“张家才女们的生活是被其后的中国改革家们视为愚昧和落后的。但现在倾听她们的故事时,我们不由要问:20世纪的‘新女性’究竟‘新’在何处?”[8]正是常州张家的女儿们——这些生活在帝国时代的中国妇女,凭着自己的持家能力、文学艺术修养,才使式微的士绅家庭得以生存和发展。这些妇女史家笔下的传统中国妇女史并不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历史”。

张门才女
曼素恩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处在新旧转型期的中国妇女史也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女权资源值得好好挖掘与继承。维新志士金天翮1903年在上海租界以“爱自由者金一”之名出版的《女界钟》一书,被认为是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妇女解放的著作。为纪念《女界钟》出版100周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在2004年举办了“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四大洲十个国家与地区的120余位海内外学者,并发表64篇论文。在新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中国的妇女解放与女权主义在以往的研究和表述中是被截然分开的,而这次大会成功地搭建了历史的链接,把过去百年间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置于世界女权主义的大背景下来展开讨论与重新评价。这次大会的成果对于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的意义是持续的,大会发表的部分中文论文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另有8篇论文作为Gender & History(《性别与历史》)杂志2006年的专号在英国出版。[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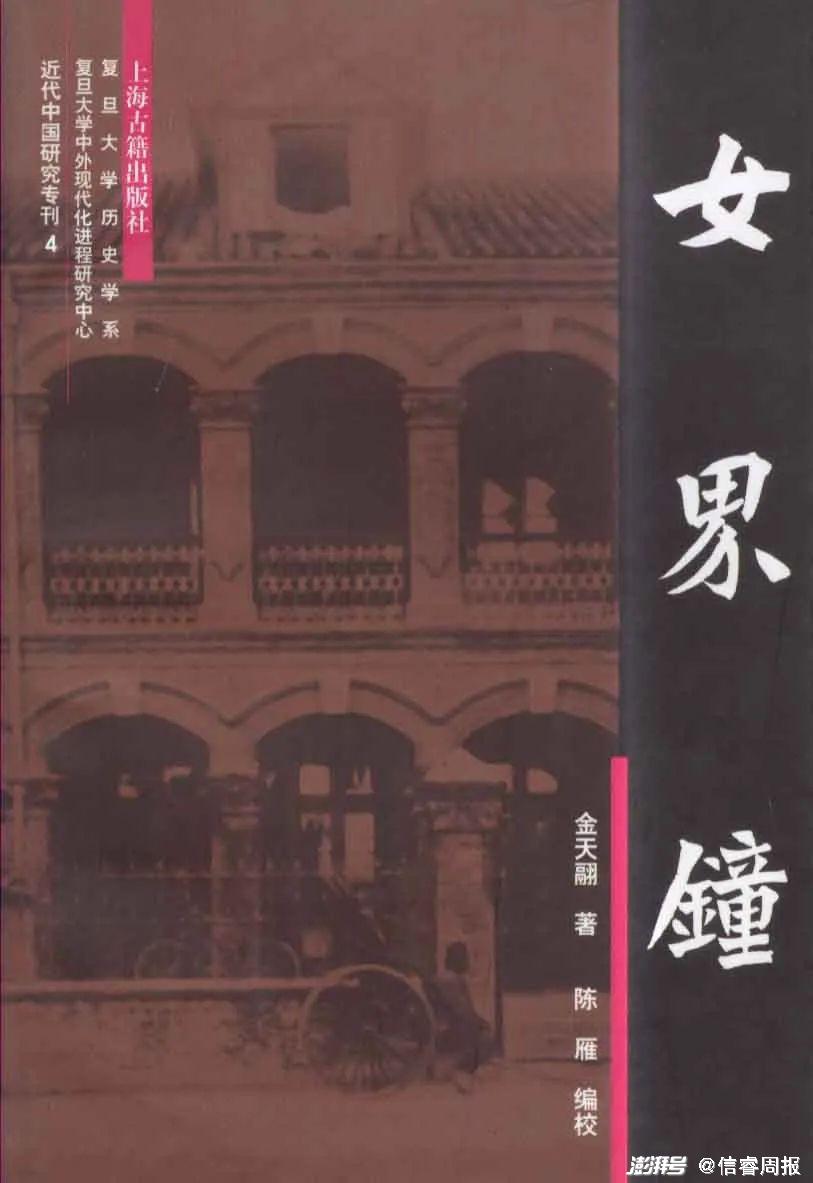
女界钟
金天翮 / 著
陈雁 / 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在《女界钟》发表110周年时,妇女/性别史家又有了鼓舞人心的发现。刘禾、高彦颐和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三位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全套的《天义》报,并在读到何殷震的女权写作后兴奋地合编了《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一书,指出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已有女权主义者明确地剖析了古代中国父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术和家庭体制诸领域的“男女有别”,进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在民族国家形态、私有制度、社会劳动中的性别歧视提出了富有洞见的批评。要知道,在何殷震写作的20世纪初,资本主义正被当成世界文明新方向受到中国男性精英的热烈欢迎。何殷震提出的分析方法对于当今跨国女权主义的理论建设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0]
中国人民大学的宋少鹏教授沿着这条研究道路完成的《“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一书,再次肯定了何殷震“女界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在无政府主义的框架下,何殷震的女权思想明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超越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文明论”,提出了“男女间革命”的方向。当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受限于政经体制而陷入瓶颈时,以何殷震为代表的中国女权先驱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为我们指出了新的方向,诚如宋少鹏所言,“无政府主义女权以及与这条脉络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女权开启了对另类现代性的探索”[11]。

女权活动或女权主义学术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当然深受西方的影响,但正如上述几项研究对中国自发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发现与肯定,值得被重新发现和再研究的还有来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女权资源。
将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socialist state feminism)这一研究范式率先用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当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王政教授。早在2005年发表于Feminist Studies(《女权主义研究》)杂志的“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国家女权主义”?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性别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一文中,王政就将原本用于研究北欧国家性别平等事业的“国家女权主义”范式挪用来讨论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女权努力。[12]
在2017年出版的《在国家中寻找妇女》(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64)一书中,王政说明了为何要将这些拒绝被称为“女权主义者”的中共干部命名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第一,是为了指出他们对五四运动以来男女平等观的坚守;第二,是要强调他们以妇女的“彻底”解放和为妇女“群众”服务为目标;第三,强调他们在党内或政府中的位置,是为了聚焦他们的女权奋斗是如何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改造,如何富有成效地促进了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的社会进步。王政对20世纪50年代城市的“妇代会”、全国妇联、中共文艺实践等的研究,将五四运动以来的女权实践与1949年以后的妇女工作有机联系起来,认为中共党内以邓颖超、蔡畅等人为代表的女权力量,巧妙地利用了体制内的资源,致力于解决性别和阶级的等级问题,并通过妇女组织发展有力地改造了男权文化。[13]
与王政主要关注城市和精英阶层不同,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贺萧(Gail Hershatter) 教授的著作《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是在陕西农村进行了长达10年的田野研究,与合作者高小贤共同完成了对72位农村妇女的访谈后写成的。农村+妇女,使这一数量巨大的研究对象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双重边缘的群体,而衡量社会主义革命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农村妇女又是非常重要的变量。依托口述完成的研究,呈现了以往的共和国史研究全然不关注的农村妇女的农事、家务、婚姻、分娩、育儿、道德观念等,展示了在基层农村党和国家的政策如何影响(或者不影响)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贺萧的研究早已超越了20世纪七八十代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妇女史时常常追问的“党和国家的政策对妇女是好还是坏”等问题,她让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关注性别,就无法理解中国革命;但性别绝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应该将性别放到一系列的权力关系中去理解。[14]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妇女运动、妇女解放和妇女工作上积累的经验展开历史性研究的努力,亦取得了不少成果。上海师范大学董丽敏教授擅长通过将近代以来丰富的文学素材与历史实践相结合展开分析,2016年、2017年她在《妇女研究论丛》发表了两篇讨论“延安经验”的论文,提出“家庭统一战线”的概念,并以延安时期的妇女纺织生产运动为例,肯定了当时妇女解放路径的有效性。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探索出的“家庭统一战线”模式有效地将性别与阶级议题相结合,集体合作生产模式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正是在“新妇女”建构的过程中,也正因为“新妇女”的参与,“新社会”才得以成立。[15]
北京大学的贺桂梅教授则从“人民文艺”出发,通过《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巧儿》等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来总结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叙事与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她特别强调中国妇女解放理论与西方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差异性与综合性,从多重交互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性别制度出发,讨论女性群体的独特性,提出要重新理解人民政治实践从内部改造婚姻家庭制度的妇女解放路径。[16]从性别视角发掘这些“中国经验”正是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宝贵资源的继承。与贺萧一样,这些国内学者也主动地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学者提出的“未完成的革命”论进行对话,指出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现实之间的不洽。首都师范大学的秦方教授在总结过去五年中国妇女史的知识路径后认为,“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妇女解放并不是一个未完成的、延迟甚或是失败的过程,而恰恰是一个通过摸索和探讨,能够形成有效的、切合实际的妇女动员和解放的模式(尽管也存在很多的挑战),这一模式反过来亦促成了中国革命的极大发展”。[17]所以,当我们从妇女/性别史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演变时,新的解释框架诞生了,女性活动的谱系得以重建。
王政在对全国妇联的研究中提出了“隐埋的政治”(politics of concealment)这一概念,认为上自邓颖超、蔡畅,下到基层妇联干部,共和国的妇女干部都甘当幕后英雄,擅长在党的中心工作名义下推动妇女工作、提高妇女权益。《婚姻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男女同工同酬的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劳保制度下56天产假的实行等都证明了“隐埋的政治”的成功,但也正因此,这一代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的努力在共和国历史中是隐形的。
今天继续这一策略是否仍能成功十分可疑。美国纽约大学的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教授在1983年出版的《父权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一书中认为,中国革命对父权制的挑战是极其有限的,但十多年后在对中国家庭与革命的关系进行再研究之后,她提出,“如果女权主义者想要成功地推动这场革命,就必须把‘后现代’社会中的革命转型放在中心位置,女权主义要在一开始就处于中心位置,成为半自发的力量。这种女权主义立场表面上看有种战斗性,但也具有反讽意义的效果:它证明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一些中心论断是有效的。它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是之前资本主义未能实现的承诺——在这场革命中,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富足应该从少数特权人的手中转移,变成所有人的权力”[18]。今天的妇女/性别史研究,除了要深入发掘中国女权思想与实践的宝贵资源,还必须同时关注女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对造成歧视、形成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社会制度进行全面的、历史的检视。

2000年,曼素恩教授为《美国历史评论杂志》(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组织了一个中国男性史研究专题,并撰写导读《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男性纽带》(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她指出,中国的性别史研究需要大力发展男性史,并认为以下原因阻碍了这一领域的发展:首先是中国史学界有待发展“性”的历史研究;其次是中国学者对男性研究和男性历史研究的价值认识不足;第三是对妇女史的强烈兴趣反而造成了对男性历史的忽视,过度地关注父权制和男性支配的问题,其后果就是使得“性别史=妇女史”。在曼素恩发出这些批评之声的21年后,中国史学界中的这些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变。沉迷于妇女史研究的学者往往很容易将男人视作铁板一块,但实际上不论是男人身份还是女人身份都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能把男人身份当成与生俱来的本质——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就犯过这样的错误,男人身份、男性特质都是持续变化的。在历史变化的过程中,男人因为拥有雄性的身体而争取到了某种至今无法摧毁的权威,但这种权威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种文化中又是由各种彼此矛盾的观念构成的。今天对这些构成男人身份/男性特质的过程、观念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对于我们解构父权制的性别文化、拓展性别史研究的领域,都具有深刻的意义。要在这一领域有更多的突破,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这也是曼素恩曾经提醒过的:中国的历史学家要注意发展对性研究(sexuality studies)持续的兴趣,性研究也是欧洲和北美男人历史和男性特质研究的起点。
目前史学界最热门的概念非“全球史”莫属,妇女/性别史研究者能为构建全球史做些什么呢?当我们跳出民族国家的窠臼,以“全球史”的规模来写作妇女的历史时,可以关注哪些问题呢?以我熟悉的近代历史为例,女权观念的跨国流动(中国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女性的全球旅行(来华的女传教士、到欧美日去留学的亚洲女性、跟随父兄在美洲打拼的女性华侨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妇女,都会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近代以来,女权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展开妇女/性别史研究,对这一领域的意义不言而喻。
妇女/性别史研究者倡导研究视野下移,不只关注精英阶层,女工、农妇、家庭主妇、性工作者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并且已经取得了出色的成果。我在此想强调的是另一种视野下移,那就是要让这些挑战历史成见的妇女/性别史研究成果进入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在各种层次的考试中纳入与妇女/性别史相关的内容,培训和赋权历史老师,将学术成果改写为普及读物,用这些挑战性别成见的研究成果来激励年轻一辈的思想与生活,这样才有可能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观与历史写作习惯。
当妇女不再只是问题而是提问者,当历史写作将妇女的问题、观点与成就和她们父亲、兄弟、丈夫、儿子的一视同仁,当性或性别相关的社会政治关系被置于历史考察的中心,当妇女的体验和叙述——哪怕只是农村妇女的口述,成为历史的核心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编纂方式所带来的成见就会受到有力挑战,妇女/性别史领域就一定会成为知识生产的热点与增长点。
注 释
[1] “History of Women”,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Women in World History, ed. Bonnie G. Smith. 4 vol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B O X E R M J. W h e 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Creating Women's Studies in Americ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该书的中文版《当妇女提问时》由余宁平、占盛利等翻译,于2006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3] RICH A. Blood, Bread, and Poetry: Selected Prose[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6.
[4] 陈东原. 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8: 18-20.
[5] 高彦颐. 闺塾师[M]. 李志生,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2-5.
[6] 郑必俊. 两宋官绅家族妇女—千篇宋代妇女墓志铭研究[M]//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第六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17-140; 郑必俊. 宋代妇女与市井文化[M]// 李小江, 等. 主流与边缘.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222—237.
[7] 李国彤. 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8] 曼素恩. 张门才女[M]. 罗晓翔,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8.[9] 王政、陈雁. 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Ko D, WANG Z. Translating Feminism in China, A Special Issue of Gender and History[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该专号由陈雁组织翻译并于2016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书名为《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10] LIU H, KARL R E, KO D. The B irth of Ch inese F e m i n i s m [ M ]. N e w Y o r 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三位教授为该书合写的导言已译成中文发表, 参见: 刘禾, 瑞贝卡·卡尔, 高彦颐. 一个现代思想的先声: 论何殷震对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贡献[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4(5)。
[11] 宋少鹏. “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2] Wang Zheng. "State F e m i n i s m" ? G e n d e r a n 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J]. 2005, 31(3): 519-551.
[13] Wang Zheng. Finding W o m e n i n t h e S t a t e : A S o c i a l i s t F e m i n i s 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M]. Berkeley: UC Press, 2017.
[14] 贺萧.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5] 董丽敏. 延安经验:从“妇女主义”到“家庭统一战线”—兼论革命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生成问题 [J ]. 妇女研究论丛, 2016(6); 董丽敏. 组织起来:“新妇女”与“新社会”构建—以延安时期的妇女纺织生产运动为中心的考察[J]. 妇女研究论丛, 2017(6).
[16] 贺桂梅. 人民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与女性形象叙事:重读《白毛女》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0(1); 贺桂梅. 人民文艺中的婚姻家庭叙事与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J]. 妇女研究论丛, 2020(3).
[17] 秦方. 在历史与性别之间—大陆地区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知识史路径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0(11).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可以关注《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集刊第8辑“妇女专刊”,该辑由宋少鹏主编,收录的10篇论文集中讨论了过去百年中国妇女解放的议题,尤其关注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
[18] 朱迪思·斯泰西. 寻找关于家庭与革命的新理论: 思考中国案例[M]// 冯芃芃, 等译. 社会性别与社会读本,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45-56; 她关于家庭研究的成果还可以关注Judith Stacey. 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 Rethinking Family Values in the Postmodern Age[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7.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54期)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