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国内思想周报|中国学界上了“影响因子”的当吗?
中国学界上了“影响因子”的当吗?

“影响因子”在今天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究竟有多重要,恐怕无需赘言。不但科学界将它奉若神明,而且人文社科学界,也对它顶礼膜拜。但它的权威性真的无可置疑吗?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江晓原、穆蕴秋两位学者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与研究,惊人发现“影响因子”只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盈利产品,从一开始就没有“学术公器”的性质。直到今天,它制造出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几乎没有真正代表过学术科研的真实水平。然而国内许多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却完全没有看到,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正在实际上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在这组系列文章的第一回合里,作者从“影响因子”及其商业公司的背景、重点产品、盈利模式入手,对这套评价体系进行了一次大起底。
“影响因子”其实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一项盈利产品。“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 )逐年发布的“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CI)和“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简称JCR),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本质上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
许多人误以为它们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而实际上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1992年又被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购。只是ISI的这一商业性质,多年来一直不太为普通公众和许多学界人士所知。

其创立者尤金·加菲尔德1925年生于纽约,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学位(1949)和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1954),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结构语言学博士学位(1961)。1956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加菲尔德已经注册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推出了第一款信息产品《目录快讯》,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
1960年加菲尔德迎来了他事业的转折点。这年他将公司改名“科学情报研究所”,与美国国家健康学会合作,获得国家科学基金(NSF)三十万美元,共同承担建设“基因文献引用索引库”项目。该项目对1961年28个国家出版的613种期刊两万册以上的140万条参考文献建立引用索引,进行编目,最终结果共五卷,其中基因类文献引用索引独立成一卷。1963年该项目顺利结项,加菲尔德原指望国家科学基金继续提供资助,将余下四卷一起出版,但他的申请未获批准。加菲尔德于是决定自己来干,独立出版,并将五卷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即科学界现今奉为圭臬的SCI。
加菲尔德在推销他的产品时,手法高明而且不遗余力。他的关键手法之一是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他利用1964年首次出版的1961年度SCI报告,统计了1961年257900位学者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情况,又统计了1962、1963年产生的十三位物理、化学和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引用情况,数据表明,该十三位学者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一年,他们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平均数量和次数远高于一般水平。
从表面上看,这确实表明优秀科学家群体有着更高的SCI论文被引用数,但这并不足以支撑加菲尔德的论断:SCI论文引用数可以反过来用于评估单个学者的学术水平。江、穆两位作者详细研究了加菲尔德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数据,发现他对数据的处理和使用至少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加菲尔德非常明显地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呈现”。第二,加菲尔德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第三,没有明确预测的有效年限。
1988年,加菲尔德把“科学情报研究所”超过50%的股权卖给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1992年4月,汤森路透以2.1亿美元价格收购了JPT出版公司。据汤森路透首席运营官说,这项交易主要是为了得到“科学情报研究所”,当时“科学情报研究所在全球拥有三十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一千五百万美元”。
至于如今汤森路透旗下“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盈利规模,作者披露了一所国内著名“985”高校的有关情况以见一斑:该校目前订阅了汤森路透七种信息产品——Web of Science(包括SCI、SSCI、A & HCI 等)、JCR、BIOSIS Previews(生物科学数据库)、CC、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德温特专利情报数据库)、Essential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ESI)、ISI Emerging Market(ISI新兴市场信息服务),该校每年为此支付的费用超过两百万元人民币。
想想全中国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全世界又有多少所类似的高校,而且国外许多高校在购买此类数据库时往往比国内高校更为慷慨,再想想“科学情报研究所”在1992年就有30万客户,就不难想象加菲尔德创建的“信息帝国”如今的盈利规模了。
此文只是起底“影响因子”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以《琅琊榜》作比:加菲尔德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梅长苏,“科学情报研究所”就好比学术江湖的江左盟,而他们卖信息赚大钱的行事倒很像琅琊阁;那么“麒麟才子,彼岸加郎”有没有暗中辅佐的靖王殿下呢?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也是有的,那就是Nature杂志了。
费孝通如何读韦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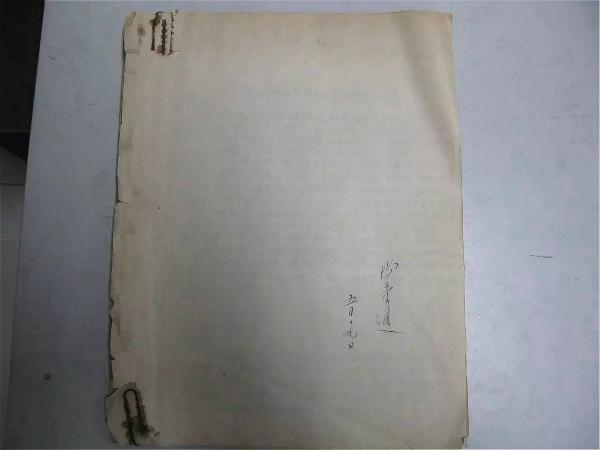

上周国内学界另一大热点是,中国人类学评论网发布了“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 研讨座谈会实录”。该座谈围绕几年前在原燕京大学阁楼上发现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的一份手稿,是费老阅读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的思考。
发现的这份手稿为什么这么重要?
首先对费孝通的个人学术史来说,王铭铭指出多方讨论后有个共识:这份手稿是费孝通在魁阁时期或前期的作品。学界通常把1936至1939年称为费孝通的“江村时代”,他完成了《江村经济》一书,那段时间他对现实中的中国工业化怎么走更为关心;1939年至1943年,在费孝通领导之下,为了躲避轰炸,在一个小庙里建立起一个类似于伦敦经济学院的地方,可谓是费孝通的“魁阁时代”,理论兴趣更强,尽管《禄村农田》延续了《江村经济》表露出来的现实关怀但他偶尔也表现出神话学和宗教学式的焦虑。
王铭铭还表示,费老这篇佚文启发他思考:在选择理论的时候,应该把自身当作选择的主体,而且对选择的东西采取消化的态度,但问题在于,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有消化外国理论的“胃”?费孝通的“胃”使他能“消化”。比如,早期他对反思性的绅士的崇尚,在他看来,绅士是不完全适应现代化的,只有反思性的绅士,甚至是像他自己说的,技术化的绅士,就像他姐姐费达生,是消化西方文化的“胃”。他早期对于绅权和士绅还有相当多的批评,而晚年提倡“文化自觉”这套理论,因为他更加受到钱穆先生的新儒学的影响,更有儒学化的倾向。这个是不是他的“胃”?士绅和文化自觉是不是他的“胃”?也很可能并非如此,因为他或许很早就开始思考宗教的问题,比如这篇佚稿中表现出的对宗教的兴趣。
其次对中国社会学史来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苏国勋指出,过去一直认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很少有人论述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费老这篇佚文的发现可以说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费先生在英国留学期间从英文学术书刊中接触到韦伯思想,大大地缩短了与国内在认识韦伯思想上的时间差,仅从学术交流史上看,它把中国社会学对韦伯思想的借鉴和研究提早了几十年,就具有很高学术价值。”
苏国勋认为费老的佚文,对韦伯思想的把握和对韦伯本人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这点在当时尤其难能可贵,因为那时韦伯的著作除了《新教伦理》外都还没译成英文。费老的佚文仅据《新教伦理》一书的论证视角评价说:“韦伯创舍弃推求社会现象之因果关系而注意社会中各种现象之关系论,他不否认经济基础在社会现象中之地位,而反对将一切社会现象归于一种原因之定命论(意即决定论——引者注)”。这不仅与从后来才问世的韦伯其他著作得出的见解吻合,而且也与当前大数据时代的科学弱化对因果性的渴求,代之以相关性扩大因果性的内涵的做法相契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社会现象单单决定于经济基础属于一种偏见,并不能解释一切现象。“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并没有一定谁是因谁是果,它们都是生活系统中的一部分。生活系统经常向着调合和统一的路上去”。社会学的追求在于使人明了“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如何调合,并不是要讨论宗教和经济在社会现象谁是因谁是果”——苏国勋表示,费老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辞说明了韦伯的思想以及费老当年的评价都具前瞻眼光。
苏国勋还提到,1990年代费老晚年曾多次谈到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从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的问题。“重视精神、观念、习俗、文化的作用,本身就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学术的一种传统,它在费老的思想发展中也是其来有自,这篇佚文即是佐证。费先生之所以在90年代多次谈及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毋宁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明显上升,以及社会学恢复以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经验性的社会研究上,甚至是对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社会工作——的一种反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认为王铭铭提到的学术之“胃”是个重要问题。从这篇佚稿可以看出,费老是一个心性上比较中国化的学者,有着中国人本身的问题感和问题化的方式。因此,他读西学的东西,读出来的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今天的学者来说,也是需要揣摩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要细致地发现,费老从韦伯那里读出了什么,这是他反映他学习过程的一个文本,也是我们再次进入中国社会学脉络的一个文本。”
渠敬东认为费孝通读韦伯这本书是有选择的,他选择了“生活系统”这个范畴作为理解韦伯的整体问题之出发点,这是中国人非常容易理解的。这其实说明,他在研读本书的基本经验意识上,已经不那么西方了,他的思考就紧紧围绕着我们的生活系统中都有哪些要素发生变化,哪些要素加入结构重组,哪些机制能够形成这样的重组过程,而不是仅仅就西方来谈西方,这样就完成了西学中国化的过程。
这个文本让渠敬东看到了读西学的核心问题:第一,对不同“生活系统”的人的样式和与政教关系的样式,要有一种知识上的理解;第二,要看到他在讨论自身系统里的问题的时候,哪些是该系统中的重要要素以及它们的构建方式是什么,这对于我理解自身社会的构成与变迁是有理论帮助和启发的;第三,这些要素并不是异文明拣选出的生活要素,而是我自身经验中的生活要素;第四,只有这样的理解过程,才能建立我与异文明的亲和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自身的系统是开放的,韦伯做到了这一点,其实就意味着已经进入我们生活系统的内部了。
“这正是我们今天来讨论韦伯和费孝通的核心。费孝通不是保守派,他知道市场、资本必然要进入中国,意味着我们在自身系统的调适中,必须把它们作为重要要素重新调适到我们自身的系统中,这才是文明的伟大发明。”渠敬东认为费老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更让我们看到,讨论西方的问题,必须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消化,不仅是回到切实的经验问题,而且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文化处境。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系统。
参与研讨会的还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清媚、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王楠。座谈会实录首发于《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01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