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戴锦华(上):别对单一的审美趣味洋洋自得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谈起电影来总令人兴奋:知识的兴奋、观点的兴奋、语言的兴奋。
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期间,澎湃新闻记者对戴锦华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从电影节制度——中国的,法国的,欧洲电影节和第五、第六代导演的关系,谈到艺术电影本身:上海这座城市和艺术电影有什么渊源?看不懂艺术片应该惭愧吗?《一步之遥》能算是艺术电影的失败之作吗?《百鸟朝凤》是好电影吗?
访谈分两部分发表。这是第一部分。

电影节的活力在冷战结束后萎缩
澎湃新闻:您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上看了什么电影?
戴锦华:没时间看电影,只看了《皮绳上的魂》。
澎湃新闻:一般您去电影节会选择看什么呢?像今年上海电影节的维斯康蒂和库斯图里卡您喜欢吗?
戴锦华:我大概会首选一些第三世界导演的电影。因为现在整个传播渠道,主流的越主流,边缘的越边缘,所以电影节是个机会,能看到一些另类的电影。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电影节的历史回顾单元我都十分熟悉,我更想看些新东西。
维斯康蒂是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导演。但有负面经验:大概两三年前,我在一个电影节上重看《魂断威尼斯》,完全找不到当年第一次看时的观感,不知道当年那种如醉如痴的观影体验是怎么形成的。可能是心境变了吧。但至今仍然喜爱他新现实主义时期的作品。库斯图里卡我一向不喜欢。
澎湃新闻:您去年当了四个电影节的评委——台湾金马奖、香港国际电影节、西宁FIRST青年影展、华语传媒大奖,您怎么看待电影节评委的工作?
戴锦华:做评委会把你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局内人,但这是一个很有限的游戏,因为你只能在入围影片的范围内选择。如今电影节的意义在萎缩,这与整个冷战结束后,艺术电影自身活力的萎缩有关。最早的欧美国际电影节扮演了三种角色:首先是对抗好莱坞,其次是把非西方国家的电影引入到西方国家的主舞台,最后是对电影艺术的边境的不断开拓。今天这三种意义都在萎缩。可我仍然觉得,在一个电影节上,我们支持什么表彰什么,可能对越来越少的、但依然存在的那些爱电影、希望使电影成为一种介入和改造性力量的人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会是个比较较真的评委。
具体到我的评判标准,无外乎两种:首先,电影作为一种极端特殊的仍在与这个世界对话和互动的艺术样式,我希望它能传达出一种对世界的别样观察。今天可见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多屏的屏幕,但这个大屏幕上消失不见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希望电影能继续显影人们盲视的区域。但另一方面,多少有些矛盾的是,我一直相信存在一种叫做电影艺术,或者说电影美学的东西。我觉得电影节应该表彰有艺术诉求、有美学原创的作品。我一直尝试协调好这两重标准。
澎湃新闻:在您参加过的这些电影节中,您有偏爱的吗?
戴锦华:我觉得近年来电影节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倒是FIRST青年影展非常特殊,从组织者到参与者,他们都保持了一种朝向电影的激情状态。他们如此高亢,我其实有点跟不上。FIRST影展瞩目的是电影工业体制边缘的青年导演和处女作,它保有某种不同于主流电影业的意趣。

澎湃新闻:今年戛纳电影节的评选结果和场刊意见之间有很大差异,评委会的水准被质疑,您怎么看?
戴锦华:对我来说,电影节的神话早就破了。尤其评委制的电影节,偶然性很多。谁是今年的评委,评委中谁的性格比较强势,都会影响奖项的形成。我自己比较重视入围电影,而没那么重视得奖电影。因为尽管各个电影节的入围机制不同,但入围影片还是会有某种代表性,评审本身则不具有想象中的权威性。
我对今年的戛纳没有发言权,因为入围片几乎都还没有看到。但对肯·洛奇再次得奖,我感到十分欣喜。肯·洛奇的影片并不完全吻合我的趣味,但他大概是今天世界上我最尊重的电影人之一,一位名副其实的“老战士”。他对自己社会立场的坚守,对这世界上不公不义的敏感,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证明,现实主义的批判和再现仍然是可能的。我很高兴他能再次胜出。但我没有参照系。
去年金棕榈颁给《流浪的潘迪》已是非议纷纷。当时我也感到不平,因为我期待《聂隐娘》胜出,结果胜出的却是法国导演的影片。但在巴黎暴恐之后,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这一选择的合理性:欧洲内部的亚非移民问题,显然比唐代故事与武侠美学的拓展来得急切。显然,那一届评委把对自身社会危机的关注放到了更高的位置上。所以,你不用预期评审结果的权威、公正,因为每一次选择的背后,始终存在着超出电影的社会动力。
澎湃新闻:您能再谈谈中国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和欧洲电影节的关系吗?
戴锦华:确实,第五代导演——准确地说是从第四代开始——把中国电影带到了欧美的视野当中。当时欧洲电影节对第五代的青睐有两个原因。首先,第五代全面登场的时候采取了欧洲艺术电影非常熟悉的模式:新浪潮。所谓新浪潮一定包含两个因素,新人新作和新电影美学的呈现。第五代集体登场的时候,同时满足了这两个因素,欧洲艺术电影节的兴奋感可想而知(尤其是法国作为new wave的命名者、新浪潮的策源地)。
国际电影节对第五代的欣喜,还体现了当时欧洲电影节的一个主要功能:引进非西方电影。因此,为国际电影节拍片成了对许多非西方知名导演的诟病。我本人也曾经从后殖民的角度批判过欧洲电影节的角色,讨论过它以其审美趣味来规范非西方电影。但此后我接受了劳拉·穆尔维在一篇短文中的观点,作为看待这一问题的另一个视角:事实上,对置身于欧美中心位置的人们说来,国际电影节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它将非西方世界的生活与议题带入了欧美的银幕。我想,对国际电影节的评委来说,以欧洲的审美趣味衡量规范第三世界电影大约是他们的潜意识,在其意识中,他们尝试将新的、不同的世界展现在欧美的视域之中。最初的第五代电影大概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和西方电影节发生了深刻的互动,尽管这多少游移于中国社会。

但是,到90年代第六代出现的时候,另一个层面的因素——文化政治突显出来了。冷战终结了,中国成了最后一个屹立不倒的社会主义大国,此时,围绕中国的冷战逻辑继续延续,欧美左右派前所未有地达成共识,同仇敌忾。我曾称之为后冷战的冷战情境。于是,国际电影节在其中充当起某种声援者的角色,以颇具热度的道德自恋发现和命名中国的所谓独立艺术家。这一次,他们不那么关注第六代是否构成中国电影新浪潮的第二浪,不关注其影片的艺术价值、审美趣味,他们将独立导演直接视作异议者。当时有一则评论令我印象很深,它只字不提影片文本却充分肯定第六代,因为作者在其中看到了昔日东欧地下电影的特征。当然也有一些欧洲电影节评委指出影片艺术上的不成熟。我问过一位电影节主席何以使用双重标准,他自己也难于作答。最终,第六代的导演们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美学风格,但最初国际电影节瞩目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政治姿态。
今天,国际电影节和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基本正常。一方面因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介入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的规模、制片层次,使我们不再需要任何的同情怜悯,更无法被忽视。当年柏林电影节主席握着张艺谋的手说,感谢你带来这么好的电影,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中国有电影——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不光好莱坞电影人蜂拥而至,很多欧洲导演也梦想要借助中国的资本,或者让自己的影片在中国市场跟中国观众见面。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电影大国,第五代、第六代的故事已成为历史。当然也可以说,我们的导演丧失了曾经的那份幸运。
理直气壮地说艺术片看不懂,是对单一审美趣味的洋洋自得
澎湃新闻:今年上海电影节开票之初异常热闹,甚至出现通宵排队,售票系统一度瘫痪的情况,怎么看待这种热情?这体现的是精神追求还是消费主义?
戴锦华: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电影最萧条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世纪之交),上海仍是外国电影和外国艺术电影最重要的基地。但是上海从来不是国片的基地,尽管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1949年前中国电影史约等于上海电影史,今天国际电影节在上海的盛况,某种意义上有其文化传统。
现代中国的艺术史有某种不连续性,电影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在一个大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中,充满了空白断裂。中国电影是怎么诞生的?一战了,欧洲片源断绝,影院断档,我们才能自己拍一些电影。中国电影的第一次辉煌是因为国际通行有声片了,我们的影院只能放默片,所以自己拍默片。然后是孤岛,欧美电影被禁绝,于是国片为王。此外始终有人怀旧民国,追忆4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的辉煌,但这背后的故事是:战后好莱坞倾销中国,把八年抗战中生产的电影一并投入,一年进口量达两千多部,当时我们才有多小一个市场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生产国片?但这个时候经济近乎崩盘、通货膨胀,好莱坞要求的利润太高,影院老板根本承担不起。冬天烧不起暖气,片商还是要求烧暖气,影院老板走投无路,唯有抵制好莱坞,这才有一大批的民营电影业出现,国产片才开始大量生产。我不是自然地把今天电影节的盛况联系到上海电影传统,这里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上海的城市文化当中,确实有对欧美艺术电影的热情。
这两年的北京电影节,也同样使中国艺术电影的导演们激动不已。连续出现了全程售罄、一票难求的情况,比如今年的塔尔科夫斯基专题,网上开票后瞬间售罄。我想这是因为录像带、VCD、DVD养育了一代电影观众:既有好莱坞电影的,也有非主流电影的。这里当然也包含了都市时尚、小资经典,包含了小资趣味形成的命名机制、身份标识和生活方式。我想大概很难区分。但总的来说,我还是乐于看到这种小众需求浮出水面。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力量的君临,总让人不寒而栗,这些小众的浮现,至少给电影产业的多元化,提供了一点启示。
澎湃新闻:您今年在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的发布会上批评一些人抱怨艺术片“看不懂”,您说看不懂就“回去学习”,“回家惭愧去”。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在“大众”和“艺术”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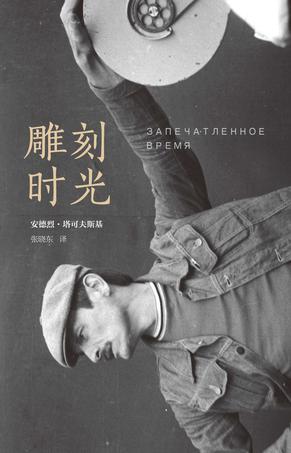
戴锦华:我通常在两个层面上使用“艺术电影”这个词。
首先我认为艺术电影是个历史现象,它出现在冷战初年反文化浪潮汹涌的时刻。它在艺术上有高度的先锋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自反,对电影媒介、电影的社会功能、电影的角色的反思;二是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即我不光拒绝你告诉我电影应该怎样,而且我就是要做那些你认为电影不可能做的事情,比如对哲学性主题的处理,对内心世界的窥视,对电影这种工业产品的工业属性的抵制,对主流价值的逆反。人们通常会说,艺术电影节奏很慢,几乎不用音乐,对白极吝啬,这并非准确的表达,但多少勾勒了艺术电影的姿态:反现代的现代主义。因为整个现代社会追求效率,追求速度,所以艺术片的节奏就是慢——长镜头,凝视,无情节,所有这一切都和电影所负载的工业文明的基本价值、和好莱坞逐渐形成的资产阶级电影美学有清晰的对抗关系;最初的艺术电影即是非好莱坞化。
此外,艺术电影还扮演了整个电影工业的实验室和发动机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恐怕艺术电影中的殉难者比商业电影要多得多,因为它在大胆实验,在尝试表达不可表达之物,在跨越围栏,它死得很难看的可能性当然比在游戏规则内的游戏者要大得多。
艺术电影和好莱坞电影最大的不同是它分享了一种批判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文化,它相信这个世界必须被改变,这个世界可以被改变。这与当时整个欧美社会的一个基本状态有关: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无法忽视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高度的亲和性。他们亲历了法西斯主义从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生长出来的历史,如果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没有别的解决可能的话,只能走向法西斯主义。这种共识使冷战格局下西方阵营的内部,出现了一股强大的自我批判力量,这种力量是拯救性的,是人们的希望所在。
于是就有大量艺术电影观众的产生。那个时候的电影都是在大影院演的,没有多厅,没有小影院,但上座率都非常好。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现象,我很清楚这种历史时刻已经不存在了。今天你不可能指望艺术电影仍然可以像当年那样成为非好莱坞式的大众艺术,赢得人们由衷的喜爱,并且完全在市场票房的意义上生存。
但今天我仍然坚持艺术电影,我坚持的是两点:首先,我认为艺术电影仍然在追求和创造电影美学。我一向都说,我不喜欢好莱坞,首先还不是因为价值,而是电影语言的单调和老旧:第一个镜头出现我已知道下一个镜头是什么,每一段故事,每一个走向我可以预期,你最多只能在技术、噱头和变奏上给我一点点新意,但优秀的艺术电影会给你美学上的震撼和快感。其次,只有在艺术电影的这个大范畴中,我们才能听到批判性的声音,才能看到那些跌出了经济版图的社会图画,看见那些完全被消声、完全被隐形的人们。如今艺术电影作为众多电影当中的一种文化类型——当然不是在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意义上——对我来说仍然是最丰富的。
说看不懂艺术电影就回家惭愧去,这当然是我的激愤之语了。今天所谓看得懂、看不懂本身好像很单纯,其实不然。当你理直气壮地说看不懂的时候,你表达的是对一种单一审美趣味的洋洋自得,是对所有差异性——且不说批判性——的拒绝,你需要的是那种熟悉感,它能带给你安全,让你最小付出最大获得。于是,资本的逻辑就变成了一种文化消费逻辑:不付出或者说最小付出而获得快感。由此获得的只能是一种感官性的快感。但电影多种多样,我还是想要一些真正给眼睛看、给脑子想的电影,而不光是给肠胃、给肌肉看的电影。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一步之遥》的实践,它算得上艺术电影吗?
戴锦华:《一步之遥》以A级商业制作的资本规模,去制作一部有自我表达、有批判意识的艺术电影,无疑是错位,是这个电影失利的内在原因。让艺术电影成为主流样式的历史空间已经不存在了,今天,艺术电影只能作为另类的、体现差异性的、代表小众的样式存在,而资本规模大到那个程度,必然会要求主流市场和主流观众:这是一次错误的相遇。
《一步之遥》曾迫使我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借助大资本来完成一种反资本的表述,建立一种非资产阶级的电影美学?起码这部电影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性的艺术,一种突破、颠覆、践踏资产阶级美学而打开的美学空间,只能是某种贫困艺术。从历史上看,广义的先锋电影运动,每一次都是在社会存在极端危机的状况下,由一群年轻人以最低成本的纪录风格开启的。它一定是那些无法进入大片场、无法动用器材的年轻人用手提摄影机,用业余演员来打开的一个电影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一步之遥》的一切都是相反的。一个外国电影研究者曾非常愤怒地说,他在《一步之遥》的每一幅画面中看到的只有挥金如土。我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表述,但他确乎表明,场景的宏大,画面的精良,这一切都意味着资本自身。在这个由资本所成就的奇观之上,有没有可能负载一种批判的、颠覆的、嘲弄的美学样式?这是个问题。

澎湃新闻:虽然如今电影节一票难求,去年也有《心迷宫》这样独立制片和院线电影交叉的成功案例,但今年还发生了《百鸟朝凤》的下跪事件。您觉得将来有在中国建立艺术电影院线的可能吗?
戴锦华:如果真有任何艺术院线出现,我会不遗余力去支持。但是我现在大概不会再去大声呼吁建立艺术院线。因为我真的倦了,我从二十几岁呼吁艺术院线呼吁到我年过半百。艺术电影院线难以成形有两个原因:首先,它的经营本身不会带来高额利润。今天,资本的逻辑支配着人们的基本行为,艺术院线注定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此外,艺术院线要想作为院线成立的话,还需要一些其他条件。比如,应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艺术电影的片库,这个片库要通过种种途径不断积累世界艺术电影的片源。否则的话,多大的产业规模也很难用足够的艺术电影来支撑一条艺术电影院线。当片源不足的时候,就会有非艺术电影混入其中,从而彻底摧毁这个院线。
我觉得真要建立艺术电影院线就要有一个整体的战略,包括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但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业已证明,在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上,我们的小众观众足够了,在绝对数量上它可能已经构成一个大众电影市场了。只是中国的电影产业仍处在一个乱局之中,还谈不到分众、分层、成熟化。如果它能较快进入这样一个分众分层阶段,我觉得这部分电影观众会受到重视的。

澎湃新闻:对《百鸟朝凤》这部电影本身您有什么评价?
戴锦华:这部电影始料未及地感动了我。一方面,我没有想到在吴天明生命里的最后一部电影,他仍然坚持着第四代的主题。由于他们自身的历史经验,第四代导演和土地,和民众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比如那种小细节:二哥手指断了,再也不能吹唢呐了。这种细节可以做各种选择,但他选了伤残农民工。这样的细节和关照,不是那段历史造就的一代人,是很难以如此自如、举重若轻的方式流露出来的。
《百鸟朝凤》使我感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唤起了我很强的怀旧感。影片固然有第四代青春受阻、梦想被粉碎的主题,但实际上它的电影语言比第四代和吴天明本人的电影语言更老,它更像50到70年代,或者说第四代全面出现之前、新时期初的中国电影的镜头语言和情感模式。当然它也不是完全回到那个时代。我非常喜欢师傅喝醉酒以后吹唢呐的那一场,手提摄影机用得非常漂亮。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部超出我预期的电影。
不过一个知名导演的遗作,一部有追求的影片,到了要靠跪来发行,这确实是挺让人悲哀的。我觉得,仅仅从吴天明遗作的角度来说,它就该有足够的观众,而事实也证明,它的观众大大超出了预期。我是买票到电影院去看的,那个剧场的观众和《X战警》没什么区别,都非常年轻非常时尚。令我感动的是,从头到尾,没人离开,也没有出戏的骚乱。只有一个地方——洋乐队和唢呐队对决,剧场略有点涣散。因为这里交代的是七八十年代的历史过渡,显然对没有历史感的一代观众来说,它有点粗糙和空洞。我曾经在商业影院中看过《聂隐娘》,那个睡觉的、抱怨的、中途退场的,让我悲愤莫名,但是《百鸟朝凤》完全没出现这个情况。我完全没想到他们的观影状态如此之好。这也向我们表明,假定年轻人都要看快节奏、看打斗,完全是主观臆测。这个电影证明了他们同样接受慢节拍,接受把个人放到历史、社会命运中去精雕细刻。对此我很受鼓舞。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