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思故我在”及其现象学的解析与重构
本文来源于哲学门
“我思故我在”及其现象学的解析与重构
倪梁康
作者简介:倪梁康,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现象学及其效应》等。(南京210008)
人大复印:《外国哲学》1999 年 04 期
原发期刊:《开放时代》1999 年第 02 期 第 45-50 页
摘要:笛卡尔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之命题被视为在两方面开现代形而上学思维之先河:一方面是它在理性中心之确立上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在自我中心之确立上所起的作用。然而对此命题从一开始便存在着两种解释的可能性:笛卡尔所确定的所谓思想之阿基米德点究竟是个体自我的存在,还是思维一般的存在?而这两种解释无疑会导致原则不同的结论产生。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基本上便是沿第一种解释的路线进行。本文试图再构笛卡尔的原初意图并重审对现代形而上学的解构方案。

一、近代思维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如果撇开如今附着在欧洲中心这个概念上的浅薄的情感色彩与狭隘的价值属性不论,那么它的理论内涵在我看来基本上可以通过“理性中心”和“本我中心”这两个范畴而得到较为大而泛之的概括。它们是两上贯穿在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也可以被扼要地标识为“究虚理”和“求自识”。
究虚理的特征最明确地表现在伽里略的思想趋向中,他可以说是开近代之纯粹理论精神之先河的第一人。这里所说的“纯粹理论精神”,乃是指那种力图摆脱有限经验的束缚,将事实(实事)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事态)加以理想化或观念化的尝试。自伽里略始,自然被看作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一本书。对自然的观察研究,必须以数学的词汇来表达。世界的直观性、相对性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理性的绝对存在大全。不仅事物被看作是可精确测量和可严格规定的,而且事实之间的联系也不再被看作是经验的联系,而是先天的因果规律联系,而作为事实之总体的自然世界则不仅被理解为一个大全,而且被理解为一个大全统一。经验的周围世界获得了“临界值形态”,它被当作是一个实际上无法达到的极点。所以这个过程也被胡塞尔标识为一个“理想化”(Idealisierung )的过程。(注:参阅: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一、二部分),张庆熊译,上海,1988年,页63。这里的“理想化”一词在原文中为“Idealisierung”, 而中文译作“观念化”有偏差,一则不尽符合胡塞尔的原意,因为他是专门用这个概念来描述自然科学的抽象特征;二则也无法使它区别于真正意义上的“观念化”,即:“Ideierung”或“Ideation”, 它被胡塞尔用来规定哲学科学的抽象性质。通过对“理想化”和“观念化”的区分,胡塞尔实际上划定了在精确的自然科学与严格的哲学科学之间的界限。较为详细的说明可以参阅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的相关条目。)确切地说,对自然的数学化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世界的“理想化”。
而求自识的特征则显然在笛卡尔的思想中表露得最彻底。这个说法的内涵将在后面的整个阐述中逐步得到展示。在这里,只要“求自识”被置于与笛卡尔的联系之中,只要它被理解为自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的基本趋向,我们便可以得出对它的大致理解:它与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的形成有关,也与近代自我形而上学和主体形而上学的形成有关。
与究虚理在伽里略那里所获得的根本展开相似,求自识在笛卡尔哲学中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趋向。而在此之前,求自识与究虚理一样,在古代思想中,甚至在中世纪的思想中都不乏先例。但无论是苏格拉底所解释的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的箴言 “认识你自己”或中纪世费其诺(M.Ficino,1433-1499年)的“认识你自己”, 还是中国古代老子的“识人者智,自识者明”或明代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没有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样依据严格方法的论证,得到纯粹理论理性的奠基。笛卡尔对自识的追求,与他对唯一的、具有最高和绝对的确然性的原则之追求融为一体,它们都立足于理论方法的基石之上。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不仅是“求自识”取向的主要代表,而且同时也是“究虚理”方法的倡导者和实施者。
自笛卡尔以降,哲学才得以可能借谢林之口而申言:“整个哲学都发端于、并且必须发端于一个作为绝对本原而同时也是绝对同一体的本原,”(注: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北京, 1983年,页274。)我们同时也可以说,自笛卡尔以降,自我才作为绝对的本原,以理论理性的姿态踏上了自身认识之途。故而我们在这里将求自识视作西方近代思维的一个根本特征。用弗兰克(M.Frank )的话来说便是,“自身意识不仅是近代哲学的一个课题,而且就是近代哲学的课题。”(注:M.Frank.Vorwortzu Selbstbewu Btseins- Theorievon Fichte bis Sartre.hrsg.von M.Frank,Frankfurt a.M.1991.S.7.)这个说法与黑格尔的理解是一致的,黑格尔认为:“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的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玖兴译,四卷本,北京, 1981年,卷四,而332。)
这里当然还需要强调在伽里略和笛卡尔之间的不同之处:物理学家伽里略所发现的是直观的运动的基本形式,它可以说明所有物体的发生,而元物理学家(形而上学家)笛卡尔所把握到的则是意识的基本真理。(注:参阅:W.Windelband,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S.336.)或许这便是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分界处,也是主客体关系的起源所在。这是与近代方法意识密切相关的近代特殊对象意识,它是使近代有别于古代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可以说,自笛卡尔起,究虚理(理性中心)与求自识(自我中心)在欧洲思想史上达到体系的、逻辑的统一。这个统一可以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命题中得到最浓缩的表达。
二、“我思故我在”:解释与发挥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哲学自产生以来所能提供的传播最广的哲学命题,曾被谢林称作“一个奇迹的发生”。(注:F.W.J.Schelling,Samtliche Werke,Stuttgart/Augsburg 1856-1861,Bd.X.S.8.)即使是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如胡塞尔也仍然在笛卡尔的旗帜下主张:“每一个认真地想成为哲学家的人都必须在一生中有一次回溯到自己本身,并且在自身中尝试一下,将所有现有的科学都加以颠覆并予以重建。哲学是哲思者的完全私人的事情。”(注:Husserl.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Hua I,Den Haag,1973.S.4)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命题既是最简单、最为流行的,同时又是最费解、最受争议的。对这个命题的解释迄今已经进行了三百多年,然而时至今日,例如德国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斯泰格米勒(W.Stegmuller)仍然可以坦率地承认,“尽管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述文献已经汗牛而充栋,至此为止却没有一个诠释能使我满意。我今天对此也只能说 ,我不明白应当如何解释笛卡尔这个定理 。”( 注:W.Stegmuller,Metaphysik,Wissenschaft,Skepsis,Berlin u.a 1969,S.19 Anm.15.)斯泰格米勒的这一坦白当然不是自认理解能力低下,而是试图表达一个对此近代哲学之标志性命题进行再审核、乃至彻底推翻的意向。“我思故我在”命题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西方主体形而上学或自我形而上学命运的浓缩,而推翻这个命题的意向自此命题提出的第一天起便层出不穷,对此可以有笛卡尔本人受到的诘难和为此作出的答辩为证。
而在笛卡尔之后,近现代各派哲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都曾或多或少地对“我思故我在”作出过自己的理解和表态,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在“我思故我在”的准备工作方面,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或者被批评为怀疑得太多,如梅勒·德·比朗,他因此而将“我思故我在”称作是“自相矛盾的”语句;或者它被指责为怀疑得太少,如近代形而上学的坚决反对者尼采,他进而认为笛卡尔在语词的圈套中停滞不前。而在“我思故我在”命题本身方面,康德从一开始便认为不是推理,而是同语反复;费希特虽然将它视作“所有知识的最高原理”,但又不同意笛卡尔对“自我”的理解;谢林一般被看作是对此命题思考最深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他将“我思故我在”解释为假言推理,但又像海德格尔一样批评笛卡尔未能确定“我在”的存在意义;而对于黑格尔来说,“我思故我在”是始终有效的第一原理,而非推理。接下来,在费尔巴哈那里,“我在”并不能合法地等于“我,笛卡尔这个人,是存在的”。(注:关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分段解释史可以参阅:H.Brands,Cogito ergo sum.Interpretationen von Kant bis Nietzsche,Friburg/ Munchen 1982.)而在“我思故我在”的总体评价方面,叔本华将“ 我思故我在”确认为分析判断,并讥讽笛卡尔并未因之而提供特别的智慧;如此等等。即便被看作是或多或少沿续了笛卡尔路线的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也并不完全在笛卡尔的意义上理解和继承“我思故我在”。(注:参阅:C.-A.Scheier,DieSelbstentfaltung der methodischen Reflexion als Prinzip derneueren Philosophiv.Von Descarterzu Hegel,Freiburg/Mulchen
1973.Ⅰ-Ⅲ,S.13-60.) 我们在这些理解和解释中实在不难看出这些理解者和解释者自己的哲学意图。“我思故我在”就好像是一面古老的铜镜,每一个人在观察它时都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形象映现出来。
甚至可以说,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解不仅决定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主流走向,而且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这门哲学发展的各个分流。
三、“自我”或“思维”的存在
如前所述,笛卡尔本人,也包括以后的许多解释者如黑格尔,都在形式上将“我思故我在”理解为第一性的原理,而非间接的推理。因而在它之前不存在一个所谓“所有思维着的东西都存在”的大前提,恰恰相反,这个前提要从它之中“引申出来”。(注:参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四,页340。)而在这个原理的质料方面, 它的首要内涵是对“我思”的提出。接下来,“我思”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原理的首要内涵,乃是因为它无需其他的中介便可以直接地自身意识到自身,成为一种类似于经院哲学的“自因”的东西,笛卡尔也将它称作“自身的确然性”。
这里需要注意:拉丁文中的“cogito”隐含着“我”和“思”的两层含义。如果笛卡尔说,“cogito”的存在是自身确然的,它构成人类知识的阿基米德之点,那么它既可以是指“思维活动”(cogitatio )本身之存在的自身确然性,同样也可以是指作为思维活动主体的“自我”(ego)之存在的自身确然性。而笛卡尔的论述在这里与在对“我思”之确定方式上的论述一样,为两种解释都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从总体上看,发表较早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偏重于对“自我”存在的确立,因而为第二种解释提供较多的依据。笛卡尔在这里明确地说:“我存在着,我生存着,这是确然的。”(注:R.Descartes,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S.20.重点号是原有的。) 而第一种解释则可以在发表较迟的《哲学原理》,笛卡尔在这里似乎更多地偏向于将“我思”理解为思维活动本身,而这个活动的主体可以被撇在一边。例如,笛卡尔在这里谈及“思维”一般、“精神(mens)对自己的确认”以及“我们的意识( conscientia)”等等。(注:R.Descartes,Principia Philosophiae,1,8,9,13.)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种说法最终并没有被笛卡尔看作是相互矛盾的,因为所谓“自我”,在他看来就是“一个思维的东西”, 就是“精神 ( mens)、 心灵(animus)、智慧(intellectus)、理性(ratio)。”(注:参阅:R.Descartes,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S.20.)也就是说,“我思”既是“我”,也是“思”。正是这种说法的含糊性才导致了后人的不同解释。
对这两个不同解释的选择事实上要取决于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在“我思故我在”或“思维即存在”的命题中,被确定的究竟是(一般)思维活动的存在,还是(个体)自我的存在。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前面已经提到过另一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我思”或“思维”是直接被意识到的,还是通过反思而被意识到的。可以说,前一个问题关系到“什么是确然的”,而后一个问题则涉及“如何是确然的”。从笛卡尔本人的阐释来看,“直接认识”应当只是对思维(cogitatio)本身的意识到, 而非对自我(ego)本身的意识到。(注:参阅:R.Descarted,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s.145,S.408,Principia Philosophiae,1,9,10.)与此相反,通过反思而意识(认识)到的则可以是作为思维活动主体的自我,当然也可以是思维活动本身,或思维内容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自身意识”必须严格地区分于“自我意识”(注:应当指出,
在现有的大多数德国古典哲学著作中译本中, “SelbstbewuBtsein”(或“Selbstgefuhl ”等)都被译作“ 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等),例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 1982年,韦卓民译,武汉,1991年;谢林,《 先验唯心论体系》, 梁志学、石泉译,北京,1983年;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1年;《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玖兴译,四卷本,北京,1981年。将“Selbst”和“Ich”都译作“自我”, 这无论如何是不妥的,因为在“Selbst”这个概念中并不一定包含“自我”的含义,自身意识也并不一定就是关于自我的意识,它也可以是指对意识活动本身进行的意识。况且在德文中对应于“自我意识”的概念还有“Ichbewu 迟sein”。此外,当代的研究已经表明,“自我意识”是对“自我”之确立和把握的前提;后面在讨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没有自身意识,对自我的反思是不可能的,因而“自身意识”在逻辑上要先于“自我意识”的形成。故而以下在引用相应的中译文时,我将“自我意识”统改作“自身意识”。)而“思维活动”当然也不能等同于“自我”。然而,这个结论实际上是在300 多年之后才通过现象学的分析而得到较为普遍的接受。
四、“我思故我在”的现象学的解构—建构概要
现在我们要将目光关注在现象学对“我思故我在”命题的解构上。莱维纳斯曾经认为,现象学之所以在当代思维中获得举足轻重的位置,乃是因为通过现象学的分析可以把握到古典思辨哲学所无法接近的东西。(注:参阅:E.Levinas,Die Spur des Anderen.Untersuchungen zur phanomenologie und Sozialphilosophie,ubersetzt von W.N.Krewani,Freiburg/Munchen 1983.S.Iff.)这个主张可以从下面的分析中获得一定的印证。
就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解析而言,我们主要可以得出两方面的结论:
一方面,无论是内感知(对自我本身的感知),还是外感知(对外部事物或其他自我的感知),它们都带有“超越”(或“共现”、“预设”)的成分。因此,自我与他人、事物一样,都是意识活动“构造”的结果,在认识论上并不具有优先的地位。较为具体地说,1.对空间事物之感知(外感知)的本质在于“超越”:原本拥有的只是事物的一个部分,但感知的意向所意指的却是一个整体。2.对他人的陌生感知的情况略有不同,但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一方面,他人的躯体不可能全面原本地被给予:另一方面,他人的心灵生活则永远不能原本地被给予。3.最后,在自身感知的情况中则可以说,自我这个本质范畴的本己特征在于,从属于它的本质只能时或地或眼下地被给予,但永远无法全时地被给予。超越在这里意味着:原本拥有的只是自我的当下瞬间,但感知所意指的则是作为总体的、全时的自我(自我连同它的所有属性和习性)。这里所列举的三种基本感知类型都带有同样的超越结构:超越出原本被给予的范围,意指一个由原来被给予之物和一同被给予之物构成的总体。——这个结论实际上已经证明,笛卡尔在确定了思维的明见性之后进一步推出自我的明见性之做法是不能成立的。(注:对这个结论的详细论述可以参阅拙文:“超越笛卡尔——试论胡塞尔对意识之‘共现’结构的揭示及其潜在作用”,载于:《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 第2期。)
而另一方面,胡塞尔并不怀疑笛卡尔在“我思故我在”命题中得以确定的思维明见性,他愿意跟随笛卡尔至第二沉思,即主张可以利用所有那些通过明白清楚的感知而被给予的东西,即纯粹意识或思维:“我们承认纯粹思维的被给予性是绝对的,然而外部感知中的外在事物的被给予性不是绝对的。”(注:参阅: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1986年,页45。)因为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超越的。正是事物的超越性才使我们对事物产生怀疑,从而导致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提出。接下来,胡塞尔进一步指出对纯粹思维的把握必须以方法反思的方式进行,并同时强调两点:首先,这种哲学的、方法的反思奠基于非课题性的原意识之上,是对原初意识活动之进行的回顾性考察,因而必须以原意识为前提,这与笛卡尔所说的“直接认识”构成“反思认识”之前提的说法是一致的。其次,胡塞尔将现象学的反思严格区别于自然的反思:现象学的反思必须是“实项的描述”,而不能是“超越的意指”。一个感知是否明见无疑,这在本质上并不取决于目光的朝向:内向还是外向,而是取决于对象被感知的方式:内在还是超越,相应还是不相应。——在这里,笛卡尔的“我思我故在”已经被还原到“纯粹思维”之上,它们在进行的过程中被原本地意识到,而后通过哲学反思而成为内在的认识对象。由此出发,胡塞尔建构起现象学意义上的“第一哲学”。(注:对这个结论的详细论述可以参阅拙文:“胡塞尔哲学中的原意识与后反思”,载于:《哲学研究》,1998年,第1期。)
胡塞尔在自我的超越性以及思维的明见性方面的确定,奠定了以后对“我思故我在”之现象学解构的基础。例如,在海德格尔与萨特对“我思故我在”的进一步追问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两个方面的倾向仍然以变化了的方式有效。
首先,在其早期的现象学研究中,海德格尔基本上是从胡塞尔的意向性现象出发来解构由笛卡尔所引发的主—客体关系问题。(注:参阅:M.Heidegger,Ontologie,GA Bd.63,Frankfurt a.M.1988.S.81f.)他所强调的胡塞尔“意向性”概念以及他本人的“在世之存在”的概念已经表明主—客体的关系实际上最终可以归结为主体自知的构造问题。(注:M.Heidegger,Grundprobleme der Phanomenologie,S.229.)同时,对存在问题的关注也使海德格尔从一开始便不断地从存在者和存在方式的杂多性角度来讨论问题。这尤其表现在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下列批评上:虽然笛卡尔的沉思明确划分了思维实体和广延实体并且使之成为哲学问题发展的主线,但他没有区分存在者的各种存在方式以及存在的差异性。更确切地说,笛卡尔在“我思我在”的这个“彻底”开端上没有规定思维实体的存在方式,“没有规定‘我在’的存在意义”,首先是没有将我们本身之所是的存在者之存在区别于其他非此在存在者的存在。(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1994年, 页24(页码为原著页码,即译本边码。以下均同) 以及M.Grundproblemeder Phanomenologie,S.219.)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德格尔早期思想基本上还是主体哲学的沿续。他一方面承认,“自笛卡尔以来,在哲学中对主体的强调得以活跃起来,在这种强调中确实包含着哲学问题的一个真正活力,它只是将古代已经在寻求的东西加以激化”;另一方面,他认为也有必要“不仅仅简单地从主体出发,而是也探问,主体的存在是否以及如何必须被规定为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并且是如此地探问,以致于在主体上的定向不单方面地是主体主义的定向。”概言之,“哲学或许必须从‘主体’出发并且带着它的最终问题‘回入’到主体之中并且可以说是不能单方面地提出它的问题 。” (注:M.Heidegger,Grundprobleme der Phanomenologie,S.219.)
其次,在对“此在主体”的探问方式上,海德格尔也明确地看到了反思方法的第二性特征。因此他同样强调在“主体”的自身理解上所存在的两种方式之间的根本差异。这两种差异在海德格尔这里是以“自身开启(Selbst -Erschlie Bung)与“自身把握(Selbsterfassung)的形式出现:“在回转意义上的反思只是自身把握的一种模式,但却不是原始的自身—开启方式”。所谓自身—开启,是指一种“无需反思和内部的感知”、“先于所有的反思”而进行的此在之自身理解,具体地说“事实的此在是在日常操持的事物中理解自身,理解它自己。”(注:M.Heidegger,Grundprobleme der Phanomenologie,S.226f.)在这个意义上的“自身—开启”显然已经带有浓烈的实践色彩,因而有所偏离于笛卡尔的“直接认识”和胡塞尔的“原意识”。但如前所述,如果对笛卡尔的“思维”概念和胡塞尔的“意识”概念做应有的宽泛理解(注:笛卡尔所说的“思”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思维”概念并不相互涵盖。文德尔班在许多年前对德文的相应翻译所做的告诫,也适用于对中译文的理解:“通常将cogitare、cogitatio译成‘思维’, 这种做法并非不带有误解的危险,因为德文中的思维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理论意识。笛卡尔本人用列举法阐述“cogitare”的意义(Medit.,3;Princ.phil.,I.,9);他将此理解为怀疑、肯定、否定、领会、意欲、厌恶、臆想、 感觉等等。对于所有这些功能的共同点,我们在德文中除了‘意识’以外, 几乎别无他词可以表示。”( W .Windelband,Lehrbuch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S.335)由此可见,昆德拉对“ 我思故我在”的理解和批评貌似机智,实则难免落入俗套:“‘我思故我在’是一位低估了牙疼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命题。‘我觉故我在’才是一条更有普遍性的真理,适用于一切有生命之物。”(米兰·昆德拉,《不朽》,北京, 1991年,页199。)后一个命题与前一个在笛卡尔那里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与昆德拉命题相似的定理在三百年前便层出不穷,例如伽森迪的诘难等等。),使它们包含所有的精神活动,无论是认识行为,还是情感行为,那么对这些精神活动的“直接认识”或“原意识”也就不仅只局限在理论认识的范围以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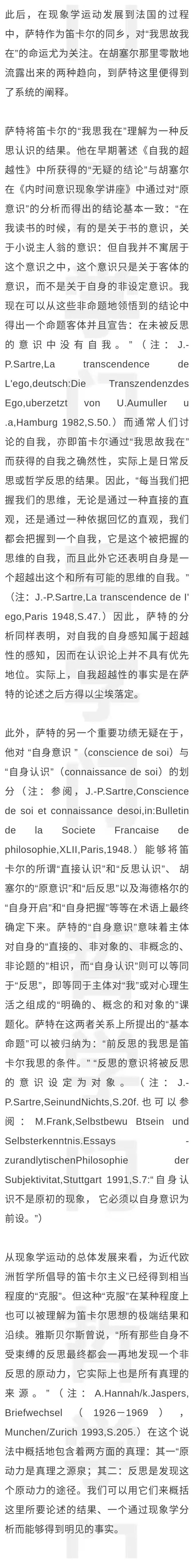
原标题:《“我思故我在”及其现象学的解析与重构》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