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好莱坞科幻电影里的隐喻:外星人入侵与冷战恐惧、原子能焦虑
好莱坞在20 世纪50 年代的科幻电影产品反映了美国政治广泛领域内的各种矛盾、冲突和争论⋯⋯它精准地触到了冷战中的美国恐惧和欲望。
——布莱恩·威兹尼(Brian Vizzini)《冷战恐惧与冷战热情:保守党与自由党在50 年代科幻中的对峙》

对于20 世纪50 年代美国科幻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集中注意那些涉及外星人入侵的叙事,着迷于解读那些外星巨兽代表了什么,并且都假想地认为,科幻电影把冷战中人们对于苏联“红色威胁”的恐惧戏剧化,并呈现到了大银幕上。50 年代的美国常常被描绘为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右翼政治势力占主导地位,执行着四处干预的外交政策,对于国内的共产主义颠覆指控在政治议程中可谓甚嚣尘上(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调查各种左派组织,其中也包括好莱坞的各种工会)。这十年中科幻电影的大量出现和流行,在回溯中看来,似乎与这种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因为科幻利用寓言来处理这些大的政治议题时,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应该说,这样的着眼点一直就很有问题:首先,它把整个十年的科幻电影在叙事上和主题上的复杂性简化为一个单一的视点;其次,它假定了那些电影完全“反映”了整个美国社会(它们其实只是实际生产和上映的电影中的一小部分正典);而且这样的观点很少能越过美国边界,去比较好莱坞之外的那些同类型电影中的细节。推动科幻电影(以及美国的社会性恐惧)的因素,远不只是冷战和与外国力量的对抗:这十年里,飞碟的目击报告不停增加,还有原子武器的精良改进和围绕它的恐慌心理;以“空天控制”为中心的太空竞赛的发端;还有美国社会的“郊区化”变迁,以及社会评论家所担心的、必然随之而来的个性化的丧失。科幻电影在五六十年代里,除了继续发扬前面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语汇,还要处理这些主题和其他种种主题内容。
在讨论这二十年里生产的科幻电影时,必须在简单地考虑政治、社会影响之外纳入更多考虑因素。从1950 年开始,好莱坞和其他国家的电影工业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考验:观众人数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电视的冲击以及青少年观众群的崛起,等等。在50 年代初期的几年里,科幻电影突然成功之后,也受到上述四种方面的威胁。虽然《世界之战》《当世界毁灭时》这样的电影都票房大卖,但到了1955 年,好莱坞各制片厂都声称科幻电影的观众群体在缩小——对于名噪一时的影片如《禁忌星球》《征服太空》等,这变成了真正的问题,因为当时特效的预算已经大为增加了。由于失去了显著的投资回报率,很多制片公司停止了耗资巨大的科幻项目,并关闭了自己的特效部门。倒是电视上开始有了更多的科幻片,挑战着大银幕上科幻电影的霸主地位(其实它们多数也出自同样的那些制作公司)。不断增长的青少年观众群(这是好莱坞大公司的主要观众群体)将科幻电影引向了另外一种方向,他们看的不再仅仅是乔治·帕尔的商业大片和《海边》那样的高端电影了。低成本电影《人体入侵者》《它们!》和非大公司出品的《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女人》《狠心女人》等电影的成功,以及它们的饱和式排片策略,或许把科幻电影重新引回到了以耸人听闻的故事和简单特效制胜的状态,但毕竟是因为他们对于新观众的重视和发行策略的创新,才避免了科幻电影类型在50 年代末期彻底从银幕上消失。另一方面,尽管美国的科幻电影到50年代末在数量上开始减少,但低成本的独立电影和大公司的科幻制作却得到了来自其他国家科幻电影成就的影响和刺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自英国、法国、苏联和日本的科幻电影的贡献。

外星人入侵威胁的故事是20 世纪50 年代以后科幻电影的一股主要叙事线索,它得到了相当多的学术关注。有一大批电影,包括《火星入侵者》《飞碟入侵地球》等都描写了这样的入侵,探讨人类对于外星来犯者的反应,要么是拿起武器的直接战斗,要么是通过“身体控制”。对于50 年代外星人入侵故事的主流解读,一直是将其类比对苏联的恐惧及其潜在的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进攻(和颠覆)。在这些电影的生产所处的时期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定期举行听证会,调查左翼渗透美国社会的问题(包括对好莱坞编剧、导演和演员的影响)。这些历史事件强化了人们的想法,即冷战刺激的恐慌症对电影制作具有直接的影响。
影片《五》和《入侵美利坚》的科幻设定都是未来核大战,后者使用了真实战争素材来描绘某外国军队的入侵,入侵者的方方面面都显示他们就是苏联人,只差直白地点名了。还有不少的科幻电影描写的是非人类的入侵叙事。于是,在批评解读都把外星人跟苏联联系在一起的情形下,对于任何形式的“他者”入侵美国(或美国领土)的故事都代表着潜在的苏联入侵和对西方的渗透。这样一来,《怪人》就变成了苏联的潜伏间谍,他一直按兵不动,直到好奇的美军士兵和科学家“唤醒”了他;《世界之战》里面肆虐的火星人是技术优越的“红色威胁”;而《火星入侵者》和《人体入侵者》则以戏剧化手法表达了这样的忧虑:灵魂缺失的共产主义复制人将替代美国的自由思想和个人主义。
《人体入侵者》在这样的解读理论中成为一个转折焦点。导演唐·西格尔(Don Siegel)再三地反驳了说他拍摄的是一部反共电影的论调,坚称他的目的是嘲弄美国社会没有个性、一致求同的倾向。“变成豆荚就说明你没有热情、没有愤怒,生命的火花已经离开了你……它让你生活在一个毫无生趣的世界里,但那……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世界。”“反共”或“反个性丧失”,成了对这部电影同样内容的不同解读。对于“冷战”解读,外星豆荚人拒绝情感、拒绝宗教、拒绝传统,这样的“入侵”被看作是典型的苏联式态度,从而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描绘成无神论的、只讲逻辑、残忍无情的国度,它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上和军事上破坏美国。然而对西格尔(以及其他支持这种“丧失个性”解读的人)而言,感情缺失的豆荚人代表的是战后的美国在进入郊区化时代的同时,朝着丧失质疑精神的、“弱智化的”社会前进的潮流。在这里,“郊区性”才是真正在拒绝美国价值中的反叛性、传统精神和独立思想,取而代之的是盲从和文化洗脑。两种解读方向都看到了影片潜在的对于政治或文化的深层态度,并且两种解读都假定了所有的观众都能理解并解码如此这般的信息。
对这些科幻电影进行的这种较为传统的基于叙事的解读,都有一个大有问题的核心假设,即20 世纪50 年代的观众都能用完全一模一样的方式来解读这些电影,并且辨认出其中同样的深层因素。威兹尼的说法与其他批评家相互呼应,他声称一部叫作《火星人入侵》的电影是“裹着一层薄纱的(同时也是简化了的)寓言,1953 年的观众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同”。这样的说法忽略了电影本身丰富的文本证据,只是为了达成一个更笼统的叙事总结。它假定了一种主流的编码方式是“所有”观众都能从电影中接收到,并且无论他们的年龄、阶级、性别或生活阅历多么不同,他们都能从中读出相同的政治的或寓言的含义。这种解读方法的风险在于否定了观众可能采取的广泛多样的视角。
对于现代接受美学研究而言,所有的那些不同视角的立场大概已经失去了被充分揭示的机会,但20 世纪50 年代毕竟还留下了一些影评,可以让我们稍微感觉到那时曾经有过的一些其他视角,它们也是有关话语的一部分。比如《纽约时报》将《火星人入侵》说成是一种“‘滑稽故事’画报,里面充满了不可能的事件和幼稚的想象”。评论者只字未提共产主义煽动者和间谍特工,更多地把这部电影看作是专门为“迎合今日那些着迷于太空的小年轻”而拍摄的。这样两种立场之间跨越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一边是成年的观众,他们具有自我意识、有能力辨认并翻译电影寓言,另一边是年轻的观众,从小就习惯了漫画书和太空奇想。这些电影到底代表了什么,它们对于多元化的美国观众到底曾经意味着什么,或者对于全球观众而言它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并没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可以说,理解这些外星入侵的科幻电影的最好的办法,是接受这样的观点:它们的幻想设定可能包含了当代各种事务和议题的蛛丝马迹,但同时也要小心地看到,它们绝不是简单反映了50 年代的焦虑和关切,而是广泛吸纳了多种多样的影响来源。

对科幻电影的文化影响中,有一种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飞碟目击报告的增加,这也为科幻电影的类型图像学带来了永久性的改变。在1947 年的一系列报道中,都出现了一种圆盘状物体悬挂天空的景象,其中一份报道称“九个圆盘,像茶碟打水漂那样飞着”。媒体使用了“飞行的茶碟”(flying saucers)这一短语,本来是嘲笑最初的那些目击报告,却不期然让这个词流行开来。至20 世纪50 年代初,随着飞碟绑架以及外星人接触的报道增多,飞碟不再作为苏联的潜在威胁,转而更多地跟外星人联系了起来。到1952 年,美国的流行新闻杂志如《生活》也会刊登《外星飞碟事件》这种标题的文章,探讨其影响。飞碟的视觉形象引发了一次类型图像语汇的转换,它变成了1950 年以后很多科幻电影的中心。火箭飞船、火箭飞车,甚至梅里埃的火箭列车等,一下子让位给了这个流线型的光滑简单的图标。《地球停转之日》的开场是克拉图的银色飞碟划过银幕,降落在华盛顿特区,从那一刻开始,科幻电影找到了一种新的符号。
这个时期内越来越多飞碟的出现,是“类型化”(genrification)过程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过程中,通过在电影中和文化中一再使用一些特定的符号,来表达类型身份的核心元素。虽然费雯·索布恰克曾反对“太空船”是科幻类型的基本组成的观点,因为“太空船并没有激发连贯一致的含义群”,但对20 世纪50 年代电影中的飞碟而言,却有着压倒性的一致表现:那是一种与神秘和毁灭性力量有关的、负面的形象。多数电影里的UFO 都是暴力入侵和破坏力量的来源:《世界之战》《飞碟入侵地球》《太空杀手》《来自太空的少年》等电影中的飞碟要么破坏美国的大片国土,要么放出其中的杀手和“身体控制”者,即使《地球停转之日》里面的巨型飞碟也还是一种潜在的破坏力量。克拉图或许是来传播和平的(他也可能带来了集权统治),但飞碟本身还是一种强权,可以让地球“停转”,它里面还藏着强大的戈特。这种负面的联想与索布恰克提出的观点一致:宇宙飞船可以看作是正面的(人类制造)或负面的(外星人),但这个观点忘记了飞碟进入到50 年代科幻大合唱的历史过程。要是把飞碟跟所有“宇宙飞船”放在同一个类别里——这个类别多种多样,包括了《月球上的第一批人》里面卡沃的飞球、《星球大战》里面的千年隼,还有《外星奇缘》里面的“黄色飞行老爷车”——就会忽略它们的图像在50 年代的银幕上所具有的文化力量。飞碟并非都是入侵的前奏(1955 年《飞碟征空》里面的外星人飞碟是高级宇航技术的样板;《禁忌星球》中的飞碟是用于探险的人类制造物),在早期那些对科幻电影的类型甄别中,它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图像学元素。
电影故事中的这些飞碟和其中的外星人的出现,常常被认为跟当时新近发现的核裂变原子能有关系。克拉图的飞碟来到地球是因为原子弹试验;《飞碟征空》中人类对于核能的掌握吸引了外星专家的注意;而《火星入侵者》和《来自太空的少年》都出现在核试验场的附近。原子弹以及后来的氢弹的文化形象在50 年代期间会发生重大改变,但科幻电影在一开始就对核能持普遍的反对态度。除了引起外星不速之客的注意之外,核试验也能诱发蚂蚁和蜘蛛变异成为巨型魔兽(《它们!》《地球大战蜘蛛》),更会毁灭地球(《世界终结之日》《海滨》),或者扭曲人类身体(《不可思议的收缩人》《奇妙的透明人》),等等。使用原子能或者核辐射并非50 年代特有的事,放射性物质在三四十年代里已经成为疯狂科学家的领地:《独眼巨人博士》里有一种放射性秘方可以把人缩小到14 英寸(约0.35 米)高;《鬼巡逻》中的坏人用放射能量光束来射击飞机使其坠毁。然而随着美国、苏联相继发展起了原子武器,科幻电影把原子能所带来的焦虑不安感进一步戏剧性强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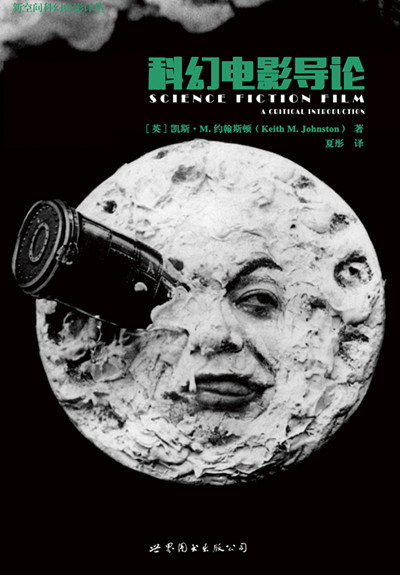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