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鲍勃·迪伦:一个“反叛者”的自我背叛之路

1985年,曾为“九叶”诗人之一的袁可嘉编选过一本《美国歌谣选》。书中收录的《时代改变了》和《就在空中飘》,正是1963年在英美世界广为传唱的迪伦名曲。20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凭借刘诗嵘、钟子林、谭冰若、郑向群、薛范、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的译者方晓光,李皖、袁越、王晓峰等乐评家,以至包括《巴布·迪伦30周年现场演唱纪念特辑》磁带文案撰写者在内的众多人士的断续努力,汉语世界对其社会意义、美学成就和文学价值的阐发,已足以构成“迪伦学”谱系中不容忽视的链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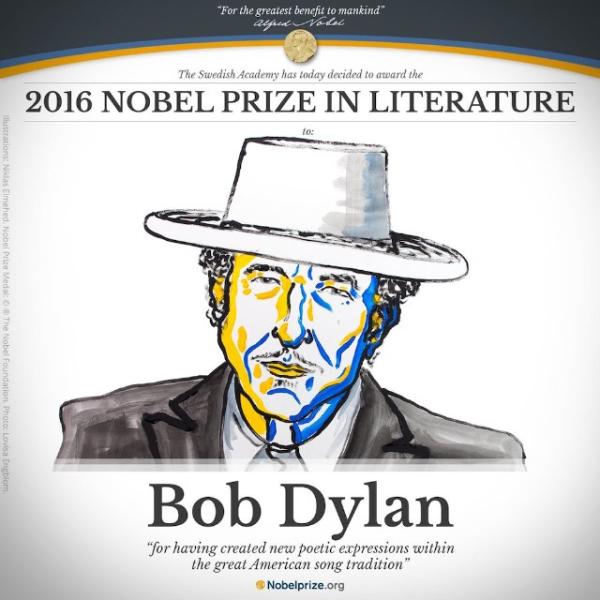
几天来,一则关于迪伦“拒领”诺奖的洋葱新闻被当作实情广为贴布,“收编”之类的字眼也不止一次被提起。这种一厢情愿的误判所透露出的,其实是一份在今日中国社会一息尚存、但一经说出却又将难免罹受错位之苦的爱与忠诚。可以说,迪伦与“摇滚”的相互缠绕,以及回响其中、关乎反抗的记忆与狂想,仍将是今后人们的接受视野中无法避开的预期。甚至不妨说,鲍勃·迪伦之所以成其为鲍勃·迪伦,恰恰是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颠转和与之因应的重重背叛的结果。

从“直接电影”代表作之一——D.A.彭尼贝克的《别回头》,到托德·海恩斯导演的《我不在那儿》,以及马丁·斯科塞斯的《无路归乡》;从1960年代的“彼得、保罗和玛丽”、“鸟”(The Byrd)乐队开始,迄今已无数次发生的翻唱与致敬;从格雷尔·马尔库斯的《老美国志异》到相关人士撰写的访谈和回忆录,围绕鲍勃·迪伦神话般的个人形象展开的各类创作和再创作,可谓层出不穷。说得刻薄点,甚至他本人的《编年史·一》【徐凯峰的中译本名为《像一块滚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也不妨看作是跻身这一行的一份投名状。如今,神话变作新闻头条(反之亦然),也算得上是“苍天不负有心人”的一例印证。
总体而言,尽管他拥有同代人中鲜见其俦(或许只有莱昂纳德·科恩除外)的词曲创作才华和表演天赋,鲍勃·迪伦却并没有超越自己的时代。相反,他倒是更像神话中的雅努斯,总是长着一副向后看的面孔。
遵照一般的心理学原理,可以认为,迪伦的精神结构大致定型于冷战趋于炽烈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参照他回忆录中的说法,“我们在小学里学的一件事就是,当空袭警报响起时要躲到书桌底下,因为俄国人会用炸弹攻击我们。我们还被告知俄国人随时都可能从飞机上跳伞降落到我们所在的城镇。这些俄国人就是几年前和我的叔叔们一起战斗的俄国人。现在他们变成了来切断我们脖子、烧死我们的怪兽……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让他们这么疯狂。人们告诉我们,红军无处不在,而且极度嗜血。”(《像一块滚石》,第29-30页)。他歌曲中透露出的敏锐与不安,似乎均可溯源于此。
这样一来,他倒是和同一时期的“垮掉的一代”更多相似,而与1960年代中后期的青年造反运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事实上,当时代的动荡逐渐酝酿成“一种富有创造力的疾病”之际,他却成了一个在场的缺席者。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他的住所就位于现场附近,但他并未登台表演。金斯堡的《嚎叫》就像是一则谶语,当年轻的人群汇集“青年”这面大旗之下、发出异口同声的呐喊时,真正赋予“青春”别样意味的人,却或则毁于疯狂,或则已在孤苦隔绝和被遗忘中悄然死去。而鲍勃·迪伦,仿佛得益于那场传说中的车祸,竟幸免于此。另外,他也始终未曾涉身于美国青年运动对异质性、神秘主义的“东方”文化的膜拜。
那么,迪伦之所以离开抗议歌曲的舞台,约翰·F·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以及学生运动趋向暴力所造成的刺激,似乎是更加确凿的动因。但是,在更大范围的参照付诸阙如的情况下,车祸、暴力,甚至毒品将只能让原本就不甚可靠的人性抉择愈发不堪重负。时过境迁,它们给人的印象,又都难免像是虚张声势、隔靴搔痒的托词。更不用说,以个人为中心的传记书写样式,原本就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迪伦的身份裂变,《我不在那儿》一片选用多名演员来呈现其妄想症式的精神投射,庶几乎神来之笔。参照格雷尔·马库斯在《老美国志异》中的叙述,迪伦及其乐队(The Band),其实是在位于地下室的录音棚里,重新体认和复活1930年代、以至更为久远的黑人布鲁斯与散落各地的民间音乐传统。换句话说,伴随诗人、预言家、冒名顶替者和亡命徒在歌曲中的交替出现,隐居的迪伦乃是在为一个“古老而怪异”(书名直译)的美国招魂。就美国社会的现实而言,从1929年的“大萧条”到贯穿整个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或“红色恐慌”,经济崩溃与政治迫害已使“美国梦”和个人主义遭遇双重打击。换个角度看,迪伦式的精神分裂,既可解释为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欺骗性人格,也可理解成是他面对吃骨头不吐人的文化工业,从金蝉和狡兔身上学来的求生之术。

从“幸存者”的身份来看,鲍勃·迪伦的“背叛”,又是当时美国社会的政治状况和音乐文化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这起事件见证了始于1930年代的美国民间文化复兴运动的一次重大转折。另一方面,鲍勃·迪伦在此期间遭遇的不安与蜕变,不仅构成摇滚史叙述的重要篇章,而且也折射出彼时英美社会内部涉及阶级构成、代际差异和民族身份等元素的冲突。
所谓“背叛”事件,指的是1965-1966年间,迪伦演唱会上持续上演且呈愈演愈烈之势的、歌者与听众及听众之间发生的激烈对抗状态。先是在美国,当迪伦在新港民歌节上突然采用电声配器演唱起自己的歌曲时,观众纷纷对他用商业化的手法玷污了民间音乐的传统与纯真表示恶感。据说,被激怒的民谣运动领军人物之一佩特·西格甚至打算用斧头砍断电缆以中止他的表演。尔后在英国,支持或反对他的观众在演出现场分裂成形同水火的两派。彭尼贝克的纪录片中就有一幕,一位刚刚看完演出、走出音乐厅的观众,满脸忿忿,冲着镜头骂了一声“真烂”(rank)。
利物浦大学的迈克·琼斯在《鲍勃·迪伦的多重‘背叛’》(2004)一文中提到,1966年5月17日,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的演出现场,有人大声向台上的迪伦喊出了那句对身为犹太人的他而言,极具侮辱性的字眼:“犹大”。借助现场录音(即后来发行的‘私录系列’唱片)的记录与传播功能,这声辱骂变成了永远的历史疮疤。琼斯就此评价说:“如今已很难想象有这么一位歌手,他在很多国家都能让观众塞满礼堂,同时却又是把票卖给了那些跑来骂他的人。”可以说,“背叛”事件既固定、也终结了迪伦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自此之后,即便迪伦推出匠心十足、立意不凡的专辑,也远无法在众声喧哗的摇滚乐场景中再拔头筹。1970年代,他的生涯隐没在因精神崩溃而虔信宗教的传闻中。1980年代,虽则美国文化工业将“摇滚”经典化的规划免不了他的助阵。他在迈克尔·杰克逊发起的《我们是世界》群星合唱中露过面,也在1988年被纳入“摇滚名人堂”。但是,他的专辑被乐评人借《这是什么狗屎》的标题予以痛挞的轶事,却也再度暴露出他的力不从心和貌似堂皇的产业叙事背后的尴尬与漏洞。当他再度追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步伐,在2002年参加向“9·11”事件中扑火救人的纽约消防队“英雄”们致敬的音乐会,他在影音群星中的位置,与在《我们是世界》中其实差不了多少。
回头来看琼斯的分析,迪伦的“背叛”选择当属艺术家不断突破自身(姑且不论它本身就由多重虚构组成)成就的尝试。而英国受众之所以用“叛徒”之名回敬这一选择,一方面源于英美两国青年抗议浪潮所应对的社会语境与前提的差异;另一方面,则与所谓“民谣复兴运动”在两国的代表人物伊万·麦考尔(Ewan MacColl)和佩特·西格(Pete Seeger)所秉持的理念有关。在他看来,西格基于20世纪前半期美国工人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对“人民音乐”实现其“自然”成长的寄望,忽略了大众媒介的兴起对工人集体意识和音乐传播方式的根本性影响。麦考尔又因为执迷于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生活和精神状况的经验主义理解,而将其理想置于前工业时代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认同,并将迪伦的风格转向视为一种代表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可见,在冷战对峙的情形之下,即便在“同文同种”的意识形态感召之下,人们也还是会“被同样的语言分离”——无论这里的“语言”指的是音乐还是英语。
由此再反观中文世界,袁可嘉在1985年的编者按语中介绍说,“作者包勃·迭兰是美国六七十年代著名歌谣作家和演唱家,曾被誉为美国群众不满情绪的代言人”。显见其所依标准,并不单纯是语言或艺术形式。值得多说一句的是,编者的编选体例是将美国歌谣分为五类:印第安人歌谣,黑人歌谣,兵士歌谣,农民歌谣和工人歌谣。迪伦的歌词因此就被纳入“工人歌谣”一类(张艺谋获颁‘五·一劳动奖章’,正是这一归类方式的有趣参照)。实际上,袁先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错位。他主编的《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1991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同样的两首歌词就与“工人歌谣”分列了开来。
就此而言,恰恰就在“摇滚乐”于1980年代的中国演变成一个宏大叙事的同时,现代化的进步主义幻象也遮蔽和筛去了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曾达成世界性共振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也正是因此之故,迪伦作为美国民间文化传承者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而他从个人主义成功学的范例跌落为毒品受害者或不受欢迎的“皇帝新衣”揭破者的故事,则在不断的重复中获得了唯一的合法性。与之相应,异乎于此的接受框架或阐释赖以建立的音乐类型学基础,也都已因其言不及义而堕入被遗忘的深渊。

透过袁越绘声绘影的说书人语体,以及格雷尔·马尔库斯或罗伯特·坎特维尔对活色生香、一以贯之的美国精神传统的牵怀,鲍勃·迪伦的人生道路与艺术生涯的选择,只有放在历史转折的大背景中,才会获得合情合理的解释。
迪伦的精神导师之一伍迪·格斯里曾经说过:“我不会去唱那些富婆的第九次离婚或者某个怪人的第十个老婆。我没时间去唱这些东西。即使有人每周付我十万块钱我也不会唱。我只唱那些普通的人们,他们干着被人认为是琐碎和肮脏的艰苦工作。我只唱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事实上,在迪伦登上历史舞台之际,20世纪美国的“民歌”已历经多次涅槃式的重生。从黑人囚徒的怨曲到西格父子对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从伍迪·格斯里“杀死法西斯”的自信到对抗美国社会内部种族主义的苦斗;从“工联”(IWW,国际工人联盟的简称)的会众歌唱到底层民众和边缘人士大联合促成的“民谣复兴”运动,音乐的主体从来都寄存在一个匿名的他者身上。
无怪乎鲍勃·迪伦、魏尔伦、格斯里等都会成为罗伯特·齐默曼(Robert Zimmerman,迪伦原名)的名字,也无怪乎他会向往重新回到早期白人移民定居点那些推销农药和种子的流动集市,或是售票展览来自暹罗的连体婴儿的马戏篷和小摊点。一如电影《醉乡民谣》末尾借鲍勃·迪伦登台演唱的远景来反衬主人公的落寞与黯淡的事业前景,战后的美国社会以竞争和成功为其立国之本,但其精神活力却永远寄托在那些失意的、不知名的、在时代的剧变面前手足无措的渺小个体身上。
迪伦曾在《自由的钟声》一曲中这样唱道:
这自由之钟把暗夜照亮
照亮了那些真正勇敢的士兵,他们拒绝向人民开枪
照亮了那些流亡的人,他们手无寸铁走在逃难的路上
…
那钟声敲给所有反叛的人,敲给所有的浪子
敲给所有倒霉的人和所有被命运遗忘的男女老少
还有那些被抛弃的人,他们正被绑在火刑柱上忍受煎熬
…
这钟声敲给所有那些不能自由表达意见的人们
敲给那些被冤枉的人、单身母亲和所有落入风尘的姑娘
敲给所有被追捕的犯了罪的人,社会已经把他们抛弃
…
(译文引自袁越《来自民间的叛逆:美国民歌传奇》)
然而,当斯德哥尔摩的评委们在2016年秋季为鲍勃·迪伦举杯之时,宣告的却是瑞典苦心经营一百来年的诺贝尔奖,试图在一个无限碎片化的时代重申其世界性影响的野心。相对于来自前第三世界的苦难叙事和前东方阵营女性作家的申诉,迪伦的“中奖”也意味着“西方”的又一次自我确认与封闭。凭借此举,诗与歌的“跨界”,兼容雅俗的“开放”,还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式的青春怀旧,似乎都有望给诺贝尔这个品牌带来更大的附加值。假如关于诺贝尔赌局赔率的传闻实有其事,赢家所投的,恐怕都是诺贝尔奖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鲍勃·迪伦之于诺贝尔文学奖,借他评论那个刺杀了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麦德加·艾弗斯(Medgar Evers)的白人凶手的歌名,将不过是“他们游戏里的一枚棋子”(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罢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