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今天,人类的语言遭遇了哪几方面的萎缩?

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1947年生于巴黎郊区,曾当过记者和自由撰稿人,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期担任过左翼组织的军事领袖。革命岁月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迹。
在《纸老虎》中,他用第二人称的方式讲述了1968年——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份——前后的经历和感受。而在2014年完成的、2016年被翻译成中文的《古拉格气象学家》中,罗兰从一位古拉格劳改营的气象学家切入,试图通过日记还原强权时代的种种温情和无奈。罗兰是一个极其重视遣词造句的作者,也极其重视细节。《水晶酒店的房间》和《猎狮人》就是极好的例子。
目前,罗兰刚刚写完一本从东西伯利亚到库页岛一行的游记,将于一月底出版,名字叫《贝加尔-阿穆尔》。谈到未来的写作计划,罗兰说:“我会继续写下去,走不同的方向和道路。我不在乎我的作品风格是否统一。”
理想中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在当下社会面临着何种危机?想象力在小说创作中占据何种位置?细节为何重要?人称的使用有有何玄妙之处?针对上述问题,澎湃新闻最近和罗兰展开了一次对谈。
文学是关于语言的艺术,是细腻而微妙的
澎湃新闻:在《现代小说,现代阅读:中国演讲录》里,你曾经提到过关于语言的庸俗化和萎缩的问题,卡尔维诺在几十年前也曾对此表示忧虑。但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确实催生了很多新生事物和新兴的表达方式,正如你几年前在这本小书里提到过的:现场直播、大众媒体等等。我们的生活被直播、颜文字和emoji充斥,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尝试用一种全新的语言去创作,比如emoji小说?
罗兰:你说得对,不过我也没说错。我们当然要掌握新的表达方式,以其为工具,催生文学语言的演变。但是没有任何新鲜事物是建立在对过去的遗忘或破坏的基础上的,反正在艺术领域不是这样。
20世纪初,当乔伊斯用《尤利西斯》掀起小说界的革命时,他用的可不是一种贫乏的、简化的英语。莎士比亚的语言,他记得清楚得很。而今天,在语言领域所发生的,至少是法语语言所遭遇的,在我看来,是一种悲剧性的、同时在好几个方面发生的萎缩:
一方面,英语的词汇、结构、表达法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入侵法语,或者更确切地说,侵入的是美语(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词汇学家阿兰·雷称之为“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外来语”)。有个很好做的实验:随便走在巴黎一条街上,一大半的店铺招牌用的都是这种外来语,还有正在上映的电影的名字、广告,几乎全是。这意味着法语失去了创造力,不再为新事物、新行为造新词,而是非常懒惰地从别的语言引进,一丁点都不改。
一直以来,外来词的引进也是语言生命力的一部分,本土语言会对外来词进行加工,加以创意、按自身的发音习惯进行再创造。而现在,当我说出software(软件)、merchandising(推销)、fashion week(时装周),当我收到一封邀请函上面写着Save the date,等等,这纯粹就是放弃努力了。此时此刻,我正听着广播里的新闻,说的是Hollande-bashing(抹黑奥朗德,奥朗德可是我们的总统……)
另一方面,语言的传统架构越来越被大范围忽略,传承中断。口头的时态在消失。大部分人无视拼写对错。然而形式是很重要的,词语的形式也是,每处不同都是细微的差异。Parler和parlé,“说”这个词的不定式和过去式,发音相同,但说的不是一回事。但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把它们混淆。拉丁语和希腊语作为法语里的科学、哲学等等各种词汇的古老源头,都被遗忘了,这些“死”的语言也不再有人教学。诚然,它们是死的,但却给了我们生命。
短信替代了古老的通信方式,短信可以出现在小说里,广告也可以出现在文学中。但文学不能变成短信或广告,否则它就不是文学。我们能够也应该让语言“吞下”许多东西,但这里头不应该包括语言本身的消失。Emoji小说?也许会有意思吧(我说不上来),但不能称其为小说。Emoji是为了写得更快,它不细腻,不微妙;文学的目的不是快快快,它应该是细腻而微妙的。

文学的职责是尊重语言并发掘其可能性
那么该如何理解诊断文学(diagnostique)?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带有一种革命性的、批判性的文学?是要去揭露或者昭示霸权或者这个时代的弊端等等?
这同时又牵涉到文学在当代的职责,或者说文学在每一个特定时代的职责。你认为文学的职责是什么,是否应不仅仅满足于一种镜像式的反射和展示,而是应该去批判、去看镜像后面的运作机制?
罗兰:是的,当然,我所说的诊断文学更重要、更本质。症候文学是一种潮流现象。就像你说的,它崇拜偶像。诊断文学则肩负批判的职责。“批判”未必是“告发”(纯粹的告发文学往往单薄,偏新闻),“批判”一词应该按康德的精神来理解:即研究某件事情成为可能的条件。
但是要小心!在文学如此广阔多姿的辽原里试图给一些概念下定义,我们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我不喜欢谈文学的“职责”,更别说“义务”。所谓的“介入文学”,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文学的目的不是教训人。社会也不是它唯一的目标。
如果说它有职责的话,那应该是更广义的职责:尊重语言,不是说把语言供起来,而是让语言鲜活地存在,发掘语言的各种可能,让人们喜欢它;创造新的形式;引人思考;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尊重他独立判断的自由。文学首先应该是自由的;纯粹的想象也有伟大的作品。
澎湃新闻:你曾说一个作家应该是孤独的,应该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相孤立,并且这种孤立是十分必要的。那么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何在这种不断的孤立中消解孤独感和自我怀疑?
罗兰:孤独其实不算是一种选择,而像是一种必然。比如普鲁斯特,你知道的,他很入世,他投身于他那个时代的生活、艺术圈,甚至社交圈。但是一旦开始写作,他就自我剥离、自我孤立了(包括身体上)。应该成为选择甚至成为一种道德的,是拒绝,拒绝一切约定俗成、一切主导的观念和潮流。“强音,你得不到我的声音”,亨利·米肖写道——我不知道米肖的作品是否有被翻成中文;这里的强音,是时代的声音。
作家像特工:他可以和别人一起生活,扎在人堆里,看起来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但他有另外一种生活,他真正的生活,在那里头他是不一样的,也是孤独的。 如何消解孤独感?我想并不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有双重生活,但在占重要地位的那层生活里,我们是孤独的,而且会一直孤独下去。至于说消除怀疑,那是绝对不行的!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应该既有足够的骄傲来认可他自己所作,又得有足够的怀疑,对自己永远不能够肯定和完全满意。这不容易。
写作靠的是持续不断的积累,而非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澎湃新闻:你的两部作品《猎狮人》和《古拉格气象学家》都和机缘巧合(serendipity)有关,写的都是某种跨越时空的机缘巧合,同时因为你把自己作为一个角色融入叙事当中,其实也在探讨写作中一个创作者投入的劳动和“天赐良机”之间的关系。你是否对此类题材情有独钟?根据你的创作经验,当这样的机缘巧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判断能够把他们发展成一个故事,一本书?
罗兰:不,我想机缘巧合并非是我情有独钟。《猎狮人》的确缘起两次偶遇,相隔十年和十万八千里,我撞见了这个人物的两幅肖像,另外一个有点类似的巧合给了我《气象学家》的线索。但是,您瞧,是您让我注意到这两本书在缘由上的相似——我从来做过这样的类比——证明您是位好读者(或者说我是个粗心的作家……)。一条河流的源头不止一处,条条细溪入大江,书也一样,一本书诞生于暗中的、隐秘的、往往连作者本人都全然不知的成因的碰撞。经常是在写的时候才发现它的起点。这个,是我所感兴趣的,这个问题:一本书如何诞生?它从哪里来?有时是偶然,但也有深埋的记忆,阅读留下的印记,等等。
的确,我喜欢在书中讲述书本身的来龙去脉。让正在朝书靠近的作者——也就是我——出场。他还不知道自己会写书,完全没概念,但不知不觉中已经在接收许多第一印象,正是这些印象后来酝酿了这本书,有了第一页。这就是我在《气象学家》里所说的来封“介绍信”。

澎湃新闻:《猎狮人》、《古拉格气象学家》,甚至包括更早时候的《纸老虎》,其实都是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游走。《猎狮人》尤其是这样,你在中国版本最后《写给中国读者》一文中提到:“为了这本书我翻阅了大量史料。关于马奈的部分,我完全没有虚构,真实准确是对伟大创作者应有的尊重。至于佩杜泽,我允许自己多写想象,却也没有远离人们对他所知之事。”在创作中,你如何处理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
罗兰:我想,和很多人一样,在创作中,我依靠的是记忆、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东西、做的梦、遗憾甚至悔恨,以及遗忘加杜撰和这一切编织而成的东西。但我想我需要有一个现实的记录。我没有人们老爱说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我这儿没有天马也不行空。要让“写作的机器”运作起来,我一般得先积累笔记,漫无目的地记,持续不断。再从这些简短描述片段的积淀里寻找某种精准的东西,写作计划可能就会偷偷冒头。也有先有计划的时候,这种时候我就的确需要让它鲜活起来(至少得让自己信服),用许多“实地的笔记”去丰满它。
对我来说,写作通常先从档案员、地理学家、地图测绘者的工作开始(摄影方面的少一些,因为图像会免去语言)。写《猎狮人》和《气象学家》,我先是亲身前往,一个是南美洲,一个是俄罗斯,记许多笔记,研习文献和以往的报纸等等。我喜欢这个写作的筹备阶段:人已经有点进入书的状态,又还不用面对写作中的困境和焦虑。写作所需的信心和能量正是在这个不慌不忙、不声不响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信心和能量,少了可不行。

澎湃新闻:您对细节似乎情有独钟,在《猎狮人》中,有十分多繁复的、精致的细节,精确到一个人所穿衣服的材质、颜色、甚至是衣服上的一粒纽扣的形态。而《水晶酒店的套房》则更是如此,它就像是一个细节描写手册。对于细节的执念是否因为受到了乔治·佩雷克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新小说派”的影响?您为何认为细节十分重要?
罗兰:我觉得重要的不是细节,是精准。我老爱引用保罗·瓦莱里的这句话,他说一个作家“不应该说下雨了:他应该造雨”。“说下雨了”,是传达信息。“造雨”,是文学。得靠词语,让事物、人物、活物来到人眼前。得用词语紧紧抓住世界不松手。这是一场斗争,因为世界不会束手就擒。比如,再来看看克洛德·西蒙的《农事诗》:这是一则伟大的文学诗篇,因为它展现的情景就像我们透过刚下火车的士兵的眼睛看到的那样,“一下子但又详尽地(或者说赤裸裸地、细致地,就像细致入微的碳素笔素描一样)”。“一下子但又详尽地”展现:这两点都很重要。
细节的作用在于为视觉对焦,就像拍照一样。不是令人昏昏欲睡的细节的堆砌,而是抓住某几个细节,场景就此得以延展开去,有时甚至就是一笔,直截了当奔描述对象的核心而去,就像一支正中靶心的箭,想视而不见都不行。这阵子我在读儒勒·雷纳尔的《日记》,他的作品估计还没中译本,他的文风很干硬,非常精准,《日记》里面全是这种简短的描写,如有神奇魔力,让东西活灵活现:“长着驴脑袋的蚂蚱”,“鸟儿看起来永远是新的,像昨天刚出生似的”;“每只母鸡头上都顶着一个红蜡印”……
至于《水晶酒店的套房》,这本书有些特别,有点“实验”:我尝试通过细节的堆砌达到某种精确,不追求任何文风。这是个文学游戏,确实是受乔治·佩雷克的启发。如果让十来个学画或学建筑的学生按着其中一间房间的描写来作画,看看画出来的会不会相似,应该会挺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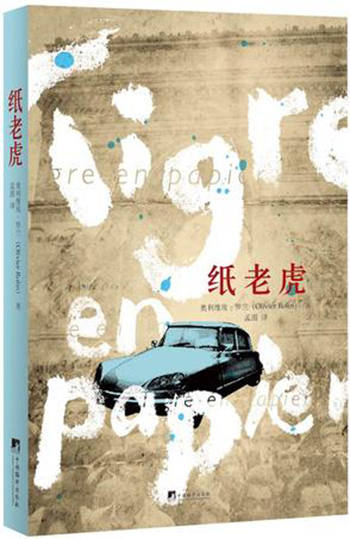
人称的转换是为了引入一种讽刺的距离感
澎湃新闻:你的书中人称的转换和运用让人印象深刻。在《猎狮人》中,那个频繁出现的“你”,是一个记者,是无意间在圣保罗发现了马奈那幅猎狮人,并且在之后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去探访马奈和这位画中人留下的蛛丝马迹的、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人。在我看来,这个“你”其实是打破和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有的时候,这个“你”甚至是带着一种闯入者的姿态进入到19世纪的法国。“你”的出现让《猎狮人》有了一种拼贴画的感觉。上一秒读者还在十九世纪马奈的居所,下一秒便切换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对这个居所的拜访。这样的安排是有意为之?
而在《古拉格气象学家》的第二部分,你通过日记来重现气象学家在集中营时的内心活动时,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的方式。第三人称穿插在以第一人称“我”为主导的叙述在古拉格的生活中,第三人称的插入就像一个节拍器,为整个叙述调节节奏。能否分享你对人称使用的一些看法?比如人称使用的诀窍或者是作用?
罗兰:是的,您读得非常好!所有一切都很重要,人称的使用也是!我经常在同一个人物身上使用两个人称代词(我/你,或我/他)。不过每本书各有不同。在《猎狮人》(或《纸老虎》)里面, 叙述者,也就是说作者,我,有时候会说“我”,这是规规矩矩的用法,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以“你”自称。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就引入一种距离感,讽刺的距离感,在写作的我和被写的我之间,被写的我被置入场景之中,是个记忆里的人物。但这也绝非什么手法: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这样,但我会,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话的时候,如果说的是一般的事,我用的是“我”,比如一些事实陈述,像“我要迟到了”,但如果说的是比较重要的事,比如对自己的指责,我用的是“你”,“你干了件蠢事”,“你讲的真不咋地,你的讲座好无聊”……这样一种在“我”和“你”之间切换跟自己对话的方式,在阿波利奈尔的诗里也能找到:“今天你走在巴黎街头女人们身上血迹斑斑/那是我不愿记起的那是美的凋零“(《地带》)。
《气象学家》的情况又略微不同。叙述者(我)以“我”自称,中规中矩。反而是气象学家这个人物,阿列克谢·范根格安姆,在书的第二部分中,在“我”和“他”之间切换。“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丝毫未动摇,阿列克谢·费奥多谢维奇在信中写道。他给加里宁和斯大林写过好几次信”。实际上,这一部分始终在直接(“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和间接(“他写道”)之间来回切换,只不过我刻意将直接引用的引号去掉了。既是出于版面美观的考虑,但更多是出于行文风格的需要,有点难以言传但我一下子就感觉到这种需要;我感觉必须要在“我”和“他”之间来回切换,才能让所有的悲哀、失望、不解、绝望和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无聊在他的话语中充分回荡。让他的话语有一种悲歌的味道,像阴郁的吟唱。

澎湃新闻:能否分享最近在读的几本书?
罗兰:我正在读《盲点》,关于西班牙作家哈维尔·赛卡斯的文学作品的论著,在我看来他是当代作重要的作家之一。我最近还重读了一遍《莫拉瓦金》,法国作家布莱兹·桑德拉尔相当出色的小说,我觉得它是20世纪初开创写作新手法的作品。这又让我想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附魔者》(后译为《群魔》),因为这两部作品讲的是虚无主义和恐怖主义,很不幸,都是今天我们无法摆脱的话题。我还在重读法国当代作家皮埃尔·米雄的《小人物传》,因为我得给一份杂志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
澎湃新闻:你对青年创作者有什么建议?
罗兰:也许一个好的建议就是别听什么建议。如果您非要我说的话,首先是:读。然后是:要骄傲。也要谦逊,要怀疑,要问自己是否你写的每句话、每个词都有存在的理由,不要过于容易自满,要自我批评。要坚持,要固执,写作是件很累人的事,往往容易让人气馁。不要试图用天花乱坠的辞藻来唬人,用无用的晦涩来吓人(新手都爱犯这样的毛病,反正以前的我也是)。别忘了,用词语创造美(不管美的定义是否相同)才是最重要的。
(罗兰的回答部分内容由林苑翻译。 )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