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读︱焦姣:与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相遇
又到一年书单时。前几天有朋友问我,有没有适合对美国历史有兴趣、想要深入了解美国历史的非专业读者的书?这次列出的三本2016年出版的美国史英文新书并非教材或泛泛之作,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及读物,相反,这三本书的作者可以说都是受过专业训练、在某一历史领域有专深研究的专家。然而,他们写出的作品并不枯燥艰深,对于大众读者来说,这些历史故事仍然活泼生动、引人入胜。一百多年前美国人的生活可能与今天的中国读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也许历史研究最大的教益不在于“抚古思今”,而是带领读者步入时间的密林,与那些完全不同于“我”的人相遇。当我们开始理解他人生活中的痛苦、挣扎、希望和信仰时,我们就迈出了成为世界公民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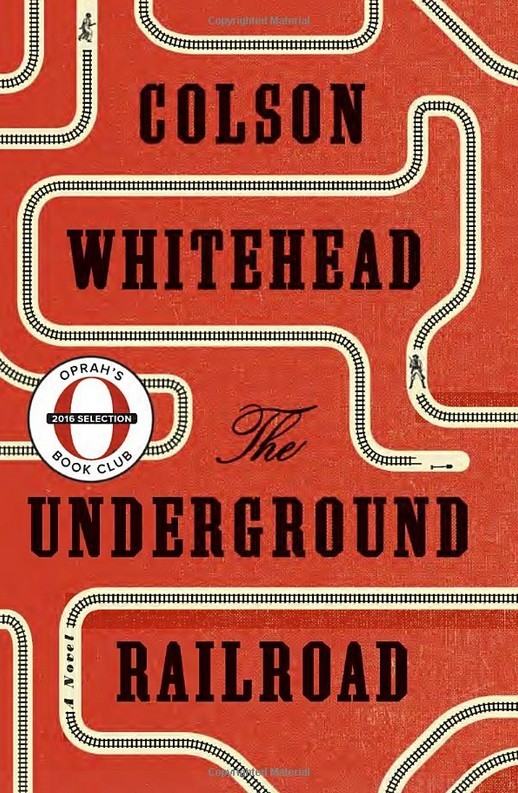
书单的第一本并非历史著作,严格说来连“历史小说”都不能算。书中的两位主人公都是虚构人物,但他们的经历却有许多历史人物的影子,书中那个运送南方奴隶逃往北方的秘密组织“地下铁路”在历史上也实有其事,并且传奇程度丝毫不下于小说中的情节。科尔森·怀特海这本小说作为201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大奖得主,不仅拿奖拿到手软,各大书店也一度卖到脱销,可是说是2016年的美国出版界大赢家,甚至有评论者认为此书可与诺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的作品相比。
近年来,美国掀起了一股“地下铁路”热。内战结束后不久,当年的废奴主义者就发表过许多讲述“地下铁路”传奇故事的著作,因为情节离奇曲折,一时大受欢迎。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一度对于“地下铁路”的真实性抱以怀疑——毕竟在内战前,帮助奴隶逃跑是非法活动,当时留下的记录本来就不多。在1850年联邦《逃奴法案》通过后,帮助逃奴者可能会被罚以重金甚至入狱,许多人为了自保都销毁了相关记录。“地下铁路”到底如何运作,有多少奴隶得到了救助,一度属于“死无对证”的领域。内战后的废奴派是不是为了自吹自擂,夸大了自己的功绩?“地下铁路”到底有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历史学家重新开始翻检内战前的通信、报纸,并且发现了一批前所未见的手稿,证实“地下铁路”和逃奴传奇都具有真实性。在公共史学领域,人们对“地下铁路”的热情也十分高涨,辛辛那提市建起了全国最大的“地下铁路”主题博物馆,美国国家公园也推出了多条“重走地下铁路”的旅游路线,在奥尔巴尼、雪城这样的“地下铁路”核心站点,地方历史协会不仅重新修复了当年逃奴藏身的房屋,还定期组织读书会、历史重现等活动,让人们深入体会这段黑暗的历史。去年,班克罗夫特奖双料得主、美国史学名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的《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Gateway to Freedom: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一书出版后也深受欢迎,多次重印。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地下铁路”女英雄哈里雅特·塔布曼的头像即将取代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被印在新版20美元纸币的正面。这是美国流通纸币上第一次出现女性的形象。
而在文学层面,这本从逃奴角度讲述“地下铁路”故事的小说,也暗合着近年来黑奴叙事传统的复兴。虽然十九世纪中期时,黑奴叙事(slave’s narrative)已经是流行的大众文学体裁,但其真实性也经常受到质疑——奴隶识字率不高,其故事往往出于白人废奴主义者的代笔甚至“再创作”。例如女奴哈里雅特·雅各布斯的畅销自传《女奴生平》写作中就有白人女作家莉迪亚·蔡尔德的影子,而读者之所以相信此书并且托名伪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详细描绘女奴遭受奴隶主性侵害的情节,绝非当时的白人上层女性能够凭空捏造的。2002年汉娜·克拉夫茨的《女奴叙事》手稿尘封一百多年后出版,一时也是洛阳纸贵,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经过多方考证,证明此书确实是一名女逃奴亲笔所撰。
怀特海这本小说正是从两名逃亡中的年轻黑奴的视角来还原“地下铁路”的故事,而其情节安排中又有两个匠心独运之处:其一,故事主线开始的时间被设置在1812年前后,这时候历史上的“地下铁路”初具雏形,实际上,一男一女两名奴隶一起逃亡的情形十分少见(历史上大多数逃奴是单身出逃的年轻男性)。怀特海如此着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展现逃奴传奇的双重性质——既是逃亡,也是探险。两位主人公出身背景的不同更是丰富了读者可以选择的视角,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了丰满的张力。其二,怀特海笔下的逃亡故事是开放性的,逃奴眼中的美国并不是“南”与“北”、自由州与蓄奴州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南北之间的冲突激化要等到1830年代之后),而是代表了美国文明中许许多多不同的面貌,其中有一些是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美国”。怀特海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也说,他有意模仿《格列佛游记》的结构,把主人公逃亡途中踏足的每一个州都看作“另一种可能的美国”,因此,每章结束时,小说的整体情节都会经历一次“重启”(rebo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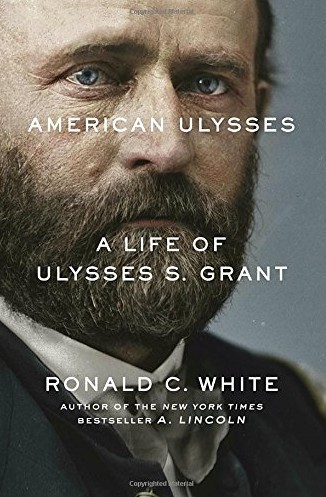
这本800多页的巨著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让人略感吃惊,但想来也不算奇怪。作者罗纳德·怀特是一名退休的职业历史学家,也是知名的传记作者,他2009年出版的同为鸿篇巨制的《林肯传》(A. Lincoln: A Biography)曾经被称作“给林肯两百岁生日最好的礼物”。正是在研究林肯的过程中,怀特发现自己开始重新理解尤利西斯·格兰特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对于美国内战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
在威廉·麦克菲利(William McFeely)1982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经典《格兰特传》中,格兰特的形象并不光彩——战争英雄,也是南方人眼中的屠夫;两届总统(差一点就参选第三届),却以腐败丑闻收场;内战时的联邦护卫者,重建时期南方黑人平等梦想的叛徒。这种不光彩并非源于格兰特人格中内在的恶,而恰恰来自格兰特人格中的平庸。麦克菲利甚至就格兰特不甚高大的身材大发感慨(格兰特身高170公分左右,在美国军人中很不起眼,尤其在格兰特与身高超过190公分、身材高瘦的林肯站在一起时,这种对比格外明显):“照片中这个平淡、懒散,没精打采地缩在帐篷前的人,既不像传闻中那个杀人如麻的战士,也不像邪恶奸诈的政客。……这个人物形象中几乎没有一点闪光之处。”麦克菲利剥去了格兰特身上所有英雄主义的外衣,发现了一个极度平庸、懦弱、无所适从的人格,他缺少任何方面的出众才华,甚至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从十七岁时跨进西点军校,到后来成为将军、成为总统,都不是出于他自身的强烈愿望或野心,而“完全是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事干”。这种对格兰特人格的解读背后,其实是麦克菲利对于美国内战,甚至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的理解:一个在和平时期一事无成的普通人,竟然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血腥、可能也是最被神化的战争。最终,麦克菲利抽离了美国内战的所有光环——解放黑奴、保卫联邦、守护宪法、捍卫自由——作为一场机械性的杀戮,南北战争是理性面具之下人类非理性一面的释放,它造就了无数毫无意义的死亡,成就了无数没有心肝的宵小之徒。
然而,怀特这本新书要做的,正是找回作为英雄的格兰特。书名中的“美国尤利西斯”既是传主名字的双关,也是怀特对于格兰特人生的隐喻。像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尤利西斯)一样,与格兰特英雄人格相关的,不仅是他在内战中大放异彩的“屠龙时刻”,还有他此前三十九年人生中漫无边际的“漂流”。不管是他在俄亥俄边疆度过的童年,他在西点养成的对于文学的爱好,他在美墨战争中对于自我和他者世界的探索,都造就了格兰特沉默、多思、富于同情心却敢于冒险的性格。哪怕在内战中,格兰特也从来不是林肯从一开始就认定的北军首领,更像是多次换帅后的无奈之选。格兰特的性格也许适合作战,但他并不是一个命定的战士,他并不是在神意赋予美利坚的“天定命运”下前进,而是在美国逐渐崛起却不知何往的时代,在诸雄并立的未知之海上航行。在格兰特从边陲无名少年成长为世界公民的途中,怀特看到的是一个朴实粗砺却又元气淋漓的十九世纪美国。
而在格兰特的美国奥德赛历险中,另一个长久被忽视的人物就是他的“佩涅罗珀”——格兰特的妻子茱莉亚。在所有美国第一夫人中,茱莉亚·格兰特的存在感是如此之淡,人们甚至连她到底哪里乏味都想不起来。茱莉亚的性格极其羞怯,因为害怕非议,她坚持不肯在生前公开自己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直到1975年才出版。然而,茱莉亚·格兰特也是内战中随军征战距离最长的军属,从1861到1865年,她随同格兰特行军超过一万英里,连林肯都发现,茱莉亚才是格兰特将军最有效的“助推剂”。格兰特十分依赖茱莉亚,在格兰特内战前的军旅生涯中,两人之间通信十分频繁,内战后,茱莉亚也是推动格兰特参选总统最积极的人之一。在怀特看来,要理解尤利西斯·格兰特生活的时代,格兰特夫妇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身为密苏里种植园主的女儿,茱莉亚甚至直到1864年都还公开携带奴隶同行(这位名叫茱莉的女奴也跟着北军踏遍了大半个美国),茱莉亚娘家的亲奴隶制立场是格兰特与他父亲(坚定的废奴派)关系中的死结,甚至格兰特本人也从岳父那里继承了四名黑奴(后来被格兰特主动解放),这些细节都折射出内战时代美国人对于奴隶制、对于财产和婚姻关系的不同理解。正如怀特所说,本书要讲的不是作为内战英雄的格兰特,而是“作为更宽广的美国故事中的主角(hero)”的格兰特。

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今年的新作《美国增长的兴衰》从出版前就广受期待。作为研究长时段经济史和通胀问题的专家,戈登近年来一直对全球经济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认为19世纪末以来,曾经加速经济增长的所有科技红利都已经用尽,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面的停滞时代。
虽然戈登最终指向的是宏观经济指数的变化,这本书读来却很有社会史的味道。尤其在描绘1870-1940年间美国人生活水平的变化时,戈登大量引用历史学家的研究,力求还原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细节:如何获得食物,穿什么衣服,工作环境如何,上哪找乐子,选择何种出行工具……这些变化看似微小,但因其影响的人口范围极广,并且深刻改变了人们对劳动力和时间的分配,最终累积为巨大的增长动力——1300到1700年间,英国人的人均产值总共只翻了一番不到,而在20世纪,美国的人均产值每32年就会翻一番。这完全改变了几代人对于“增长”的生命体验。
在预测未来方面,这本书则是一个关注长时段的经济史学家对当前技术乐观派的质疑。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戈登就对所谓“信息革命”的重要性表示怀疑,认为信息科技带来的经济进步无关紧要,根本当不起“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名头。以最直观的标准来看,1870年到1970年之间,每个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力、卫生、交通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劳动和生活形态,进而改变了商业组织和工作场所管理的逻辑。相比之下,信息革命只是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影响了大众的消费方式,对于经济生产和企业组织并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今年美国大选之后,坊间流行一个新词:“知识分子泡泡”(intellectual bubble),用以指代那些身处大学校园、新闻媒体等“高智商高学历人群”中,与大众脱节、不能理解普通百姓疾苦的知识分子。如果按戈登的观点来看,与其说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不谙世事,倒不如说对信息经济充满信心的硅谷科技精英们才是真正生活在“泡泡”中的群体。他们因为自身所处的经济部门“异乎寻常”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整体低迷全无感觉,而“极客”们营销的许多新产品也限于小圈子内部的自娱自乐,或是将这些产品通过资本运作转化为虚无的经济数据泡沫。
另一方面,当下流行的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中,往往强调分配不公和不平等问题对经济增长的伤害。然而在戈登看来,不平等问题与其说是增长停滞的肇因,不如说是增长放缓的伴生物。在过去三十年中,尽管美国的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逐年攀升,已经快要回到大萧条前的水平,但不仅大众消费者的生活标准(standard of living)没有出现明显增长,总体的资本回报率也在下降。换句话说,“重新分配蛋糕”并不能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动力,增长的停滞是长期、全面而持续的。
在戈登看来,他只是指出了一个简单得近乎常识的事实:经济的总体增长从来都不是均匀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对于那些笃信技术进步论的人来说,戈登给出的可能是对于未来最灰暗的估计:1870-1970年这个爆发式增长的“特殊世纪”只是人类文明中昙花一现的异象,它已经结束,并且再也不会回来。而对于已经习惯把经济增长看作历史“背景音”的我们,增长的停滞背后潜藏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恐怕是难以估量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