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年度建筑师|马清运:建筑不是永恒的,就像食物,也是会过期的
原创 时尚先生 时尚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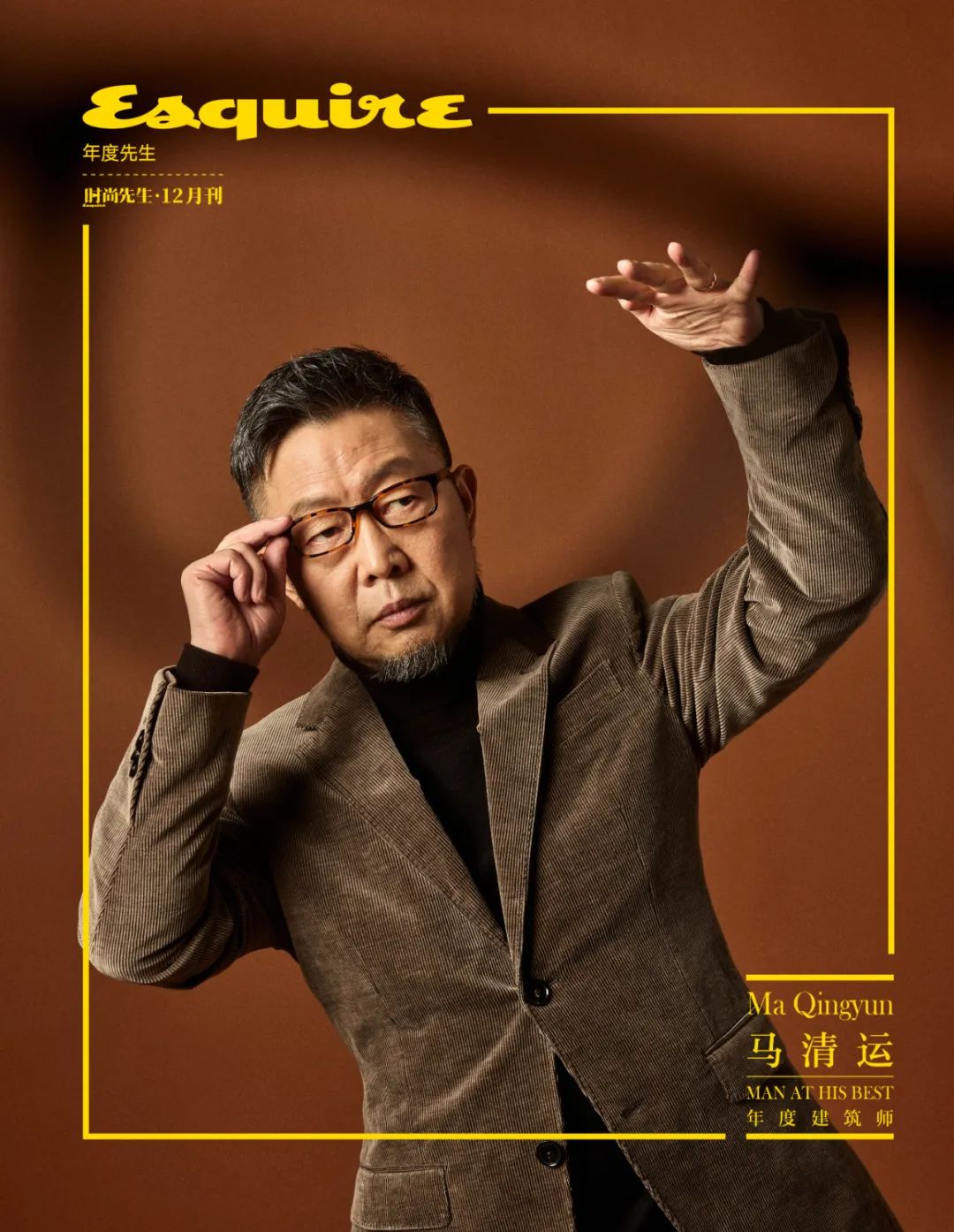
在建筑师群体里,
马清运属于特立独行的存在,
很多设计显得古怪、反传统,
他认为建筑不应该符合传统审美。
他甚至觉得对于建筑来说,
时间的意义不大,
一座建筑应该有个保质期。
56岁的建筑设计师马清运蓄一撮胡子,搭着框架眼镜,黑色的长筒靴快到膝盖,和十几年前的形象几乎没有差别,只是多了些白色的胡茬。作为马达思班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创办人、著名建筑师、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第一位华人院长,他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比起这些名头,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艺人马伯骞的父亲。
他的私人微博除了发布每天的设计“功课”,几乎都和儿子马伯骞有关。不久前,父子俩一起参加了江苏卫视一档综艺节目,录制时间不长,集中在三四天,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陪伴。
“很多人只愿意让家长知道自己成功的时候,不想让他们看见自己奋斗。”马清运说,这次旁观儿子工作,他对儿子所处的那个遥远世界更清楚了些。他带着调侃的语气告诉我们,录制综艺时,父子两人被安排在不同的酒店,每天录制完各自回去,早上在化妆间才见上面。他对儿子的世界充满好奇,默默坐在旁边观察:小马有专门的化妆师,甚至还有个管品牌的工作人员跟着,拉着箱子,在小马化妆期间递产品,让他录口播。
他说,很欣慰看到儿子把做艺人、唱歌当成事业,就像他对建筑的热情一样。
父子两人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对于自己认准的事情,少有迟疑,非常坚决,能够付出很多代价。

棕色西服套装 Ermenegildo Zegna
黑色高领 私人物品
马清运走上建筑师的道路非常偶然。上世纪80年代,他正读中学,在一本叫《中学科技》的杂志上,看到了高考专业填报指南,上面说,学建筑系,需要有绘画基础,同时要有很好的形象思维——正好和他的趣味对得上。他立即决定学建筑,并将其作为长久的职业,”不着急,慢慢来”。之后的路径看起来十分顺遂:考上清华大学建筑系,本科毕业后拿到奖学金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之后入职美国知名建筑事务所,在所内出色完成工作的同时,他还在宾大兼职教学。1995年,毕业四年后,他在纽约成立了马达思班建筑设计事务所,之后扩张到上海。
在建筑师群体里,马清运属于特立独行的存在,很多设计显得古怪、反传统,他认为建筑不应该符合传统审美,而是应该别具一格,“令人产生好奇心”。他甚至觉得对于建筑来说,时间的意义不大,一座建筑应该有个保质期,就像食物一样。
这种风格早在学生时期就形成了。在清华,他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学霸,当时中国刚刚兴起国际旅游,学生们最流行的设计项目是做五星级酒店,他跑去研究古建筑。连去食堂打饭,他都要等快关门了再去—懒得排队,还要说话,麻烦。
在他过去的设计师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并不是城市地标性建筑,而是远在陕西省蓝田县的山村。那里是马清运的老家,他按照自己的想法为父亲建造了一座房子,取名“父亲的宅”。马清运说,父亲没有读过书,并不理解建筑师是做什么的,于是他“想在他眼皮子底下盖一个”。
“父亲的宅”用了四年才完成,父亲也参与了建设,帮他请工人 ,外墙砌的石头是父亲和村民们从附近河里摸的,足足攒了三年。马清运说,他不愿意用建筑师的语言和眼光去评价这个作品,对于他来说,它远远超出一个建筑作品的意义:这是父子两个人互相信任的证明,也是让父亲参与、理解他所处世界的方式。
父亲参与了马清运的建筑,马清运也参与了马伯骞的综艺。时间或许是有价值的,它让一些事情形成了呼应和连接。

Esquire:您好像很少接受采访,很多人都不知道您是怎么走上建筑设计这条路的。
马清运:我爸爸原来是个军人,后来做裁缝,我妈妈也是裁缝,她的手特别巧,如果我有所谓的“工匠精神”或者对手工艺的专注度,都和我妈有关。前段时间玉山酒庄展览上用的酒标就是她的刺绣作品。现在想想,他们做服装和我做建筑其实一样,也要画图,也要一个整体打碎再组合起来。他们要把二维的面料变成三维的衣服,也有物理功能,可能比建筑还建筑。
小时候我就住军队大院儿里,那是个小王国。有做文工团的,有美工,如果要演话剧,是整个大院所有工人一起参与,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组织。小时候我学了很多年的画,就是跟院儿里的师傅学的,没事就去找他。小时候大家不是学画画就是学武术,要么就是打架,我选择性、有正义感地参与打架(笑)。
Esquire:在清华读建筑的时候,您算是标准学霸吗?
马清运:我应该不是最学霸的那一类,我基本上都是在做自己的事,不太合群,现在也是。比较谁好谁坏,肯定是有一个基础的、公认的衡量尺寸,如果你在这个尺寸上,那么可以衡量长短,但我基本上没在那个尺寸上待过,没法比较。
Esquire:那您跑到哪个尺寸上去了?
马清运:比如大家都会做设计,要争高分,我就是去学理论,做理论。80年代初有国际旅游了嘛,流行设计有现代化功能的五星级酒店,要么就是体育场,而我就去做古建。成绩我永远是比及格好一点点,75分,到哪儿永远都是75分。
那个时候我有点儿特立独行,现在想起来就是不好意思,不愿意跟别人比较。我比别人好,我会不好意思,他比我好我也不好意思。我现在也不太会吵架,不太懂拒绝,也没法看别人被拒绝。对我来说,最好跟别人没关系是比较好的状态。
Esquire:集体活动您参与吗?比如去食堂吃饭,也是一个人?
马清运:对,没错,我吃食堂都自己去,而且去得比较晚,不用排队。我不愿意站在别人边上,如果排队,前后都有人,还得说话,特累,一般食堂快关门了我才跑去。这还有个好处,你知道吗?到最后食堂师傅不管剩下东西分量多少,“哗哗”全给你盛到碗里去。比如买丸子,大家一块排队的话,一人俩丸子,我最后去就“咵”直接倒给我,足有一大碗,三人份。
Esquire:毕业后您出国了。当时选择出国的人多吗?你们这一届清华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一般都去哪里了?
马清运:当时留学已经不算新鲜事,特别是清华,所有人都在申请。我记得应该有一半,或者60%的人都出国了,剩下来的绝大多数都进了大院,就是那种几千人的设计院,属于国企。
Esquire:您是什么时候确定要把建筑作为自己未来职业的?
马清运:就是开始报考大学专业的时候,我记得是在1983年。其实我一直没为此着急过,因为知道反正这行是要做一辈子的,来日方长。从宾大毕业后,我就有创业的想法,但那会儿家里没钱,总要养活自己,就在美国一个大的建筑事务所工作,类似于中国的大院。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去教课。我愿意一直参与到建筑核心知识的生态里,因为应用,就是做房子,每天都差不多。所以我一边教课,一边在大院内做设计师,不算全时工作,这是非常少见的。
后来干脆自己开了独立的建筑事务所。刚开始设在纽约,相当于大家一起成立小小的工作室,共同创作,不算生意,只有五六个人。后来在上海的马达思班就是要正经拿项目、有前台的公司了,变成了生意。
Esquire:对您来说,什么是好的建筑,您有自己的标准吗?
马清运:这个问题有点儿难,让我想想。我觉得作为建筑师来说我没办法评价,基本我做的建筑都是好的建筑,别人的建筑对他们来说也肯定是好的。但如果仅仅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觉得一个好建筑应该有三种“不器”的素质:
第一,它能够改变一种生产组织的结果;第二,它应该解决甚至是唤醒了一种技术的改进;第三个呢,我觉得它应该让人产生探索的兴致,让人感兴趣。
Esquire:玉山石柴(“父亲的宅”)是您很重要的作品吗?您什么时候有给父亲建一座房子的想法?
马清运: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有想过。图纸是我在宾大读书的时候画的,一直到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才开始正式做这件事。它是我学生时期各种思考的结晶体,但我不太愿意用建筑师的语言来评价它,因为它的含义已经超过了那些,是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重要的作品。
在我们陕西,一般都是爸给儿子盖房子,那是传承,但我是给我爸盖房。在传统标准下,相当于父亲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是反传承。这是我和我父亲共同的勇气。一个父亲允许儿子按照他的想法给自己盖房子,是父亲对儿子最大的信心,这是这个房子真正的意义。
另外,我当时还有个想法是,我一定要让我爸知道我学建筑是干吗的,在那之前,我猜想他并不完全理解。我爸没读过书,所以我很想在他眼皮子底下盖一个。
Esquire:您的父亲有参与这个房子的设计和建造过程吗?
马清运:有,这个房子就建在玉山镇的一个村子,我父亲的老家,他在那里出生、长大。我小学的前半段也在那里生活过。做这个作品用了三四年时间,不是一次完成的,先搭个架子,外墙砌的石头是我和村民一起在附近的河里摸的,一年也摸不了那么多,所以一直攒了三年的石头。
我爸也下河摸了石头,村民也是他张罗来的,建房子的劳力也是他找的,相当于我们一起建造了这个房子。
Esquire:后来他在这个房子里生活过吗?
马清运:住过大概十几年,很多地方他不习惯,但他很喜欢。
Esquire:您好像说过一个观点,觉得建筑都不是永恒的,都会被时间抹去。您怎么看待时间对于建筑的意义?
马清运:我觉得时间其实对于建筑没太大的意义,无非是材料的变化,主要是对人有意义。因为人在变化,建筑的意义是由人来赋予的。比如我们选择一个建筑做历史遗迹,为什么不选择另外一个当遗迹呢?谁来决定审判的标准?
所以从我的意义上讲,建筑不但是有时限的,而且是有过期日期的。
Esquire:今年热播综艺《五十公里桃花坞》里的桃花坞也是您设计的?
马清运:对,是我设计,也是我开发的,我参与了投资。桃花坞主要是想建立一个社群。我反问你两个问题吧,像你这个年龄的年轻人,说到社群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Esquire:对于现代社会中这批接近00年出生的年轻人,从有记忆就开始有网络,虚拟的连接要远远多于现实,社群对我们来说应该就是互联网上的共同体。就像您儿子会在网上和他的粉丝团互动一样。
马清运:对,年轻人的社群已经没有场景了,只有叙事和剧本的属性,桃花坞实际上是创造一个社群的空间场景,期待这个场景里能生长出一个乡村社群,设计理念就是这个。
其实我做的无非是生产、生活和生存这三种工具。为什么农民很穷?因为他们基于土地的生产已经带不来附加值了,所以他一定要离开土地,去寻求和土地无关的生产方式。一个民工在城市里可能照样能赚很多钱,但他往往没有尊严,他不但抵触城市,也抵触乡村,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没有变成一体。
Esquire:您近几年一直在做乡村振兴工作,是在蓝田建立玉川酒庄的过程中开始有这个想法的吗?
马清运:对,其实就是给土地附加值,让农村的生活更有尊严,只要是对农村好的都应该是乡村振兴工作。我在深汕特别合作区那边做了一些项目,想慢慢实践一些想法,让农村的生产方式更有价值。
Esquire:您近期在南方比较活跃,大马设计也一直在进行南方的(深汕,广州)项目,大马设计和马达思班是什么关系?您预计大马设计的成就会超过马达思班吗?
马清运:马达思班其实是特别经典的做建筑实践的公司,大马设计有了活儿交给马达思班,给我设计费,我给它交图,属于技术咨询服务。大马设计未来需要有孵化和加速的能力,特别还要有教育的板块在里面。
孵化指的是,比如你是大学毕业的年轻设计师,你可以在大马设计创业,我可以给你带来项目,帮你管理财务,甚至帮你拓展市场,相当于扶着你上路。加速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个做无人机的,你有特别好的技术,但你做的东西特别土,无人机看着没人要,我会通过设计加速你们科技产业的迅速成功。但总体来说,大马设计和马达思班是合作关系,不存在谁超过谁。

棕色西服套装 Ermenegildo Zegna
黑色高领 私人物品
Esquire:最近您和马伯骞一起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和儿子一起工作是什么体验?
马清运:我就知道采访最后的落点肯定又到这个话题了(笑),你对我的兴趣应该都是因为马伯骞(笑),我知道。就像我跟我爸一样,他参与了我的建造,就更了解我的生活。这次录节目,我旁观小马工作,就更了解他。
其实还挺难的,很多人不愿意自己家长知道自己干吗的,只愿意让家长知道自己成功的时候,不想让他们看见自己奋斗。
Esquire:您觉得马伯骞工作时和生活中的状态有差别吗?
马清运:差不多,我们两个特别像,有非常柔的一面,就是生活里无所谓,但也有很硬的一面,为了坚持的东西可以付出特别多。
Esquire:你们一共录制了多久,这之间你们都在一起吗?
马清运:大概三四天。我们住的地方不一样,他是大腕儿明星,有自己住的地方,我住的不是(笑)。录完我们各自回去,早晨在化妆室里才见面。而且他有自己的化妆师,还有一个人专门管品牌,拉着一箱东西。他往那儿一坐,对着镜头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那个。
Esquire:您在节目里开玩笑说,您跟爱人都是学霸,是清华同班同学,结果生出马伯骞这个没有学霸基因的儿子,做了很长时间心理建设。您原本对他的期待是什么?
马清运:其实我们没什么期待,我跟我爱人属于那种一辈子得到太多的人,又是学霸,又是清华,就没什么动力去逼迫孩子。就是好像成绩好这件事对我们相对不那么重要。小时候他和弟弟在上海读小学,如果学习不好,感觉在学校也挺难的。只要他们一回家,我打眼一看,哎哟,其实只要不是很痛苦就够了,多少分都行,我就不问他们学习的事儿了。
Esquire:关于他想做练习生这件事,他跟您商量过吗?
马清运:商量过,这是个大事了。他初中在美国读的,念的那个男校演舞台剧和话剧都会算入学分他每学期都要演一个,我当时就觉得挺牛的。后来他说以后想要做歌手,高中就去读了艺术高中,是一个美国公立学校。那个学校的学生都是最穷的社区里挑出来的相对有天赋的孩子,基本都是黑人、拉丁美洲人这种,只有一个或者两个亚洲学生。他总跟我说自己的嘻哈水平还很业余,但实际上,他应该还挺专业的,他的嘻哈是从街上和黑人朋友们混出来的。
Esquire:您是从什么时候确认他走这条路是让人放心的?
马清运:一开始他说想走这条路,我倒不是不放心,就是觉得我帮不了他,如果他学建筑,我可以帮忙,唱歌这事我不行。
从他参演《明日之子》我就感觉他肯定可以,我在美国全程追了节目。
Esquire:您觉得您跟儿子之间是一种怎样的父子关系呢?
马清运:比中国传统下的父子关系开放一点儿,但也有些区域是不愿意进入的。比如他在这个行业遇到的困难,我会觉得这东西我帮不了你,我就不要去深究,你自己解决就行。还有就是感情,这个他有自己的空间。
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只能尽量约束自己,做孩子的榜样,但没法成为他们的老师。很多事情应该我先做到。


摄影:苏里
采访、撰文:殷盛琳
策划:陈博
统筹:暖小团
化妆、发型:小新
时装编辑:李萌
造型助理:Simon
场地提供:Factory工厂文创影像空间
原标题:《年度建筑师|马清运:建筑不是永恒的,就像食物,也是会过期的》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