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跟着大师读大师:名作家的文学课
外国的很多大作家都写过一些类似“经典导读”和“文学评论”性质的书,这些书往往非常好看,而其妙处,在我看来,全在于用强烈的主观偏好、独特的品味姿态表达自己的创作理念。

20世纪初,伍尔夫不仅以小说名世,同时更是诸多报刊的特约撰稿人,写下了350余篇书评随笔。不同于她小说的意识绵延,其评论亲切晓畅,通透深刻,毫无枝蔓。她以“普通读者”的姿态,不摆架子,一扫评论浮泛空洞、故作艰深的毛病。在其引导下,读者或许很快就能改变阅读惯性,从生活经验、心理类型和性别意识出发,获得女性直感的纤微敏锐。在她眼中,奥斯汀是个讥诮世情的讽刺家、机智冷峻的观察者,懂得怎样把“道德信念”和“取乐心态”掺和起来。夏洛蒂·勃朗特是个宣泄型的激情作家,小说并无太多侧影、色彩,被情感力量所驱动,竟来不及观察解决问题。作为现代主义小说先驱,伍尔夫并未贬低现实主义,而是说明她想要的更高现实——“精神流动的现实”。

亨利·詹姆斯与伍尔夫都意在开拓“心理现实”的深广性,但詹姆斯显然更“守成”。《小说的艺术》里挑选的几位作家(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福楼拜、乔治·桑、乔治·艾略特),说明美国作家对欧洲传统的承继。詹姆斯善于区分作家的“天才”和“习惯”,两者都可能成就杰作,却不是同一种“伟大”。屠格涅夫没有司各特、狄更斯敏捷的才思,不假思索的热烈,不是一个“即兴表演家”。然而,詹姆斯赞赏他“勤能补拙”的“好习惯”、“苦功夫”。“他是一个做好笔记再写小说的人”,建立素材的“仓库”,里面堆满了生活琐事、性格特征、叙事状物的描绘。“倘若需要,他会把它保存二十年,直到用到它的时间到来。”

劳伦斯和詹姆斯形成了巧妙的“照应”:一个英国作家对美国文学进行了长久凝视。毫无疑问,劳伦斯的小说评点同样激情狂野。有时是匪夷所思的离题万里,有时是不可理解的不可理喻,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其评论的天才。他对爱伦·坡的理解如此独特,把恐怖小说也能解读成性爱小说。劳伦斯大谈新旧意识交替,灵魂毁灭与创造的“生机论”,最终通过性爱实现(其实,这套理论也给罗素“推销”过)。然而,我很喜欢劳伦斯别有用意的跑题,他认为坡把小说变成了“化学实验”。我想只有劳伦斯才会发现坡的“机械呆板”,而非人云亦云。“他从不用生命的观点观察事物,他几乎总是用物质的观点看事物,眼里都是珠宝或大理石什么的。”劳伦斯从不相信理性分析,只相信作品的“生命体征”:身体的反应和血液的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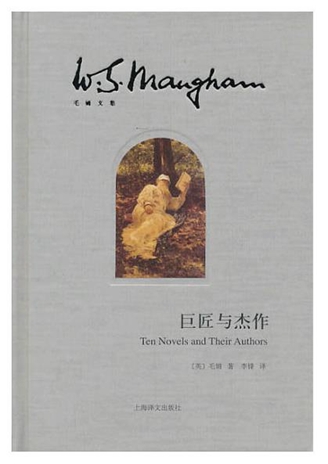
1945年,毛姆应邀给美国《红书》杂志列了一份书单,挑选了心中的十佳小说,并围绕作家作品写了系列书评,促成了《巨匠与杰作》的问世。显然,列书单是件既费力又挨骂的“得罪事”,更何况只能选十本。毛姆每每解释“自己选择极为武断”,依据只有一个:小说是否带来愉悦。不管小说多深刻,多伟大,如果读来痛苦,就不会选入。这样的观念造成了这本书的风格:随性轻松、率意幽默。毛姆采用了一种“肖像式评论法”,随意拉扯作家的私生活,小趣闻。一边是写作品的“巨匠”,另一边是拈花惹草的托翁染了梅毒,福楼拜让现任情人打探猎艳对象,司汤达追求异性时还会“做笔记”,青年巴尔扎克竟然恋上“老熟女”。毛姆总是能从作品里找到巨匠的人格障碍和道德缺陷。

“艺术和宣传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所谓纯审美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受到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或者政治上的信仰忠诚所浸染。”奥威尔借此表明了他的评论立场:没有纯然的审美,艺术无法撇清与道德的关系。这本评论集吸引人的正是审美和道德的角力。他对亨利·米勒的评点,最有意味。那时《北回归线》仍在英美遭禁,奥威尔赞赏它真实呈现了信仰崩溃后的“庸俗肉体”与“丑化的性生活”。尽管,他的肯定是如此不温不火,冷冷淡淡。“这样的书无疑把大钟摆摆得太远了,但他摆的方向却是正确的。”“它能够胜任地完成任务,而不是虚情假意,拖泥带水。”因为,奥威尔原本期待就不高,“乔伊斯基本上是一个艺术家;米勒则是一个观察细腻但是感情麻木的人在把他对人生的看法说出来而已”。

纳博科夫反感奥威尔这种带有政治寓意的作家。理查德·罗蒂曾有意把他俩一起讨论,用“团结”与“反讽”界定了二人的艺术特性。纳博科夫是奥威尔的反面:崇尚“纯艺术”的虚构游戏,让语言文体压倒了故事道德。《文学讲稿》对奥斯汀、狄更斯、普鲁斯特和福楼拜的分析,都是微观的“文本分析”,无尽放大了小说的“艺术性”。甚至,纳博科夫把“昆虫学”的研究方法移入在小说分析中,把作品当成了“标本”。《文学讲稿》告诉你什么是“典范的分析”,你很难再找出一本兼具科学思维和艺术气质的经典导读。在他笔下,普鲁斯特不再繁复,乔伊斯不再迷离。纳博科夫的条分缕析,洞察感知,堪称“文学侦探”。

卡尔维诺比纳博科夫的口味宽得多,他自言是个杂食性读者。在我看,《为什么读经典》绝不仅是本阅读指南,它有更多的意义(对于作家和我们皆是如此)。卡尔维诺借此书装置了一个大容器,重新界定了“经典”的十几个义项,把从荷马到格诺的几十位作家通通收纳进来。他的特点也许就是博爱,前言中他用一句话表达爱每个作家的理由。读来简直是种“武断的精确”。正文是对这些理由的阐释演绎,让人诧异的是,卡尔维诺把作家变为了形容词:司汤达是张力;普希金是清晰、讽刺和严肃;海明威是唯实,轻描淡写。他也爱上了经典的“缺陷”:果戈里用洗练、恶意和适度来歪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贯、愤怒和毫无分寸来歪曲。经典不是没缺陷,而是它的缺点不可复制。

库切和卡尔维诺有种默契,在《异乡人的国度》开篇,他也分析了“何为经典”这个问题。只不过,库切探讨了“经典历史化”理解的过程。他的评论范围极广,既有对笛福、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前辈大师,里尔克、卡夫卡、穆齐尔等德语作家的分析;也有对博尔赫斯、布罗茨基、戈迪默、奥兹、拉什迪、莱辛等20世纪巨匠的评点。然而,库切却没有落入浮泛,他看重作家风貌的“总体性”和“纵深性”:既把具体作品放在作家创作序列里横向比较,又把作家成就置于社会历史意识中参考定位,看出景深。

作为法国新小说派的主将之一,克洛德·西蒙在《四次讲座》里谈论了他的写作、阅读和记忆。可以说,他的评论完全指向自身创作经验,基于阅读兴趣。他把鲜花给了普鲁斯特、福克纳,却把枪口对向了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西蒙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传统”的厌倦:单义铁板的人物,漫画般的心理类型,道学家的伦理教谕。他反感福楼拜小说命定的因果之链,认为巴尔扎克只有描写段落有价值,其余都是乏味的社会学兴趣。这是一种寓言思维,人物无不成了德行的象征符号。西蒙以艺术史的视野,将中世纪绘画与传统小说类比。普鲁斯特、福克纳等人的伟大在于颠覆与搅乱:原先意义预先存在于作家的工作之前,而现在,意义将由这一工作来生成。

自《新手》中译本出版后,你也许知道了并不“极简”的卡佛。读了《需要时,就给我电话》中收录的12篇书评后,我爱他的评论,甚于他的小说。卡佛写小说,就像画冬日的树,没几片叶子,却是枯淡的自然,自然到了无趣。他的评论也简单,是明朗的枝干,清晰的轮廓,像油画刀冷硬狠准的“刀法”。他对巴特尔梅(另译为巴塞尔姆)的评论,可谓是“钦慕中的失望”,怀着崇敬之情指出了巴特尔梅的退步、缺陷和失败。卡佛认为,这位“文学偶像”靠伟大的天才写了“非人的喜剧”,架空了故事中一切合理性,不受道德责任和价值意义的约束。模仿者只学来了他的扎眼样式,却做不到巴特尔梅表现爱与失落、绝望与胜利时的出人意料。卡佛同样惋惜,巴特尔梅的才智和幻想慢慢沦为了怪异有趣的俏皮话,缺乏贴近人心的“同情”,丧失了力量与复杂。他开始创造无聊。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