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赫伊津哈:一个“游戏的人”的怅惘与忧愁
“当世界比现在年轻五个世纪的时候,生活中的一切外在形式都比现在要清晰。痛苦与欢乐之间的距离、灾难与幸福之间的距离,似乎都要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的更大。人们经历的一切事情直接和绝对性程度,与当今小孩子们在精神上的快乐和痛苦是一样的。”
——赫伊津哈《中世纪的秋天》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92年12月7日-1945年2月1日)这个名字应该并不陌生。无论是他那本著名的《中世纪的秋天》(一译为《中世纪的衰落》),还是脍炙人口的《伊拉斯谟传》,以及极具启发性的《游戏的人》,都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也获得了不俗的评价。
作为19世纪后期的欧洲学人,赫伊津哈身上拥有许多与茨威格等巨匠所共享的特征。一方面,那一代文化巨匠大多出身贵族或殷实家庭,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出类拔萃的个人天赋。另一方面,他们多数人在一战之后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幻灭,这些经历极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思索与写作。作为20世纪荷兰最伟大的文化史学家和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赫伊津哈的一生有些故事尚不为我们所熟悉。他的生活与爱,忧愁与怅惘,都能为我们理解其文化史研究进路有所帮助。勾勒赫伊津哈的故事,也能为我们在展开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时期荷兰乃至西欧社会的画卷时,提供一个有趣的个案。

格罗宁根城
1872年12月7日,赫伊津哈出生于格罗宁根一个四万余人的小镇上。他的祖父雅各布·赫伊津哈是浸信会牧师,一生持守信仰。可惜,这位牧师的儿子,也就是赫伊津哈的父亲迪尔克·赫伊津哈则是不折不扣的逆子。他在参加牧师神学资格考试前三周,逃离了阿姆斯特丹,甚至以自杀来威胁自己的父亲。当父子两人从今天法国边境的斯特拉斯堡返回荷兰时,雅各布牧师领回来的是一个迷恋葡萄酒、现代科学和年轻女服务员的儿子,并且身患梅毒。迪尔克后来取得了莱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回到格罗宁根担任大学生理学教授。
幼小的约翰·赫伊津哈两岁时就失去了母亲(他的父亲很快就续弦了)。我们的主人公从小热爱锡兵和世界地图,常常和哥哥一起在家里排兵布阵。他还特别热衷于收集各种钱币,讨论城堡、贵族和骑士的徽章。从中学时代接触拉丁文开始,他就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终其一生,除了荷兰语、法语、德语、英语之外,赫伊津哈还会说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就阅读古代文字方面而言,除了欧洲那一代知识人标配的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之外,他还能阅读古挪威文、梵文和阿拉伯文。在大学接触到梵文后,赫伊津哈感到这正是他想象中最富有诗意的语言形式,并最终以印度古代戏剧中的小丑角色为主题,完成了博士论文。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赫伊津哈后来并未成为东方学家,而是回归了西方研究,尤其是中世纪晚期的历史文化。在他晚年的回忆中,赫伊津哈说他从1900年开始,逐渐又意识到了基督教伦理法则对自己生活的重要性。他感到,曾经吸引他的古代印度世界与他内心的距离过于遥远。虽然,当时东方文化在西方形成一股热潮恰恰就在于这种疏离所带来的神秘感。他写道,“首先是寂静寺庙里模糊和黑暗的氛围,然后是朝着远方闪闪发光的神圣雪山山顶的凝视”,单单是这幅图像就足够令人神往。可是,像他这样的西方人难以真正理解佛教世界里的悲伤。

读大学时期的赫伊津哈(中间戴帽子者)

正如他对于小丑的研究一样,赫伊津哈认为愉快的生活才应当是人生的真相,这种愉快体现在哥特式建筑、圣方济各的言行和但丁的诗歌中,体现在巴赫、舒伯特的音乐中,更体现在赫伊津哈美好的家庭生活当中。在哈勒姆中学做历史教员的时候,他遇到了自己的贝雅特丽齐,来自米德堡的玛利亚·斯霍勒尔。1902年婚后的十二年中,赫伊津哈和玛利亚生了五个孩子,家庭生活充满了各种乐趣。赫伊津哈在家里打扮成一个马戏团老板的样子,孩子们则假扮各种野兽围绕着父亲打闹。玩累了,就到院子里和母亲坐在一起,孩子们不停地讲笑话,或者在母亲琴声的伴奏下歌唱。那时候的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亮出獠牙之前,正在享受着最后的黄金时代。赫伊津哈和茨威格一样,都曾经多次怀念那个时代的美好生活。然而,正因为这种曾经的美好,才显示出现实真相的残酷。也许,直到那个时候,赫伊津哈才能更深切地理解佛教思想世界里,遥望远处雪山的悲伤。
1914年7月21日,巴尔干局势日趋紧张,奥匈帝国仍然在准备着王储对萨拉热窝的访问。世界仍旧平静,赫伊津哈的宇宙却开始坍塌了。那一天夜里,他写信给挚友彼得·范安洛伊夫妇:“今晚玛利亚去世了。她既没有醒过来,也没有痛苦。”
1915年,赫伊津哈去往莱顿大学任教。他仍然热情地为孩子们准备生日聚会和圣尼古拉斯节,每年都会专门为孩子编写和导演话剧。然而,1920年,长子迪尔克去世之后,赫伊津哈就再没有写过一部戏剧:“因为,没有人能够再来演船长了。”他后来写作《游戏的人》,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启发。或许,这本学术作品,也代表着一种对曾经生活的怀念。
审美、游戏与想象:中世纪文化史研究的基石
1905年的时候,赫伊津哈成为格罗宁根大学通史和荷兰史教授。十年之后,他迁居莱顿大学担任通史教授,直到1942年他因公开批评纳粹政策而遭停职。

1919年出版的《中世纪的秋天》是赫伊津哈的成名作,也被视为20世纪文化史研究的基石之一。赫伊津哈以优美的笔调描绘了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情景,并为之涂抹了一层悲观主义的底色。作为布克哈特的粉丝,赫伊津哈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并将历史视为最高的诗歌艺术。因此,在历史写作中,赫伊津哈追求一种灵动的精神,力图以文字复活那些已经逝去的往昔,并同古人形成通感。
为了实现这种动态,赫伊津哈特别强调对比。在《中世纪的秋天》中,这种对比的关系比比皆是,从肉体和精神、死亡和生活、梦想和现实,到形式和内容、图像和文字。这一切,都是指向布克哈特所曾经阐述的对立: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对立。然而,与布克哈特不同,赫伊津哈试图将文艺复兴更加拉向中世纪,而并非作为一种断裂。正如他在书中所写道的,在现在和过去,能够使人生成为一种享受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书籍、音乐、美术、旅行、对大自然的享受、体育、时尚、社会的虚荣心,以及对感官的麻醉。”
赫伊津哈还特别强调历史想象的重要性。在一篇《论历史想象的美学成分》的讲演稿中,他提问到:人类是不是已经变得过于温顺和人道,因此难以理解历史?人们如何才能真正理解几个世纪前,我们祖先的那种激情,比如看似野蛮的等级制度、对天主恩赐的权利的尊重以及封建服务与忠诚的概念?为此,他鼓励研究者去想象,去创造戏剧性的效果,使历史真正鲜活起来。他对历史这门艺术的科学化抱批判态度,认为历史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数字变成了概念的主人。可是,在数字之中,故事却崩溃了。无法在历史中去感触那些灵魂的喜悦与痛苦,就无法形成历史图景,历史也就被消解为一个个专门学科中生冷的模型。
赫伊津哈一生的阅读经历中,但丁是无可比拟的巅峰。他认为,但丁使一切的对比在更高的和谐中实现了统一,而这种思想正是继承了《旧约》、教父和经院神学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但丁是中世纪文化所结出的最伟大、最甘甜的果实,也就是中世纪这个秋天中最大的收获。与许多英法史学家对经院神学体系僵化的批评不同,赫伊津哈反而认为,13世纪带来了制度性的秩序和天堂般的和谐,“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里,精神被封闭在(这种秩序和和谐)之内,犹如一颗钻石被镶嵌在黄金框架之中”。
《中世纪的秋天》在荷兰文本出版后反应平平,学界不少人批评其中征引过于琐碎,且表达太过文学化。然而,这本书反而在德国和法国学界引发了良好的回应,尤其是当时的史学界先锋康托洛维奇和马克·布洛赫对之大为赞扬。从这个角度来说,赫伊津哈与年鉴学派也有不浅的渊源。或许后来年鉴学派重视日常生活中个人的处境,并从中探讨时代流变特征的路径,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赫伊津哈的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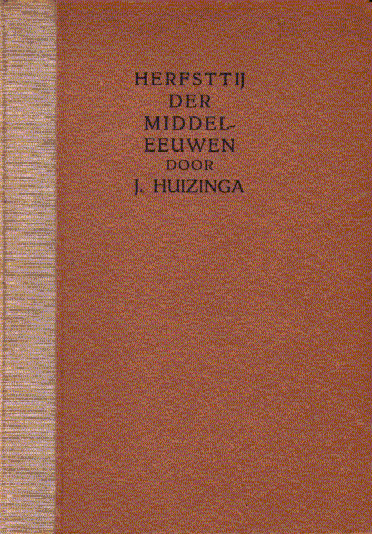
事实上,与布克哈特的最大不同在于,赫伊津哈认为12世纪是任何时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充满创造和建设的时代。在这一点上,他反而与英国学者拉什道尔以及美国学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有着类似的看法。他认为,12世纪的时候,异教日耳曼文化和罗马宫廷文化及随着城镇发展而来的市民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使基督教得到了重新阐释。用他诗意的语言来说,“当时的变化犹如音调变得更为明亮而节奏变得更为活泼的一首曲子,犹如从云彩后面放出万丈光芒的太阳”。如果用他所喜欢的巴赫的曲子来做比喻的话,就像是进入了《哥德堡变奏曲》的第二个变奏当中,而且一定是古斯塔夫·莱因哈特的大键琴版本。
在赫伊津哈的笔下,你仿佛能看到书本背后那双热爱历史而又热爱生活的眼睛。他曾经诙谐地写到,12世纪伟大的经院神学家阿伯拉尔身上一定会带有某些奥斯卡·王尔德的特质。虽然这两位文化巨匠的性取向不尽相同,但是都曾做出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事来,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有一条损人损到骨子的“毒舌”。而当他评价托马斯·坎普的《效法基督》时,并没有过多关注其中的神秘主义、苦修主义思想,而是从文体上解释了它的成功:“(《效法基督》中)充满着平行的长句和平淡的半音,诵读起来犹如小钟表的叮当之声。恰恰是这种单调的节奏,使它像是绵绵细雨之夜中沉静的大海,又或是秋风在落叶缝中发出的丝丝叹息。”
作为欧洲文化史的研究者,赫伊津哈也对德法之间的战争持有相当深远的看法。在他看来在,这不仅仅是两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权利上的争夺,更不单单是争夺欧洲霸权的问题。在这些战争的背后,隐藏着罗马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在欧洲绵延数个世纪的冲突。它们的第一次分道扬镳就是15世纪的文艺复兴。因此,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贯穿于整个西方文化历史之中的日耳曼和罗马文化之间的创造性对比,而这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一种无可克服的矛盾。
战争中的黄昏恋
对于出生在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文化巨匠来说,一战是他们生命的分界点。晚年的赫伊津哈,面对着战争、投降、控制、匮乏等等悲惨局面中唯一的慰藉,就是在他花甲之年又遇到了真爱。

1937年,当一切看起来继续走向美好的时候,赫伊津哈家里来了一位新的女管家兼秘书。这就是阿姆斯特丹天主教商人家庭的女儿,奥古斯特·斯霍尔翁可。那个时候,这位女秘书年仅28岁,赫伊津哈刚刚65岁。在她工作了两周之后,赫伊津哈就给她写信,询问她是否能够扩大她的职责范围。亦即在学术和家务的协助之外,还能充当赫伊津哈的司机,并且,还要“当不可缺少的女主人、适当地做可爱的女儿,但最主要的是做我永远最爱的人”,以及“最最可爱的大宝贝和小宝贝”。我们不知道赫伊津哈丧妻之后数十年间在私生活上的操守——从他父亲的经历来说,他可能会比较谨慎。他曾说,父亲在他小时候常常头痛欲裂的情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这是梅毒引起的。这位强调秩序与神圣性的史学家,并不掩饰自己对奥古斯特的爱。那一年的圣尼古拉斯节,他送给对方一盒香粉,并希望两人共浴之后“在你的身上闻一闻它的味道”。虽然在后来的信中,赫伊津哈确实也说过,他们的婚姻和年龄差比较“正常”的人相比,更应当充满克制。当然,那时候他可能真的老了。

就在德国宣布终止对荷兰管控前两周,赫伊津哈安静地病逝于戈尔德兰省的德·施特格,享年73岁。也许和同时代的其他史学家相比,赫伊津哈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派,没有体大思深的学术体系,但是他灵动的笔触和对历史的洞见,仍然能为今天的中世纪文化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启迪。
【附录】
赫伊津哈作品的中译本:
1、《中世纪的衰落》(根据霍普曼的英文节译本),刘军、舒炜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2、《游戏的人: 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07年(2017年再版);付存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中世纪的秋天》(根据佩顿和马里奇1996年的英文全译本),何道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017年花城出版社再版。
4、《伊拉斯谟传》,何道宽译,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版。
5、《17世纪的荷兰文明》,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
研究作品:[荷兰]威廉·奥特尔斯佩尔,《秩序与忠诚:约翰·赫伊津哈评传》,施辉业译,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